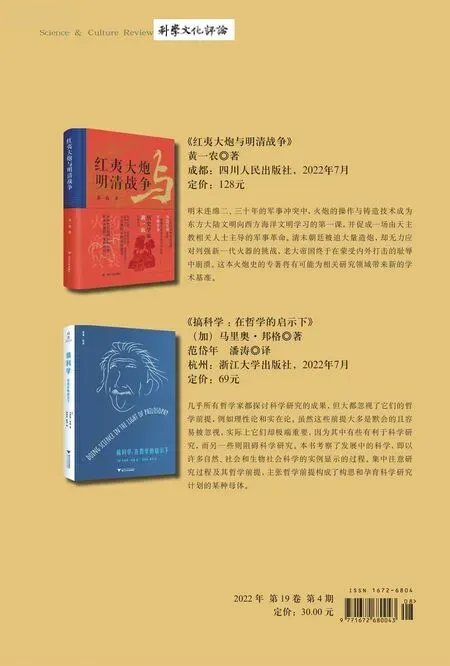中印兩國的早期科技交流與交鋒(1950—1966)
王勇忠
1950年4月1日,中國和印度兩個亞洲大國正式建交。1954年,周恩來總理和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1889—1964)總理實現互訪,并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此后,兩國在日內瓦會議和亞非會議等重大國際事務中密切配合,雙方關系逐步走入友好合作的“蜜月期”。然而,隨著國際格局的調整,特別是受到西藏問題和邊界問題的直接影響,從1959年起,中印關系迅速冷卻,進入“碰撞期”[1]。以往學界對于兩國關系的研究,由于受到中印邊境沖突這一重大事件的影響,主要集中于政治、外交和軍事領域,本文力圖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雙方在科技領域交流與交鋒的視角對這一時期的兩國關系進行考察,以期重新審視科學與政治的復雜關系。
一 初期的科技交流
印度科學大會(The Indian Science Congress,以下簡稱“科學大會”)是印度科學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印度科學界最大的半官方科技組織之一,其常設機構是印度科學大會協會,由兩位英國化學家仿效英國科學促進會研究工作者年會的形式發起組織,于每年的首個星期一在不同城市舉行年會,以推進和促進印度的科學事業。1914年1月,第1屆年會在加爾各答舉行,來自印度各地和國外的105位科學家參加了會議,共提交了植物學、化學、民族志、地質學、物理學和動物學等領域的35篇論文。1947年的第34屆年會由尼赫魯親自擔任總主席,他參加了隨后的歷屆年會。正是由于他對在印度,特別是在年輕一代中發展科學氛圍的持續興趣,極大地豐富了科學大會的活動,使之成為政府向科學界宣傳政策和與科學家進行聯系,以及邀請外國科學家的場所。科學大會的經費一半左右由印度政府承擔,1953年起還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資助。時至今日,科學大會在推動印度科技發展等方面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
1947年8月,印度正式獨立,科技事業的發展揭開了嶄新的篇章。尼赫魯等印度領導人十分重視科技的發展,指出“只有科學技術才能解決饑餓、貧窮和不衛生、無知和愚昧、使人麻木的習慣和傳統、大量資源的浪費等問題”[2],并由總理親自擔任科學界最重要組織“科學與工業理事會”的主席,負責指導和協調全國的科技工作,另設有“醫學研究理事會”和“農業研究理事會”。1951年,自然資源與科學研究部成立。1948—1953年4月,印度共新建了11個研究所[3],其對科技事業的重視由此可見。20世紀50年代初期,印度的科技水平要稍高于中國。
1950年11月,印度國家科學院發出召開南亞科學史討論會的通知,中科院副院長竺可楨表示極愿前往,但是由于此時距離開幕只有幾天時間,準備不充分,因此未能成行,只得致函外交部,請駐印度使館將會議資料寄送一份,并請其代為接收和寄交南印度科學院捐贈給中科院的刊物,以及中科院贈送給對方的《科學通報》和《中國科學》等6種共18冊刊物,并請其繼續協助辦理與印度其他科學研究所開展刊物交換的事宜[4]。1951年1月,在征求外交部的意見,認為“印度目前對我國似欠友好的態度并不影響我國派代表出席該討論會”[5]后,中科院派出了中山大學的胡煥庸、中科院的吳征鎰和侯學煜,以及在印度貝巴薩尼克植物研究所工作的徐仁等參加了由印度遺傳育種學會主辦,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南亞科學合作館資助的“南亞栽培植物的來源與分布討論會”。會上,胡煥庸代表中科院致辭時說:“我們兩國間的科學合作定會推進全亞洲人民的福利及繁榮,希望印度及中國植物學家此后可以攜起手來密切合作,共同向科學的進步方面推進。我們人民間的團結合作萬歲。”[6]期間,駐印度使館舉行酒會招待在德里的重要科學家、與會專家、研究部門負責人、報社記者、蘇聯參加印度水利工程討論會顧問團、英國、美國、錫蘭和新加坡代表等約百余人。同年6月,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印度,參觀了國立物理研究所、中央農業研究所、基本科學研究所和印度科學研究所等眾多科研機構。
從1952年起,印度多次邀請中國參加科學大會。1953年,印度《新世紀報》在對大會進行報道時,惋惜中國與蘇聯科學家未能出席。但是,由于當時的中印關系和中國國內的實際情況,以及領導國內科研事業和與國外科研機構交流的中科院正在進行機構和學科方向的調整等原因,僅以郭沫若院長的名義向第41屆年會致以賀電:“為了保衛亞洲及世界和平與發展進步的科學事業,我們兩國的科學家今后必將進一步加強聯系與更密切合作。”[7]即便如此,1949—1954年,印度仍然是除日本之外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與中國科學界聯系最為緊密的國家,而在亞洲國家中,兩國重要科研機構間的圖書交換量也僅次于日本,并且與日本青年科學家和中國的聯系主要集中在社會政治問題不同,印度科學界一般不脫離科學業務,交流的主要內容是各研究所間的學術聯系,集中在生物學,特別是植物方面,包括森林植物、水產生物、經濟作物、藥物、蟲害和古生物等,以及數學、物理和考古等少數方面,主要方式是索取和贈送書刊、資料,交換標本和種子等[8]。
除此之外,中印雙方還有一些科學家層面的交往。從1948年12月起,殷宏章應英國學者李約瑟的邀請,赴印度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南亞科學合作館科學官員。1949年以后,他接到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回國工作的邀請,而聯合國方面則希望他能夠再任職兩年。因此,他專門赴駐印度使館征求意見。使館方面考慮到他如果離開,“在目前情況下很難再有較進步之中國人進去,所以認為他可仍留在印度擔任現職”[9]。在與中科院商議后,他于1951年任滿后才返回國內,擔任實驗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員。與之類似,徐仁于1946年在印度勒克瑙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后留在貝巴薩尼克植物研究所工作,“功績甚為卓著,在整理收藏品及鑒定登記標本方面貢獻甚大且有永久價值”[10],但是,他堅持返回祖國,在給研究所所長的信中曾寫道:“解放后的建設時期現已到來,需要科學家甚殷,科學家必須在場為國家及人民努力工作。”[10]
二 以科學大會為中心的科技交流
1954年5月,印度政府和科學大會協會再次通過駐印度使館邀請中科院派生物、物理或工程學方面的科學家出席第42屆年會。外交部考慮到1954年蘇聯派科學家代表團出席第41屆年會和到各地參觀訪問取得了較好影響,專門致函中科院,希望其能夠與對外文委及有關部門盡早考慮參會事宜,并送上了科學大會的有關材料和上次年會情況的簡報[11]。同年10月,尼赫魯訪華,再次提及此事。隨后,周恩來指示中科院應派人參加此次年會。中科院經與外交部章漢夫副部長商議,并經陳毅副總理批準后,決定派出由5人組成的代表團赴印。1955年1月3日,由首席代表錢端升(法學家),代表侯德榜(化學家)、狄超白(經濟學家)、汪胡楨(水利工程學家)和薛愚(藥學家)等組成的中國代表團經由新德里抵達會議舉辦地巴羅達市。代表團此行的目的是“建立和增進我國科學工作者與各國、特別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與我國建交的其他亞洲國家科學工作者之間的友好和聯系;適當地、實事求是地宣傳我國五年來在科學方面的成就;盡可能了解與會各國,特別是印度科學的情況”[12]。1月4日,會議開幕,共有1000多位印度科學家出席,中國、蘇聯、西德、英國、美國、日本、緬甸和瑞士,以及聯合國有關機構的48名代表列席會議。尼赫魯致開幕詞,指出“印度的科學研究與生產結合得不夠,科學應該為和平服務,但不應僅見于口頭宣傳;科學界的正統派與異端派應該互相容忍,不要壓制;印度科學界對生物重視不夠,尤其要注意培養師資”[12],并號召科學工作者參加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中國代表團作為外國代表團中唯一的代表在會上宣讀了祝詞,還和蘇聯等國一起向科學大會贈給了大批的科學書籍[13]。期間,錢瑞升團長作了《新中國的科學研究》的大會報告,聽眾多達1000余人,反響熱烈,在各分組所做的《關于制堿和氮氣肥料聯合制造新法》《珍視祖國的文化遺產——中藥》《新中國五年來水利建設的成就》等報告也獲得了不錯的反響。會議中,中國與蘇聯、緬甸和印度科學家交流較多,印度的大部分科學家較為熱情,對中國各門自然科學等所詢問的問題較多,但是對中國的情況了解很粗淺,甚至完全沒有了解。在歷時5天的會議結束后,代表團還受印度政府的邀請,赴艾哈邁達巴德、孟買、浦那和新德里等地參觀了紡織研究所、基本科學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等科研機構、工廠和學校,并應邀參加報告會和座談會。期間,尼赫魯還專門請侯德榜為擬建設的供給重水的肥料廠的廠址多提意見。通過這次訪問,中國對于印度科學的情況有了大致了解,如“獨立以來科學研究仍有較迅速的發展,建筑與設備都比較新式和完備……有一定數量的比較著名的科學家,以物理、化學、醫學較多,尤其以物理學家為多……科學家完全是英、美教育培養出來的……科學界的領導成分親英美的居多”等[12]。印度科學家也較為正式地提出了希望向中國學習的一些內容,包括如何用本國文字翻譯外國科學名詞和表達科學概念或邏輯、如何迅速和大量地培養地質人才、如何進行計劃與統計、水利工程快速施工的經驗、酸堿肥料工業的經驗,以及如何解決人口過剩的問題等。隨后,代表團在參加完印度共和日慶祝活動后返回國內,其中的部分成員則繼續前往巴基斯坦,參加其召開的科學促進協會年會。隨后的幾年,中國先后派劉崇樂(昆蟲學家);張肇騫(植物學家)、潘孝碩(物理學家)、周同慶(物理學家)、沈家瑞(動物學家)和莊孝僡(生物學家)等參加了第43—46屆年會。期間,中科院還曾因拖延向中央報告受邀參加第43屆年會一事受到周恩來的批評,并指定陳康白等人做檢討并通報[14]。
1956年2月,中國派段學復和龔昇參加了印度舉行的黎曼Z函數國際會議,正是在這次會議上,與著名數學家高善必(D. D. Kosambi,1907—1966)等人取得了聯系。次年,高善必受邀來華,并受到周恩來的接見,向其介紹了印度統計學方面的發展和對中國統計學的建議,而與他一道來華的統計學家馬哈蘭諾比斯(Mahalanobis,1893—1972)對華也十分友好,之后還曾招收中國留學生。同年9月,印度副總統拉達克里希南(Radhakrishnan,1888—1975)訪華。期間,他參觀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并做了演講,代表印度科學工作者祝賀中國科學事業在建設未來的偉大文明方面獲得進一步的成就。演講結束時,郭沫若院長和500多位在場的中國科學工作者一致用印地語高呼“印地—秦尼巴依巴依”(中印兩國是兄弟)。在這一時期,兩國之間的科技交流達到了高峰,科學大會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平臺。
1959年,印度邀請中國參加第47屆年會,并提出希望中科院古脊椎研究所楊鐘健所長能夠出席,但是楊鐘健由于身體原因不能乘坐飛機,加之考慮到當時印度已經有“對我極不友好的反華情緒,以及印度科學家和資本主義科學家與會期間可能故意挑起對我們的指責和非難”[15],中科院黨組對參會人選進行了慎重的研究,決定派出政治上較強,又有適當學術地位,同時在國際活動上有經驗,能應對這種局面的人選參加會議。經多方協商,最終選派了周培源和趙九章作為代表參會。出發前,陳毅副總理召集有關人員,對中印關系作了分析,并指示:“在印度對我國不友好的氣氛下,仍應落落大方,前往參加。我們應強調中印友好及科學經驗交流,避免談到邊境問題。如有人惡意污蔑,可在發言中指出這些污蔑是與中印友好及加強科學經驗交流精神不符的。我們應避免糾纏于一般性的辯論和爭吵。”[16]會上,駐印度大使也做了具體的指示,即:“不主動引起邊境問題的辯論,如有人談到這個問題,應指出應由兩國總理會談來解決;不主動爭取作學術報告,如對方要求時,可以報告并舉行座談會;如美國和印度代表談到中印關系,對我進行污蔑時,應按照當時的情況做適當的表示;會期內可在附近參觀訪問,會后參觀不宜走得太遠。”[16]12月30日,周培源和趙九章抵達新德里,印度科學研究和文化部代表以及中國駐印使館的代表到機場迎接。1960年1月3日,大會開幕,尼赫魯在致辭中未涉及中印關系。周培源則作了大會發言,除了代表全國科協及世界科協致賀詞外,還提出加強中印友誼及科學文化的交流等建議。期間,科學大會協會從未正式派人來同中方接洽有關學術報告的問題,而周培源等人也根據大使的指示,未主動爭取,只是列席了幾場報告會,并參觀原子能研究基地、抗生素工廠、國立化學研究所和國立物理研究所等機構。在印度政府的壓力下,印度科學家對和中方接近有所顧慮,但一般也比較友好,只是對兩國邊境事件表示憂慮。總的來說,中國代表團是“在印度政府有意冷淡和行政效率低下結合的情況下被接待的。……消息被封鎖,一般記者不來訪問。……印度政府對我們的接待,比起去年,在表面上還有些改進”[16]。
1960年初,印度制定“前進政策”,要求軍隊和有關武裝力量把巡邏隊和哨所推進到中方控制區域,雙方關系繼續惡化。直至1960年12月27日,中科院才收到了從北京市內寄發的印度國家科學研究所邀請中國參加該會成立25周年大會,以及會后可以參加第48屆年會的信函,但是考慮到這一邀請并未通過外交渠道,也不是以科學大會協會名義發出,而且距離次年1月2日的會期太近,所以中國未派代表參加這兩個會議[17]。但與此同時,1960年12月5日,印度又照會中國外交部,請其派代表參加印度科學重要成就之一的原子反應堆的揭幕典禮。經報請周恩來后,周培源參加了這一典禮。1961年4月,周恩來率團訪問印度,謀求和平解決邊界問題未果。同年10月,印度通過外交途徑正式邀請中國參加1962年的年會,但是由于當時雙方關系已然十分惡化,故中國未派代表團參加。據統計,1959—1961年,除高善必于1960年再度訪華之外,兩國科學界只有10余項涉及人員往來、資料或種子交換和致賀電等方面的往來。1962年10月,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正式打響,兩國科學界的聯系也就此中斷。
三 20世紀60年代的科技交鋒
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破裂后,此前在中科院的國際科技合作中占最重要地位的與蘇聯和東歐國家間的合作轉入低谷,甚至出現停滯。隨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之爭,中蘇雙方均加強了對其他國家的經濟、軍事和科技援助,如中科院與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和古巴等國的科技合作大多始于這一時期。而在地緣政治的考慮之下,蘇聯與印度在政治、經濟、軍事和貿易方面也開展了全方位的合作,甚至在中印發生邊界分歧時公然沖破《中蘇同盟條約》,釆取偏袒印度的立場[18]。這一時期,舉行科學討論會成為了中印雙方在科技領域交鋒的主要形式。
1963年,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以下簡稱“世界科協”)為了更有效地促進會員國之間的溝通與合作,繼巴黎辦事處、布拉格中心和印度中心后,在第24屆執行理事會上一致通過了在北京建立世界科協東亞區域中心的決議。1964年8月21—31 日北京科學討論會的召開,便是發揮北京科學中心在促進國際科學交流方面作用的重要舉措。它是我國自1949年以后第一次承辦的大規模國際性學術會議,會議主題為討論“有關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和文化,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的科學問題”[19],有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 44個國家和地區的 367人參會,論文內容涉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等各領域,為聯通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科技交流,打破美蘇冷戰持續升溫所造成的學術壁壘,增進各國科技發展水平的了解和交流奠定了基礎。同時,此次會議也帶有強烈的建立“反修”“反帝”統一戰線的政治內涵。中國曾邀請印度參加,但是遭其拒絕,并且印度還在報刊上聲稱世界科協執行理事會“揭露了”中國借世界科協的名義在北京舉行科學工作者座談會,并以多數派擊敗了中國代表想分裂這一組織的“企圖”,并稱中國沒有向世界科協提供座談會的正式情況,也沒有向在歐洲的其他國家發出邀請[20]。
而在此前的7月27—31日,印度在蘇聯的支持下已召開了“被看作是在蘇修的指使和支持下同我們唱對臺戲的行為”[19]的印度科學討論會(又名“科學與國家討論會”)[21],共有28個國家的45名亞非科學家以觀察員身份與會,收到論文130篇。由于政治原因,會議未邀請以色列、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參加。會議的主要內容幾乎都圍繞討論印度的科學和經濟建設問題,特別是處于危機的糧食問題,以及大力宣揚其工業和科技成就,如印度原子能委員會宣揚其是東南亞生產同位素最多的國家,愿意提供設備和專家在東南亞建立一個生產和分配同位素的中心;宣稱已決定和國際原子能機構共同在曼谷建立分光計工程以共同研究使用原子反應堆;第四個五年計劃對科學研究的投資將比第三個五年計劃增加一倍;能夠在18個月內生產一枚用于軍事上的原子彈等[22]。這樣的日程安排引發了部分外國代表的不滿,認為大會沒有討論農業和公共衛生等專門問題的機會,他們又很難參與對于印度科學發展的討論。大會期間只是在科學和國際關系小組會上討論了新興國家科學發展的特殊問題,以及印度與發展中國家的科學資源,并探討了交換情報、出版物及人員的可能性[23]。印度表示愿意以派出科技人員或接受外國科技人員赴印度學習的方式為其他亞非國家提供幫助,并接受了菲律賓代表提出的出版亞非科學公報、埃塞俄比亞代表提出的要求提供技術書籍和教材,以及東非科學院提出的歡迎印度在天然資源勘探方面和設備方面給予技術援助等要求[24]。會后,印度還組織與會代表參觀了各工業工程和科學研究機構,以便他們了解同印度進行科學合作研究的可能方向。雖然印度政府和科協的負責人在會議的開幕詞、歡迎詞以及討論科學與國際關系議題時均未提到中國,也沒有發表反華言論,但是通過比較可看出上述兩場科學討論會的內容有諸多相似之處。爭取更多國家參會成為了中印雙方爭奪的焦點,如黎巴嫩僅有的兩位原子核物理學家之一的納賽爾就以母病不能外出時間太久為由謝絕了印度科學討論會的邀請,決定參加北京科學討論會,并希望能與在美國認識的錢三強和錢學森會面;突尼斯則決定派出兩位科學家赴印參會,而面對中方的邀請,突尼斯外交部文化司表示將應邀參加,并稱人選由新憲政黨負責提名,但是名單遲遲未出。
此外,印度科學討論會還有另外一項重要的議題,即召開1965年專門討論“科技對正在發展的國家中的作用”的亞非科學家大會籌備會議,希望能夠成立亞非科學組織,以作為地區性科技合作的常設機構。因此,會后成立了由蘇聯、印度、錫蘭、肯尼亞、加納、伊朗、黎巴嫩、菲律賓、突尼斯、阿聯等國組成的會議籌委會。
為了與北京科學討論會相抗衡[25],1966年4月25日—5月2日,印度在新德里召開了亞非科學討論會,主題是“亞非國家在促進和利用科學技術方面的合作”[26],共有32國的58位代表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派出觀察員與會。蘇聯積極支持這個會議,除動員受到它影響的國家參會外,在經濟上也給予了大力支持,如為很多代表購買機票等。會上,甘地夫人指出要將科技用于消除貧困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印度代表提出要建立“亞非科學政策及亞非科學院”,蘇聯則提出要“把軍備競賽的巨大費用用于提高千百萬人的生活水平”,其他與會代表提出的意見包括亞非國家在科學事業上要自力更生、各國需要有自己的科學政策、要把國民經濟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科學研究,指出在不發達國家中科技不被重視,表示了對科學家外流問題的關切,期望加強彼此之間的合作等。期間,成立了由錫蘭、東非、埃塞俄比亞、印度、印尼、伊朗、日本、黎巴嫩、尼日利亞、突尼斯、土耳其、阿聯和蘇聯組成的亞非科學討論會常設機構執行委員會。但是,此事也引起一些與會國代表的不滿,如伊朗代表提出了蘇聯不是亞洲國家的質問,馬達加斯加代表提出為何只有英語地區國家而沒有法語地區國家等,由此,執委會中又增加了馬達加斯加、柬埔寨和塞內加爾等國[27]。最終,會議決定在印度和阿聯設立辦事機構,并確定于1969年在開羅召開下一次討論會,商定屆時將成立亞非科學家常設組織,并在各成員國設立分會。針對這次會議,中國科協代表團負責人在世界科協第24次執行局會議上指出:“中國對亞非國家和亞非地區舉行的科學討論會一貫是積極支持和熱情歡迎的,但是印度反動派搞這個‘亞非科學討論會’,其目的是同蘇聯修正主義者勾結起來,聯合反華,是為了妄圖破壞北京科學討論會的巨大影響,破壞亞非科學界的團結。既然是‘亞非科學討論會’,為什么多次的籌備會議不邀請中國、越南、朝鮮、巴基斯坦等許多亞非國家參加,而實際上由不是亞非國家的蘇聯來操縱?顯而易見,這是盜用亞非之名,行破壞亞非科學界團結之實。”[28]
然而,由于在1965年9月在布達佩斯召開的世界科協第八屆全體大會上蘇聯代表團以組織的手段將中國排擠出世界科協,中國科協與世界科協的聯系被迫中斷,再加上“文革”等原因,原定于1968年召開的第二次北京科學討論會未能舉行,中印之間在科技領域的交鋒告一段落。
四 結語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眾多左翼科學家倡導新型的科學國際主義,走出實驗室,登上政治舞臺,先后倡導成立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科協等國際科學合作組織,此后又組織召開普格華許會議,期望科學能夠超脫于政治,以科學倫理為武器,防止科技知識的濫用,消除核武器和生化武器,阻止戰爭和其他形式的武裝沖突,維護全人類的幸福和安全,這場科學左派運動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曾經具有十分廣泛的影響。然而,由于美蘇對抗的“冷戰”局面和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各國之間復雜多變的關系,他們的這種努力遭遇了極大的阻力和困難,甚至逐漸淪為各方實現其政治目的的工具,印度對科學大會的重視、世界科協“區域中心”的建立、印度科學討論會、北京科學討論會、亞非科學討論會、北京暑期物理討論會的召開和亞非科學家常設組織的設立無不展示了這一點。綜上所述,中印兩國在科技領域的交流與交鋒既受到中印關系波折變化的影響,也帶有深刻的時代烙印,展現了科學合作的特殊性,也是對外科技援助中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