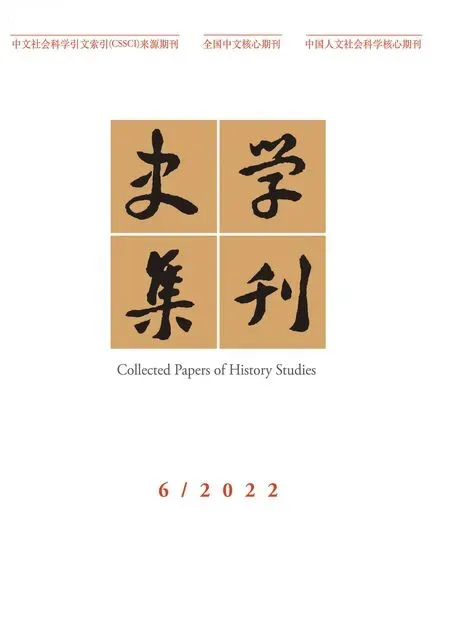論皇侃經學思想的主體與本質
梁滿倉
(中國社會科學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從兩漢至南北朝,經學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漢儒的訓詁章句之學、魏晉的經義之學和南北朝的義疏之學。(1)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二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730頁。南朝儒家經典的義疏當屬皇侃的《論語義疏》最為典型。研究者多從佛、玄、道思想與皇侃經學思想關系的角度加以論述,甚至有學者認為,皇侃注經已經玄學化了。(2)張文修:《皇侃〈論語義疏〉的玄學主旨與漢學佛學影響》,《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朱漢民:《玄學的〈論語〉詮釋與儒道會通》,《天津社會科學》,2010年第3期;宋力:《淺析〈論語義疏〉玄學化的注經特色》,《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8期;徐望駕:《佛教文化與皇侃〈論語義疏〉》,《宗教學研究》,2009年第3期;徐望駕:《皇侃〈論語義疏〉道教語詞芻議》,《湛江師范學院學報》,2011年第5期;徐望駕:《皇侃〈論語義疏〉中的佛源詞》,《中山大學學報論叢》,2005年第4期;柏宇航:《論佛教對皇侃〈論語義疏〉的影響》,《河北北方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這些論述毫無疑問地反映出皇侃經學思想某一方面的特色,但不能反映其本質特征。皇侃經學思想的本質特征是什么?具體表現在什么地方?本文欲就此問題獻芹以就正于方家。
一、《論語義疏》的儒家主體特征
《北史》評價南北朝雙方各自的學術特點說:“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3)《北史》卷八一《儒林列傳上》,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709頁。清人皮錫瑞這樣評價南朝經學的“約簡”:“說經貴約簡,不貴深蕪,自是定論;但所謂約簡者,必如漢人之持大體,玩經文,口授微言,篤守師說,乃為至約而至精也。若唐人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不過名言霏屑,騁揮麈之清談;屬詞尚腴,侈雕蟲之余技。如皇侃之《論語義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講,多以老、莊之旨,發為駢儷之文,與漢人說經相去懸絕。”(4)(清)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76頁。誠然,南朝經學與兩漢時相比顯示出極大的差異,但這種差異畢竟不是本質上的,皮錫瑞所用“說經”二字,表明這種差異只是注經方法上的。
應該說,南朝與兩漢的經學有異有同,南朝經學家注經時加入了佛教玄學,這在兩漢時是沒有的,這是方法上的“異”,但是,南朝的經學并沒有因此變成玄學或佛經,它還是儒家經典,這是本質上的“同”。然而不少論者往往把注意力放在方法之異上,而忽視了本質之同。或許是因為本質之同太淺顯了,人們認為沒有研究和強調的必要。正是由于人們常常對一般常識性的東西熟視無睹,因而放棄了對常識背后問題的進一步追問。例如南朝學者“儒玄雙修”,在文獻記載中俯拾皆是,是人所共知的常識。但很少有人進一步問,誰在儒玄雙修?雙修的主體是儒者還是玄學家?這個問題對于認識南朝經學尤其是皇侃經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毫無疑問,皇侃不是玄學家。他注《論語》與何晏、王弼有本質不同。何晏、王弼是魏晉時期的玄學家,他們的“貴無論”奠定了魏晉玄學的一整套思想體系,他們注《論語》是站在玄學立場上,試圖借儒家經典闡發其玄學思想。而皇侃注《論語》,是力圖保持完整的儒家體系。他說:“侃今之講,先通何《集》,若江《集》中諸人有可采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別有通儒解釋,于何《集》無妨者,亦引取為說,以示廣聞也。”(5)(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自序》,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6-7頁。皇侃所說何《集》即何晏《論語集解》。這部著作以儒家正宗《魯論》為基礎,經過西漢張禹兼講《齊論》,發展成為世所貴的《張侯論》。何晏又將東漢馬融、鄭玄、苞咸、周氏,曹魏陳群、王肅、周生烈等七種儒家解說集于一書。盡管作為玄學家的何晏作《集解》時“又采《古論》孔注,又自下己意”,(6)(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5頁。加進一些玄學,但總體上沒有影響儒家體系的完整。這是皇侃義疏《論語》先通何《集》的一個重要原因。皇侃始終是一個經學家,《梁書》把皇侃列入《儒林列傳》:
侃少好學,師事賀玚,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國子助教,于學講說,聽者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善之,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解職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侃既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年,卒于夏首,時年五十八。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義》并見重于世,學者傳焉。(7)《梁書》卷四八《儒林·皇侃傳》,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680-681頁。
皇侃一生始終從事儒學講誦,吸取佛道概念和一些思想納入《論語集解義疏》,卻不破壞儒家體系的完整,不改變《論語》的儒家性質,這個事實與其說是“儒玄雙修”,毋寧說是皇侃對儒家立場的堅持和吸收其他學說的養分對儒家思想加以豐富和提高。
皇侃《論語集解義疏》與何晏《論語集解》相比有兩個顯著變化:
一是玄學思想數量增大。《論語集解義疏》中的玄學家,何晏、王弼、郭象自不待言,除此之外,還有繆播。繆播字宣則,晉懷帝時任給事黃門侍郎、侍中、中書令,后被司馬越所殺。繆播所注《論語》在《論語集解義疏》中保存了17條:
1.釋“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人之極也,能審好惡之表也,故可以定好惡。若未免好惡之境,何足以明物哉?
2.釋“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學末尚名者多,顧其實者寡。回則崇本棄末,賜也未能忘名。存名則美著于物,精本則名損于當時,故發問以要賜對,以示優劣也。所以抑賜而進回也。
3.釋“子見南子”:應物而不擇者,道也;兼濟而不辭者,圣也。靈公無道,眾庶困窮,鐘救于夫子。物困不可以不救,理鐘不可以不應,應救之道必明有路,路由南子,故尼父見之。涅而不緇,則處污不辱,無可無不可,故兼濟而不辭。以道觀之,未有可猜也。
4.釋“子路不悅”:賢者守節,怪之宜也。或以亦發孔子之答,以曉眾也。
5.釋“夫子矢之曰”:言體圣而不為圣者之事,天其厭塞此道耶。
6.釋“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圣教軌物,各應其求,隨長短以抑引,隨志分以誘導,使歸于會通,合乎道中。以故剛勇者屈以優柔,儉弱者勵以求及。由之性也,以勇為累,常恐有失其分,覓功衒長,故因題目于回,舉三軍以致問,將以仰叩道訓,陶染情性,故夫子應以篤誨以示厥中也。
7.釋“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夫投竿測深,安知江海之有懸也?何者?俱不究其極也。是以西河之人疑子夏為夫子,武叔賢子貢于仲尼,斯非其類耶?顏回盡形,形外者神,故知孔子理在回,知淵亦唯孔子也。
8.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死生者,所稟之性分;富貴者,所遇之通塞。人能命養之以福,不能令所稟易分。分不可易,命也。能修道以待賈,不能遭時必泰。泰不可必,天也。天之為言自然之勢運,不為主人之貴賤也。
9.釋“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居理足,本無危亡。然賢而圖變,變則理窮,窮則任分,所以有殺身之義,故比干割心,孔子曰:“殷有三仁也。”
10.釋“子曰:有教無類”:世咸知斯言之崇教,未信斯理之諒深。生生之類,同稟一極,雖下愚不移,然化所遷者,其萬倍也。生而聞道,長而見教,處之以仁道,養之以德,與道終始,為乃非道者,余所不能論之也。
11.釋“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大夫五世、陪臣三世者,茍得之有由,則失之有漸。大者難傾,小者易滅。近本罪輕,彌遠罪重。輕故禍遲,重則敗速。二理同致,自然之差也。
12.釋“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子游宰小邑,能使民得其可弦歌以樂也。
13.釋“割雞焉用牛刀”:惜不得導千乘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也。
14.釋“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博學之言,亦可進退也。夫子聞鄉黨之人言,便引得射御,子游聞牛刀之喻,且取非宜,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其不知之者,以為戲也;其知之者,以為賢圣之謙意也。
15.釋“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玉帛,禮之用,非禮之本。鐘鼓者,樂之器,非樂之主。假玉帛以達禮,禮達則玉帛可忘。借鐘鼓以顯樂,樂顯則鐘鼓可遺。以禮假玉帛于求禮,非深乎禮者也。以樂托鐘鼓于求樂,非通乎樂者也。茍能禮正,則無持于玉帛,而上安民治矣。茍能暢和,則無借于鐘鼓,而移風易俗也。
16.釋“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爾時禮壞樂崩,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為圣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啟憤于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予之不仁”者何?答曰:時人失禮,人失禮而予謂為然,是不仁矣。言不仁于萬物。又仁者施與之名,非奉上之稱,若予安稻錦,廢此三年,乃不孝之甚,不得直云不仁。
17.釋“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則文”:君子過由不及,不及而失,非心之病,務在改行,故無吝也。其失之理明,然后能之理著,得失既辨,故過可復改也。小人之過生于情偽,故不能不飾,飾則彌張,乃是謂過也。(8)參見(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83、106、148、149、160、271、302、398、415、426、446、447、458、468、469、500-501頁。
在上述17條中,第一、第七、第十條中的“極”,第二、第九、第十一、第十五條中的“名”“實”“本”“末”,第三、第五、第六、第八、第十、第十四、第十六條中的“道”“理”“無可無不可”,第六、第八、第九條中的“分”“性”,都是玄學概念或命題。繆播《晉書》中有傳,本傳中絲毫反映不出他與玄學關系的信息,然而通過《義疏》可看到這個貌似與玄學無關的人卻是個玄學家。
二是容納了佛道思想。東晉南朝玄學乃西晉之余緒,一方面玄學家不少,佼佼者不多;另一方面又與佛教相融合。東晉張憑、殷仲堪,南朝劉宋顏延之、釋慧琳,蕭齊沈馬粦士、顧歡,蕭梁太史叔明均屬此類。張憑、殷仲堪已有專文論述,(9)王云飛:《張憑〈論語〉注研究》,《船山學刊》,2012年第1期;王云飛:《殷仲堪〈論語〉注研究》,《唐山學院學報》,2012年第1期。顏延之和釋慧琳曾是政治同僚,釋慧琳著《白黑論》、何承天著《達性論》,均為詆呵佛教之論。“永嘉太守顏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檢駁二論,各萬余言”,被宋文帝贊作“尤為名理,并足開獎人意”(10)(梁)僧佑撰,李小榮校箋:《弘明集校箋》卷一一《何令尚之答宋文皇帝贊揚佛教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76頁。之論,足見其佛教立場。顏延之釋《論語》“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說:“射許有爭,故可以觀無爭也。”他釋“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說:“秉小居薄,眾之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也。”他釋“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說:“譖潤不行,雖由于明,明見之深,乃出于體遠。體遠不對于情偽,故功歸于明見。斥言其功故曰‘明’,極言其本故曰‘遠’也。”(11)參見(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54、95、304頁。爭與不爭、失與得、明與遠,這些命題具有鮮明的佛學色彩。
顧歡是道家,然而卻說“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道則佛也,佛則道也”,(12)《南齊書》卷五四《顧歡傳》,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931-932頁。實則把佛納入道之體系。他在釋《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說:“此明非求非與,直以自得之耳。其故何也?夫五德內充,則是非自鏡也。”顧歡所說的“明”借用的是佛教概念,即“智慧”,用“明”形容五德內充。顧歡釋“未知生焉知死”說:“夫從生可以善死,盡人可以應神,雖幽顯路殊,而誠恒一。茍未能此,問之無益,何處問彼耶?”這種解釋也有佛教輪回的意味。他釋“回也其庶乎?屢空”說:“夫無欲于無欲者,圣人之常也;有欲于無欲者,賢人之分也。二欲同無,故全空以目圣;一有一無,故每虛以稱賢。賢人自有觀之,則無欲于有欲;自無觀之,則有欲于無欲。虛而未盡,非‘屢’如何。”太史叔明也發揮說:“顏子上賢,體具而敬則精也,故無進退之事,就義上以立‘屢’名。按其遺仁義,忘禮樂,隳支體,黜聰明,坐忘大通,此亡有之義也。忘有頓盡,非空如何?若以圣人驗之,圣人忘忘,大賢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復為未盡。一未一空,故‘屢’名生也焉。”(13)參見(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15、274、279-280頁。顧歡所說的圣人“無欲于無欲”“全空”,太史叔明所說的“圣人忘忘”,也頗有“本來無一物”的禪味。
上述兩個變化,能否說明皇侃的經學思想玄學化或佛道化了呢?當然不能。吳承仕《經典釋文敘錄疏證》對漢末以來諸家對《論語》的注疏做了如下統計:
何晏所集七家,并何為八;江熙所集十三家,并江為十四;皇《疏》所引二十八家,并皇為二十九。通為五十一家。(14)吳承仕著,秦青點校:《經典釋文序錄疏證》,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52頁。
從這個統計中可以看出,魏晉至南朝梁,對《論語》的注疏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何晏《集解》,第二個階段是江熙《集解》,第三個階段是皇侃《義疏》。這三個發展階段反映出這個時期經學發展的兩個問題:
第一,儒家思想始終占主體地位。何晏《集解》八家,除何晏之外,馬融、鄭玄、苞咸、周氏、陳群、王肅、周生烈幾乎都是儒家。皇侃《義疏》的儒家主體性前已論述,此不再贅。此只論江熙《集解》的儒學主體性。
江熙《集解》十四家最具儒家特色的是江熙和范寧,(15)關于江煕與皇侃的思想聯系,可參見高僑均:「江煕『集解論語』と皇侃『論語義疏』——魏晉六朝における『論語』解釋」、『六朝學術學會報』第9集、2008年、101-129頁。關于范寧的思想,參見[日]吉川忠夫著,王啟發譯:《六朝精神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9-114頁。玄學色彩最鮮明的是郭象和繆播。江熙字太和,東晉時人,官至兗州別駕。他注《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論語》,保存在《義疏》中的《論語注》102條,從內容看很少有玄道佛思想痕跡,當為儒家解經。范寧也是東晉時人,官至豫章太守,在郡大設庠序,取郡四姓子弟,課讀《五經》。他曾著論痛斥何晏、王弼玄學說:“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后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16)《晉書》卷七五《范汪附范寧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984-1985頁。范寧注《論語》有54條,亦為儒家解經無疑。郭象解經15條,繆播解經17條。二人加起來還抵不上范寧一人所注。如果把江熙、范寧二人所注與玄學家所注做一比較,更可以彰顯其儒家特色。然而江熙、范寧、郭象、繆播注釋同一條《論語》的數量有限,為了便于比較,我們把王弼的注釋也加進來。
《論語·述而》:“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郭象注道:孔子“傷器存而道廢,得有聲而無時”,由此引申出器與道的問題。而江熙注道:“和璧與瓦礫齊貫,卞子所以惆悵;虞《韶》與鄭衛比響,仲尼所以永嘆。彌時忘味,何遠情之深也!”范寧注道:“夫《韶》乃大虞盡善之樂,齊,諸侯也,何得有之乎?曰:陳,舜之后也。樂在陳,陳敬仲竊以奔齊,故得僭之也。”(17)參見(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163頁。江熙之解側重解釋孔子的感情所在,范寧之解則在說明齊國之所以有韶樂的原因。《論語·子罕》說:“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王弼注道:“譬猶和樂出乎八音,然八音非其名也”,涉及名與實的關系。而江熙注道:“言其彌貫六流,不可以一藝取名焉,故曰‘大’也”,(18)參見(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206頁。意在說明“大哉”的意思。《論語·陽貨》說:“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王弼注道:“孔子機發后應,事形乃視,擇地以處身,資教以全度者也,故不入亂人之邦。圣人通遠慮微,應變神化,濁亂不能污其潔,兇惡不能害其性,所以避難不藏身,絕物不以形也。有是言者,言各有所施也。茍不得系而不食,舍此適彼,相去何若也”,言及圣人通遠慮微,應變神化,避難不藏身,絕物不以形之特質。江熙注道:“夫子豈實之公山弗盻乎?故欲往之意耶。泛爾無系,以觀門人之情,如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山而不悅,升堂而未入室,安測圣人之趣哉?”(19)參見(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452-453頁。雖涉及形與道之抽象,但側重點在于闡述孔子志向和子路之愚昧。綜上所述,同樣的注,江熙、范寧與玄學家顯然不同,前者說經,后者說理;前者具體,后者抽象;前者實,后者虛。可見江熙、范寧之注儒家色彩是鮮明的。
第二,儒家思想體系的成熟。比較注釋《論語》的三個階段,可以發現儒家思想主體有一種越來越開放包容的趨勢。魏晉時期玄學大盛,但何晏集解《論語》,除個別地方做玄學發揮之外,所集絕大部分都是儒家學者所注。何晏之所以如此,當然想借儒家《論語》宣揚自己的思想,但如果玄學理論發揮或集入過多,恐怕不會得到當時經學界的接受和認可,反而對宣揚自己主張不利。這也反映了當時在玄學思想沖擊下,儒家相對封閉以自我保護的狀態。這種狀態可以說是因自身體系不成熟而缺乏包容和自信的表現。魏晉時期,何晏用玄學利刃在儒家相對封閉的經學本體上撬開了一個口子,然而到了江熙《集解》,更多玄學思想被加進來,到了皇《疏》又主動引進了佛道思想,而這種引進又是在儒家體系不變的基礎上進行,與其說是儒家的玄學化或佛道化,毋寧說是儒家主體由于成熟而更加開放包容的表現。因為只有主體的成熟,才會在吸收引進不同思想的同時而不被改變本質。
二、皇侃經學思想的儒家特性
莊子說:“六合之外圣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內圣人論而不議。”(20)郭慶藩輯,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內篇·齊物論》,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83頁。盡管論而不議,也足以說明儒家圣人對六合之內人和事的關照。況且,孔子之后,歷代儒家學者對六合之內的事理且論且議且闡發。可以說,關照現實,服務現實是儒家思想的傳統。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思潮中,玄學所關照的是形而上的幽深與玄遠,佛教所關照的是冥冥中的彼岸世界,因此,關照現實是儒家思想區別于上述二者的鮮明特性。(21)關于皇侃經學思想的儒家性質及與現實的關系,學界已有不少成果問世。如陳金木:《皇侃之經學》,“國立”編譯館1995版。日本學者今井裕一發表了系列研究皇侃的論文,如「聖·賢の境界:皇侃『論語義疏』における顔回」、『國學雜誌』第117輯、2016年、97-113頁;「至徳の証明:皇侃『論語義疏』における泰伯」、『國學院中國學會報』第61輯、2015年、34-44頁;「皇侃の『命』について」、『國學院中國學會報』第54輯、2008年、44-58頁。日本學者豬股宣泰也發表了系列研究論文,如「『論語義疏』に見える皇侃の學問観·人間観と教化論」、『集刊東洋學』第88集、2002年、42-61頁;「『論語義疏』に見える皇侃の思想」、『集刊東洋學』第80集、1998年、1-19頁。
東晉之后,朝代更替、政權禪代一個接著一個,臣子變為天子,天子又被迫“禪位”給自己的臣子。在這種循環往復中,所謂“忠”的觀念被消磨得全無蹤影。不僅禪代者不忠,就是一些無篡位之心或無篡位之力的臣僚,看著自己所賴以取得俸祿的朝廷更主易姓,也安之若素,不肯以身殉忠,更甚者還為“禪代”推波助瀾。以劉宋為例,蕭道成輔政,權勢漸重,在劉宋政權岌岌可危之際,尚書令王僧虔和左仆射王延之卻持“中立無所去就”態度。(22)《南齊書》卷三二《王延之傳》,第585頁。褚淵、王儉等均為劉宋之臣,卻成為南齊蕭道成的佐命元勛。在一次宴會上,蕭道成對他們說:“卿等并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褚淵當即答道:“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23)《南齊書》卷二三《褚淵傳》,第429頁。宋時公卿甘作蕭齊臣子,并以未早識龍顏為愧,可見他們對劉宋王朝存亡處之淡然的態度。
對皇位的篡奪使“忠”的觀念遭到進一步破壞,而“忠”的觀念崩壞,又使對帝位的篡奪之風愈演愈烈,從外族他姓發展到皇室內部。南朝宋、齊兩代,宗室內部互相殘殺尤為酷烈,被殺者中,上輩有叔祖,同輩有兄弟,晚輩有侄孫。閱宗室諸王列傳,這些被殺之人,有的是企圖篡位,有的是被牽進了帝位爭奪的旋渦,有的是被視為對皇位的威脅。總之,他們的死,大多與帝位之爭有直接或間接關系。“遙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縈,前見子殺父,后見弟殺兄”。(24)《魏書》卷九七《島夷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142頁。在這種父子兄弟殘殺中,儒家所提倡的孝悌在皇室中也只剩下一些支離的碎片了。
魏晉以來在政治斗爭中臣下所表現的不忠,宋、齊時期皇室所表現的不孝,對梁武帝的影響極深。他自己就是趁著齊末宗室大殺戮所造成的政權虛弱取而代之的,因此,他對不忠不孝所造成的危害有著切膚之感。他即位的當年四月便下詔說:“朕以寡薄,昧于治方,藉代終之運,當符命之重,取監前古,懔若馭朽。思所以振民育德,去殺勝殘,解網更張,置之仁壽。”(25)《梁書》卷二《武帝紀中》,第36頁。這里的“取監前古,懔若馭朽”,絕非即位時的套話,而是反映了他對不忠不孝給政權穩固造成沖擊的憂心。所以,南朝蕭梁建立以后,梁武帝一直致力利用種種手段重新培育儒家傳統的倫理道德。皇侃的日誦《孝經》二十遍當與這種社會背景有關。
作為儒家學者,皇侃對儒家忠孝道德重建的關心和參與,不僅僅表現是在日誦《孝經》二十遍,更重要的表現是在《論語義疏》中對忠孝觀念的闡發。
皇侃關于“孝”本質的論述,表述了移孝入忠、忠孝合一的觀念。這個觀念在《論語義疏》中多有涉及。《論語·為政》:“臨民之以莊,則民敬;孝慈,則忠。”皇侃注釋:“言君居上臨下,若自能嚴整,則下民皆為敬其上也。”“言君若上孝父母,下慈民人,則民皆盡竭忠心以奉其上也。故江熙曰:‘言民法上而行也,上孝慈,則民亦孝慈。孝于其親,乃能忠于君。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也。’”(26)(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39頁。皇侃在“江熙曰”前用了一個“故”字,既表示了他對江熙注解的贊同,又表示了他與江熙解釋之間相通的邏輯關系。這種相通的邏輯關系可以從皇侃注釋孔子的另一段話中看出來。有人問孔子為什么不從政,孔子回答說:“《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也。奚其為為政?”皇侃對此注釋說:“言人子在閨門,當極孝于父母,而極友于兄弟。若行此二事有政,即亦是為政也。”“此是孔子正答于或人也。言施行孝友有政,家家皆正,則邦國自然得正。亦又何用為官位乃是為政乎?”(27)(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40頁。人如果在家孝悌做得特別好,從政后自然就正直忠誠,用不著把他放到官的位置上后再要求他正直和忠誠。這與江熙所說“孝于其親,乃能忠于君,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是一個意思。皇侃在注釋“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時說:“又言若民中有善者,則舉而祿位之;若民中未能善者,則教令使能。若能如此,則民競為勸慕之行也。”(28)(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39頁。這里的“善”顯然是指忠孝行為,闡釋了皇侃任用忠孝之人,培養忠孝之人,從而使忠孝蔚為風氣的主張。《論語·子罕》:“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皇侃注釋說:“人子之禮,移事父孝以事于君則忠,移事兄悌以事于長則從也。故出仕朝廷、必事公卿也。”“孝以事父,悌以事兄,還入閨門,宜盡其禮也。先言朝廷、后云閨門者,勖已仕者也,猶‘仕而優則學’也”。(29)(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223頁。在南朝梁積極推進儒家忠孝道德時,上述這些關于忠孝的闡發,顯然是一種理論和輿論上的助推。
禮儀制度在南朝梁得到極大的發展。梁武帝即位后,十分重視禮對治理國家的作用。“詔求碩學,治五禮,定六律,改斗歷,正權衡”。天監四年(505),梁武帝又下詔置五經學館,一時間,懷經負笈者云會京師。梁武帝還“親屈輿駕,釋奠于先師先圣,申之以燕語,勞之以束帛”。由于他的提倡和推動,梁朝的儒學水平大大高于東晉和宋齊,出現了“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的局面。(30)《梁書》卷四八《儒林列傳·序》,第661-662頁。同時,南朝梁又是禮制建設的關鍵時期。尚書仆射徐勉曾這樣敘述梁朝以前五禮制度建設的情況:
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咨稟衛將軍丹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制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殂,遺文散逸,后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于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斂所余,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修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代,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太半。(31)《梁書》卷二五《徐勉傳》,第380-381頁。
為此,梁武帝專門下詔說:“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實宜以時修定,以為永準。但頃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貴總一,不以稽古,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先,外可議其人,人定,便即撰次。”(32)《梁書》卷二五《徐勉傳》,第381頁。于是梁朝建立后,制定五禮制度的工作有序展開,最后完成了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的五禮大典。
了解了上述社會背景,我們就可以理解皇侃撰寫《禮記講疏》,并將《禮記講疏》上奏給朝廷的行為,這是出于一個儒家學者對現實的強烈關照。這種關照同樣表現在《論語義疏》中。《論語義疏》中關于禮的注釋,大多圍繞禮與治國關系的主題。
關于禮在治理國家中的作用。《論語·陽貨》:“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皇侃注釋說:“夫禮所貴,在安上治民,但安上治民不因于玉帛而不達,故行禮必用玉帛耳。當乎周季末之君,唯知崇尚玉帛,而不能安上治民,故孔子嘆之云也。故重言‘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明禮之所云不玉帛也。”(33)(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457頁。禮的根本作用在于安上治民,而玉帛只是禮的形式,只重視形式而忽視其本質內容,就會使禮變成一個空殼。《論語·衛靈公》:“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皇侃注釋說:“雖智及、仁守、蒞莊,而動靜必須禮以將之,若動靜不用禮,則為未盡善也。”(34)(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412頁。治國當然靠智、仁、莊,然而沒有禮,智會有搖擺之失,仁會有松弛之失,莊會有嚴厲之失,所以要達到安上治民的目的,禮是最根本的要素。
禮是治理國家的有效手段。《論語·里仁》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皇侃注釋說:“為,猶治也。言人君能用禮讓以治國,則于國事不難,故云‘何有’,言其易也。”“若昏闇之君,不為用禮讓以治國,則如治國之禮何?”(35)(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89-90頁。如果用禮治國,治理國家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臣之從君,如草從風。故君能使臣得禮,則臣事君必盡忠也;君若無禮,則臣亦不忠也”,(36)(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69頁。昏君把國家治理得一團糟,就是因為丟掉了禮。
治理社會風氣也是治理國家的內容之一。《論語·學而》:“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皇侃對此注釋說:“人君行化,必禮樂相須。用樂和民心,以禮檢民跡。跡檢心和,故風化乃美。故云‘禮之用,和為貴’。和即樂也。變樂言和,見樂功也。樂既言和,則禮宜云敬。但樂用在內為隱,故言其功也。云‘先王之道斯為美’者,先王謂圣人為天子者也,斯,此也。言圣天子之化行,禮亦以此用和為美也。云‘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若小大之事皆用禮而不用和,則于事有所不行也。云‘知和’云云者,上明行禮須樂,此明行樂須禮也。人若知禮用和,而每事從和,不復用禮為節者,則于事亦不得行也。”(37)此段文字,中華書局校點本分句解釋,不便整體引用,故此處征引《叢書集成新編》本《論語集解義疏》。參見(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論語集解義疏》,《叢書集成新編》第17冊,新豐文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00頁。社會風氣包括人心和人的行為。這兩個方面需要禮樂合力治理,樂和民心,禮檢民跡,行禮須樂,行樂須禮,皇侃此論,強調了禮對治理社會風氣的重要作用。
人是治理國家的主體,治國者的素質高低,與其禮的修養有密切關系。《論語·堯曰》:“不知禮,無以立也。”皇侃注釋說:“禮主恭儉莊敬,為立身之本。人若不知禮者,無以得立其身于世也。故《禮運》云‘得之者生,失之者死’,《詩》云‘人而無禮,不死何俟’,是也。”(38)(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524-525頁。人而無禮不得立身和生存,同樣治國之人無禮,國便不能立,亦不能存。所以皇侃說:“得制禮樂者,必須德位兼并,德為圣人、尊為天子者也。所以然者,制作禮樂必使天下行之,若有德無位,既非天下之主,而天下不畏,則禮樂不行;若有位無德,雖為天下之主,而天下不服,則禮樂不行,故必須并兼者也。”(39)(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153頁。
上述皇侃《論語義疏》中關于“忠”“孝”“禮”等問題的闡釋,植根于六合之內的孔子之論,針對當時振興儒家道德和完成禮制建設的社會現實而議論發揮。它既不是沒有任何根據的無源之水,也不是沒有任何指向的抽象空談,而是理論基礎與現實意義的有機結合。因此,皇侃《論語義疏》具有鮮明的儒家特性。
三、《論語義疏》對儒家思想的理論提升
義疏之學興起于南朝。清人皮錫瑞說:“夫漢學重在明經,唐學重在疏注;當漢學已往,唐學未來,絕續之交,諸儒倡為義疏之學,有功于后世甚大。”(40)(清)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第186頁。蒙文通先生說:“及今文章句淪亡,義疏遂猾起于齊梁之際。”(41)蒙文通:《經學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頁。南朝義疏之學的興起,當與佛教盛行有關。《維摩經略疏垂裕記》:“疏者疏也,決也,疏通經文,決擇佛旨故曰疏也。”(42)(宋)智圓:《維摩經略疏垂裕記》,《大正新修大藏經》第38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715頁。《摩訶止觀》卷七下:“第九安忍者,能忍成道,事不動亦不退,是心名薩埵。始觀陰界至識次位八法,障轉慧開,或未入品,或入初品。神智爽利,若鋒刃飛霜,觸物斯斷。初心聰睿有逾于此,本不聽學,能解經論。覽他義疏,洞識宗途。”(43)(隋)智:《摩訶止觀》,《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6冊,第99頁上欄、中欄。可見“義疏”一詞是由佛教經典而來。
皇侃是儒家學者,主張儒經獨尊。他解釋孔子“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說:“此章禁人雜學諸子百家之書也。攻,治也。古人謂學為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其經也。異端,謂雜書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于諸子百家,此則為害之深,故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斯害也已矣者’,為害之深也。”他還對何晏注“云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說:“云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者,善道,即五經正典也。有統,統本也。謂皆以善道為本也。殊途謂詩書禮樂為教之途不同也,同歸謂雖所明各異而同歸于善道也。云異端不同歸者也者,諸子百家并是虛妄,其理不善,無益教化,故是不同歸也。”(44)此段文字,中華書局校點本分句解釋,不便整體引用,故此處征引《叢書集成新編》本《論語集解義疏》。參見(梁)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叢書集成新編》第17冊,第502頁。這反映了皇侃對儒家經典的根本態度。然而皇侃并不一概排斥異端,《論語義疏》中出現許多佛教和玄學的詞語和概念。如果細加分析可以發現,皇侃不是簡單地使用這些概念,而是在方法論意義上的創造。佛教義疏是“疏通經文,決擇佛旨”,是“覽他義疏,洞識宗途”,那么,《論語義疏》應該是疏通儒家經文,決擇儒家之旨,洞識儒家宗途。《論語義疏》對名物制度訓詁忽而略之,對儒家思想的本旨發而弘之,這是對佛玄思想方法的運用和借鑒。用義疏的方法發掘儒經中的義理,是皇侃經學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其義理性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總結規律。皇侃《義疏》對規律的總結表現為對學習的認識。孔子說:“學而時習之。”皇侃則緊緊抓住“時”字發揮。他說,學有三時:人中、年中、日中。所謂人中,即學習要在適當的年齡,年紀太小則學不懂(幼則迷昏),太大了學不進去(長則捍格)。所謂年中,即一年當中選擇合適的季節學習相應的知識(學隨時氣,則受業易入)。他還引用《王制》“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一語,并解釋說:“春夏是陽,陽體輕清,詩樂是聲,聲亦輕清,輕清時學輕清之業,則為易入也。秋冬是陰,陰體重濁,書禮是事,事亦重濁,重濁時學重濁之業,亦易入也。”(45)(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2頁。查《禮記·王制》無此語,不知此《王制》出自何書。或從《禮記·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一語而來。所謂日中,即將所學日日修習,不要有一日之廢。皇侃把“時”分為三個方面:生理之時,四季之時,日月之時。在人生最好的年齡,在不同的季節安排不同的學習內容,并加以持之以恒的堅持。選擇、安排、堅持與學習之間的聯系,實際上就觸及學習的規律問題。
其二,揭示本質。皇侃《義疏》對事物本質的揭示表現在對“孝”的深層思考。《論語·學而》:“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皇侃解釋“好犯上”為懷有諫諍之心,釋“鮮”為“少”。懷有諫諍之心的孝悌之人之所以“少”,是“不欲存孝子之心使都不諫”,即肯定一部分人即使懷有“犯上”諫諍之心,也是孝悌之人。這就否定了孝悌者必以無違為心,以恭從為性,沒有犯顏諫諍之心。皇侃引用其師賀玚的話說:“今按師說云:‘夫孝者不好,心自是恭順;而又有不孝者,亦有不好,是愿君親之敗。’故孝與不孝,同有不好,而不孝者不好,必欲作亂。”(46)(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5-6頁。孝與不孝,不是看其表面上是否恭順,因為表面的恭順,有的是出于對長輩的尊敬,也有的是出于“愿君親之敗”的邪惡目的。孝與不孝,要看恭順背后的動機,這就深入到了對“孝”的深層次探討。
揭示本質還表現在對人性的探討。《論語·為政》:“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也。’”馬融注道:“所因,謂三綱五常也。”人類十世乃至百世的歷史之所以可知,是因為三綱五常世世相因而不改變。皇侃則進一步把五常歸為人性:“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也。就五行而論,則木為仁,火為禮,金為義,水為信,土為智。人稟此五常而生,則備有仁、義、禮、智、信之性也。人有博愛之德謂之仁,有嚴斷之德為義,有明辨尊卑敬讓之德為禮,有言不虛妄之德為信,有照了之德為智。此五者是人性之恒,不可暫舍,故謂五常也。”(47)(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42頁。這種認識,是對曹魏劉劭理論的繼承。(48)劉劭《人物志》:“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實,各有所濟,是故骨植而柔者謂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質也。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色平而暢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五質恒性,故謂之五常矣。”參見(魏)劉劭著,梁滿倉譯注:《人物志·九征》,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8頁。人性之常不變是就其質而言,就量而言是有變化的。皇侃疏《里仁》說:“里者,鄰里也。仁者,仁義也。此篇明凡人之性易為染著,遇善則升,逢惡則墜,故居處宜慎,必擇仁者之里也。”(49)(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81頁。怎樣認識人性?皇侃認為,金木水火土或者說仁義禮智信包含在天地之氣當中,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就天然賦有五常之性。性與情是不同的兩種東西,性是與生俱來的,“性是生而有之,故曰生也。情是起欲動彰事,故曰成也”。皇侃還提出“性無善惡”的命題,那么,仁義禮智信五常不是“善”么?皇侃認為,五常不但不可以名之為“惡”,也不能稱之為“善”。這個論斷是符合辯證法的。試想,如果認為有“善”五常,就不能否認有“惡”五常。既然人性稟五常之氣,那么只有濃薄之分,不應有善惡之別。(50)(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445頁。
其三,抽象概念。《論語·為政》:“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皇侃注釋說:“此章美顏淵之德也。回者,顏淵名也。愚者,不達之稱也。自形器以上,名之為無,圣人所體也;自形器以還,名之為有,賢人所體也。今孔子終日所言,即入于形器,故顏子聞而即解,無所咨問。故不起發我道,故言‘終日不違’也。一往觀回終日默識不問,殊似于愚魯,故云‘如愚’也。”(51)(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31頁。在皇侃看來,孔子思想是形而上的,一旦表現為語言,就落入具體的“有”。而領會圣人之無,只有通過他的語言。而顏回是能夠領會圣人形器以上之“無”的。《論語·公冶長》:“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皇侃注道:“夫子之言即謂文章之所言也。性,孔子所稟以生者也。天道,謂元亨日新之道也。言孔子六籍乃是人之所見,而六籍所言之旨,不可得而聞也。所以爾者,夫子之性,與天地元亨之道合其德,致此處深遠,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聞也。”(52)(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110頁。文章表現為“言”,是具體的、可見的,而文章之“旨”是深而遠的,不可直接得到的。
在有些地方,皇侃又把儒家形而上的抽象歸為“道”或“理”。《論語·述而》:“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皇侃注釋說:“此孔子重《易》,故欲令學者加功于此書也。當孔子爾時,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也。所以必五十而學《易》者,人年五十,是知命之年也,《易》有大演之數五十,是窮理盡命之書,故五十而學《易》也。既學得其理則極照精微,故身無過失也。云‘無大過’者,小事易見,大事難明,故學照大理則得一,不復大過,則小者故不失之。”(53)(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167頁。《論語·衛靈公》“予一以貫之”,皇侃注釋說:“貫,猶穿也。既答曰‘非也’,故此更答所以不多學而識之由也。言我所以多識者,我以一善之理貫穿萬事,而萬事自然可識,故得知之,故云予一以貫之也。”他注釋何晏“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也”說:“元,猶始也。會,猶終也。元者善之長,故云‘善有元’也。事各有所終,故曰‘事有會’也。事雖殊涂,而其要會皆同,有所歸也。致,極也,人慮乃百,其元極則同起一善也。是善長舉元,則眾善自舉,所以不須多學,而自能識之也。”(54)(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394頁。《易》中有“理”,一善之理貫穿萬事,這是皇侃對“理”的抽象。關于“道”,皇侃在注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時說:“道者,通物之妙也。通物之法,本通于可通,不通于不可通。若人才大,則道隨之而大,是人能弘道也。若人才小,則道小,不能使大,是非道弘人也。”(55)(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409頁。《論語·衛靈公》:“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皇侃注釋說:“謀,猶圖也。人非道不立,故必謀道也。自古皆有死,不食亦死,死而后已,而道不可遺,故‘謀道不謀食’也。餒,餓也。唯知耕而不學,是無知之人也。雖有谷,必他人所奪,而不得自食,是餓在于其中也。雖不耕而學,則昭識斯明,為四方所重。縱不為亂君之所祿,則門人亦共貢贍,故云‘祿在其中矣’。故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曰‘與其死于臣之手,無寧死二三子之手’是也。學道必祿在其中,所以憂己無道而已也。若必有道,祿在其中,故不憂貧也。”(56)(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410-411頁。在皇侃看來,道和理一樣,是可以貫通萬物并使人安身立命于上的東西。皇侃甚至認為,“道”和“理”是同一個東西。他在注釋何晏“凡人任情喜怒違理”時說:“未得坐忘,故任情不能無偏,故違理也。”他又在注釋何晏“顏淵任道,怒不過分”時說:“過猶失也。顏子與道同行舍,不自任己,故曰‘任道’也。以道照物,物豈逃形?應可怒者皆得其實,故無失分也。”他注釋何晏“怒當其理,不移易也”時說:“照之故當理,當理而怒之,不移易也。”(57)(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126-127頁。凡人任情,所以違理;顏淵任道,所以當理,可見“道”和“理”是一個概念。
其四,辯證思維。皇侃在《論語義疏》中,提出了一些辯證范疇。例如“無知”與“有知”的關系。《論語·子罕》:“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皇侃注釋說:“知,謂有私意于其間之知也。圣人體道為度,無有用意之知,故先問弟子云‘吾有知乎哉’也。又,‘無知也’,明己不有知知之意也,即是無意也。”“雖復鄙夫,而又虛空來問于我,我亦無隱,不以用知處之,故即為其發事終始,竭盡我誠也。即是無必也”。他解釋何晏“知者,知意之知也。言知者,言未必盡也。今我誠盡也”說:“知意,謂故用知為知也。圣人忘知,故無知知意也。若用知者,則用意有偏,故其言未必盡也。我以不知知,故于言誠無不盡也。”(58)(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214頁。皇侃在這里揭示了懷有無知之心,才能廣納知識,最后達到無所不知的辯證關系。再如“同”與“異”的關系。《論語·憲問》載,一個擔草筐的人譏笑孔子不肯隨世而變,孔子因此感慨,讓不了解自己的人不譏笑自己是很難的事。皇侃對此注釋說:“賢圣相與,必有以也。夫相與于無相與,乃相與之至。相為于無相為,乃相為之遠。茍各修本,奚其泥也?同自然之異也。”(59)(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集解義疏》,第385頁。意思是,圣賢之間的交好,是以相知為前提條件的,這是因為他們“同”。然而這不是最高境界的交好。交好于無交好才是交好之至;互助與無互助才會互助得長遠。因為這是通過各修其本而達到的溝通,是同自然之異。“異中之同”高于“同中之同”,其中的道理是很深刻的。
總結規律、揭示本質、抽象概念、辯證思維這些具有濃厚理論思維的義理內容在魏晉以前的經學里是罕見的。直到魏晉時期,王肅始對經學進行義理方面的闡發,而皇侃則把王肅經學這一特點進一步發揚光大。北宋陳祥道說:“孔子之世,師道既明,異端未起,由辨議無間而作,故圣人之答問言理而足矣。”“然而孟子之世,許子之言盈天下,孟子思欲拒诐說,放淫辭,不得已而有辨焉。難疑問答,不直則道不見,故其為言尤詳于《論語》”。(60)(宋)陳祥道:《論語全解·原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86年,第196冊第64頁。孔子時代用問答形式承載儒理,孟子時代則用直辨形式表達儒理,之所以如此變化,是因為時代發生了“許子(許行)之言盈天下”的變化。同樣,魏晉以前,思想界儒家獨大,沒有什么學派對儒家的地位構成沖擊和威脅。而魏晉時期,玄學由興轉盛,東晉南朝,佛教又異軍突起,玄學對事物本源的抽象思辨,佛教對生命去從的超世闡釋,都極大地吸引著當時的士人群體。在這種形勢下,經學如果固守名物制度的訓詁,剖章析句,但誦師言,勢必在玄佛二家形而上的理論優勢面前相形見絀,從而失去吸引士人群體和知識精英的魅力。因此,大力闡發儒家經典的義理,使經學具有形而上的理論形態,是經學能夠和玄佛并立爭榮的需要和前提。魏晉時代王肅對義理的闡發是播下思想的種子,皇侃時已經開花結果,使經學在思想理論形態上有了顯著的提升。他們所堅持的儒學體系,是魏晉南北朝乃至隋唐吸收玄學和佛教思想的堅實本體;他們所闡述的儒家義理,是隋唐以后產生的理學和心學的思想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