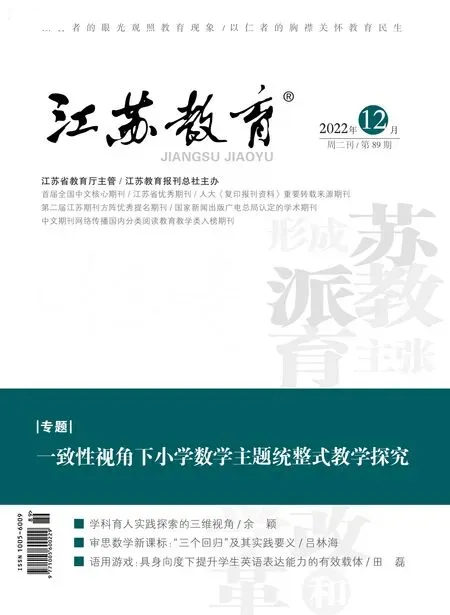審思數學新課標:“三個回歸”及其實踐要義
呂林海
新課標一經發布,便引發了數學教育理論界,特別是一線實踐界的巨大關注,學習新課標、領會新課標、實踐新課標幾乎成了一種思想和行動的共識。在各種講壇講座、課題活動、教研活動中,言必稱“要結合新課標來研究”“要體現新課標的思想”“要站在新課標的高度來審視自己的教學”……這些話語構成了一種時髦、一種言語范式,甚或一個“價值制高點”。仿佛誰沒有圍繞新課標來展開課題研究、思考教學活動或落實教學行為,就是一種落后、一種不合時宜,甚至是一種方向錯誤。
然而,如果專家指導、教學設計、教研活動等都歸結到新課標,一切都唯新課標的指示來辦,甚至用“言必稱新課標”的說辭來寬泛地說教、指揮,很可能會滋生一種思考的懶惰性,一種思想的簡單性,一種實踐的機械性。新課標只是一個藍本,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大致的方向,但絕不可能面面俱到,它希望實踐者去豐富它、思考它、完善它;新課標蘊含著極為廣闊的解讀空間、認識空間、實踐空間,它為一線教師提供了巨大的行動創新可能,但也對每位教師的教育理解力、思考力和創造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乃至考驗。我們應當看到,圍繞目標、內容、實施和評價等組織起來的新課標,絕不僅僅是具體知識點的內涵呈現、教法指引、評價指示(如果是那樣,將其稱為“教師教學行動指南”則更為適切),而且新課標也無法做到如此“瑣碎”和“細致”,它仍然只是一個較為上位的“啟示性文本”“精神性文本”。它其實要解答的問題是,“數學新課程的精神要義是什么”“數學教學的總體建議是什么”“教學評價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很明顯,具有“上位引領性”的新課標無法做到事無巨細地澄清所有的要點,它期待著一種實踐的變通和創新。
由此可見,對于新課標的認識和把握,直接沉浸于細節深處,去掌握目標、內容、實施和評價等方面的具體內涵,當然也是需要的,但肯定是不夠的。筆者認為,目前更加重要的工作,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從數學教育的本質出發,去透視新課標背后的精神要義和深層意蘊,以此來真正指引“精雕細刻的細節性工作”,這樣便可讓實踐者更清晰、更準確甚至更科學地“走進新課標、習得新課標、把準新課標”。基于此,本文試從“回歸數學的本質”“回歸學習的本質”“回歸教學的本質”的“三回歸”視角,對新課標背后的關鍵要義做出解析與把握。
一、回歸數學的本質

抽象性讓數學與科學在本質上區分開了。盡管數學與科學都需要建模,或體現模型化的特點,但數學是科學模型化的內核。這是因為,科學模型的最終解決,其實是一個數學模型的解決。科學的建模是“兩次建模”,第一次是從現實經驗世界“建構出”一個“物理模型”(這是圍繞力、電、磁等物理體系建構的),第二次是基于這個“物理模型”“抽象出一個數學模型”,構建出“數學關系”。最后,解決了這個“數學模型”,就形成了一種“反身效應”,即反推出這個現實世界物理問題的解決。所以,新課標提出,“要關注現實世界的問題,要讓學生從經驗到的社會生活中體會到數學的魅力與價值”,這不僅體現了數學建模及其“反身效應”的核心特質,而且符合荷蘭數學教育家弗賴登塔爾所謂“數學是常識的精微化”的精妙論斷。但我們要警惕,我們的確要讓數學與生活世界勾連,但我們應將更大的教學筆墨安置在對“數學關系”的認知、體悟和建構上,而非過多關注一種“科學建模”的過程。數學課更關注的應是“第二次建模”(即數學抽象),而非“第一次建模”(即科學建模)。數學課在本質上不是科學課。
進一步地,新課標提到了“數感”,其實,這就是一種對數量和數量關系的直覺,也就是一種“抽象關系的直覺”;新課標也提到了“推理意識”,這同樣體現了對學生在抽象體系中進行“邏輯思維培養的價值”,其涵養的也是一種“抽象性思考的能力”。另外,如“模型意識”“應用意識”等,其實都無法和“抽象性”這一本質相剝離,它們都是“抽象性”的一種體現或延伸。

二、回歸學習的本質
新課標字里行間體現出了一種對學習“參與隱喻”的明顯強調。例如,新課標提出:“以核心素養為導向,進一步強調學生獲得數學基礎知識、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動經驗(簡稱‘四基’),發展運用數學知識與方法發現、提出、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簡稱‘四能’),形成正確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1]在這段“宣言式”的表達中,可以看到,學生所學到的并不僅僅是“基本的知識和技能”,而且要“運用”知識與技能去“參與”到“數學的問題解決活動”之中,在活動的參與過程中形成能力、發展品格、涵養情感。“參與”成為新課標所隱隱強調的關鍵理念,這其實與學習科學的最新發展方向相呼應。美國著名學者喬納森在《學習環境的理論基礎》一書中清晰地指出:“學習理論者已經見證了指導大部分基礎教育(K-12)學校實踐的占支配地位的‘獲得隱喻’開始轉向‘參與隱喻’,‘參與隱喻’認為知識從根本上是處于實踐之中的。”[2]基于此,我們應當認識到,新課標所要求的并不僅僅是“知”,也包含“行”,更包含在“知與行”的聯結中生成的“識”,這即是一種見識、洞識、慧識,是一種基于“知行合一”生發出的最深層、最隱秘的“智慧素養”。
回歸學習本質的第二個要義,即“回歸學習的情感性本質”。西方的理性主義長期以來將學習規約在“理性的范疇之中”,情感通常被認為是對理性的干擾,甚至是對理性的損傷。由此,長久以來的學習理論都忽視“學習的情感維度”,相關的研究雖然不排斥情感存在的意義,但他們至少認為,相對于認知加工、心智建構等理性機制而言,情感或情緒的機制是旁枝末節、意義甚微的。但其實,“這種見識”越發被證明是一種偏見,甚或是一種短視。隨著美國南加州大學達馬西奧、哈佛大學海倫等學者的最新研究紛紛產生,學術界越來越認識到,“情緒不僅不是無關緊要的,它還是認知和學習導航的‘情緒舵’,學習的過程離不開情緒”。海倫明確地指出:“情緒并不是認知的附屬品,相反,它就像好奇、焦慮、挫敗、興奮或在看到美時心生崇敬那樣,構成認知能力的一個維度。”[3]美國當代哲學家諾斯鮑姆早就點明:“情感不僅僅是理性創造物心理機制的動力來源,它甚至就是創造物的理性自身非常復雜和凌亂的組成部分。”[4]由此,學習科學研究者們提出了一個名為“情緒思維”的研究工具,借此來對“情緒和思維彼此交織的認知機制”進行更加深入和詳盡的學術刻畫探究。我們應當追蹤當前學習科學關于學習情感本質的最新研究發現,并審視新課標中體現出的對于學生學習情感的關注。例如,新課標提出,要“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提升學生的探究熱情”“對身邊與數學有關的事物有好奇心”“樹立學好數學的信心”等,這些表述本質上都關涉學生的學習情感,這些表述所隱含的更深層教學意涵,對教師挖掘學科情感、激發學術直覺、打造安全情境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與挑戰。

三、回歸教學的本質

回歸教學本質的第二個要義,是關注教師的激情投入。數學課堂給人的感覺往往是理性的、嚴謹的,是一種不應有情感摻雜其中的“純粹”課堂。這種認識其實是不全面的。一件事物“存在”某種特性,并不是其“排斥”另一種特性“存在”的“充分條件”。這種“充分性”的“絕對實現”只有一個可能,就是這兩個特性之間是絕對“相互排斥”“非此即彼”的。此即“排中律”發揮效應的關鍵意涵。由此,“男與女”是互斥的,“長與短”是互斥的,但“理性與情感”不是互斥的。一個有理性的人,未必是一個沒有情感的人;反之亦然,一個情感充沛的人,未必就是一個邏輯混亂的混沌之徒。對教師而言,特別是對數學教師而言,需要在展現數學邏輯嚴謹、體系規整的“理性化特質”的同時,更表現出自身對數學的強烈情感、滿懷摯愛,他本質上應是一個“激情”教師。“激情”是引發教師全力投身教育、展開高質量教學的必要前提。英國學者戴杰思在《教育與激情》一書中清晰地點明,“具有教學激情的教師是那些在與兒童、青少年和成年人相關的工作中具有責任心、激情滿懷、投入智力和充沛情感的人”“教學是一個富有創造性和冒險性的職業,激情并不是一種選擇,而是對高質量教學不可或缺的存在”“激情投入的教師是那些絕對熱愛他們所做事情的人”[5]。進一步地,我們還要認識到,“激情”絕不是一種矯飾、一種表演,“激情”只能自然流露,從教師對學生的一個眼神、一個表情、一個手勢、一個微笑中自然顯現,這種顯現是一種默會,一種“教師和學生之間的心領神會”,一種教師和學生“心靈間被激起的相互聯系、相互肯定、相互融合、相互成全”,它意味著“你與我之間的”關懷和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