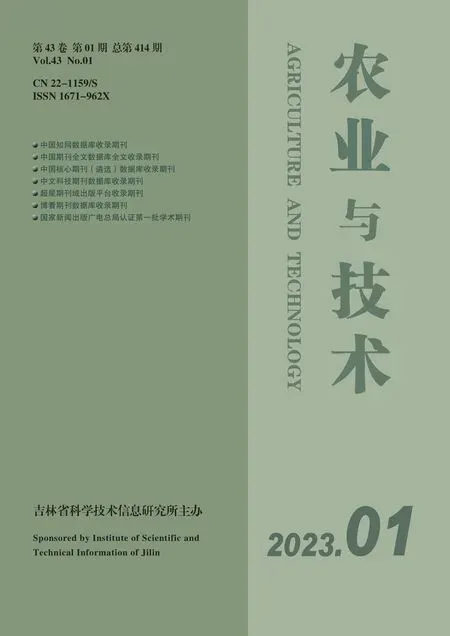農村體育貧困多中心治理的社區實踐策略研究
——基于重慶市的考察
楊梅周泓伶盧鴻毅李壓利
(1.重慶理工大學管理學院,重慶 400054;2.重慶理工大學創新驅動創業協同研究中心,重慶 400054;3.重慶市體育局,重慶 400015)
我國已經取得了脫貧攻堅的偉大勝利,消除了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但是農村減貧工作仍然任重道遠。既要解決共同富裕道路中的相對貧困問題,提升農村居民生活質量多個維度的獲得感與幸福感[1];又面臨防返貧的嚴峻挑戰,其中因病致貧、返貧人口占比近40%,加大了農村健康、經濟和社會的脆弱性[2]。體育是一種運動方式、文化活動,且具有人文價值、教育教化功能,以及商品屬性,在增進參與者的身體素質、幸福、健康和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從根本上解決因病致貧、返貧,提升人力資本使用效能的有效之策,是健康扶貧的重要內容、文化扶貧的內在支撐、教育扶貧的外延形式、產業扶貧的多元手段[3-5]。發展農民體育事業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抓手,意義重大。然而,當前農村體育貧困現象明顯,農村人口與體育供給仍然不匹配[6],農村居民體育權益保障水平總體仍處于較低水平,體育機會和體育能力匱乏[7],迫切需要扶“體育之貧”。積極推進農村社區建設,打通全民健身“最后一公里”,為農村居民提供精準化精細化的體育健身服務,是實現體育脫貧的現實著力點。為保障廣大農民群眾的公共體育服務享有,本文考察重慶市農村社區全民健身“六個身邊”工程實施情況,圍繞農村居民體育權利,從體育機會、體育資源、體育能力3個維度,探索政府-市場(企業)-社會組織-農村居民“四位一體”的我國農村體育貧困治理在社區層面的實現路徑和實踐策略。
1 重慶市農村社區全民健身“六個身邊”工程現狀
重慶市是地處西部地區的直轄市、特大城市,人口眾多(其中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979.01萬人,JP3占30.54%;各少數民族人口為217.08萬人,占6.77%),集大城市、大農村、山區、庫區(三峽庫區)于一體,社區類型和體育環境豐富多樣,具有典型性和研究的示范效應。2017年,國家體育總局提出了全民健身“六個身邊”工程,即完善群眾身邊的體育健身組織,建設群眾身邊的體育健身設施,豐富群眾身邊的體育健身活動,支持群眾身邊的體育健身賽事,加強群眾身邊的體育健身指導,弘揚群眾身邊的體育健身文化,是新時代群眾體育的四梁八柱[8]。本文通過對重慶市農村社區“六個身邊”工程實踐效果的問卷調查和實地考察,探索農村社區體育貧困治理的實現路徑和工作重點。
1.1 農村社區健身組織:自組織,數量少,規模小
農村社區健身組織大多是居民自發組織、自由組建的健身團隊,如壩壩舞隊(廣場舞)、腰鼓隊、擺手舞隊等,規模小,十幾個人到四五十人不等。一般不收取活動費用,也沒有約束和規范管理,多以村委會廣場或居民院壩為活動場地。基層綜合性文化體育服務中心/綜合文化服務中心是鄉鎮、街道辦事處專門負責群眾體育工作的部門,有文化體育專干(沒有固定崗位名稱,只有具體分工),但是鄉鎮、街道,以及居/村委會都不對農村居民“自組織”的健身團隊進行指導和管理。目前重慶市、區縣2級體育總會沒有實現全覆蓋,市級體育協會數量較少(2019年共有54個),農村社區沒有體育協會等社會組織,農村社區健身組織呈現“小散弱”的特征。
1.2 農村社區體育健身設施:匱乏單一,使用不充分
調查顯示,農村體育資源仍然相對匱乏,鄉鎮健身廣場覆蓋率較低(2019年48%),沒有健身設施的農村社區還占有較高比例(46%)。體育健身設施類型比較單一,主要有2類,農村體育健身工程標配的1個籃球場和2個乒乓球臺;與城市社區相同的休閑娛樂型體育設施。2類體育設施被納入全民健身路徑,主要由政府(體育局)提供。農村的健身設施多集中安裝在村辦公室、村便民服務中心或者當地村小學附近,由于農村社區散點式的居住特征,再加上留在農村的多為老年人、婦女和兒童,普遍缺乏運動技能和體能,健身設施的使用并不充分。在個別社區,籃球場和乒乓球臺大多數時間是“停車場”“晾曬場”,休閑體育設施沒有專人維護和保養,閑置廢棄,或變成晾曬工具,晾衣、曬菜。
1.3 農村社區體育健身活動:參與度低,滿意度不高
調查結果顯示,70%以上的農村居民體育意識薄弱,認為干農活就是體育鍛煉,因而參與健身活動的積極性不高,僅有24%的農村居民經常進行體育鍛煉。重慶市頒布了《重慶市全民健條例》《重慶市全民健身實施計劃》《重慶市全民健身公共服務體系提升計劃》《重慶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建設體育強市的實施意見》等文件,各區縣積極開展“全民健身月”活動,鄉鎮或街道每年舉辦約20~30場群眾文化體育活動,主要是送春聯、游園活動、傳統節慶活動,涉及體育的以廣場舞展演為主,對農村社區體育健身活動的支持力度有限。另外,廣場舞、棋牌等還會因為場地、噪音等與社區其他居民產生沖突,體育健身活動的滿意度普遍不高。
1.4 農村社區體育健身賽事:數量少,影響弱,社會參與度低
調查結果顯示,90%的農村社區基本不舉辦社區體育賽事,占比10%的農村社區由于有傳統民俗體育活動,或常態化的體育健身賽事,主要是作為鄉村旅游、文化商貿活動的項目,吸引市民和外地游客參加,社區居民參與度不高。賽事資金渠道來源單一,一般是基層政府財政撥款、當地村委會適當補貼,由居/村委會或文化服務中心組織。除了廣場舞、擺手舞大賽參與隊伍較多,其他體育賽事參與人數較少,對農村居民參與健身活動的帶動作用不明顯,受訪者中有50%的農村居民甚至不清楚社區是否舉辦體育賽事。
1.5 農村社區體育健身指導:極度匱乏,專業性有待提升
調查結果顯示,98%的調查對象認為目前農村沒有或嚴重缺乏專業的健身指導,占比81%的農村居民認為需要得到健身指導。鄉鎮或街道每年會出資邀請專業教師和教練給社區居民進行文體活動的培訓(如舞蹈、瑜伽等),參與人數一般在20余人/次。在村委會/居委會這個層面,基本不開展體育活動培訓。從調查的情況來看,幾乎所有的農村社區都沒有聘用職業性社會體育指導員,偶爾會有公益組織、志愿者送體育下鄉,但不是常態化的體育指導。區縣體育局每年都要定期集中培訓公益性的社會體育指導員,培訓時間較短,鄉鎮或街道的名額也不多,一般10~20名,真正下到農村社區基層的社會體育指導員更是寥寥無幾。
1.6 農村社區體育健身文化:文化挖掘不充分,有效宣傳不足
重慶市境內有多個民族自治縣,土家族擺手舞、高腳馬;苗族跳大鼓、蘆笙舞、龍舟節;仡佬族打篾雞蛋、平橋耍龍等民族體育項目得到較好的保護,在農村有專門的表演隊伍,但除了土家族擺手舞成了健身鍛煉中的民族廣場舞,其他項目更多在節慶表演,趨于形式化。發端于西方的現代體育受到大眾的認可和推崇,并逐漸向農村地區滲透,本地體育文化比較缺位,農村社區體育健身文化的宣傳以墻報、宣傳欄、宣傳單等線下手段為主,農村居民會關注公告欄內容,但僅是看看而已,沒有付之行動。
2 農村體育貧困多中心治理面臨的問題
2.1 政府主導力量單一
計劃經濟時代,我國公共體育服務基本依靠政府供給,是體育事業,由政府統籌。加上競技體育優先發展,城鄉二元發展結構等影響,農村體育投入有限,發展嚴重滯后。進入新時代,體育產業逐漸成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極大地促進了城市體育發展,在農村地區也發揮了體育扶貧的積極作用。隨著“農民體育健身工程”“雪炭工程”“體育扶貧工程”等的相繼實施,公共體育服務加快向農村拓展與延伸。但是由于基礎薄弱、欠賬太多,農村體育事業發展仍然落后于國家公共體育發展標準。農村體育供給仍然主要依靠“政府主導、政府干”,通過財政投入和政策等要素驅動,缺乏各治理主體的聯動作用。鄉鎮(街道)文化體育服務中心/綜合文化服務中心負責文化體育工作,但相關部門管理形式流于表面。
2.2 市場賦能推動力不足
市場(企業)通過體育扶貧和商業開發,拓展了農村體育產品的供給渠道。但是由于市場(企業)進入農村體育市場剛性阻力較大,加之農村體育人口少,且呈現非經濟、低消費的特征,體育產業發展的推動力不足,市場(企業)對農村社區體育發展的拉動并不顯著,作用有限。
2.3 社會組織參與程度低
農村社區的村/居委會作為村民自治組織,負責傳達上級(國家、省市、區縣)的文件精神,協助文化體育服務中心或綜合文化服務中心組織相關體育活動、賽事,參與治理的空間狹窄。然而,農村社區缺乏體育協會、體育俱樂部等社會組織,一般是通過社會服務機構、基金會和社會團體(個人)的自愿性供給或扶貧,“拾遺補缺”作用不強。
2.4 農民健身意識薄弱
農村居民作為主體,體育意識淡薄,健身活動參與率低,缺乏主動性和積極性,是主觀原因。客觀上,農村居民需求表達渠道不暢,缺乏話語權。目前社區體育供給基本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為,經費有限、總量不足,存在供給錯位的問題,對于全民健身活動、健身賽事等的管理和指導沒有下沉到社區。
3 啟示與建議
3.1 政府主導下多元主體的協同共治
作為一個有著50979萬農村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僅依靠政府“輸入式”治理是難以完全解決體育供給不足的問題。在現代社會治理中治理主體逐漸多元,呈現出權力的多向度運行特征[9],這種多中心的秩序,突破了政府或市場單一權力中心的壟斷與集中化[10],可以克服政府失靈或市場失靈。美國學者奧斯特羅姆夫婦(Vincent Ostrom and Elinor Ostrom)[11]將“多中心”概念引入公共治理領域,形成多中心治理理論,核心思想是構建起政府、市場和社會共同參與的“多元共治”模式,通過多個決策中心的合作、競爭、協同,實現公共服務充分供給和資源最優配置[12-14]。多元主體相互獨立做出決策,多樣化的協商與合作是多中心治理的關鍵特征。在農村體育貧困“政府-市場(企業)-社會組織-農村居民”四位一體的多中心治理格局中,政府的主導作用是關鍵因素。政府需要完善頂層設計,加強各級政府之間、不同部門之間的溝通和協作,加大公共體育的投入力度,將全民健身費用納入財政預算,以公共財政投入和政策為保障發揮主導性治理功能;政府放權給市場,企業按照供需關系的市場經濟規則生產和提供公共體育產品,并承擔社會責任,政府分權給社會組織,社會組織發揮扶智、賦能、幫助弱勢群體等方面的特殊優勢,發揮“拾遺補缺”的作用,政府權利下移到社區,農村居民通過村民自治組織表達自身利益和訴求,并積極參與體育治理,從而在社區層面,形成政府-市場(企業)-社會組織-農村居民“上下互通”“橫向互動”的相互補充、協同共治。

圖1 農村社區體育貧困多中心治理實現路徑
3.2 體育機會、體育資源、體育能力3個維度的多元共治
3.2.1 體育機會的全面植入:聚焦一老一小,融入日常生活與學習
從提高生活質量的角度,充分考慮農村居民“居家+戶外”“生產+鍛煉”“健康+休閑”的多重訴求,將體育健身設施與休閑農業、鄉村旅游、景觀人居環境整治等有機結合,利用道路、院壩、田園、森林、草原等修建健身步道、戶外運動配套設施、體育公園,將體育健身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舉步可及,就地、就近、就便健身。從提高生命質量的角度,推進體育健身與養老服務的融合;借鑒社區醫療服務的經驗,建立社區健身服務中心,配備社會體育指導員、運動康復師,形成體養結合、體醫結合的體育服務模式;同時,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市場(企業)興辦農村體育服務機構,增加非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教育減負提質,中小學生課外體育活動社區化成為新的趨勢;學校向社區開放體育設施,并持續性為社區提供專業的體育指導和體育技能培訓;通過家校社交互聯動,促進全民健身與學校體育的協調發展,實現“生涯體育”的目標。
3.2.2 體育資源的互惠共建:點軸圈面,全方位,全覆蓋
把社區作為全域整體布局中的健身點來打造,關注所有人(全齡人口),尤其是老人、兒童的需求,以需定供,適度超前,常規體育健身項目與新興體育健身項目并舉,重點培育和發展群眾自發性健身項目;以健身路徑、登山步道、騎行道等將社區(健身點)串聯成線,形成農村公共體育服務體系的發展軸線。以鄉鎮、街道為中心,打造與農村社區體育配套、分層分類、環狀分布的健身圈;通過健身設施、健身活動、健身賽事、健身指導、休閑資源、文化活動等市場化供給,形成15~30min的日常體育健身圈,30~60min的周末體育健身圈,60~90min的節假日體育健身圈。政府在資助建設鄉鎮健身廣場的同時,要主抓中小型場館、體育公園等重要體育節點在農村的建設,采取政府購買、公私合作、承包經營等方式,向市場(企業)和社會組織開放公共體育服務運營權。農村體育基礎設施建設是農村體育事業發展的重要支撐,也是當前亟需補齊的短板。點軸圈面的布局加強了體育資源供給的統籌規劃和社會整合,形成縣(市、區)、街道(鄉鎮)、社區(村)3級群眾健身服務網絡,全方位、立體式覆蓋農村社區,充分體現公共服務的公平性和均等化。
3.2.3 體育能力的有效提升:思想引導,文化自覺,體育指導
要從思想意識、價值觀、道德觀上正確引導,積極引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主流文化,移風易俗,培養體育素養。政府要承擔宣傳、教化等功能,充分挖掘體育的多元價值,弘揚體育精神。同時,大力培育社區體育社團、單項體育協會、體育俱樂部等社會組織,引導支持社會組織通過體育公益、慈善和志愿者,讓文化進村入戶,普及健身知識,推廣健康生活方式,提升社區體育氛圍。深入挖掘鄉村文化,將社區體育活動與生活樣法、文化活動融合,營造具有地方、地域特質的社區體育文化。注重提升體育活動的愉悅感和體育社交機會,用體育自覺來增強個人健身行為,帶動農村社區全民健身活動廣泛開展。我國農村公共體育服務供給一般都重在設施場地等“硬件”資源,科學健身指導一類的“軟件”服務極為缺乏;政府向市場購買公共體育服務應該逐漸向購買技能培訓方面轉變,并將其納入醫保體系,成為一種體育福利供給,并向廣大農村地區傾斜;同時,健全農村體育志愿服務組織體系,體育指導員下沉社區,常年開展惠民服務,傳授科學健身技能,幫助農村居民實現每天參加1次以上的體育健身活動,學會2種以上的健身方法的全民健身目標。運動自覺、運動安全、運動有效才能提高體育能力、提升體育素養,調動農村居民參加體育健身,參與社區體育治理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