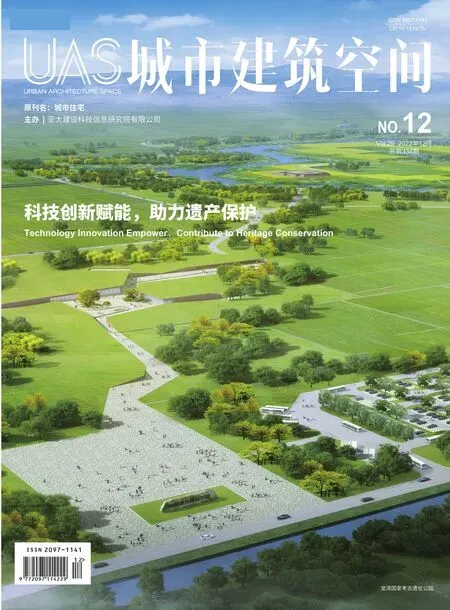蘇州工業遺產保護與適應性再利用對策研究
文/蘇州科技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 徐 捷
0 引言
在“退二進三”的城市化浪潮中,我國產業結構“大洗牌”,很多老牌工廠面臨遷址和倒閉的窘境,城市中出現越來越多空閑且失去場所意義的工業建筑及構筑物,但上述工業遺存見證了城市建設的發展和工業文化的興衰。蘇州的工業發展歷史悠久,作為江南地區手工業發達的城市及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其保護更新發展水平一直位于我國前列。現有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體系對工業遺產關注較少,導致飽含城市記憶、體現城市特色的工業建筑被拆除,故實現保護與適應性利用的動態平衡迫在眉睫。
從工業遺產更新歷程來看,工業遺產已突破單純保護的桎梏,逐漸衍生出其他效益,成為城市更新的主力軍。適應性再利用工業遺產可為舊建筑注入新機能,滿足新時代發展需要。本文以蘇州工業遺產為研究對象,從蘇州工業的發展及布局、工業遺產的保護與再利用方式等方面出發,開展歷史研究和現狀梳理,分析蘇州工業遺產保護與再利用現存問題,并提出相應的對策。
1 布局特征與現狀
1.1 布局特征
作為“東方威尼斯”,蘇州歷史城區水陸雙棋盤的格局一直未變,工業發展促進城市發展,蘇州的絲織工業尤其發達,“水鄉成一市,羅綺走中原”描繪出當時紡織業繁榮發展的盛況。傳統工業生產和運輸要求靠近水源以及交通便利,故蘇州早期的工廠和倉庫主要分布于運河兩側,如蘇綸廠和蘇經絲廠,即蘇州歷史上首批近代工廠,隨后出現嘉美克紐扣廠、蘇州針織總廠、第一絲廠、太和面粉廠等。隨著1908年滬寧鐵路蘇州段通車,陸路交通逐漸取代水路交通,工廠企業逐漸建造于古城北部鐵路附近。
蘇州從漢代起手工業就很發達,其在城市發展中處于主導地位,明清時期遺留至今的手工作坊多鄰近街道,民居和商業混合分布,呈現兩者融為一體的“前店后坊”“上宅下店”等形式,是蘇州極具特色的家庭式勞作和作坊式勞作的代表。
蘇州工業在空間發展上受上述要素影響,故工業遺產現狀布局呈現沿運河兩側帶狀分布以及作坊、店鋪和起居混雜分布的特征。工業遺產是城市記憶的重要載體,對其進行適應性再利用可促進蘇州城區“城水共生”。
1.2 現狀
從2017年到2020年底,工業和信息化部先后公布4批共162處國家工業遺產認定名單,蘇州目前尚無國家認定的工業遺產。2021年6月,蘇州市姑蘇區古城保護委員會發布29處地方認定的工業遺產清單,其認定的工業遺產保護再利用現狀如表1所示。

表1 蘇州工業遺產保護再利用現狀
2 現存問題
2.1 工業文化挖掘不深入
在城市發展洪流中,耳熟能詳的工廠被拆除,如張小泉剪刀廠如今已被拆除改為住宅,生產過“環蝶牌”針織品的蘇州針織總廠在破產后也已消失。目前,已被列入保護清單的工業遺產相對保護較好,但工業遺產作為相對年輕的歷史文化遺產類型,還有很多尚未被列入保護清單。此外,蘇州作為歷史悠久的工商業城市,其民族工業發展一直處于我國前列,對蘇州發展作出過巨大貢獻的工業遺存均未被認定為工業遺產,應深入挖掘蘇州現存工業遺存,適當擴大保護范圍,保護工業文化。
在城市特色不明顯的當下,工業遺產再利用應深入挖掘工業遺產的場所精神及特定的文化內涵,此為保護更新工作的核心。
2.2 同質競爭缺乏創新性
在目前的適應性再利用實際案例中,多將工業遺產戴上“消費文化”的帽子,利用工業遺產的特色建筑風貌,打造創意產業基地、主題博物館以及商場、酒店等商業性質場所。文創基地打造的同質化現象極為明顯,應引起重視。蘇州現有3處工業遺產在更新改造中被定位成文創園,如前身為蘇州電力電容器廠的容創意產業園,企業在再利用時,根據廠房的建筑特征,將其改造成以Loft形式為主的餐飲、攝影等商業店鋪,委托專業公司管理,以收取租金獲得利潤的方式進行運營。調研發現,對于產業園和文化創意缺乏準確定位,目前多以文化、創意的名義進行商鋪出租,缺乏工業文化支撐,對原有文脈、場地精神的繼承與發揚不足,導致過度商業化。此外,運營僅關注經濟利益,忽視整體風貌的協調和歷史文化價值的保護,同時存在土地經營性質轉變等法律問題,缺乏統一的規劃管理和監督保障。
2.3 參與力量單一且薄弱
在市場化更新背景下,我國現階段的工業遺產保護與再利用仍采用以政府為主導、專家學者參與保護的“自上而下”模式,房地產商進行適應性再利用,將其開發為商業、辦公等用途,尚未深入到社會公眾層面。如前身是新光絲織廠的桃花塢創意產業園,2007年剛改造完成時,由于絲織廠的建筑風貌較好和“一種工藝入駐一位大師”的倡議,文創園內聚集多個名家工作室,所涉藝術形式有木刻年畫、玉雕、蘇扇等,短期內以工藝美術大師坊的招牌推動文創園發展,但隨著地價上漲及后期投入不足,導致其陷入幾乎沒有藝術家入駐的困境。
目前,我國社會層面的工業遺產保護力量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民間保護意識薄弱;社會參與形式單一,覆蓋人群不全;專業人才匱乏,缺乏專業知識培訓;缺少信息雙向反饋機制及可持續的資金來源,導致社會參與在遺產保護中的法律地位尷尬,難以獲得社會認同,遠未內化成為適應性再利用的動力。
3 對策
3.1 加強保護,深挖工業遺產文化
目前,蘇州尚無國家認定的工業遺產,故應加強申報和保護工作。工業遺產適應性再利用在國外主要為場所體驗式,活化模式是將“文化”作為可增值的觸媒因子,帶動工業遺產本身的價值和再利用后的產業,創造新活力。蘊含于工業遺產中豐富的工業文化值得被充分挖掘,必須突破一般文化遺產靜態保護的觀念,從經濟效益主導下的開發轉向注重社會效益的城市文化營造,關注工業遺產所關聯的“人”的社會感知和消費愿望,并將其作為再利用的基礎,回應新的消費需求。
3.2 定位明確,與周邊區域融合發展
在城市存量更新背景下,工業遺產作為工業文化的縮影,成為城市未來再生的催化劑。由于每個城市的區域條件和發展背景不同,其工業發展狀況也不同,故工業遺產具有明顯的在地特征。工業遺產自身特色明顯,建造時為了運輸以及取水方便,地理位置大多相對優越,同時工業遺產的體量較大,為切實保障其完整性,應在城市層面對不同的工業遺產保護與再利用后的功能、定位、業態及其與區域的關系等進行審核,使其融入城市更新大背景中,充分遵守城市總體規劃的原則和整體效益,使其與基地的周邊定位及城市空間相適配,既保護遺產又物盡其用,進而保障城市利益。工業遺產保護與再利用面對的是已經確定的物質實體空間結構和特定的社會結構形態,保護可根據法定的程序和制度,但適應性再利用的過程是對現存既定關系的改變,故所有適應性再利用均為特殊個案,不可能存在統一模式,應實現精準化、差異化發展。
3.3 多元主體,共同促進保護與更新
工業遺產保護與再利用后的活力受到社會公眾的關注與參與狀況的影響,除了“自上而下”的更新外,需要更多“自下而上”的力量。國外相對成熟的工業遺產更新保護主體包括政府、市場和社會等多方力量,故我國保護更新應號召多元化主體共同參與文化遺產保護和更新,積極探索政府或市場引導、公眾廣泛參與的更新模式。如在市場主導下,實際操作過程中可就地產商所開展的城市更新設計及該地塊的詳細保護計劃向市民征求意見,從而有效保護工業遺產,確保地塊更新設計的合理性。此外,工業遺產的保護與再利用的成功與否除了取決于更新是否契合原地塊,還與人們的關注度和參與度有關。政府應正視并響應此種社會意愿,推進工業遺產保護的“群眾運動”。
4 結語
在城市更新建設如火如荼的當下,文明城市須正確面對城市發展以及產業發展進程中的每個文化片段,因各個文化片段的拼貼、疊加才發展為今天的城市。針對倒閉、廢棄的工業廠房,既應保護又應充分挖掘其潛在價值,使之不會被歷史拋棄,以更積極且合理的方式實現“舊屋換新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