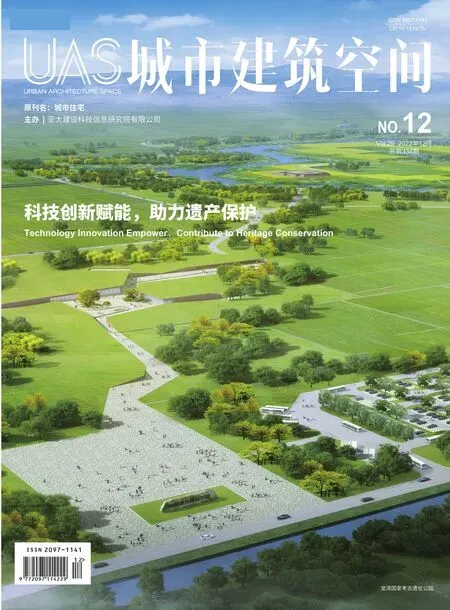重慶城市生態公園體系建構研究
——以雙橋溪—后河—萬家山公園體系建設為例
吳有鵬
(重慶大學建筑城規學院,重慶 400030)
0 引言
城市生態公園作為諸多綠地類型中的一種特殊存在形式,是城市綠地系統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于城市生態公園概念的界定,最早有鄧毅提出“位于城市城區或近郊,以保留或模仿地域性自然生境來建構主要環境,以保護或營建具有地域性、多樣性和自我演替能力的生態系統為主要目標,提供與自然生態過程相和諧的游覽、休憩、實踐等活動的園林”;重慶對于城市生態公園的概念界定和建設要求更明確具體,2022年2月1日施行的《重慶市城市生態公園管理辦法》將其定義為:“是指用地性質為非建設用地,但緊鄰城市建設用地或者被建設用地包圍,具備山體、水系、林地、草地、濕地等自然景觀資源,且具有保障城市生態安全功能和一定的城市公園服務設施,能夠滿足市民游覽觀光、休閑運動需求的綠地。”城市生態公園作為EG類區域綠地的一種特殊規劃用途,其與風景游憩用地、郊野公園、生態保育綠地存在一定范圍的功能重疊,是對這三類綠地兼收并蓄的集大成者(見表1)。普適的公園規劃設計策略難以適配重慶城市生態公園建設的具體需求,因此研究探索適合重慶城市生態公園建設的規劃設計策略是當前面臨的重要議題。

表1 城市生態公園與其他三類用地的研究內容比較
1 重慶城市生態公園建設現狀問題
根據《重慶市主城區綠地系統規劃(2014—2020)》統計數據,渝北區城市生態公園建設進程和成果最為突出,占建設總面積的46.5%。最少的渝中區僅占0.6%。城市生態公園總體數量和面積雖然在提升,但隨著城市邊界的急速拓張和各區域發展水平的差異化,傳統城市生態公園建設的諸多問題也日益凸顯,筆者認為其主要存在以下4個問題。
1.1 連通性差,生態空間單一破碎
傳統城市生態公園建設以人工建造的復合人工系統為主,其生態穩定性與生態效應低于自然原生演替形成的植物群落。重慶雖擁有良好的自然山水格局,但緊鄰城市建成區的部分重要山體水脈卻缺乏城市生態公園等綠地覆蓋,其中以重慶城市重要山脊線龍王洞山余脈最為典型。城市內部生態空間未與自然山水格局相銜接形成體系,對于城市的無序擴張難以形成有效的控制和引導。
1.2 可達性低,內外交通銜接錯位
城市綠地的可達性指標對評價城市環境質量、衡量自然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有著重要的潛在價值。重慶城市生態公園選址往往位于城市建成區邊緣山地或建成區中不可破壞的山體,其本身地形的復雜性導致外部可達性成為最能影響城市生態公園活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傳統城市生態公園設計忽略周邊公共交通站點分布,城市生態公園入口選址未銜接外部交通,導致其可達性低、游客量小。另外,由于重慶城市生態公園與城市界面存在一定高度差,其與外部慢行步道的銜接程度往往能夠影響人們出行目的地的選擇。
1.3 游憩性弱,景源節點設計缺失
城市生態公園相比一般城市內部公園,應更強調自然性、復合性、游憩性,為城市居民提供比一般人工城市公園更原真多元的自然體驗。重慶傳統城市生態公園建設往往受習慣性影響,與一般城市公園的規劃方法無較大差異。而城市生態公園特征更接近郊野公園,其規模普遍更大,景觀資源更豐富,城市生態公園規劃設計應當充分挖掘景源,對于景源匱乏區域,可適當結合周邊文化塑造景觀,形成功能復合、特色凸顯、自然為主、人工為輔的景源節點體系。
1.4 同質化重,特色文化溯源不足
“千園一貌”已經成為當前城市公園建設的主要問題之一,其根本在于對地域特色文化的溯源不足。重慶傳統城市生態公園設計手法和設計要素也逐漸趨同于一般城市公園,致使城市形象特征不突出、地域文化屬性不匹配,對重慶地域文化的發掘利用不足,與周邊其他城市公園差異化不明顯,無法吸引穩定優質的客流。文化是城市公園的靈魂,千篇一律、沒有靈魂的公園無法與城市居民的需求達成共鳴,從而難以為城市提供公共服務價值。
2 渝北區雙橋溪—后河—萬家山生態公園體系建設實踐
2.1 研究背景
本次規劃設計范圍為重慶市渝北區空港新城萬家山、后河、雙橋溪3個公園,規劃設計總面積達408.28hm2。基地北靠龍王洞山脈,南接空港城市居民區,西臨嘉陵江,東望江北機場,整體地勢東高西低,整體最大高差達268.6m。基地被4條東西方向城市主干道和快速干道和兩條南北方向軌道交通分割,大量高壓走廊和輸油管線穿插設置在基地內部。由于周邊道路施工不斷開挖土方,導致出現基地邊界模糊多變、邊坡地質情況不穩定、局部地表嚴重裸露等問題,加之其本身自然植物群落單一,系統多樣性不足,綜合導致其目前生態穩定性差,生態本底十分脆弱。本次規劃創新地提出將3個原本分開劃定的公園統一規劃形成一個融合生態觀光、休閑娛樂、康養運動、親子互動、科普教育、商務交流等多功能于一體的,全年段可參與的宜居宜業的新渝式復合型城市生態公園系統。
2.2 重慶生態公園體系建構策略
2.2.1 生態修復:修復多樣生境,構建生態廊道
城市生態公園多為城市近郊邊緣的非建設用地,是銜接城市與自然的最佳生態廊道,但由于城市建設的不可控因素及其自身的自我演替能力較差,導致其生境破碎,甚至生態廊道割裂。建設山地城市生態公園系統,首先應當對自然基底進行系統修復,構建具有多樣化自然生境的生態廊道,使其生態自我條件能力增強。本次規劃設計通過綜合運用社會調查分析模型和GIS等數字化研究手段,分析研判基地生態現狀并提出4個生態修復策略。
1)植物補種 對植物覆蓋度較低及植物種類單一的區域進行優勢補種,補種香樟、馬尾松、黃葛樹、刺槐等重慶鄉土優勢樹種,并進行混交,優化植物生態結構,促進植物群落正向演替,形成穩定的地帶性植被系統。
2)駁岸固土 通過對基地內河流沿岸區域進行地質研判,在易發生地質災害的駁岸進行混凝土加固,并在河岸消落帶區域種植青茅草、苔草、狗牙根等耐淹固土的草本植物,從而減少土壤流失引發的水土問題。
3)山體修復 對于裸露山體修復,首先應確保土壤穩定,再選用生長快、固土能力強的鄉土植被進行栽植。根據山體受損處坡度大小采用不同修復技術,坡度大于70°山體采用植被混凝土護坡綠化技術,坡度介于40°和70°之間采用防沖刷基材(PEB)生態護坡技術,坡度小于40°緩坡采用燕巢法修復技術。
4)緩沖控制 生態廊道的緩沖區域作用機制類似細胞膜,能夠影響廊道的質量和寬度,通過栽種一條緊密的緩沖帶,能夠在一定情況下過濾進入廊道的機會邊緣物種,從而控制生態系統的穩定性。
2.2.2 交通可達:構建交通體系,加強內外聯系
城市生態公園的可達性是公園游客流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次規劃設計主要通過以下3個方法提高公園的可達性。
1)分設入口,銜接樞紐 通過對周邊公共交通站點的梳理,在大型軌道交通樞紐、大型停車場、公交總站周邊設置公園主入口,在公交站點及小型停車場設置次入口,能夠有效地引導不同來向的游人進出公園,同時方便不同出行方式的游人到達公園。
2)生態選線,貫穿全園 生態公園的主干道設置迥異于一般城市公園,需在綜合運用RS、GIS等數字分析手段對自然本底進行生態敏感性分析的基礎上,因子賦權、運算、疊加得到選線適宜性評價,進行初步選線分析,通過連通性和路線長度將道路選線劃分為重要和次要兩種類型,最后結合初步選線和選線適宜性分析,綜合考慮基本農田、管線等限制性因素,最終得出貫穿公園體系的主園路及次園路,為實際園路體系建設提供參考依據。
3)多層連通,功能轉換 由于公園被多條城市主干道、快速路分割,故采用平接、下穿、橫跨的方式進行多層連通縫合破碎斑塊,使公園在可達性層面形成統一整體。生態公園建設以不搞大開發為原則,在建設時,將基地內因周邊建設施工產生的施工便道、現狀原有的步行小道、農田周邊的田埂路都加以修整利用、功能轉換,統一納入公園原路的分級體系中。城市生態公園規劃設計應當在維護自然生態本底的前提下構建合理高效的園路交通體系,加強公園內外部建成環境的溝通聯系,激發更大范圍內市民參與公園活動的興趣。
2.2.3 文化煥活:根植地域文化,移植特色文化
山地城市發展限制條件較復雜,其發展速度也較沿海平原城市緩慢,城市文化活力也深受影響。城市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層次互動共生,構成一個有機聯系的城市文化系統。城市生態公園作為城市文化的重要承載空間之一,是彰顯城市文化和城市形象的重要媒介平臺。本次規劃設計通過根植渝北地域文化,以鄉愁文化、康體文化、耕讀文化為文化基底,提取相關文化要素,并與物質空間、行為活動相結合,形成具有文化意蘊的景觀節點。
2.2.4 特色凸顯:挖掘特色景源,塑造景觀地標
凱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提出“地標(Landmark)”為城市意象五要素之一,作為人們日常辨識、構建城市印象的實體。山地城市生態公園往往具有遠高于地表的山體空間,是天然的城市地標。結合城市廊道空間構建有鮮明特色的城市地標構建筑,形成城市景觀焦點。本次規劃設計通過對基地景觀地形風貌提取,形成溪谷、丘谷、河谷、山谷的風貌段落,以動、樂、靜、游為段落主題,挖掘并塑造花落嫦溪、竹林春曉、尋鄉古道等十大特色景觀,以4個全園視線高點構建最佳觀景點,形成山-城相望、城-園共生的美麗圖景。
3 結語
在生態文明建設與公園城市建設的雙重指引下,城市生態公園在重慶城市建設中不僅具有生態涵養作用,更承載著文化宣傳、休閑康養等復合功能。建設城市生態公園體系本質上是系統修復自然和城市的關系,重構人與自然融合共生的和諧棲居環境。研究以重慶空港新城雙橋溪-后河-萬家山生態公園體系規劃實踐為例,提出并探討將城市建成區包圍或緊鄰的受損、閑置、廢棄的用地斑塊通過系統性生態修復、文化煥活整合轉化成為特色凸顯、城園互動的城市生態公園體系,希望能為重慶等山地城市綠地轉型升級、存量空間提質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