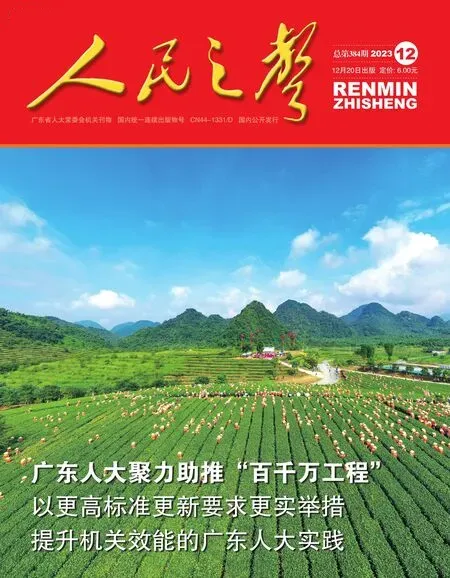彩票樹公信 立法須升級
不久前,江西南昌一位彩民花費10萬元購買5萬注相同號碼的“快樂8”彩票,精確押中2.2億元巨獎,其一系列看似有違常識的巧合,激起了輿論場上的質疑聲浪。究竟是暗箱操作,還是猜疑有誤?相信有關部門的調查終將提供有說服力的結論。但這一事件的真正價值,并非僅僅探求個案的真相,而是將彩票業的公信、監管等深層問題再次推入公共討論的視野,引發了全社會的深入思考。
自1987年試點發行福利彩票、1994年啟動體育彩票以來,我國彩票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目前市場規模已穩居世界第二。多年來不斷籌集、增長的彩票公益金,為公益事業提供了巨大能量,見證了彩票業“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品質。然而,彩票業30多年的演進過程也歷經風雨的困擾,從西安寶馬彩票案、廣西福彩烏龍事件等爭議風波時有發生,到“審計風暴”揭開的彩票違規違法亂象,直至多名官員因彩票貪腐而落馬,都不同程度地沖擊著彩票業的公信力,暴露了監管不足的現實困境。
彩票業所面臨的公信、監管等挑戰只是表征,其根源是法制供應的欠缺。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國彩票業是順應改革開放、沖破觀念牢籠的產物,先天刻有“摸著石頭過河”的烙印,無論是福彩還是體彩,都是在無法可依的狀態下先行探索。直到2009年《彩票管理條例》以及2012年相關實施細則的出臺,才填補了彩票立法的空白。不過,層次較低的立法位級、過于簡約的制度設計,并不足以改變彩票業“邊發行邊立規則”的格局。在實際運行中,依然依賴層次更低的部門規章、政策性文件不斷填充“制度補丁”,這就進一步放大了效力不足、規則不全、銜接不暢等制度缺陷。可以說,彩票業的法治化建設水平,已嚴重滯后于彩票業的快速變遷,亟需出臺更高層級的彩票專門法律,以應對不斷加大的監管難度和市場風險。
事實上,近年來從全國兩會到社會各界,要求制訂彩票法的呼聲可謂經年不息。201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工作機構和有關部門已分別起草了彩票法草案立法建議稿。此后,彩票法還兩次列入了人大年度立法計劃。然而,基于一些立法難題尚未達成共識,彩票法雖有積極進展,其立法速度卻未達到社會預期。
其中的一大焦點,乃是如何理順彩票業的管理體制。依據目前的制度架構,由財政部門主導彩票業的監管,民政、體育部門分別負責福彩、體彩的管理,這種多頭管理的格局,難免埋下權責不清、監管缺位等隱患。同時,民政、體育部門下設的彩票發行、銷售機構,其市場化經營與事業單位屬性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亦難免滋生銷量為王、惡性競爭等弊端。對此,不少業內人士認為,應當設立專門的彩票監管機構,對彩票業實行垂直化管理,并將彩票管理與發行、銷售全面分離,進而徹底褪去“部門彩票”的色彩,回歸“國家彩票”的本位。可以說,這些改革動議不僅事關彩票業的發展方向,也是拆除彩票法立法障礙的關鍵所在,因而有必要在認真評估的基礎上盡快完善改革方案、邁出改革步伐,并最終開辟“改革推動立法、立法確認改革”的通途。
除了與體制改革的聯動互促,彩票立法的又一個重心是如何堅守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進一步提升彩票業的公信力。從目前的制度設計和實踐運行看,這方面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比如,彩票開獎不妨由彩票發行、銷售機構改為第三方機構進行,彩票領獎有必要引入與開獎時相似的公證機制,從而強化彩票的公正性和透明度,消除公眾可能的疑慮。再比如,彩票公益金使用的公示,不僅需要細化資金的流向,還應當公開使用的實效,如此才能全面樹立陽光彩票的形象,促進彩票公益價值的社會認同和支持。還有,面對“江西2.2億巨獎”之類的彩票爭議事件,亟需構建客觀公正的調查制度,明確調查機構、程序、方式等要素,并合理平衡公眾知情權與個人隱私權之間的沖突……總之,如何塑造覆蓋彩票業各環節的有效監管和社會監督機制,有待彩票法作出精細的制度安排,也是其應盡的立法使命。
“江西2.2億巨獎”的最終結局,不應止于爭議的平息,而是應當成為推動立法進步的契機。歸根結底,健全的法律制度、優良的法治環境,才是彩票業行穩致遠的根本保障。一個依法監管、良性運行、公信至上的彩票市場,不僅能充分煥發彩票的生機和活力,也將最大程度地激活民眾參與公益的熱情,掙脫“一夜暴富”的誘惑,奔赴大愛無疆的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