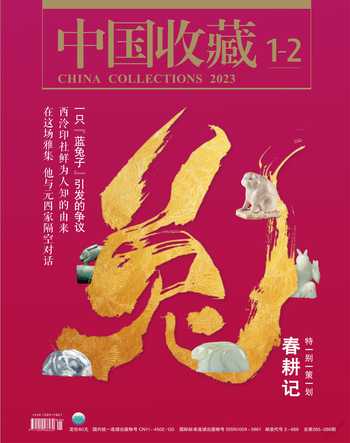質樸先民樂農忙
石釗釗
華夏文明自古便是以農耕文化為主的悠久文明,當我們的先祖在黃土地上辛勤忙碌之時,也正是農歷一年中最好的時節(jié)。土地在中原文明中常被認為是“母親”的化身,她伴隨著春雨的滋潤涵養(yǎng)萬物,也滋養(yǎng)著生活在大地上的人們。當寒冬拂過蒼茫大地,回暖的春日也預示著農忙的開始,這正是質樸的東方人對腳下熱土的珍視。
開始使用農具
自上古時期開始,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已經在河流沖擊的平原上種植經濟作物。位于浙江余姚地區(qū)的河姆渡文化有著發(fā)達的犁耕稻作農業(yè)經濟,浙江省博物館收藏有河姆渡遺址出土的帶藤條殘木柄骨耜(圖1)。這件農具以偶蹄類動物的肩腫骨制成,古代先民手持骨耜耕作時可手握木柄、腳踏插入橫孔的木棍,即可輕松以耜翻土。這件新石器時代的出土農具不僅是河姆渡文化稻作文明的重要實證,也證明在此時除了使用石器外,也出現了更適宜水田耕作的骨質農具。農耕滋養(yǎng)下的河姆渡人在生活富足之余也將紡織、漆木器為代表的手工業(yè)文明系統(tǒng)化、專業(yè)化,使之成為高度發(fā)達的社會生產力,并逐漸影響社會階層的劃分。這種在農耕文明影響下出現的權利體系,也成為上古文明具備早期國家形態(tài)的濫觴。

西周是中國禮制的完備時期,在經歷了商朝的統(tǒng)治后,周人已經意識到禮制對于農耕文明具有深刻而長遠的影響。周禮中有關于“迎春”的祭祀,當時的周人在儀式之前需要提前以紙札、竹篾制成象征春日農耕的春牛,并取象征豐收的五谷填滿春牛的腹部。掌管祀時之職的芒神以竹鞭抽打春牛,借以祈愿新年五谷豐登、平安喜樂,頗為生動活潑。
借助牲畜之力
敦煌莫高窟作為中西文明交流的寶庫,在保存佛教美術瑰寶之外也融入了許多中原的農耕文化。現存莫高窟南區(qū)中部的第23窟是敦煌的代表性洞窟之一,其主室初創(chuàng)于盛唐時期,前室及甬道部分在中唐吐蕃統(tǒng)治時期與晚唐五代時期曾有重修。主室覆斗形的窟頂四披分別繪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 觀音普門品”“彌勒經變”“阿彌陀經變”題材佛教故事,四壁則以西壁開龕塑像,北、東、南三壁則以聯通敘事的形式繪“法華經變”故事情節(jié)。
讓我們將目光置于主室北壁,此壁畫面中央繪佛說法圖尊勝畫像,圍繞中心說法圖分別繪表現“法華經變”中的“序品”“方便品”“譬喻品”“信解品”“授記品”“從地涌出品”等故事。此壁畫左上角“牛耕圖”壁畫(圖2),描繪新綠之中烏云層層,普降甘霖下水天一色。其右側四塊新田濃綠蔥蔥,一農人肩扛兩捆金黃的麥穗正行走于田埂之事;左側留白作牛耕圖,畫中一農夫正于田間牽黃牛耕田,牛身掛直轅,后置鐵犁,農夫左手持鞭高高揚起,畫面生動別具風味。按考古出土文物看,唐代已經廣泛運用“一牛耕田”與“二牛抬杠”等耕犁方式。

此時的耕犁以鐵質為主,不僅有長直轅,也出現更為適合江南深耕的曲轅犁。敦煌所在的河西走廊地區(qū)此時已普遍出現鐵犁牛耕法,壁畫中的直轅犁不僅適用于河西地區(qū)平淺的土壤、具備耐用的特質,也從側面證明了這一時期敦煌地區(qū)鐵質犁頭的廣泛使用。此幅農耕圖下有四人于地頭席地而坐,正于田間休憩飲食,敦煌的畫師通過牛耕、麥收、歡宴將敦煌地區(qū)的農耕形象保留于千年壁畫之中,成為難得一見的古代農業(yè)繪畫典范。唐代經變繪畫盛行,其中“法華經變”常以天降甘露表現農耕豐收場景,滋潤的青苗與豐收的喜悅不僅表現出佛法對世間眾生的無限護佑,也表達了當時人民期許美好收成的愿望。唐代時期敦煌糧食生產頗為富足,不僅供給自身用度,也成為戍衛(wèi)邊疆的重要儲量基地。糧草豐沛的敦煌不僅成為當時沙漠綠洲的富饒之地,也因此成為絲路商道的重要樞紐,將東西文明匯集于此。

我國古代農業(yè)文明頗為發(fā)達,最早所見以牛耕地至遲不晚于東周時期。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漢畫像磚《牛耕圖》(圖3)出土于徐州睢寧地區(qū),畫中不僅生動表現了漢代先進的“二牛抬杠法”的農耕,還細致地將耕牛肌肉的線條刻畫出來,從側面增添牛耕場景的生動性。而甘肅嘉峪關五號墓出土的耕牛題材彩繪磚畫,則利用絢麗的色彩記錄了1600多年前先人利用耕牛犁地的生活場景。仔細看來,畫中還著重描畫出農人滴落的晶瑩汗珠,好似滋潤了農田,將人的情節(jié)性表達得淋漓盡致。
農婦參與其中
敦煌榆林窟第2 5窟是中唐吐蕃占領時期的重要洞窟,按主室北壁“彌勒經變”故事畫上藏文題記并結合壁畫中吐蕃風格故事推測,此窟應建成于吐蕃占領瓜州之時,而吐蕃當時還并未占領沙州地區(qū),即大歷十一年(776年)至建中二年(781年)之間。此壁“彌勒經變”壁畫表現依據《彌勒下生成佛經》內容繪制,中心畫面以彌勒龍華樹下成道后三會說法題材為主,周遭場景則生動表現彌勒降生時的閻浮提世界美好種種,如“一種七收”“樹上生衣”“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等等。其左上“一種七收”壁畫(圖4)原根據鳩摩羅什大師翻譯《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果爾時閻浮提中常有好香,譬如香山流水美好、味甘除患、雨澤隨時,谷稼滋茂,不生草穢,一種七獲,用功甚少,所收甚多,食之香美,氣力充實。”畫中布局有下至上,一男子頭戴笠帽,正以“二牛抬杠法”驅趕一紅一褐兩頭耕牛拉動犁頭,將腳下土地深耕成畦;身后一農婦雙手捧箕,正沿著新耕的田壟播撒種子。畫面左上,一片片莊稼茁壯成長,正有一白衣農人健步前弓,手持鐮刀奮力收割。于此播種、收獲上側,有男女二人堆谷揚場,左側男子持釘耙將稻谷高高揚起,右側農婦則持帚將落下的稻谷歸攏一處。在這樣歡快的豐收場景之后能見高僧講經圖,可見當時佛教在宣揚的其思想時也將華夏文明的“人本農事”作為其重要的藝術創(chuàng)作題材之一。

從大歷史觀看來,中國人對農業(yè)的重視與尊崇似乎不為自身所在的階級地位而定,而是一種關乎全民、上下一致且通感深刻的社會普遍信仰。自周禮形成之時,西周先民即以“重食”為主,大量的盛食器成為周代禮器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以“列簋”配合“列鼎”制度表現權利,還在西周晚期將青銅禮器的形制逐步細化,創(chuàng)制出簠、盨等盛裝祭祀黍、稷、稻、粱的食器來區(qū)分不同階級與功用。農人對農事的關心,本身也是一部中國古代節(jié)氣史,以農時為主的中國農歷也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