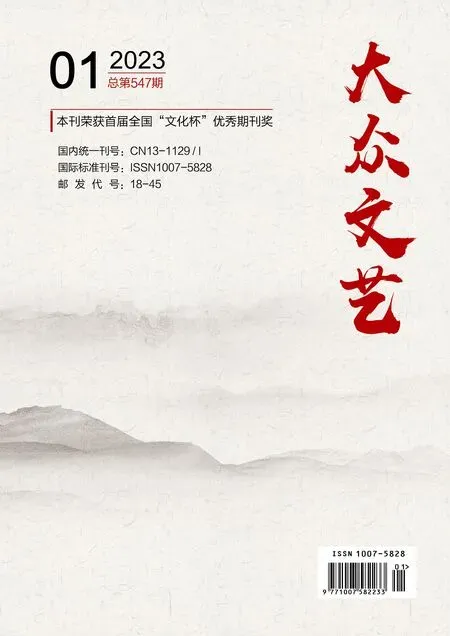回憶-影像下“杭州新浪潮”的實驗特質*
陳洪衛
(河北傳媒學院研究生院,河北石家莊 051432)
一、德勒茲時間-影像的入口:回憶-影像
(一)時間-影像與綿延
吉爾·德勒茲其人,為法國后結構主義哲學家,也是眾多現代西方哲學家里,最“電影”的一位哲學家,他的哲思深受尼采、柏格森等人影響,強調潛在與生成的世界,認為電影是詮釋我們與世界的潛在聯系,延續我們思想的一種“力”。這一思想大為激發了藝術家的創造力生成。他撰寫了兩部重量級的電影著作《電影1:運動-影像》《電影2:時間-影像》,開啟了電影研究的新時代。德勒茲在其中將電影劃分為兩類:一是有著最符合觀賞邏輯的經典好萊塢式電影(運動-影像)、二是以現代主義電影為代表的“意識流”電影(時間-影像)。德勒茲的立場站在了現代主義電影這一邊,認為打破常規時間敘事的“意識流”類電影才是更能體現電影本體的電影。這也符合德勒茲自柏格森那里承繼而來的“心流”綿延時空觀。時間-影像主要涵蓋了回憶-影像、夢幻-影像、晶體-影像三大類。三者分別為時間-影像的入口、內部及最理想狀態。時間的永恒、思維的延展,在回憶-影像這個入口中得到初步彰顯。仔細探討回憶-影像,避不開柏格森的綿延思想與時間倒錐體。
綿延是貫穿于柏格森生命哲學的一個時間概念[2],他認為綿延就是“去空間化”的時間。有這么三種時間類型:源初時間、物理時間、“綿延時間”。其一,源初時間帶給世界有流變、運動、創造的性質,是時間本來的樣子。其二,物理時間則是基于傳統的慣性認知:以空間與運動來衡量時間,時鐘每走動一刻,在鐘表的空間中都會進行運動位移,從而人們知道時間在流逝。其三,“綿延時間”則不同于傳統的以空間來定義時間的方式,綿延摒棄了空間與運動,從柏格森的心理事實出發,更關注于時間本身的存在與意義。這是最接近于源初時間的一種時間類型,時間在每一刻都在質變。人的意識在運作之時,思想在拓展,時間在游移,沒有固定的空間廣延性在,不以空間的運動來衡量時間,時間從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間,精神可以游移古今與萬里之外。例如說當我們在電影院觀影時,物理時間上只經歷了兩個小時,但是好電影會讓我們感受到像是經歷了一生。這即是“綿延時間”的體現。
(二)潛在與記憶倒錐體
潛在是回憶-影像的另一個重要概念依托,主要通過柏格森的時間倒錐體(圖1)來說明它的時間觀念。柏格森認為有這么一個倒錐體,承載了我們人類所有的精神生活。[3]平面P代表了現實正在發生的事與即將面對的事,錐體SAB則代表我們的所有記憶。而倒錐體的尖點S則代表現在,同時也是平面P上的一個點。A’’B’’、A’B’、AB則是回憶的不同深度,代表了當前的記憶橫截面,越靠近錐底則越靠近我們的深層潛在記憶。[4]整個記憶運動是雙向的,尖點S不斷從當下平面P獲得感知,從而生成記憶儲存于倒錐體之中。而每一刻尖點S識別當下,都帶著倒錐體SAB已有儲存的過去,去影響參與當下記憶的判斷與認識。整個倒錐體一直處在雙重往返運作生成之中。過去記憶自上而下向著當下自由運動、流變,成為構成我們精神生活的一個生命體。由于記憶的運動,人的精神活動運作更頻繁。記憶的積累在每一次新的感知體認的時候都會加重,過往的記憶影響并參與每一次新的感知,每次感知都是新的創造。

圖1
通過梳理綿延與潛在,我們得以獲得理解回憶-影像的基礎。繼而我們來探討回憶-影像。德勒茲在《電影2:時間-影像》中開篇便指出柏格森區分“識別”的兩種形式:自動識別與刻意識別。通過兩種識別也由此區分出了兩種影像:感知-運動影像與純視聽影像。自動識別指的是那些平常基礎層面上的識別再認,如迎面向你走來了一個人,你識別出這是你的朋友這一類的慣性認知,可以說指向的是事物本身的日常識別。刻意識別對應的是純視聽影像,指的是你面對一種情況,自動日常反應失效,不得不“愣神兒”[5]游離的時刻。如迎面朝你走來一個陌生人,他對著你打招呼,你第一時間想不起他,自動識別失敗,你不得不經過刻意識別,在潛在深層的記憶中打撈質料使得最終你們相認。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由當下回到過去,再由記憶返還到現在。
二、“杭州新浪潮”的記憶時空呈現
(一)“杭州新浪潮”——區域電影下的江南電影
中國藝術研究院的賈磊磊教授曾提出過區域電影理論,將我國的電影從空間層面上劃分為了區域板塊。在其表述中,有別于西部電影中生死存亡的憂患意識,江南的詩書畫傳統以及豐饒的水資源、田園地貌給予了這片地域以溫柔的美感,也給予了這片地域衣食無憂的環境[6],基于此,我們可以發現當代的江南電影更多地在主題上述說著人與自然相互依偎以及文化沖突等相關母題。2019年顧曉剛的《春江水暖》、仇晟的《郊區的鳥》、祝新的《漫游》這三部來自杭州的電影均在國內外的重磅電影節上取得了成果和矚目,隨著“杭州新浪潮”的叫法逐漸在業界中散開而來,可以將其看作是江南電影的其中突出代表。而后在2021年出現的《她房間里的云》與《柳浪聞鶯》亦加入了“杭州新浪潮”的創作陣營。
《春江水暖》用卷軸式的長鏡頭拍出了江南地貌的美感和家族故事。仇晟《郊區的鳥》將鏡頭對準了勘探地質的青年,涉及了回憶和夢境,繼而牽連出了幼時自己與小伙伴的故事。祝新的《漫游》以一個小女孩寫作文的故事而帶出與回憶夢境串聯的故事。而《她房間里的云》這部在2021年FIRST現場被搶票到售罄的電影則更是在個體記憶、幻覺中穿梭。《柳浪聞鶯》講述了在現代化的同時我們民族文化也逐漸消失的哀傷。歸結來看,“杭州新浪潮”的影像有某些特點:即憑直覺去創作、細膩表達生活的某個剖面、透著阿彼察邦般的自然感悟、秉著第六代導演章明《巫山云雨》般的朦朧、抑或是帶有先鋒實驗性的視聽表達。審視《郊區的鳥》《漫游》《她房間里的云》其中的回憶與生命體驗,從而探尋其中回憶-影像的哲學意味。
(二)記憶與時空呈現:《郊區的鳥》《漫游》《她房間里的云》
仇晟的《郊區的鳥》、祝新的《漫游》以及鄭陸心源的《她房間里的云》立足于杭州這一江南城市、影片故事來自青年導演的個體記憶、在回憶與超現實中探尋著自己的感知與情感。《郊區的鳥》導演仇晟在采訪中稱這部影片是“一場對回憶的調查”。回憶在影片中占據的分量舉足輕重。地質勘探人員夏昊為了研究地沉現象而與團隊成員游走于郊區。青年夏昊自始至終處于一種游移的狀態,即與當下的環境,城市有陌生感。其一體現為他對人群的冷淡,其二體現為他對這座現代化城市的陌生感,其三片名《郊區的鳥》,已然提到了郊區,這是一個不屬于中心的地域。種種暗示梳理出了青年夏昊的邊緣疏離感。青年夏昊像莫迪亞諾《暗店街》中失憶的主人公一樣,在勘探過程中尋找著自己逝去的童年過往。伴著秋風與落葉的校園,青年夏昊從舊書桌里拿起了一本日記,開始進入刻意識別,游弋在潛在回憶里:童年的夏昊有著自己的小團體,與小伙伴們一起掏鳥窩、玩游戲,后來大家逐漸長大,小團體成員也挨個兒逐漸走散。在這段記憶里,夏昊想起了自己的幼年時光。時間在記憶中游走,流動,觀眾透過過去的童年部分的影像再來看待青年的夏昊,便體會到了那種滄桑感與過去的厚重感。
影片《漫游》在聲音方面,注重自然聲響,涉及了對自然的探尋,表達了人與自然相互依偎的母題。整部影片穿插著自然意向、回憶、夢境、柔光畫面,呈現出了一種思維運作的夢幻質感。風、閃電,山洞回聲,流水。種種意向串起了小女孩李森林的回憶和幻想。[7]具有一種阿彼察邦式自然的神秘主義氣息。不同于《郊區的鳥》在呈現回憶畫面時直接用大段連續童年畫面呈現,《漫游》中小女孩的回憶、夢境,均是通過類似于閃回的片段而進行的畫面閃現體現。多次碎片化的記憶體現現實時空與過去時空、臆想時空的關聯。《她房間里的云》在國內首次出現是在2021年的第15屆FIRST國際青年電影展上。在自我探索與表達上,鄭陸心源運用了先鋒性的攝影手法來呈現著她的私人杭州記憶——負片、雪花、全黑白的視聽,富含故障藝術與拼貼感的后現代性風格。負片下的老家拆除畫面即震撼又有種荒誕虛假感,真實與幻想并置,亦是導演的獨特杭州記憶個體表達。
三、回憶-影像對創作的實驗性啟示
(一)創造力的形成:時間回溯、主觀性、抽象性
時間倒錐體是一個流動的循環生成過程。當下不斷與過去交織、我們帶著過去的厚重而前行。生命的多維度、時間的當刻體驗,都在告知人類可以有更豐富的情感、思想、體悟。拋掉線性的日常生活,人獲得了本真境界,從而確立了自我,進而才能創造帶有自己獨特思想的藝術作品。電影是存放視聽要素的海洋,通過不同的視聽組接,藝術表達的聲畫分離,承載住了我們記憶的厚重。在回憶-影像中打破運動-影像的桎梏,把思維與時間從線性的日常中解放出來。繼而意識到,我們的過去經歷,我們的生命正在流淌。
“主觀性具有了一種新意義,它不再是運動的或物質的,而是時間的和精神的”[8]。德勒茲在《電影2:時間-影像》中如此表述道。隨著運動-感知鏈條的斷裂,時間變為非時序性時間,情感作為了主觀性的一個維度,使得回憶-影像具有主觀性。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表達了詩意的人生,潛在回憶喚醒想象的潛能。時間在回憶中反復來回,我們終以體現到時間之于自我的那一面。只有保有創作者的主觀性,作品才有追求深度的內涵。從這個層面講,電影需要鼓勵以“杭州新浪潮”為代表的多元先鋒性的藝術創作。
德勒茲作為一個不斷創造概念的哲學家,他認為哲學就是創造概念。[9]汪民安教授曾講過,為何哲學中一定要有諸多晦澀的學術名詞“來難”為學生,是因為簡單的詞語概括不了深奧的內涵,我們能做的也就是與真知保持一定的遙望距離,從而不斷我們的學習。在德勒茲創造了一眾概念后,可以發現一個共同點:抽象概念激發創造力,抽象對藝術家具有啟發性。回望電影史,我們可以看到歐洲先鋒電影中的德國表現主義、法國印象派電影、法國超現實主義誕生出了不少的實驗杰作(如《一條安達魯狗》《微笑的布迪夫人》)。而這些實驗影像的誕生,也即是受到了抽象的先鋒繪畫的影響,從而激發出了藝術家的創造力。
(二)德勒茲與“杭州新浪潮”于中國本土電影的新啟示
當下的藝術發展展現出藝術與科技、哲學結合的新趨勢。重讀德勒茲的電影著作或許可以為我國的影視行業發展提供養分。在電影哲學的角度下,我們可以發現,在我們的新一代、新力量的創作者身上,他們的作品中帶有哲學的生命意味。來自個人的生命體驗,將時空放置于過去、現在、未來三個維度去并置處理,在這個間隙中,進行自我生命的思索。立足于當下的社會環境與時代發展,他們作出了自己的思想表達。“杭州新浪潮”的出現是中國創作新力量的涌現,他們不再囿于傳統的電影制作方式繼續講訴宏大的生命議題。而是從自我出發,取材于自我生命體驗的作者表達,飽含對家鄉的感受。邱炯炯的《椒麻堂會》也開始為“川派電影”出圈。期待更多的各地新浪潮出現,這一趨勢將促進中國本土影視行業的良性發展。
“關注人在數字時代的主體性,與激發電影研究活力,成為當前時代重提德勒茲的兩個原因[10]”——李洋教授如此坦言。電影誕生于世百余年來,從雜耍到藝術,西方電影理論無疑對于電影的本體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對于泛影像化的當下,德勒茲及其獨樹一幟的電影哲思則對當下有著更大的理論意義。新媒體藝術,實驗影像等后現代性強的藝術現象多元出現,帶有極強作者風格的新導演頻出,而帶有綿延生成性質的德勒茲電影哲學則可以從學術層面去研究這些新藝術現象。德勒茲的電影理論與“杭州新浪潮”的創作現象可以為構建“中國電影學派”的形成,創造我們自己的電影話語體系,提供一個新的研究角度。
結語
回憶-影像作為時間-影像的入口,承載著綿延與潛在的“心流”生成狀態。它打破了日常時間的線性走向,在過去與現在之間流動循環,使得人類探索著自己的潛在過去與能量,體會著自我的存在與感知,由此人具備了主觀性,確認了自己的主體性。當我們重置時間的時候,可以發現生命的回溯與綿長,感受到生命是縱向的,而不是簡單的生老病死的橫向運作。[11]“杭州新浪潮”作為區域電影的新創作力量,在個體記憶與時空錯置之間進行著南方故事的個體表述。作為中國電影新力量之一,其實驗性與個人性更新了我國以往傳統的創作方式,使影視的創作主體不再單獨屬于北京,而開始在各個地域發酵。由賈磊磊教授劃分的區域電影中,“杭州新浪潮”以其實驗性、先鋒性做到了區域電影的旗手。期待在此之后,各地電影都開始引發自己的電影“新浪潮”,促進我國電影行業的多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