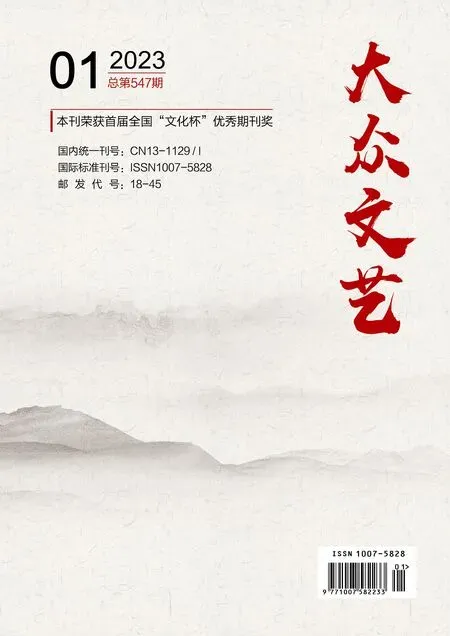本雅明“辯證意象”的語圖維度再闡釋
莊 懿
(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5)
二十世紀初語言學轉向的發生促使了人的思維的轉變,以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為代表,他將語言視作一個封閉的系統。本雅明并不贊同索緒爾將語言視為外在于人的系統的觀點,于是他從卡巴拉教派的神秘主義入手建構語言哲學,探討語言與人的存在之間的關系。他從語言哲學的角度出發,回歸原初語言來重現事物的真理,實現最終的救贖。在神學—語言哲學的框架下,本雅明以非中介的辯證法來解放真理,使之從主客二元對立認識論的遮蔽中呈現出來。“辯證意象”就是本雅明提出的有力的認識和批判工具,它蘊含著對時間和歷史的顛覆性理解以及語圖的辯證關系,構成喬治·迪迪-于貝爾曼和W.J.T.米歇爾對藝術作品乃至各種圖像問題思考的根基。
本雅明的“辯證意象”體現過去記憶與現在視覺所見之物之間的辯證關系,于貝爾曼正是從這一點入手,試圖通過視覺細節中的斷裂、差異和重復來接近人類的思想樣態與生命情態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本雅明認為語言是“辯證意象”之地,“辯證意象”以文字與圖像相遇的形式呈現,意義或理念在這個過程中自我生成,這啟發了米歇爾提出的圖像轉向論以及“元圖像”概念,讓圖像言說自身,從而實現對語言言說圖像的傳統的顛覆。借助米歇爾、于貝爾曼與本雅明思想之間的重疊和錯位,或許能為“辯證意象”概念的理解提供更加全面的觀照。
一、“辯證意象”的根基:本雅明的語言哲學
笛卡爾以來的主客二分認識論,使人類以同一性、精確性來控制一切事物,主體從而凌駕于客體之上,甚至滲透到語言領域。[1]在以主體理性為基礎的符號語言中,自然事物的意義是由理性主體賦予的,理性主體具有絕對的優先性;而在圖像語言中,自然事物的樣態能夠呈現其本質而沒有被主體的認識需求所遮蔽,客體具有優先性。類似地,本雅明通過統一事物的本然狀態來呈現事物樣態的豐富性,推崇客體優先性,將圖像語言視為打破主體統治地位的關鍵。
二十世紀的語言學轉向帶來了語言與人的思維和存在方式間的深切關聯,語言不再是傳達意義的工具。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下,本雅明建構了一種容納歷史哲學的語言神學,緬懷并追尋原初的純語言。純語言不是本質存在,而是通過碎片的重組和并置從而不斷接近的可能性,迥異于形而上學中至高無上的理念。
本雅明批判索緒爾以棋盤與棋子之間的關系來類比語言系統與要素之間的關系:“棋子的各自價值是由它們在棋盤上的位置決定的,同樣,在語言里,每項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各項要素對立才能有它的價值。”[2]在本雅明看來,索緒爾的語言觀是唯名論的,語詞與事物之間聯系隨意且偶然,本質上取消了人的主體性。索緒爾關注整體語言的社會性,個體語言并不具有實體性。羅蘭·巴特進一步指出了社會性的語言結構對個體言語的壓抑,處在語言之中的人難以脫離語言來批判或思考語言。但是與索緒爾不同的是,羅蘭·巴特具有歷史唯物主義傾向,把語言學納入符號學,從而揭露符號本身的歷史性。本雅明則是抑制主體以保障客體優先性,最終目的是抵達自行生成和顯現的非同一性的真理。他為命名集式的語言找到神學根基,指出了語言以對應的方式發揮自己的建構力量。語言并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一個抽象的整體,也不是語詞、話語、文字等具體事物的集合,而是存在于語詞、文字、聲音、圖像之間的矛盾、沖突和張力中。
本雅明早期的語言哲學是在神學的框架下展開的,整體邏輯可以用“起源即目標”來概括,即人如何從起源墮落,并重新尋找救贖回歸原初的起點的過程。“起源”不是指生成,而是“在變化和消逝中正待生成者”的歷史性范疇。起源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學總體,而可以被視作一種變動不居的節奏。[3]本雅明探討的是如何打破線性的歷史進程,反對同質的空洞的時間,從斷裂、差異中尋找爆破的可能性。于貝爾曼將本雅明的“元語言”中的“元”理解為正在形成的危機。[4]因此“元語言”實際上包含兩個維度,一個是已經失落了的原初語言,另外一個是在試圖迫近過去時在瞬間的爆破中抵達的原初語言。
在本雅明看來,語言最初是由上帝賦予人的一種天賦。在《創世紀》第一章中,上帝是通過“說要有——便有了”來創造萬物與人類的,上帝以名稱這一創造性語詞的方式來使人類得以存在。[5]在上帝的命名下,萬物的存在得以與上帝的創造性語言同一,分有上帝的神性,直接在場。上帝的語言直接顯現了事物本身的真理與知識,是無中介的、純粹的和完滿的絕對真理。被上帝命名的人類和事物就是知識本身,二者是統一的。在伊甸園中人類的語言是完美的,能夠完滿地傳達精神實體、語言實體以及神性的啟示。但是在人類亞當和夏娃受到了蛇的誘惑之后,得到了有關善惡的知識,否定并放棄了名稱。這時人類語言的名稱是外在的知識,成為對上帝語言的拙劣模仿,傳達外在于自身的事物。人類墮落之后,作為表意符號的語言混亂不堪,通過外在的認識判斷來獲取事物的真理在本雅明看來是徒勞的,名稱作為高貴的神性的表征淪為被奴役的工具。
于是本雅明著手考察如何將人類語言擢升為純語言。這一帶有烏托邦色彩的起源既體現的是主客間最原初的同一關系,又是一種有待完成和實現的狀態,不斷地以流動的節奏引領著救贖的實現,在四分五裂的經驗碎片中閃爍著微弱的光芒。而人類必須探求新的方式來抵達主客同一的源初關系。本雅明并不是走中立調和的路線,而是以爆破和毀滅一切的“辯證意象”來接近真理。
本雅明的語言哲學中的時間錯位,為“辯證意象”提供了理論基礎。“辯證意象”發生于當下,以過去的記憶拉開與當下體驗之間的距離。在這雙重距離與時間錯位中,一種本真性的綜合得以實現。“辯證意象”既是人認識事物與自身關系的工具,又是人類批判自身的工具,因此是與人的存在密切相關的。本雅明預設了語言與精神存在的同一性,語言既是突破緊張關系時參照的起源,也是想要達成的目標,盡管目標的實現可能發生于斷裂、爆破的瞬間。“辯證意象”的產生基礎就是這樣的一種與精神存在同一的語言得以實現的瞬間的可能性。
二、“辯證意象”的運作原理:星叢式的認識論與方法論
“辯證意象”將過去的記憶與當下的體驗以星叢的方式關聯在一起,從處于當下歷史文化的連續性中的各種文化現象中爆破出來。這種星叢式的運作原理,早已在本雅明的語言哲學中有所體現。在《譯者的職責》中,本雅明論述了諸種語言之間的親緣性,是由不同語言之間互補的表意擢升出來的總體性,而這種總體性就是純語言的特征。純語言或者上帝語言,既是原初世界的起源,又是墮落的世俗語言要求得救贖的目標,本雅明將目標的實現置于動態的過程中,需要通過翻譯這一直接中介來達成。純語言是對事物真理和上帝旨意的直接顯現,是通過翻譯使原作和譯作互補并調和而成的抽象總體性,與“星叢”概念的運用有著內在的一致性。
在《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的“認識論批判”導言中,本雅明詳細地論述了理念、現象與概念之間星叢式的關系。語言是與精神內容對應同一的透明性容器,理念的表達即語言的自我表達。對于真理而言,表達是首要的。這是一種從《論原初語言和人的語言》中延伸出來的觀點:人在語言之中傳達著他自己的精神存在。[5]語言不是傳達的媒介,而是傳達能力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傳達的事物本身,因此真理不需要像認識一樣借助中介建立起和對象之間的聯系。與認識和真理之間的差異相對應的則是概念和理念之間的差異。本雅明指出了概念起著中介的作用,通過對現象進行分解、收集和整合,使現象消解為星叢結構連接點的元素,從而參與理念的存在。理念只有在“概念對物的元素的組合中表達自己”[6],將現象吸納入自身之后進行再現。因此概念作為現象和理念之間的中介是極為重要的,在同一個過程中既拯救了現象,也表現了理念。
本雅明的星叢構型方式實際上是為了避免主觀意圖的介入,使真理成為一種中性的“由理念構成的一個無意圖的存在”和“意圖的死亡”[6]。因此真理是無法通過認識以一種占有的方式捕獲的,主觀意圖也無法與其發生聯系,而只能通過理念這一表征來接近。[7]通過概念這一中介,理念和現象之間的關系得以建立,它們不是從屬關系,也不是一與多、普遍與特殊的關系,而是星叢式的關系。這就意味著要素與要素之間是一種并置的關系,現象借助概念這一中介抽離出原本的邏輯語境,以要素的形式浸潤在星叢之中,而理念在這些要素的排列中以星叢的形式得到顯現。
本雅明對“辯證意象”生成的論述,正是借助了這一邏輯,將過去經驗與當下的體驗、圖像本身與圖像的可讀性星叢式地并置在一起,讓“辯證意象”如集體無意識般自行顯現,從而具有了短暫易逝的烏托邦色彩。以星叢的構型生成的“辯證意象”使人對精神與事物、語言與圖像之間關系進行深入的認知與反思,這又是通過“新穎”(novelty)賦予人們震驚體驗來實現的。盡管本雅明是用意象化的方式來拯救現象與理念,但這個過程離不開語言的參與,語言是與“辯證意象”的生成相互纏繞的,服務于“辯證意象”的讀解,是承載并呈現“辯證意象”的媒介。于貝爾曼認為,理解“辯證意象”等同于閱讀辯證意象,這是因為閱讀不是去解讀圖像本身,而是用文字對圖像進行批判性的再加工。“本雅明關于圖像的可讀性應被理解為圖像本身的一種本質的時間運動(可讀性不壓縮圖像,因為它生自于圖像),它不是圖像的解釋。”[4]真理就產生于圖像與語言之間的時間距離當中,生成于圖像和批判性闡釋圖像之間的張力當中。
借助米歇爾的理論,我們或許可以更好地理解圖像本身與圖像可讀性之間的張力或者說辯證距離。受到“辯證意象”的啟發,米歇爾進一步發掘語言與圖像之間的關系,在語言與圖像互滲的層面上提出了一個類似于“辯證意象”的批判工具——“元圖像”。圖像是由原初的形象(image)轉變為經過人為扭曲的具有實際用途的圖像(picture)的過程,通過將實際的圖像元素進行拆解和重組,以接近甚至抵達原初的圖像。形象與圖像之間的關系,并不是現象與本質之間的關系,而是類以家族相似的識別邏輯形成的克隆關系。[8]原初的形象并不是現象的本質或者經過抽象的一般形式,而只是與圖像相似。這些相似性盤根錯節地交織在一起從而構成了親緣家族,原初形象是我們所感受到的相似性的交織,它既是自身,又是他者,是在場的缺席,缺席的在場。與米歇爾相比,本雅明“辯證意象”更具有整體性,探尋的是總體救贖的可能性,因此語言與圖像并不是中性的元素,而是蘊含著爆破一切的批判性力量的。米歇爾的“元圖像”則是徹底后現代的,試圖拆解一切總體性,與異質、多元的社會融為一體。圖像的價值和作用不必被放置于社會語境中進行考察,而是社會本身[8]。
三、“辯證意象”的實現:從寄喻到新穎
本雅明對元語言的追尋,是試圖在打破線性時間進程的同時尋找新的救贖方式,來接近語言的原初狀態。他將“辯證意象”視作通向起源的認識論工具和批判武器,考察不同時期的“辯證意象”如何成為社會變革的內在動力:“就像十七世紀寓言是辯證意象的準則一樣,到了十九世紀新穎(novelty)便成了辯證意象的準則。”[9]
十七世紀的巴洛克悲苦劇的呈現樣態是星叢式的,體現了理念是一個歷史性的、開放的和充滿張力的場所,文字、聲音和圖像的混合使用使得語圖關系的重要性得以顯現。悲苦劇以不具備任何美感的廢墟形態拯救藝術本身,這體現在其寄喻性結構當中。傳統的理論家往往將寄喻視為一種“描述性圖像”[6],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是約定俗成的,忽略了寄喻性直覺本身所具有的原初力量。他們誤解寄喻的原因在于,作為約定俗成的符號系統的文字遮蔽了寄喻的表達特性。本雅明認為,寄喻不是一種描述方式,而是表達本身,是和語言、文字一樣的表達。[6]更準確地說,寄喻是陳規與表達之間的辯證關系。寄喻符號內在于約定俗成的符號系統,又極具創造性、生機勃勃和自由。[6]寄喻符號不是被賦予和被規定的,更偏向于象形文字,能夠以圖像的形式直接與神義建立聯系。
一方面,寄喻的創造力和生命力體現于它迥異于象征的特性。與象征相比,悲苦劇中的寄喻不斷地在能指和所指之間滑動,與明確的意圖或者固定的意義發生沖突并試圖征服它們,從而實現不斷的自我更新。不僅如此,悲苦劇的意義產生于聲音與文字之間的斷裂。[6]詞語沒有固定的所指,不再是人類進行對話或交流的工具。另一方面,寄喻符號本質上依托于人圖像式的思維方式,只有這種無須任何規定的直觀,才能極具爆破性和生命力地自行生發出神圣的力量。無序而又尚未定型的圖像還是人類思想樣態呈現的形式,寄喻所使用的文字是圖像式的,因此能夠真正進入到本質當中。[6]巴洛克式寄喻的特點就在于文字的圖像性,圖像就是和魯內文相似的碎片,直接沐浴在神靈光芒的照耀下而不被任何理念、意指或意義所遮蔽,因此隱晦地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怪誕的廢墟狀態。寄喻這種充滿歧義性的碎片形式并不妨礙理念的生成,相反,正是在這黑暗的廢墟中散落四處的碎片上閃爍著理念的光芒。因此,悲苦劇的語言打破傳統悲劇語言的規范性,以不斷變化、跳躍和流動的形式模仿悲苦的情感。
更進一步地,語詞與物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十分明顯和積極的。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理論認為藝術模仿的是神造的自然,但是本雅明指出這種神造的自然實際上是墮落的、衰敗的和消逝的,過度世俗化的實物本身并沒有任何美感可言,因此不會綻放出光芒。這種不斷重復的語詞和無言的畫面結合在一起,以展示一種憂郁悲傷的情感。[6]人通過與物同一,去理解和感知物,才能夠從物那里對自己的本性進行反思。破碎的語詞和無聲的畫面顯示出沒有主體的語言摧毀主體的統治,試圖恢復自然的歷史。語言的“沉默”不是指不發出任何聲音的緘默不語,而是太多的聲音和話語造成了一種表面上的虛無和頹廢,其內在卻是對生命的真切感知和有力表達。
而到了資本主義時代,“辯證意象”不再是通過寄喻中的語圖關系實現自我生成,而是通過傳統經驗與當下體驗之間的時間錯位造成的新奇感生成的。[4]本雅明擺脫了語圖互滲的維度,而是以一種徹底意象化的方式來理解歷史,反對回憶永恒過去、當下稍縱即逝、期待美好未來的進步歷史觀。而在全新的歷史觀指引下的“辯證意象”是曖昧的(ambiguity)[10]“辯證意象”存在于不同時期的集體意識當中,[8]但它強調的是當下的體驗,主體在辨認和感知到集體無意識的瞬間,也就獲得了救贖的潛能。因此“辯證意象”既是一種認識事物的方式,也是批判自身和實現救贖的工具。
“辯證意象”的救贖性,恰好是米歇爾所缺乏的。他看到了本雅明“辯證意象”作為方法論的有效性,于是在調和語圖沖突的層面上提出了“元圖像”概念。他摒棄了“辯證意象”散發的憂郁絕望的氣息,解除“辯證意象”蘊含的整體性。盡管他明確指出過圖像就是本雅明所說的“辯證意象”,以蒙太奇的方式將各種要素并置在一起,與當下直接發生關聯,但他并不強調并置所有元素之后會生成真理,因為物質載體與圖像之間是關系性的,這就消解掉了主體的作用和意義,也就消解掉了“辯證意象”的救贖性質。圖像成為主體本身而產生了生命和欲望。這種自我指涉的元圖像,可以是任何事物。[8]那么米歇爾的“元圖像”也就與本雅明的“辯證意象”徹底分道揚鑣。
結語
本雅明早期的語言哲學以神學的方式考察了人類語言與歷史的起源,力圖通過彌合現象與理念、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分裂來恢復一種原初的總體性。以語言哲學為基礎,星叢理論構成本雅明認識和批判的工具,其目的在于深刻反思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現象,在傳統經驗與當下體驗的錯位中接近歷史的總體性面貌。以諷喻的表達方式到對新穎的追求為特征的“辯證意象”,使人從烏托邦的幻想中看到一絲救贖的希望。借助迪迪-于貝爾曼和T.J.米歇爾的理論,我們可以更好地看到“辯證意象”與圖像之間的關系及其救贖的潛能,為我們提供了深入理解“辯證意象”概念發展的新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