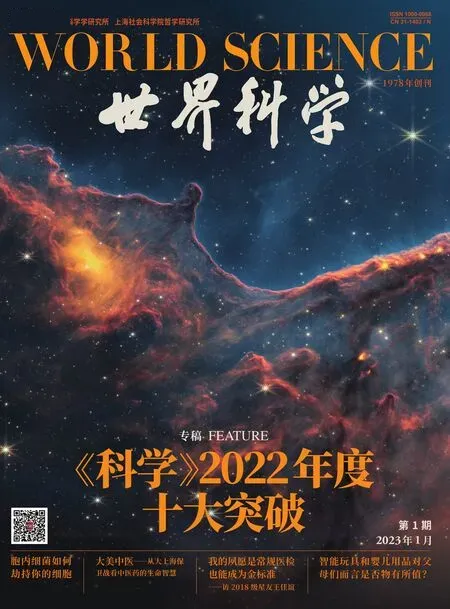物理學家創造出了一個非常小的黑洞
編譯 苦山

2022年,一組研究人員宣布,他們進行了一項涉及現代物理學中大部分神秘理論的實驗,在量子計算機中模擬出了一對黑洞,并通過一段被稱為蟲洞的時空捷徑在它們之間傳送了一條信息。
物理學家們稱,這項成就是幫助理解引力和量子力學之間關系的又一個小小進展——引力塑造了宇宙,而量子力學主宰著粒子的亞原子領域。
“這很重要,因為從構造和結構來看,我們得到的是一個嬰兒蟲洞,”加州理工學院的物理學家瑪利亞?斯皮羅普魯(Maria Spiropulu)說,她同時也是指揮這項研究的基礎物理量子通信通道項目組的負責人,“我們希望,我們可以一步一步地制造幼兒蟲洞和成年蟲洞。”
他們的報告發表在《自然》雜志上,報告中,研究人員用謹慎的措辭對研究結果做了描述:“這項工作是在實驗環境中觀察可穿越蟲洞動力學的一次成功嘗試。”
斯皮羅普魯博士和她的同事們創造并運用的蟲洞隧道所穿越的并非真實的物理空間,而是一個“層展”的二維空間。這些“黑洞”也并非能夠吞噬計算機的真實黑洞,而是量子計算機中的一行行代碼。嚴格來說,他們得出的結果只適用于一個簡化的“玩具模型宇宙”——確切地說,這是一個類似于全息圖的模型,由位于時空邊緣的量子場來決定模型內部會發生什么,有點像是湯罐頭上的標簽可以描述罐頭里的內容那樣。
有一點需要講清楚:這個實驗的結果并不意味著我們很快就能擁有(甚至永遠都不可能擁有)像電影《超時空接觸》(Contact)中的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或者《星際穿越》(Interstellar)中的馬修?麥康納(Matthew McConaughey)那樣可用來漫游銀河系的宇宙地鐵。
“我猜最關鍵的問題,或許也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是這樣的:我們是否能說從模擬中得到的是一個真正的黑洞?”哈佛大學物理學教授丹尼爾?賈弗里斯(Daniel Jafferis)說,“我比較喜歡‘層展黑洞’這個說法。”
他補充道:“我們只是利用量子計算機來找出當你處于這種引力情況下時會是什么模樣和感受。”他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生亞歷山大?茲洛卡帕(Alexander Zlokapa)是這篇論文的主要作者。
物理學家們對這篇論文既感興趣又很謹慎,他們擔心公眾和媒體會錯誤地認為研究人員已經創造出了真實的物理蟲洞。
“我想讓《紐約時報》的讀者明白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下面這點,”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量子計算專家斯科特?阿倫森(Scott Aaronson)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如果這個實驗制造了一個真實的、物理層面的蟲洞,那么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論稱,每當你用紙和筆畫出這東西時,你也可以制造一個真實的、物理層面的蟲洞。”
麻省理工學院的物理學家丹尼爾?哈洛(Daniel Harlow)沒有參與這項實驗,他指出該實驗的基礎是一個非常簡單且不切實際的量子引力模型,用它來研究簡直就和用紙筆來研究沒什么區別。
“所以要我說,這項實驗并沒有教會我們任何關于量子引力的新知識,”哈洛博士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但另一方面,我認為這是一項令人興奮的技術成就,因為如果我們連目前這樣都做不到(在這項實驗之前我們確實沒做到過),那么就絕對不可能模擬更有趣的量子引力理論。”他補充說,我們可能需要10到15年的時間才能開發出足夠大的計算機來做這件事。
斯坦福大學的物理學家倫納德?薩斯坎德(Leonard Susskind)并未加入研究團隊,他同意哈洛的觀點。“他們正在意識到,他們有能力做成這個實驗,”他說,“這項研究中真正有趣的事情是證明了利用廣義相對論分析純粹的量子現象的可能性,誰知道這能領我們走向何方呢?”

1934年,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匹茲堡的卡內基技術學院(現為卡內基梅隆大學)
愛因斯坦的兩面
1935年,物理學的詞匯表中加入了“蟲洞”一詞,當時它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中最為怪異的幾個預言之一。廣義相對論描述了物質和能量如何扭曲空間,來創造出我們稱之為引力的東西。同年,愛因斯坦和他的同事納森?羅森(Nathan Rosen)在一篇論文中指出,世界上可能存在穿越時空、連接成對黑洞的捷徑。物理學家約翰?惠勒(John Wheeler)后來將這些連接通路稱為“蟲洞”。
起初人們覺得,蟲洞似乎沒有實際的作用。理論認為,任何東西進入它們的瞬間,它們就會砰的一聲關閉。它們從未在科幻小說之外被觀察到過。
也是在1935年,上述發表的一個月前,愛因斯坦、羅森和鮑里斯?波多爾斯基(Boris Podolsky)取得了另一項突破,他們認為這項突破將令量子力學的不確定性受到質疑。他們指出,量子規則允許愛因斯坦所說的“幽靈般的超距作用”的發生。對一對粒子中的一個做測量將決定另一個粒子的測量結果,即使兩個粒子相距光年。愛因斯坦認為這個預測是荒謬的,但如今物理學家們稱之為“糾纏”,并每天都在實驗室里利用這種特性。
直到幾年前,這種量子把戲還被認為與引力無關。因此,物理學家們無法運用某種“量子引力”理論去解釋,在宇宙大爆炸或黑洞內部的內外空間碰撞時發生了什么。
但在2013年,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理論物理學家胡安?馬爾達塞納(Juan Maldacena)和薩斯坎德博士提出,這兩種現象——幽靈般的超距作用和蟲洞——實際上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只是各自用了不同但互補的數學語言來描述。
按照這種邏輯,這些幽靈般的糾纏粒子由同樣神秘的蟲洞連接起來。我們可以用量子力學來研究引力,反之亦然。事實證明,可以在愛因斯坦的引力方程中找到和描述量子現象的方程式類似的東西。
“要使用哪種描述主要取決于你的偏好,因為它們給出的答案是完全一樣的,”賈弗里斯博士說,“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發現。”

在量子計算機中,物理學家使用一種稱為“門”的操作線路,在代表兩個黑洞的量子比特之間的虛擬空間中打開一條捷徑,并在它們之間發送信息
逃生艙口
最近這次蟲洞實驗試圖利用廣義相對論中的數學來檢驗量子魔法的其中一個方面,也就是所謂的量子隱形傳態,以考察是否能借此揭示物理學或引力的新特性。
在量子隱形傳態中,物理學家使用一系列量子操作,在自己不知道信息內容的前提下,將信息發送到相距數米或數千米、糾纏成對的兩個粒子之間。這項技術有望成為下一代不可破解的“量子互聯網”的核心。
物理學家喜歡把隱形傳態的過程比作兩杯茶。先朝一杯茶里放一塊方糖,它會即刻溶解——然后,量子鐘滴答一聲,方糖就會完整地出現在另一個茶杯里。
在薩斯坎德博士、賈弗里斯博士、麻省理工學院的高蘋和劍橋大學的理論物理學家阿倫?沃爾(Aron Wall)分別發表了兩篇彼此獨立的論文之后,這個實驗變得不再是空中樓閣。畢竟,他們提出了一種可以穿越蟲洞的方法。高博士和他的合作者說,我們所需要的是在蟲洞出口末端設置一小劑負能量,以支撐“艙口”足夠長的時間,讓信息逃脫。
在經典物理學中,沒有負能量這回事。但在量子理論中,能量可以是負的,它會產生反引力效應。例如,所謂的虛粒子利用從真空中借來的能量瞬息出現又瞬息消失,它可以落入黑洞,以能量的形式向大自然欠債,而黑洞必須償還。斯蒂芬?霍金在1974年計算出,這種緩慢的泄漏會導致黑洞失去能量并收縮。
當斯皮羅普魯博士提出嘗試在量子計算機上重現這種蟲洞魔法時,她在能源部的同事和贊助商“都認為我徹底瘋了,”她回憶道,“但賈弗里斯說,就這么干吧。”

能證明研究人員所記錄下的的確是“類蟲洞”行為的線索之一是,信號是按照它們進入蟲洞的順序從蟲洞另一端涌現的
駕馭不確定性
在普通計算機中(包括你口袋里的手機),計算的貨幣是比特,它可以是1或0。量子計算機則基于量子比特運行,量子比特可以是0或1,也可以兩者皆是,直到被測量或觀察。這使得量子計算機在某些特定的任務中具有超強的能力,比如分解大數和(也許有一天)破解加密代碼。本質上,量子計算機的原理是同時運行程序的所有可能變化,以得出一個結論。
斯皮羅普魯博士說:“我們讓不確定性成為我們的盟友并擁抱它。”
為了充分發揮潛力,量子計算機需要數千個工作的量子比特和一百多萬個“糾錯”的量子比特。位于加州威尼斯的谷歌量子人工智能實驗室的負責人哈特穆特?奈文(Hartmut Neven)表示,谷歌希望在2030年前實現這一目標。奈文也是斯皮羅普魯博士團隊的成員。
加州理工學院的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理查德?費曼(Richard Feynman)曾預言,量子力量的最終用途可能是研究量子物理本身,就像在這項蟲洞實驗中一樣。
“我很高興看到研究人員能夠實現費曼的夢想。”奈文博士說。
蟲洞實驗是在谷歌的梧桐2號計算機(Sycamore 2)的一個版本上進行的,該計算機有72個量子比特,研究團隊只用了其中9個量子比特來限制系統中的干擾和噪聲,9個中有2個是參考量子比特,在實驗中扮演著輸入和輸出的角色。
另外7個量子比特包含兩份代碼,描述的是一個名為SYK的全息宇宙的簡單模型的“稀疏”版本,該模型以它的三位創造者命名:哈佛大學的蘇比爾?薩奇德夫(Subir Sachdev)、密西西比州立大學的葉錦武和加州理工學院的阿列克謝?基塔耶夫(Alexei Kitaev)。兩個SYK模型都被裝進了同樣的7個量子比特中。在實驗中,這些SYK系統扮演了兩個黑洞的角色,一個將信息擾亂為無意義——相當于在量子層面吞下了它——另一個則將信息重新彈出。
費米實驗室量子研究所所長,也是這篇發表于《自然》期刊的論文作者之一的約瑟夫?萊肯(Joseph Lykken)表示:“我們往它里面扔了一個量子比特。”他指的是那條輸入的信息——一系列由1和0構成的量子模擬信息。這個量子比特與SYK量子比特的第一個副本相互作用,它的意義被擾亂成隨機的噪聲,然后消失。
隨即,在量子鐘的滴答聲中,兩個SYK系統被連接起來,負能量的沖擊從第一個系統傳到第二個系統,短暫地將后者撐開。
隨后,信號以未被擾亂的本來形態重新出現——它出現在第九個也是最后一個量子比特中,這個量子比特被連接到了代表蟲洞另一端的第二個SYK系統上。
萊肯博士說,能證明研究人員所記錄下的的確是“類蟲洞”行為的線索之一是,信號是按照它們進入蟲洞的順序從蟲洞另一端涌現的。
在與賈弗里斯博士的論文一起發表于《自然》期刊的另一篇文章中,薩斯坎德博士和斯坦福大學的物理學家亞當?布朗(Adam Brown)指出,這些結果可能會為普通量子力學中一些仍然神秘的方面提供線索。例如,當方糖在第一個茶杯中溶解后,它為什么會以原本的形態出現在另一個茶杯中呢?
“令人驚訝的不是這條信息以某種形式傳遞了出去,而是它傳遞出去時沒有被擾亂。”兩位作者如是寫道。
在一次采訪中,萊肯博士他們補充說,最簡單的解釋是,信息通過了一個蟲洞,盡管是一個“非常短”的蟲洞。在量子力學中,自然界可想象的最短長度是10-33厘米,也就是所謂的普朗克長度。根據萊肯博士的計算,他們的蟲洞可能只有3個普朗克長度。
“這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小、最寒酸的蟲洞,”他說,“但這真的很酷,因為現在我們觸及的顯然是量子引力的領域了。”
資料來源 The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