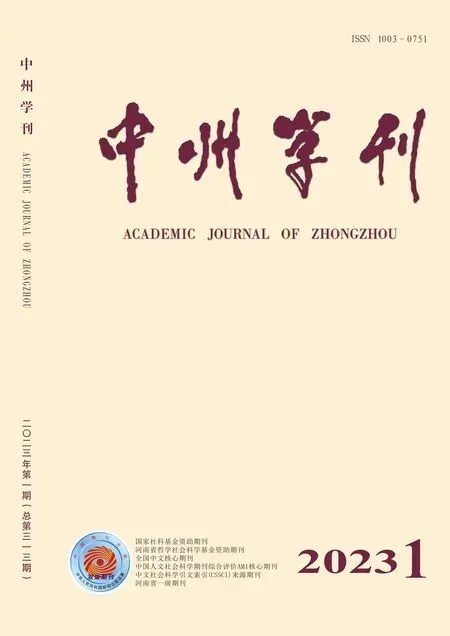唐、五代時期民眾就醫(yī)服藥觀念的形成
張劍光
一個時代人們的生活質(zhì)量與醫(yī)療衛(wèi)生技術的水平有很大的關系,同時和一個時期的醫(yī)療體系是否完善有關聯(lián)。在一些史書、筆記、墓志中,對唐、五代時期人們接受醫(yī)療的態(tài)度和藥物有若干記載,如《朝野僉載》卷三云:

以往關于唐代人就醫(yī)診病的研究,人們主要的興趣是集中在醫(yī)療技術、醫(yī)療制度、疾病的種類、醫(yī)家的著作等問題上①,而缺少從百姓立場出發(fā)討論普通民眾對醫(yī)藥的態(tài)度。在本文的研究中,我們力圖從人們對得病就醫(yī)的真實態(tài)度中,來準確地了解唐、五代時期的社會生活風貌。
一、百藥救療:州縣官員醫(yī)藥診治體系的建立
唐代的皇宮內(nèi)有專門的醫(yī)學校,有專門的醫(yī)療機構,主要服務對象是皇帝和皇室人員。如殿中省尚藥局有奉御二人、直長四人、主藥十二人、藥童三十人、司醫(yī)四人、醫(yī)佐八人、按摩師四人、咒禁師四人、合口脂匠二人。尚藥奉御是“掌合和御藥及診候之事”,侍御醫(yī)“掌診候調(diào)和,司醫(yī)、醫(yī)佐掌分療眾法”[2]324。尚藥局主要是為皇帝服務,人數(shù)眾多,分工明確,分科較細。太常寺還有太醫(yī)署,設太醫(yī)令二人、丞二人、醫(yī)監(jiān)四人、醫(yī)正八人、醫(yī)師二十人、醫(yī)工一百人、醫(yī)生四十人、典學二人。“凡醫(yī)師、醫(yī)正、醫(yī)工療人疾病,以其全多少而書之,以為考課”[2]408-409。從醫(yī)師、醫(yī)工的人數(shù)來看,太醫(yī)署主要是為皇帝醫(yī)療服務的,同時擴展至整個皇宮的治療。生活在皇宮里的人們,其實都能享受到政府較為完備的醫(yī)療服務。
皇宮內(nèi)的這套醫(yī)療服務體系,肯定是超過了帝王和內(nèi)宮的需要,因而宮外的一些高級官員身體一旦出現(xiàn)情況,皇帝常會派出醫(yī)務人員前去治療,顯示出皇帝對這些大臣的恩寵和關懷②。如李大亮“尋遇疾,太宗親為調(diào)藥,馳驛賜之”[3]2390。房玄齡得病,“敕遣名醫(yī)救療”[3]2464。馬周病消渴,“彌年不瘳”,唐太宗派出的“名醫(yī)中使,相望不絕”,“太宗躬為調(diào)藥,皇太子親臨問疾”[3]2619。張長遜,“會有疾,車駕親幸其第”[3]2302。雖沒有記錄唐太宗是否給了醫(yī)藥,但從其親自探病來看,應該會派宮內(nèi)醫(yī)者醫(yī)治的。君臣關系融洽,帝王關心大臣身體,派出名醫(yī)出宮醫(yī)治,是君臣關系和諧的一種特殊現(xiàn)象。
唐代長安城,官方有制度性的醫(yī)藥診治體系,不過只能惠及部分官員:“諸文武職事五品以上官致仕有疾患,在京城者,官給醫(yī)藥,在外者,亦準些量給,以官物市供。”[4]這里當然主要是提到致仕官,即五品以上的致仕官不管在京城內(nèi)外,政府都會給醫(yī)藥。那么,對在職的五品以上官員而言,自然也會得到太醫(yī)署等醫(yī)療機構的照顧。
以上都是與皇宮有關的高級官員得病時中央機構中太醫(yī)署等部門的治療。而那些京城的一般官員,即五品以下的官員,顯然是享受不到這樣的待遇,還有就是地方上州級衙門里的官員,他們得病后怎么辦?
《唐六典》卷三○談到唐代的京兆、河南、太原府,設醫(yī)學博士一人,助教一人(開元初置),醫(yī)學生二十人(貞觀初置)。大都督府醫(yī)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十五人。中都督府醫(yī)學博士一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十五人。下都督府,醫(yī)學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十二人。上州設醫(yī)學博士一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十五人。中州醫(yī)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十二人。下州醫(yī)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下;學生一十人。并且規(guī)定:“醫(yī)學博士,以百藥救療平人有疾者。”[2]750
從這段資料談到的唐代制度來看,除了皇宮以外,全國三個都城和各州普遍設立了醫(yī)學校,主要是為了能有效地醫(yī)治百官和百姓的疾病。三個都城中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估計日后有不少會被安排在各級政府機構中,對各部門官員的疾病作專門性醫(yī)治。因此,對中央政府和三個都城的五品以下官員而言,他們生病后主要由這些學成后的醫(yī)學生進行專門的醫(yī)療服務。
三個都城外,凡是州一級的行政治所,都有一定數(shù)量學醫(yī)的學生,碰到疾病侵身,他們會作一定的醫(yī)治。不過從這些醫(yī)學校大多只設博士一人和助教一人及他們的出身來看③,醫(yī)學生對醫(yī)療知識和技能的學習,應該是比較基本和粗疏的,也沒有見到具體的細化分科,醫(yī)學生學成后,實際上是一個全科醫(yī)療人員。其次,由于醫(yī)學的學習不是短期就能完成的,一個醫(yī)學校只有十多個醫(yī)學生,相信這部分醫(yī)務人員對一個州一級的城市來說是杯水車薪,各州的醫(yī)療資源顯然不夠,人員是缺乏的。從中我們可以推測出,這些只具有粗疏醫(yī)學知識的醫(yī)務人員通常情況下應該只能保證官員及其家屬的醫(yī)療,普通百姓如有身體不佳等情況,這些官方培養(yǎng)的醫(yī)務人員不一定都能滿足他們的需求。
從上面的資料中可以確信,政府機構中是有專職醫(yī)務人員的。事實上,從一些資料的記載中我們的確能夠看到唐、五代時期州級地方政府中有專職的醫(yī)者值守,醫(yī)治政府機關的官員和附近部隊的軍官。唐太宗貞觀七年(633年),唐臨“奉使江東”,揚州針醫(yī)甄陁就對他說了一個人死后進入地府的故事[5]。這里說的“針醫(yī)”,意謂他主攻的專業(yè)是針灸,但能與政府的使者交往,而且明言是“揚州針醫(yī)”,顯示他有官方的身份,應是官府的醫(yī)者。再如徐智通,“楚州醫(yī)士也。夏夜乘月,于柳堤閑步,忽有二客笑語于河橋,不虞智通之在陰翳也”[6]。徐智通應該是楚州官府中的醫(yī)者。唐末蜀將陶福立功后,“至郡守,屯戍興元府之西縣,暴得疾,急命從人朱軍將詣府迎醫(yī)李令藹。令藹與朱軍將連騎馳往”[7]241。興元府中有醫(yī)生,一旦府中官員有病情,能立即前往診療。
地方政府機構里的醫(yī)者,往往是政府的正式官員。柳芳為郎中,他的兒子柳登生病,“時名醫(yī)張方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且言:‘子病,唯恃故人一顧也’”。第二天早晨張方福“候芳,芳遽引視登。遙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按脈五息,復曰:‘不錯,壽且逾八十。’乃留方數(shù)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8]618。雖然將張方福的診病寫得有點神化,但可以看到官員或者家屬生病,就會找官方的醫(yī)者診治,醫(yī)者會按脈看相,留下藥讓病人服用。張方福“初除泗州”,應是剛剛到泗州任職。
地方州衙高官達人們,生病后通常會請醫(yī)者到家或到治所來診治。蕭仿為廣州刺史,“曾有疾,召醫(yī)者視”。這里的醫(yī)者雖然沒有明確是地方政府機構中的醫(yī)者還是民間醫(yī)者,但官員生病就找醫(yī)者來醫(yī)治,這在當時可能是通常的做法,醫(yī)者和刺史可能是比較熟悉的。這位醫(yī)者云:“藥用烏梅子,欲用公署中者。”于是蕭仿“乃召有司,以市價計而后取”。烏梅子衙門里就有,但蕭仿要按市場價出錢,說明他“廉亦如此”[9]。可知醫(yī)者診斷后,藥品可以用公署中的,也可以到市場上采購,再按醫(yī)囑服用。醫(yī)者對公署中有什么藥材十分熟悉,估計是政府的專職醫(yī)務人員。州府里的一般官員,也能接受官方醫(yī)者診治。如文明元年(684年),“毗陵掾滕庭難患熱病積年,每發(fā)身如火燒,熱數(shù)日方定。召醫(yī),醫(yī)不能治”[10]。由于是一種怪病,醫(yī)者也沒有辦法診治。
官員的家屬,同樣能享受到相應的醫(yī)療服務。如有一婦人,“從夫南中效官”。她“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愈”。說明有多位醫(yī)者診治過,但都沒治好。后來她到京城一醫(yī)者處治療,醫(yī)者“知其所患”,于是請來女病人的一位姨奶,私底下先對姨奶說:“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個蝦蟆走去,然切勿令娘子知之是誑語也。”姨奶按照醫(yī)者的話去做了,“此疾永除”[7]124。既然說是“頻療”,那最初在丈夫做官的地方肯定是接受了政府機構中醫(yī)者的醫(yī)治。
在《唐六典》中,并沒有記載縣級政府機構里醫(yī)學博士的設置,也沒有醫(yī)學生,說明縣級政府由于規(guī)模較小,不再有這類人員的設立。問題是,如果縣政府中的官員得病,他們能夠得到官方醫(yī)療診治嗎?
我們在徐鉉《稽神錄》中看到一條資料,或許對縣級政府里的醫(yī)療體制能有一定的了解。
高郵縣醫(yī)士王攀,鄉(xiāng)里推其長者。恒往來廣陵城東,每數(shù)月,輒一直縣。自念明日當赴縣,今夕即欲出東水門,夜泛小舟,及明可至。既而乃與親友飲于酒家,不覺大醉,誤出參佐門,投一村舍宿。向晚稍醒,東壁有燈而不甚明,仰視屋室,知非常宿處,因獨嘆曰:“吾明日須至縣,今在何處也!”久之,乃聞其內(nèi)躡履聲,有婦人隔壁問曰:“客將何之?”因起辭謝曰:“欲之高郵,醉中誤至于是。”婦曰:“此非高郵道也。吾使人奉送至城東,無憂也。”乃有一村豎至,隨之而行,每歷艱險,豎輒以手捧其足而過。既曙,至城東常宿之店,告辭而去。攀解其襦以贈之,豎不受,固與之,乃持去。既而入店家易衣,又見其襦放在腰下,即復詣其宿處尋之,但一古冢,并無人家。[11]49-50
此條材料《太平廣記》卷三五五也有引用,只是將“醫(yī)士”作“醫(yī)工”。在唐代的一些史料中,稱醫(yī)者為“醫(yī)士”的,的確常會見到,但據(jù)上引《唐六典》記載,太醫(yī)署中有醫(yī)工一百人,猜測《太平廣記》中作“醫(yī)工”也是有據(jù)可依。這則故事中說了揚州有一位醫(yī)士王攀,應該是個德高望重的人,醫(yī)療技術雖沒有直接描寫,但應該是有較高水準的。他每隔數(shù)月,就會去一次高郵縣輪值,應該是作為一個醫(yī)者到高郵縣去值守診病。這種值守,一般不會是為了普通人而去的,而是為了當?shù)氐墓俑藛T及其家屬治病才設立的一種制度。王攀值守多少時間,這里沒有說,所以我們沒法知道高郵縣像王攀這樣的醫(yī)士有幾個人是互相輪值的,或者說只有王攀一個人每過一段時間才去一次,不過從他十分強調(diào)“明日須至縣”來看,似乎更有可能是有人和王攀輪班的。
王攀一般是晚上從揚州城東出發(fā),利用小船作為交通工具,第二天就可以準時到達高郵當值。也就是說,當時從州城派出醫(yī)者到各縣輪值,估計縣級機構是沒有專門醫(yī)者崗位的設置,而州級機構里應該有多名醫(yī)者崗位設置。這樣的醫(yī)士,應主要是為縣級府衙中的官員進行醫(yī)療服務的。
故事中揚州醫(yī)士到高郵縣當值的事例,如果不是個案,那么就有可能是當時縣級醫(yī)療體系的一種通常情況,其他各州各縣,或許也存在這樣的模式。
二、走馬呼醫(yī):百姓得病后醫(yī)藥診治的普及
官員之外,普通百姓得病后是否全如上述《朝野僉載》卷三說的那樣因為“無醫(yī)人”而只能靠祭祀治療?從各種資料記錄來看,的確有地區(qū)缺少醫(yī)藥,但并不是全部都缺,當時大多數(shù)人是會延請醫(yī)生治療的,醫(yī)藥診治的觀念越來越普及,主動請醫(yī)生診斷后吃藥,在經(jīng)濟稍發(fā)達地區(qū)成為習俗。
其實,稍有點財富或社會地位的人,生病后都會請醫(yī)診療。馬逢生活比較窘困,時王仲舒為郎中,與馬逢友善。王仲舒責怪馬逢說:“貧不可堪,何不求碑志相救?”意謂你文采這樣好,為啥不靠替人家寫碑志賺點生活費。馬逢笑著說:“適見人家走馬呼醫(yī),立可得也。”[12]217一些有錢人或者社會地位較高的人家,生病后“走馬呼醫(yī)”,如果治不好,肯定就會請馬逢寫墓志了。死后有經(jīng)濟實力請人寫墓志銘,應該是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不是官員,亦是士大夫。
一些人通過經(jīng)商,富有錢財,得病后請醫(yī)者診治也是十分多見,畢竟生命可貴,錢再多也換不到命。如在長江流域有一富商,南來北往,一直居住在船上,“中夜暴亡,迨曉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yī)士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梁新認為他是吃了東西中毒,富商的仆人說富商喜歡吃竹雞。梁新說:“竹雞吃半夏,必是半夏毒也。”于是梁新叫仆人“搗姜捩汁,折齒而灌之,由是方蘇”[7]。醫(yī)士梁新恰好住在船居富商的“鄰房”,富商生病后是有錢延醫(yī)治療的。
普通人得病也會請醫(yī)者診治。段成式說“江左數(shù)十年前有商人,左膊上有瘡”,這個瘡很奇怪,“如人面,也無他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也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膊內(nèi)肉漲起,疑胃在其中也”。當然這里描寫有點過頭,說得比較虛幻,但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瘡中短期內(nèi)沒辦法結(jié)痂。經(jīng)過一位“善醫(yī)者”治療,“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shù)日成痂,遂愈”[8]1091。這位醫(yī)技較高的醫(yī)者,治療上有獨特的方法,最后商人的瘡口結(jié)痂治愈了。
從目前見到的一些墓志銘來看,有相當一部分人病逝前,都請醫(yī)者診治過,實在無法救治才離開人間。如我們以揚州地區(qū)的一些墓志為例,很多人在死之前都有請醫(yī)者診病的過程。如果年紀比較輕,家人大都會全力延請醫(yī)者救治。如42歲的揚州李崇,“染疾經(jīng)旬,醫(yī)藥無助”,最后死于家中[13]61。來治安夫人田氏,“不幸染疾,藥石無救,終于揚州江陽縣崇儒坊之私第”,僅48歲[13]73。鄒氏,元和元年(806年)死,“不幸遘疾,藥餌無助”,享年26歲[13]86。像這樣的年輕媳婦,肯定結(jié)婚不會太長時間,家人更是會請醫(yī)者來救治。吳郡陸公夫人宋氏,“不期抅疾,藥餌無功”,享年三十有五[13]91-92。張仕濟,讀書特別用功,“因?qū)W成勞,遂遘微疾,遍尋醫(yī)術,有殛無瘳”,死時才22歲[13]93。這里我們列舉的都是二十多歲至四十多歲的中青年人,他們均因患有疾病,所以請醫(yī)者治療。
即使年紀較大的人得病,也會請醫(yī)者救治。李彥崇,五十有二,“暫縈小疾,藥餌難救,奄歸夜泉”[13]157。臧暹妻魏氏74歲,“遘疾經(jīng)旬,徒施藥餌”[13]178-179。任玄“中年以寒暑所侵,忽嬰羙疹,千方以療,粗獲其瘳”。不過一年后,“疾乃兇基”,還是得病死了,年五十七[13]244。唐末孫綏,“遭二豎之致疾,伏枕逾月,百藥不瘳,圓虛匪仁,纖我囗尊德”,死時81歲[13]279。當然總體上說,死后有墓志銘的人,一般是社會上層家庭,因而他們和醫(yī)藥診療的關系自然是比較緊密的。
宗教人員生病,也會用醫(yī)藥治療。廣陵法云寺僧珉楚,“既歸,有同院人覺其面色甚異,以為中惡,競持湯藥以救之,良久乃復”[11]42。當然,這里所持的湯藥有可能是懂醫(yī)學的僧人在救治。
如果是傳染性疾病流行,那么全民就會接受醫(yī)者救治。地方政府會從醫(yī)學治療上著手,考慮用湯藥醫(yī)治。李吉甫在淮南任節(jié)度使時,“州境廣疫”,“亡歿相踵”。一秀才對他說:“某近離楚州,有王煉師,自云從太白山來,濟拔江淮疾病,休糧服氣,神骨甚清,得力者已眾。”雖然不是正宗的醫(yī)生,是個道士,但他能治病。于是李吉甫“令作書,并手札,遣人馬往迎。旬日至,館于州宅,稱弟子以祈之”。王道士對李吉甫說:“相公但令于市內(nèi)多聚龜殼大鑊巨甌,病者悉集,無慮不瘥。”大鍋子里煎龜殼為藥,把病人集中起來讓他們喝。王道士的治療是有效果的:“既得,王生往,令濃煎。重者恣飲之,輕者稍減,既汗皆愈。”[14]雖然這則故事的記載有點神奇,但實際上很多道士掌握了不少醫(yī)學知識,他們是能夠醫(yī)治不少疾病的。
我們認為,隨著醫(yī)學技術的發(fā)展,人們在醫(yī)療技術上的認識不斷深化,城市中的普通民眾,特別是一些大城市,人們基本建立起了有病就醫(yī)的觀念,得病后一般都會設法延請醫(yī)生,或到醫(yī)生家里,求藥醫(yī)治,這一方面說明唐代人的醫(yī)療知識漸漸在增長,同時也說明唐代人的生活質(zhì)量有所提高。當吃飯問題解決后,人們還是想在醫(yī)藥救護上有所提高。
當然,我們亦不能過分地相信唐代和現(xiàn)代人一樣,是有病只找醫(yī)生醫(yī)治的,事實并不是如此。我們對唐代人的就醫(yī)診治還是要辯證地來看。
其一,說唐、五代時期人們生病了就能找醫(yī)診治,也不是絕對的。《全唐文》卷七二九崔龜從《宣州昭亭山梓華君神祠記》談道:“先是疾作,醫(yī)言疾由寒而發(fā),服熱藥輒劇,遂求醫(yī)于浙西。廉使盧大夫為臣命醫(yī)沈中象乘驛而至。既切脈。”“如其言,涉旬而稍間,經(jīng)月而良已。自以為必神之助,又自為文以祝神,因出私俸修廟之壞隳,加置土偶人馬,垣墉之畫繪者一皆新之,大設樂以享神,自舉襟袖以舞。”“吳越之俗尚鬼,民有病者不謁醫(yī)而禱神,余懼郡人聞余感夢之事而為巫覡之所張大,遂悉紀其事,與祝神之文刊之于石,因欲以權道化黎甿,使其知神雖福人,終假醫(yī),然后能愈其疾耳。”[15]按照他的意思,生了疾病,看醫(yī)生是必然的,但同時要向神祈福。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是兩者都會兼顧,既就醫(yī),又要信巫信神。
所以唐代有一些人在信醫(yī)信巫中來回搖擺,有時相信醫(yī),有時相信巫,更有些人得了病醫(yī)、巫都信。唐初傅奕,“生平遇患,未嘗請醫(yī)服藥,雖究陰陽數(shù)術之書,而并不之信”[3]2717。他不看醫(yī)生的做法,時人稱他為“縱達”,意謂看得開,說明不請醫(yī)服藥的做法并不是士大夫中的主流。不過,唐代也有很多人在醫(yī)藥無法治愈疾病時,在內(nèi)心深處會傾向巫術,有些人認為巫術對治病還是有些用處的。如泉州晉江巫陳寨,“為人治疾多效者”[11]57。也許巫掌握了一定的治病技術,或多或少懂一些醫(yī)療方法。當時有很多人是醫(yī)藥和巫術、宗教祈禱兼信,幾者聯(lián)合運用,只要能治好病,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五代蜀國眉州下方壩一戶人家,“夫妻皆中年,唯一男既冠,忽患經(jīng)年羸瘠。日加醫(yī)藥,無復瘳減。父母遂虔誠置《千金方》一部于所居閣上,日夜焚香,望峨眉山告孫真人禱乞救護”[16]30。先是用藥,但藥治無效,于是焚香求孫真人救護。
其二,唐代總體上是個缺醫(yī)少藥的時代。唐德宗貞元年間(785—805年),談到頒《廣利方》的原因,是“或僻遠之俗,難備于醫(yī)方;或貧匱之家,有虧于藥石。失于救療,遂至傷生”[17]。邊遠地區(qū)不可能有完備的醫(yī)療體系,很少有醫(yī)護人員,貧窮人家請不起醫(yī)生,因而只能靠醫(yī)方自行解決生病問題。中唐李德裕任浙西觀察使,他看到的仍然是:“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厲疾者,舉室棄之而去。”[3]4511一些邊遠地區(qū)和山區(qū),大多是“絕無醫(yī)人”“病無與醫(yī)”④。百姓們連正常的生活都很艱難,自然是很少會請醫(yī)服藥。即使在城市,哪怕是在長安這樣繁華的城市,醫(yī)者數(shù)量和總?cè)丝诘谋壤彩鞘值偷模⒉荒苡行У刂尾【热恕?/p>
三、知疾深淺:醫(yī)者對民眾就醫(yī)服藥的影響
各級官方醫(yī)學校培養(yǎng)的醫(yī)學生,一般而言最后都在官方機構中任職。就民間而言,醫(yī)者的來源呈現(xiàn)多樣性,他們并非一定要經(jīng)過醫(yī)學校的培養(yǎng),有些可能是醫(yī)學世家,接受了家學教育;有些在自我摸索中成名成家,自學成為名醫(yī)。學者認為六朝以后,隨著醫(yī)藥世家的不斷涌現(xiàn),醫(yī)學的家學傳授是當時社會上醫(yī)者增多的重要原因。范家偉[18]、于賡哲[19]等先生就這個問題展開過討論,在此我們不作贅述。醫(yī)者的增多,自然為百姓看病帶來方便,因而民眾對看病服藥觀念的改變實際與醫(yī)者有很大關系。
唐代醫(yī)者的種類較多,他們?yōu)槊癖姷木歪t(yī)帶來了不少方便。比如部分宮內(nèi)醫(yī)官有時會以個人身份幫普通人治病。鄭云逵與王彥伯相鄰而居,兩位都是有一定專長的醫(yī)生,其中王彥伯是尚藥供奉,結(jié)果碰到了巧事:“嘗有客求醫(yī),誤造云逵,診曰:‘熱風。’客又請藥方,云逵曰:‘藥方即不如東家王供奉。’客驚而去。”[12]217病人跑錯了一戶人家,來到了王彥伯的隔壁。也就是說,醫(yī)官平時在家里會替人診病開方。有一朝士身體不舒服,去找尚藥局奉御梁新,梁新一看就說:“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梁新的意思是為什么不早點來看啊,現(xiàn)在風疾已深,沒辦法治了。朝士一聽嚇得沒命,策馬回家[7]123。朝士是以個人的身份找梁新,而作為醫(yī)官,梁新可以替人診疾,并沒有因為自己的身份受到限制。
各地似乎都有一些名醫(yī),一般都有一手絕活,他們開診治病,產(chǎn)生了很大的個人影響。開元中,“有名醫(yī)紀明者,吳人也,常授秘訣于隱士周廣,觀人顏色談笑,便知疾深淺,言之精詳,不待診候。上聞其名,征至京師令于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驗焉”[20]。其實這位紀明在診病時特別會觀察人的面部,從臉上看出一個人是否身體健康。因為他的這種觀察成功率較高,他就成了名醫(yī),被征召到掖庭宮替皇帝的后宮妃子診病。
替民眾診病的一般以民間醫(yī)者為多,在一些城市里,民間醫(yī)者的數(shù)量很多。一些醫(yī)者是地方上的名醫(yī),通過平時的診病傳出了名聲,并且有一定的醫(yī)治專長。有些病比較復雜,沒有一定的技術專長的確還無法治療。崔慎由為浙西觀察使,“左目眥生贅,如息肉,欲蔽瞳人,視物極礙,諸醫(yī)方無驗”。一天,淮南判官楊員外牧“自吳中越職”,談起揚州有姓穆的善醫(yī)眼,于是崔慎由“請遺書崔相國鉉,令致之”。幾天后,崔鉉回信說:“穆生性粗疏,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審,勝穆甚遠。”于是譚簡來到浙西,看了崔慎由的眼睛,說:“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于中,則必效矣。”崔慎由說:“如約,雖妻子必不使知。”譚簡說:“須用九日,晴明,亭午于靜處療之。若其日果能遂心,更無憂矣。”九天后,崔慎由“惟語大將中善醫(yī)者沈師象,師象贊成其事。是日,引譚生于北樓,惟師象與一小豎隨行,左右更無人知者”。手術開始,“譚生以手微捫所患,曰:‘殊小事耳。’初覺似拔之,雖痛亦忍。又聞動剪刀聲。白公曰:‘此地稍暗,請移往中庭。’象與小豎扶公而至于庭,坐既定,聞櫛焉有聲。先是,譚生請好綿數(shù)兩,染絳,至是,以絳綿拭病處,兼傅以藥,遂不甚痛。譚生請公開眼,看所贅肉,大如小指,豎如干筋,遂命投之江中,方遣報夫人及子弟”。從這段描述來看,是動了一個眼睛的小手術。手術后,譚簡馬上“以狀報淮南”,崔鉉很緊張,回信說:“自發(fā)醫(yī)后,憂疑頗甚,及聞痊愈,神思方安。”[21]這種動剪刀割眼睛上贅肉的手術,在當時來說是比較難做的,而且術后還要注意消炎,所以從揚州找了專科醫(yī)者越江來到潤州。因為病人是重要的官員,所以才這樣興師動眾。
盡管不在官方體制之內(nèi),但唐代很多醫(yī)者的診治水平也是很高的,有些人還有特殊的技能。比如有一少年眼中常常會看到一面小鏡子在晃動,醫(yī)者趙卿診斷,“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于閣子內(nèi),且令從容,俟客退后方得攀接。俄而設臺子,止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中久候不至,少年饑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這時趙卿出來對他說:“郎君吃膾太多,非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饑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乃權誑也,請退謀餐。”[7]124在不知不覺中,他讓少年服下了食用醋,醫(yī)治好了他的病。在這個病例中,趙卿掌控了病者的心理活動,以技巧使病人飲用了醋,達到了治療效果。針灸亦有不少高手。甄權特別擅長針灸,狄嵚苦風患,“手不能引弓”,甄權對他說:“但將弓矢向垛,一針可愈矣。”于是在他的肩隅一穴位扎一針,“實時能射”[22]100。雖說宋人的記載有點神,不過的確可以說明扎針的效果特別明顯。
有一些醫(yī)者沒有太大名聲,只能在市里擺攤,豎個榜做廣告,在城市熱鬧地段設攤替人看病,但這種比較接地氣的醫(yī)者是普通民眾最方便找到的,他們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城市的普通人群。鄜州馬醫(yī)趙鄂新到京都,于通衢自榜姓名,云“攻醫(yī)術”,想替人看看小毛病,混口飯吃。有一得病朝士看到趙鄂,并不抱什么希望,隨便一問,“趙鄂亦言疾已危,與梁生所說同”。趙鄂轉(zhuǎn)而一想,說:“只有一法,請官人剩吃消梨,不限多少時,咀龁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朝士一聽,馬上策馬回家,“以書筒質(zhì)消梨,馬上旋龁”。此后十多天,他只吃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病竟然好了[7]123。趙鄂豎榜治病,應是當時一些民間醫(yī)生普遍都采用的方法。
佛道兩教中有很多人潛心研究醫(yī)學,他們對醫(yī)療服務觀念的傳播功不可沒。廣州監(jiān)軍吳德墉離開京師時,兩腳蹣跚,三年后回來,“足病復平”。唐宣宗問他怎么好的,他說是羅浮山人軒轅集醫(yī)治的。宣宗此時比較相信道教,于是把山人請到京師,還想授官[12]258。羅浮山人治病應該是有一套方法的,監(jiān)軍能夠請他治療,說明他在廣州地區(qū)已有不小的名聲。
總體上說,盡管人們對診病有很大的需求,但醫(yī)者傳統(tǒng)上屬方伎之類,地位并不是太高,離社會上層普遍的尊重還有一些距離,但這恰恰說明他們在社會基層很有市場,在滿足普通人群的醫(yī)療需求方面他們做出了巨大貢獻。《唐語林》談到柳仲郢任鹽鐵使時,奉敕要給醫(yī)人劉集一場官。劉集“醫(yī)行閭閻間,頗通中禁,遂有此命”,在民間和禁中都行醫(yī),可能醫(yī)技不錯,宣宗皇帝才有這個任命。柳仲郢手疏執(zhí)奏曰:“劉集之藝若精,可用為翰林醫(yī)官,其次授州府醫(yī)博士。委務銅鹽,恐不可責其課最。又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臣未敢奉詔。”如果醫(yī)術好,就給個翰林醫(yī)官或醫(yī)博士,而鹽鐵是國家的經(jīng)濟命脈,而且鹽鐵場中所擔任的是小官,劉集沒搞過經(jīng)濟,鹽鐵場官這種低級官位,對他來說沒有什么意思。于是宣宗御筆批給劉集絹百匹,“放東回”[12]44。表面上柳仲郢好像說得很有道理,但實質(zhì)上是對醫(yī)人的一種輕視。《通鑒》也談到此事,司馬光干脆稱劉集是“閭閻醫(yī)工”,胡三省更說劉集既無職于尚藥局,也不待詔于翰林院,與官方無涉,只是“以醫(yī)術自售于閭閻之間”[23]8057-8058,對民間醫(yī)工的口氣是不以為然的。
即使到了五代后唐莊宗時期,人們?nèi)杂X得醫(yī)者低人一等。劉后生皇子繼岌,“后父劉叟以醫(yī)為業(yè),詣鄴宮自陳。后方與諸夫人爭寵,恥為寒族,笞劉叟于宮門”。后唐莊宗“好俳優(yōu),宮中暇日,自負藥笈,令繼岌攜敝蓋相隨,自稱劉山人求訪女,后大怒,笞繼岌”[22]120。《北夢瑣言》記述這件事時,說莊宗“自負蓍囊藥篋,令繼岌破帽相隨,似后父劉叟以醫(yī)卜為業(yè)也”[7]190。醫(yī)者不但只是為人醫(yī)治疾病,還兼做占卜,徒弟一副落拓寒酸打扮,這大體上能反映出民間醫(yī)者真實的社會地位,而從另一個側(cè)面看,他們的服務對象主要是社會下層民眾。
當然,民間醫(yī)者存在的問題很多。如因為社會對醫(yī)者的需求,使醫(yī)者能獲得較大經(jīng)濟利益,所以醫(yī)者隊伍里混進了不少貪圖錢財?shù)娜耍t(yī)技水平不高,錢是照收不誤。后人就談道:“醫(yī)之于人,功次天地。其間濫謬盜名取貲,無功有害,藥乎藥乎,謬劑而已。”[24]49只是想著病人家的錢財,而不會醫(yī)治,開出的藥方根本和病情不相符。但我們也從中可以看到,普通人得病后對醫(yī)療診治的渴望。
也有的醫(yī)者會過度治療。其時治療診斷,不少人比較相信針灸:“凡病膏肓之際,藥效難比,針灸之所以用也。針長于宣壅滯,灸長于氣血,古人謂之‘延年火’,又曰‘火輪三昩’。”針灸可以起到藥物所不具備的效果,對于宣泄壅滯作用極大。正因為如此,“今人有病必灸,亦大癖也”[24]52,一旦有什么問題,醫(yī)者就給人針灸,成了一大癖好,實際上是一種過度治療。所以社會上流“不服藥勝中醫(yī)”,此話雖然不一定全對,但“疾無甚苦,與其為庸醫(yī)妄投藥反敗之,不得為無益也”[25]。如果過度治療,或者碰上庸醫(yī),反而會使病人受害。
總體來看,唐、五代時期醫(yī)者數(shù)量增多,社會各個層面都有很多醫(yī)者的存在,他們滿足著不同層次百姓的醫(yī)療需求。其中有些醫(yī)者的技術很高,有些醫(yī)者技術全面,雖不一定很專深,但在一般疾病的治療方面能滿足社會需要。從這方面來說,民眾就藥服藥觀念的形成,與醫(yī)者數(shù)量增多、技術提高有密切關系,這是唐、五代時期醫(yī)學發(fā)展到一定高度出現(xiàn)的結(jié)果。
四、君子之存心:民眾就醫(yī)服藥觀念形成的原因
對唐、五代時期的多數(shù)人來說,已形成生病后應該就醫(yī)的觀念。那么,為什么能在這個時候社會上普遍形成病后就醫(yī)觀念?或者說形成這種觀念的原因是什么?
一是與當時政府和士大夫們的大力推廣和提倡有關。政府設立醫(yī)學校,培養(yǎng)醫(yī)學生,掌各地巡療,從制度上提倡醫(yī)學,而且還不斷頒布藥典藥方,傳播醫(yī)學知識,這些前人已多有研究,我們不作過多論述。從士大夫的角度而言,他們?yōu)閭鞑メt(yī)學知識做出了很大貢獻。比如陸贄在政治生涯的最后時期,被貶忠州,“家居瘴鄉(xiāng),人多癘疫,乃抄撮方書,為《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于代”[3]3818。對陸贄這樣做的原因,后人評論說:“陸宣公在忠州,裒方書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禍,蓋君子之存心,無所不用其至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yī),非惟衛(wèi)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恥言之。近時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驗方,流布甚廣,皆仁人之用心。”[26]自唐入宋,士大夫傳播醫(yī)學知識不遺余力,他們?nèi)屎裼眯模氡M各種辦法讓老百姓積極就醫(yī)治療,通過撰寫和傳播醫(yī)方使人們能抓藥救治病人。
隨著醫(yī)學知識的普及,知識階層中很多人或多或少地掌握了一部分醫(yī)學知識。比如吳人茹子顏,“以明經(jīng)為雙流尉。頗有才識,善醫(yī)方,由是朝賢多識之”[27]。這位官員通過科舉進入仕途,但他“善醫(yī)方”,懂醫(yī)學,是能夠治療一些疾病的。地方官員也力圖把醫(yī)學知識傳播給整個社會。鄧景山任揚州節(jié)度使,“有白岑者,善療發(fā)背,海外有名,而深秘其方,雖權要求者皆不與真本”。有醫(yī)療技術,卻秘不授人。恰巧碰到白岑為人追訟,“景山故令深加按效,以出其方。岑懼死,使男歸取呈上。景山得方,寫數(shù)十本,榜諸路衢,乃寬其獄”[28]。通過威嚇使白岑拿出了方子,然后向全社會傳播。
一些官員和士人盡力禁止巫術,努力把人們引導到醫(yī)藥治療上來。羅珦嘗刺廬、壽二州,“自壽以治行第一,就加御史中丞,入為司農(nóng)卿、京兆尹”,在廬州時,“病者舍醫(yī)事淫祀,公皆去其弊”。其時“民間病者舍醫(yī)禱淫祀”,不看醫(yī)生看巫婆,所以羅珦“下令止之”[29]。他在廬州前后有七年,推動民間有病找醫(yī)生觀念形成是他重要政績之一。可知,一些人得病之后,的確不是先找醫(yī)生而是相信巫術和祈禱,但唐代的地方官在努力推動人們養(yǎng)成就醫(yī)習慣,改變傳統(tǒng)的一些觀念和做法。
二是和城市內(nèi)的藥材銷售方便和藥材煉制技術提高有關。因為就醫(yī)服藥的需求量大增,人們對藥材的需要量也在增加,因而就醫(yī)服藥觀念的流行和藥材銷售其實是相互作用、互為因果的。城市里有專門的藥肆出售藥材,藥材是各個市場上經(jīng)銷的重要商品。李肇《國史補》談到宋清賣藥長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貶,輒賣藥迎送之”[30]。張易在洛陽,常與劉處士一起游玩,“嘗賣藥于市,市中人既不酬直,又大罵劉”[11]114。東西兩都的市場上,藥材是重要的商品。其時人們喜食丹藥補身體,因而佛道的丹藥十分吸引人,常成為市場上的商品之一。章全益“于成都府樓巷舍于其間,傍有丹灶,不蓄童仆,塊然一室。鬻丹得錢,數(shù)及兩金即刻一像”。一般的仙人如果有黃白之術,就會想到賺錢了:“點水銀一兩,止一兩銀價。若丸作三百粒,每粒百錢,乃三十千矣。”因此宋人認為,出售丹藥“其利溥哉,但所鬻之丹亦神矣”[7]221。
五代蜀國后期劉蟾攝成州長道縣主簿。宋朝克復蜀國后,他“匿于川界貨藥,改名抱一。開寶中,于青城鬼城山上結(jié)三間茅屋,植果種蔬,作終焉之計。每一月兩三度入青城縣貨藥,市米面鹽酪歸山”[16]32。川蜀之地,藥材貿(mào)易十分興盛,青城縣市中,自然是有藥材交易,而且是市場上的大宗商品。這里說的雖然是宋初的事情,但五代末與宋初這短短的時期內(nèi)應該不會有太大變化。如成都府城有“鬻龍骨叟,與孫兒輩將龍骨齒角頭脊之類凡數(shù)擔,至暮貨之,亦盡”。其龍骨來自去府城七十余里的一個山洞里,“齒角頭足皆有五色者,有白如綿者,有年深朽腐者,大十數(shù)丈,小三五丈。掘而得之甚多。龍之蛻骨與蟬蛻無異”[16]67。估計可能是一大堆恐龍化石,被這戶人家運了出來銷售到市場上。南唐陳陶退隱在西山,“先產(chǎn)藥物僅數(shù)十種”。北宋開寶中,陳陶“角發(fā)被褐,與一煉師舁藥入城鬻之,獲資則市鲊就爐,二人對飲且啖,旁若無人”[31]。在山里采集藥材后到城市出售,這是他生活的主要來源。城市里有專門的藥肆出售藥材,病人可以直接到藥肆中付錢取藥。
一些藥材出產(chǎn)較為豐富的地區(qū),有專業(yè)藥材交易市場。高承《事物紀原》卷八《藥市》云:“唐王昌遇梓州人,得道,號易玄子,大中十三年九月九日上升。自是以來,天下貨藥輩,皆于九月初集梓州城,八日夜于都院街易玄龍沖地,貨其所賚藥,川俗因謂之藥市,遲明而散。”宣宗年間在梓州城出現(xiàn)了藥市。當然這個藥市是短期內(nèi)出現(xiàn)的還是以后一直有的,今天已很難搞清,但可以看到在巴蜀山區(qū),因為藥材出產(chǎn)豐富,形成了以藥材交易為主的集市,地方特色十分明顯。
除藥材外,市場上還將藥煎熬后合成藥丸。藥丸的制作有一定的技術要求,唐末,有位鐘大夫說在湘潭時,他和幾個商人在岳林寺設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藥后,要退即飲海藻湯。或大期將至,即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須指揮家事,以俟終焉。遂各奉一緡,吞一丸。他日入蜀,至樂溫縣,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樂溫,得與話舊,且說所服之藥大效。無何,此公來報肋下痛,不日其藥果下,急區(qū)分家事,后凡二十日卒。某方神其藥,用海藻湯下之,香水沐浴卻吞之。昨來所苦,藥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吃了這藥之后,這位鐘公“面色紅潤,強飲啖,似得藥力也”,說明寺僧合成的藥確有效果。做成藥丸出售,一些寺廟似乎比較拿手,技術上都有一套。成都覺性院,“有僧合此藥賣之,人多服也”[7]130,說明社會上吃藥丸治病是習以為常的。
一些賣藥者同時行醫(yī),藥和醫(yī)有機結(jié)合在一起。唐代末年,成汭鎮(zhèn)江陵,溫克修替成汭管藥庫。后來形勢發(fā)生變化,克修流落渚宮,“收得名方,仍善修合,賣藥自給,亦便行醫(yī)”[7]212。他收集到了一些藥方,就合成各種藥物,再出售,同時替人行醫(yī)治療。王彥伯的醫(yī)術十分著名,他常常“列三四灶,煮藥于庭。老幼塞門來請”。彥伯指著幾個灶頭上的藥說:“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飲此。”病人們根據(jù)他的話,“皆飲而去”[12]300。
病人可以直接到藥肆中付錢取藥。建康人杜魯賓在都城開藥肆“以賣藥為事”,有個豫章人“恒來市藥,未嘗還直”,還欠著不少錢。一天,此人又來,“市藥甚多”[11]119。藥肆里的藥材應是收購后再加工出售。《續(xù)玄怪錄》談到揚州北邸有賣藥王老家[32]114,應該是一個比較有影響的藥店。天寶末年,有一姓張的給姓李的一席帽,說:“可持此詣藥鋪,問王老家,云張三令持此取三百千貫錢。”又說此藥鋪為藥行[32]158。
當然,唐、五代時期人們病后就醫(yī)觀念的形成,畢竟還有其他一些因素。如整個社會文化知識的傳播,人們的科學素質(zhì)在不斷提高,對醫(yī)藥認識的深化是必然的。再如隨著城市經(jīng)濟的發(fā)展,人們的生活在不斷改善,唐代城市居民的生活水準在提高,很多人有余錢可以請醫(yī)服藥。
總之,從唐、五代時期普通人的角度來觀察,越來越多的人得病后會請醫(yī)者救治,會據(jù)方服藥,得病后家人對醫(yī)治越來越重視。這一切說明,唐、五代時期人們的生活質(zhì)量在不斷提高,而人的壽命也越來越長。隨著城市和商業(yè)的發(fā)展,人們就醫(yī)服藥的觀念已經(jīng)形成,并且基本普及。
注釋
①如于賡哲有《唐代疾病、醫(yī)療史初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從疾病到人心——中古醫(yī)療社會史再探》(中華書局2020年版)等論著,主要研究了唐代主要疾病、唐代官方醫(yī)療機構、醫(yī)人水平、醫(yī)籍受眾、藥材產(chǎn)地與市場、疾病觀、醫(yī)者形象、醫(yī)學教育體系、瘟疫等問題。②于賡哲認為太醫(yī)署、尚藥局、藥藏局三大中央醫(yī)療機構,服務的對象是皇室、官僚貴族、宮廷、禁軍、官奴婢等(《唐代疾病、醫(yī)療史初探》第二章第一節(jié),第26—27頁)。③黃正建等對《天圣令》復原唐《醫(yī)疾令》第三十條說:“諸州醫(yī)博士、助教,于所管戶內(nèi)及停家職次內(nèi),取醫(yī)術優(yōu)長者為之。軍內(nèi)者仍令出軍。若管內(nèi)無人,次比近州有處兼取。皆州司試練,知其必堪,然后銓補,補迄申省。”(黃正建等:《天一閣藏明鈔本天圣令校證》下冊,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78頁)也就是說,各州的博士、助教是在各州中挑選有醫(yī)術的人充當,這些人有的可能并沒有受過嚴格訓練,只是民間的醫(yī)者。中唐時期魏光乘“好題目人”,即根據(jù)人的特點起綽號,如把拾遺蔡孚說成“小州醫(yī)博士詐諳藥性”(《朝野僉載》卷四,《全唐五代筆記》第一冊,第189頁)。一些州的醫(yī)博士其實只是知道點藥性而已,有的甚至連藥也不懂。《北夢瑣言》卷五《薛少師拒中外事》談到唐末蜀中的醫(yī)官楊仆射“殊不識字”,所以病人說“安可以性命委之乎”,不肯吃楊醫(yī)官的藥一定要到長安看病(《北夢瑣言》卷五《薛少師拒中外事》,《全宋筆記》第一編第一冊,第64頁)。④于賡哲在《唐代疾病、醫(yī)療史初探》第二章第二節(jié)“地方醫(yī)療機構的使命和局限性”(第29頁)談到了這一問題,引述了多條發(fā)生在黔中、崖州、睦州、汀州、海南等地的資料,說明在邊遠地區(qū),唐代幾乎是沒有醫(yī)藥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