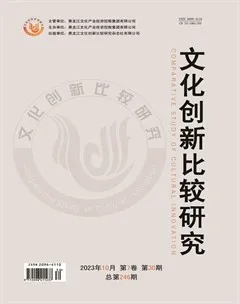石黑一雄《長日留痕》的創(chuàng)傷書寫
劉穎昕
(海南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海南海口 571158)
《長日留痕》是2017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獲得者、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的第三部長篇小說。作品于1989年獲得布克獎,被譽為英國戰(zhàn)后文學(xué)最優(yōu)秀的作品之一。作為英國文壇“移民三雄”之一,石黑一雄善于將西方元素與日本元素巧妙結(jié)合,創(chuàng)作出風(fēng)格別致的國際化小說。在《長日留痕》中,他以現(xiàn)實主義手法描繪了英國的政治和文化及個體思想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進程中的變化,以質(zhì)樸、細膩且典雅的敘事風(fēng)格,通過男管家的主觀敘事視角,講述了一段為期6天的旅程,并交叉著他對過往人生和職業(yè)生涯的追憶與思考。在管家史蒂文斯零散且不可靠的回憶敘述中,揭示個人經(jīng)歷對個體的創(chuàng)傷及在大英帝國衰落現(xiàn)實中的集體創(chuàng)傷。
“創(chuàng)傷”一詞來源于希臘語中的“傷口”,后被應(yīng)用于心理創(chuàng)傷。而弗洛伊德、詹尼特等人對創(chuàng)傷心理機制的研究具有開拓性。創(chuàng)傷記憶作為跨學(xué)科研究的焦點,如今也作為一種研究方法被廣泛應(yīng)用在文學(xué)批評中。“籠罩在現(xiàn)代文學(xué)中的人物心理的分裂、疏離感、異變和價值觀的沖突等,也從另一個側(cè)面透露了創(chuàng)傷記憶的心理陰影。”創(chuàng)傷是石黑一雄作品中永恒不變的主題之一,美國著名作家喬伊斯·卡羅爾·歐茨曾經(jīng)評價:“石黑一雄是我們當中最擅長闡釋‘失去’這一主題的詩人。”[1]正如石黑一雄所說“我所寫的是關(guān)于個體如何面對痛苦的記憶”[2]。《長日留痕》 以日記體的形式展開敘述,“日記的形式具有一個額外的優(yōu)勢,那就是間歇性時間結(jié)構(gòu)。作為分散微小碎片的集合體,日記是一種反映自我意識的斷斷續(xù)續(xù)、自相矛盾、支離破碎的理想形式”[3]。石黑一雄以時間順序建構(gòu)敘事框架,同時將對過去的回憶和現(xiàn)實并置交叉,逐步完成了對史蒂文斯自我的重識和內(nèi)心的救贖。對于史蒂文斯而言,對過往經(jīng)歷的回憶,是他慰藉內(nèi)心的一種方式,但也是他掩蓋過去的借口。因為在他閃爍其詞的措辭和辯白中,讀者能夠很快捕捉到敘述者在敘述過程中的不可靠性。而這種不可靠的回憶敘述也成為史蒂文斯創(chuàng)傷經(jīng)歷的佐證。
1 史蒂文斯的創(chuàng)傷表征
創(chuàng)傷事件會使人形成創(chuàng)傷記憶,而人對身份的認同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敘述與記憶實現(xiàn)的。作為服務(wù)于達林頓府這樣顯赫門第的管家,史蒂文斯畢生的職業(yè)追求就是成為一位“與其地位相稱的尊嚴”的管家。而他一味沉浸在對職業(yè)信仰的追求,過分壓抑和逃避了對親情與愛情情感的表達,最終導(dǎo)致了個人尊嚴的消盡和自我身份的缺失。
1.1 來自家庭的原始創(chuàng)傷
史蒂文斯對于自我情感的克制與壓抑,與他原生家庭中情感的缺失不無關(guān)聯(lián)。弗洛伊德曾在其心理分析理論中提到,成年之后很多不合乎常理的行為大多是因童年創(chuàng)傷的影響。在沒有遭受過一些災(zāi)難性事件的前提下,諸如史蒂文斯的這種創(chuàng)傷可以歸結(jié)為結(jié)構(gòu)性創(chuàng)傷。首先,在史蒂文斯的回憶敘述中,未曾提到過自己的母親,自童年以來母愛的缺失可能對他的心理產(chǎn)生了很深刻的影響;其次,父親對于史蒂文斯兄長死亡的冷漠,史蒂文斯的兄長死于南非戰(zhàn)爭,可悲的是這次陣亡源于作戰(zhàn)指揮官的嚴重失職。事件發(fā)生的10年之后,同樣作為管家的老史蒂文斯竟恪守職責(zé)地去侍奉這位前來拜訪的指揮官。史蒂文斯更是辯解道,父親雖然對指揮官將軍十分憎恨,但卻壓抑了自己的情感,表現(xiàn)得過于冷淡和麻木。死亡是最極端的創(chuàng)傷經(jīng)歷,情感的麻木、漠然是受創(chuàng)后的基本表現(xiàn),受創(chuàng)者表面上平靜淡然,實際是一種被動的屈從。而這種冷漠也同樣影響著史蒂文斯面對至親之死創(chuàng)傷時的態(tài)度。
相較于母愛的缺失和兄長的死亡,疏離怪誕的父子關(guān)系更是加劇了史蒂文斯的創(chuàng)傷。老史蒂文斯曾經(jīng)也是一位工作卓越的管家,從史蒂文斯小時候開始父親就詳述著其作為管家的經(jīng)歷:一位侍奉主人旅居印度的管家,在注意到餐桌下面蹲著的老虎時,卻依舊淡定自若地表現(xiàn)出與身份相稱的職業(yè)素養(yǎng)與尊嚴。父親一直期望用強大的超我無意識甚至犧牲本能與自我,為史蒂文斯樹立職業(yè)典范,也將自己偏執(zhí)的觀念灌輸給他。這直接導(dǎo)致了父子倆除了工作無話可談,甚至父親在彌留之際依舊給予管家工作以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忽視了自己的生命和父子情。面對難得抽空來探視的史蒂文斯,父親的談話內(nèi)容卻是“樓下的一切順利嗎”。當父親在去世前對兒子表露真心時說道,“我為你感到驕傲。真是個好兒子。但愿我對你曾經(jīng)是位好父親。我想我并不是”,而史蒂文斯給出的回應(yīng)竟是 “抱歉我特別忙,我們可以明日再談”。可見,父親的身體狀況已經(jīng)不能影響到其對工作的執(zhí)著與忠誠。究其原因,無疑是老史蒂文斯將自己偏執(zhí)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強加于他的兒子,以父親為職業(yè)標桿和作為“偉大管家的尊嚴”致使史蒂文斯喪失了主體性,受到來自父親潛移默化的影響。要成一位符合職業(yè)原則的完美管家,就需要無限接近于父親的理想與標準,放棄對個人意愿的服從與堅守。內(nèi)化對欲望客體的尋找,并成為欲望的對象。
1.2 盲目追求職業(yè)尊嚴的個體創(chuàng)傷
史蒂文斯面對家庭關(guān)愛缺失的麻木及父親的專制,使其埋下了創(chuàng)傷的種子,也直接導(dǎo)致了他在事業(yè)和愛情中留下無法彌補的悲劇。職業(yè)尊嚴是史蒂文斯畢生都在追尋的目標,但他的追求終究是虛妄的,不加辨別地執(zhí)行達林頓勛爵的各種命令。小說中有一處細節(jié):達林頓勛爵因為擔心影響府邸與德國人的外交關(guān)系而要求開除兩個猶太女仆,史蒂文斯意識到這會是一個錯誤的決定,但卻依舊被“我對這種情況下應(yīng)該履行的職責(zé)是非常清楚的” 的信念所左右,即使面對肯頓小姐的強烈反對,也未能阻止其開除了她們。他更是在此次事件之后提醒肯頓小姐“我們的工作職責(zé)不允許我們只顧及自己的癖好和個人情感,而是要遵從主人的意愿”。史蒂文斯在對自我身份的價值追求中淪為對主人唯命是從的仆人,將完成主人的任務(wù)視為對自我肯定的標準。
1923年,達林頓勛爵府上舉行了一場盛大的非正式國際會議,史蒂文斯將其視為自己人生和事業(yè)的轉(zhuǎn)折點。而就在會議最重要的一個晚上,老史蒂文斯突發(fā)疾病與世長辭,聞訊趕來的史蒂文斯并沒有為父親悲傷,而是出奇地將關(guān)注的重心聚焦在女廚師莫蒂默太太圍裙上散發(fā)出的濃重的烤肉氣味。父親的離去沒有影響到史蒂文斯對管家職業(yè)的堅守,在他眼中注視的是衣冠不整的莫蒂默太太,嗅到的是與死亡氣息相悖的“烤肉味”。與此同時對“職業(yè)精神” 的過分追求,讓史蒂文斯產(chǎn)生了扭曲的價值判斷,他曾經(jīng)認為達林頓勛爵為世界的和平與正義奉獻了自己的一生,那么為主人服務(wù)的管家也在間接地為整個世界服務(wù)。而史蒂文斯對主人和畢生追求事業(yè)的所有尊嚴與幻想都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主人達林頓勛爵被指控犯下了叛國罪郁郁而終后而破滅,釀成了難以磨滅的創(chuàng)傷。
對于兩性情感的壓抑和逃避是史蒂文斯創(chuàng)傷經(jīng)歷的又一表征。肯頓小姐是達林頓府上出色的女管家,她工作認真負責(zé)且性格活潑而陽光。肯頓小姐曾多次將自己親手采摘的鮮花送到史蒂文斯工作居住的配膳室,以表達對他的關(guān)心和好感,但卻被史蒂文斯無情地拒絕了,他將肯頓小姐的行為視為一種威脅,因為他始終在堅持著作為一名稱職管家的原則,杜絕與肯頓小姐產(chǎn)生除工作之外的關(guān)聯(lián)。在屢次向史蒂文斯示愛而無果后,肯頓小姐毅然選擇答應(yīng)他人的求婚,離開了達林頓府。在史蒂文斯回憶的敘述中,曾多次提及數(shù)年后肯頓小姐寫給他的信,他總是拿出來反復(fù)閱讀沉湎于往事之中。一直以來他都在隱藏壓抑逃避著對肯頓小姐的感情,去維護著他一直堅守的職業(yè)尊嚴。因為男女管家相好在他看來是私通,會被趕出達林頓府,“私通事件對府內(nèi)井然的秩序是一種極為嚴重的威脅”。在這次為期6 天旅程的最后,史蒂文斯特意去拜訪了肯頓小姐,本想邀請其回歸達林頓府繼續(xù)工作,卻得知肯頓小姐已然決定回到丈夫和女兒身邊繼續(xù)生活,史蒂文斯發(fā)出了“我的心行將破碎”的感嘆,這也是他壓抑多年首次向肯頓小姐表達愛意,然而一切都為時已晚。史蒂文斯為了追求管家的“尊嚴”,抵制住了兩性關(guān)系中的情感誘惑。對于童年受創(chuàng)者來說,分裂是人格構(gòu)成的主要原則,意識的分裂,阻擾了正常的知識、記憶、情感狀態(tài)與生理經(jīng)驗的統(tǒng)合;自我觀感的分裂,阻擾了自我認同的統(tǒng)合。因此,史蒂文斯無法像正常人那樣與他人建立起親密的關(guān)系[4]。愛情帶來的創(chuàng)傷是不可見的,但卻成為史蒂文斯內(nèi)心深處無法彌合的傷痕,終生未娶的他放棄了擁有愛情、家庭生活的權(quán)利,也為自己書寫了痛苦一生的愛情悲劇和創(chuàng)傷記憶。
1.3 歷史變遷中的社會性創(chuàng)傷
史蒂文斯回憶里書寫的不僅是個人的創(chuàng)傷,也與二戰(zhàn)后大英帝國的衰落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是一種歷史的創(chuàng)傷。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曾經(jīng)的“日不落帝國”——英國逐漸喪失了世界霸主的地位,一部分英屬殖民地也開始取得屬地自由權(quán)。昔日的英國貴族走向沒落,達林頓府也未能幸免。二戰(zhàn)后,達林頓勛爵被定為親納粹派,被冠以叛國罪的罪名,臭名昭著,最后郁郁而終。而這一系列的社會歷史性事件摧毀了史蒂文斯一直堅守的尊嚴和精神信仰,曾經(jīng)的“輝煌成績”變成了他的恥辱,在人生暮年體驗了生存意義的缺失和虛無感。府邸易主后,史蒂文斯被作為“包裹的一部分”被轉(zhuǎn)交給了新主美國人法拉戴先生。法拉戴先生代表著崇尚自由民主和開放的美國,期盼弱化與史蒂文斯主仆之間的階級身份差異,但史蒂文斯一時間無法適應(yīng)美國文化,加劇了他的失落和痛苦。“他的作用常常是映射一段歷史時期、其中的一些人或特定的文化、種族、性別,集體性地經(jīng)歷了巨大的創(chuàng)傷。”[5]史蒂文斯如同一個活化石見證了英國社會歷史的巨變,也映射了英國管家階層的集體創(chuàng)傷。
2 不可靠敘述與創(chuàng)傷
不可靠敘述的概念最早是由敘事理論家韋恩·布斯提出。在《小說修辭學(xué)》一書中,韋恩·布斯指出“當敘述者說話或行為符合作品的道德規(guī)范(即隱含作者的規(guī)范),敘述者是可靠的,反之,即為不可靠”[6]。《長日留痕》以主人公第一視角自傳體的敘事展開,史蒂文斯支離破碎、有時甚至相互矛盾的敘述構(gòu)成了回憶的不可靠性。而一旦回憶觸及痛苦時,史蒂文斯便會選擇性地暫停或是回避,一些評論家將其歸結(jié)為自我否定或自欺欺人。在審視史蒂文斯的敘述行為和道德選擇中,必然會發(fā)現(xiàn)其在認知上的偏差和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盡管他這么做并非出自惡意,也非有意而為之。隨著旅游進程的推進,史蒂文斯越發(fā)地陷入過去的回憶而不能自拔。作為一生忠誠服務(wù)于達林頓勛爵的管家,卻可能在過往的工作中間接地成了親納粹黨的幫兇,復(fù)雜的情緒使其背負了沉重的壓力。在史蒂文斯極力塑造的紳士風(fēng)度的外表下,是他對數(shù)十年人生過往的悲嘆與無奈。
2.1 零散的回憶
圍繞回憶的矛盾沖突來展開故事,一直是石黑一雄善用的手法,回憶既是小說的敘述形式,也是他建構(gòu)情節(jié)和主題的方式。他認為“記憶本身就是一個看待事物的透鏡”[7]。小說中提及了兩次重要的會議,1923年那次恰逢老史蒂文斯病逝,1936年的非官方會議期間肯頓小姐間接地向史蒂文斯表達了愛意,卻被冷漠回絕,不久后她便心灰意冷地離開了達林頓府。史蒂文斯一直以來對職業(yè)精神的過分追求、對達林頓勛爵的愚忠和對內(nèi)心情感的壓抑,導(dǎo)致了他冷漠和罔顧的性格。可悲的是主人公本人卻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問題,在對職業(yè)生涯的回憶敘述中,他毫不掩飾地宣稱“我主要的滿足是源于我在那些歲月里所取得的成功,而且我今天唯一感到驕傲和滿足的是我曾被賜予如此的殊榮”。面對自身的人格悲劇,作為敘述者的史蒂文斯渾然不知,而是沉浸在父親離世和肯頓小姐離開那兩晚中其承擔管家工作時的優(yōu)秀表現(xiàn),并將其視為“油然產(chǎn)生極大成就感”的職業(yè)輝煌時刻。史蒂文斯由于自身的認知局限,向讀者呈現(xiàn)著現(xiàn)實生活與過往經(jīng)歷間的不可靠敘述。
2.2 錯置的回憶
小說中,有一段對于肯頓小姐哭泣場面的敘述,而史蒂文斯卻在自己過濾式的回憶中進行了曲解。最初,他將那一晚肯頓小姐的哭泣歸因于她姑媽的離世,因為姑媽給予了肯頓小姐母親般的疼愛。史蒂文斯對于至親之死的冷漠讓他沒有對肯頓小姐產(chǎn)生憐惜,反而以更加嚴苛的標準督促她完成工作。可很快史蒂文斯又否定了自己的回憶,他更加堅信當天肯頓小姐的哭泣是因為她接受了別人求婚。回憶的模糊與不確定性印證了史蒂文斯在面對過往時的矛盾,他深知自己是有意壓抑著對肯頓小姐的情感,內(nèi)心的失落讓他刻意選擇了逃避歷史。史蒂文斯的敘述是帶有情感選擇性和過濾性的,“夸大或縮小,省略或添加,扭曲或簡化,因此歷史是被加工過的記憶”[8]。從史蒂文斯被自己改寫的記憶中,很容易捕捉到他不愿再現(xiàn)或是看不清的現(xiàn)實。
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史蒂文斯對于二戰(zhàn)期間和20世紀40年代后半期達林頓府和達林頓勛爵的去世只字未提,我們不禁要反問,他為何刻意地隱瞞了這段歷史?毫無疑問,對于他和達林頓勛爵共同經(jīng)歷的這段屈辱的歷史,史蒂文斯再次進行了選擇性的遺忘。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學(xué)》中闡明了遺忘運作的精神機制,他認為那些人們有意掩蓋而想不起來的回憶或是暫時的遺忘癥是受壓抑驅(qū)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后,達林頓勛爵的政治錯誤被揭示出來,而史蒂文斯畢生對職業(yè)的所有尊嚴和追求也伴隨著社會現(xiàn)實被無情地否定和駁斥。如果史蒂文斯在回憶敘述中承認這段歷史,就相當于承認了其服侍的主人在“世界事物”中的失敗,也同時包含了對自我的否定。弗洛伊德在對夢的解析中提到,人的心靈中存在一些被壓抑的愿望,“這些愿望屬于原發(fā)系統(tǒng),而它們的滿足會遭到繼發(fā)系統(tǒng)的反對”[9]。所以史蒂文斯采取了錯置的回憶來進行自我安慰與麻痹,不去直面歷史真相。
2.3 對主仆關(guān)系的否定
面對創(chuàng)傷歷史,施暴者可能會不自覺地對其進行否定和壓抑,或是采取某些必要的防御機制。一直以來,史蒂文斯都在竭盡所能地維護和崇尚著達林頓勛爵的完美貴族形象,認為其在人品和道德方面沒有任何瑕疵。即便是在政治錯誤被曝光之后,史蒂文斯依然辯解道:“達林頓勛爵是位具有偉大思想情操的紳士——這種情操使那些你會碰見地對他大放厥詞的人相形見絀。”史蒂文斯一邊沉浸在服務(wù)于偉大紳士的價值滿足中,卻又多次在公開場合不承認他與達林頓的主仆關(guān)系。旅途中,史蒂文斯被問訊到是否曾服務(wù)于達林頓勛爵一事,他卻用“啊,不,我現(xiàn)在受雇于約翰·法拉戴先生,這位美國紳士從達林頓家族中買下了那幢房子”的說辭予以遮掩。而面對他人的繼續(xù)追問,史蒂文斯以著急趕路為由回絕了。另一次是當現(xiàn)在的雇主約翰·法拉戴的朋友韋克菲爾德夫婦來到府邸做客時也提到了類似的問題,當時史蒂文斯依舊予以否認,他的回答也一度引起法拉戴的不解。史蒂文斯雖然矢口否認他與達林頓勛爵的主仆歷史,但越是刻意地回避就越是放大了他的窘迫與慚愧,他終于漸漸意識到自己曾傾其所有附庸于他人的人生價值不過都是自我欺騙的謊言。
3 創(chuàng)傷后的身份重構(gòu)
史蒂文斯通過回憶的敘述來揭示他曾不自知或是自我隱瞞的傷痛,宣泄了個體創(chuàng)傷。在6 天的旅程中,他找到了重塑自我和重新評價過去的契機。他開始審視自己曾經(jīng)對新主人作出的解釋“盡管并不全是假的,卻是那么令人遺憾地不充分”,或許他開始努力正視和重新思考曾經(jīng)所犯下的錯誤。旅行的第一天,在一位陌生男子的建議下,史蒂文斯爬上了一座小山,面對“數(shù)英里范圍內(nèi)最讓人心曠神怡的鄉(xiāng)村景色”,他被深深地震撼,“正是從觀看風(fēng)景的那時起,我才相信我第一次開始具有了愉快的心境,這將有利于我以后的旅行”。也正是從這一個經(jīng)歷開始,他逐漸卸下了在達林頓府馬不停蹄工作的緊迫感,石黑一雄也希望借助傳統(tǒng)英式鄉(xiāng)村美景的治愈性,讓史蒂文斯?jié)u漸走出創(chuàng)傷的陰霾。一路上,史蒂文斯遇到了很多當?shù)氐挠用瘢麄儫崆榈卣写蚪o予他幫助,甚至還邀請他加入村民們暢所欲言的日常交談中,而這一切都是他在達林頓府不曾擁有過的體驗——輕松自如的生活。著名創(chuàng)傷理論專家和治療專家德瑞·勞和朱迪斯·赫爾曼認為,創(chuàng)傷的修復(fù)需要“在關(guān)系中”完成。向一位具有同情心的傾聽者見證或講述自己的創(chuàng)傷經(jīng)歷,傾聽者可以幫助幸存者將創(chuàng)傷事件重新外化、對創(chuàng)傷經(jīng)歷進行重新評價,幫助幸存者對自己做出公正闡釋,重建正面的自我評價[10]。
小說的最后史蒂文斯遇見了一位傾聽者,并向他袒露心聲,卸下偽裝地說道:“在我侍奉他的所有的那些歲月,我堅信我一直在做有價值的事。可我甚至不敢承認我自己曾犯了些錯誤。真的——人須自省——那樣做又有什么尊嚴可言呢?”史蒂文斯過往的經(jīng)歷凝結(jié)了他的人生悲劇,而他對自我的認知和主體性的追求也在愚忠的服侍中消弭。面對史蒂文斯,陌生人勸慰他說:“那你就必須自我解脫。夜晚是一天中最美好的部分。你已干完了白天的工作。現(xiàn)在你能夠雙腿擱平來休息了,而且要享受人生。”[11]史蒂文斯在靜默許久之后終于認同了他人的忠告,決定改變自己,積極地面對易主之后全新的管家生活和余下的人生之途。父親的驟然離世和肯頓小姐遠走他鄉(xiāng)在史蒂文斯的心中留下了更多難以磨滅的傷痛,值得慶幸的是在6 天的旅行中,他終于意識到了自己對尊嚴、克制和冷漠的執(zhí)迷及它們所造成的人生遺憾。并且在對往事的回憶與反省中,認清了二戰(zhàn)后的英國社會現(xiàn)實,重視自我。二戰(zhàn)后的國民身份和大英帝國身份重構(gòu)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lián)系,在這場旅行的終點——濱海碼頭,史蒂文斯幡然醒悟。而濱海碼頭的隱喻象征著“自我與他者碰撞的閾限空間”[12],史蒂文斯在對自身由“異”趨“同”的過程中突破固有的認知框架,尋找身份認同。
有學(xué)者評價史蒂文斯的生活是無趣的、無意義的,因為他“是過去世界的幸存者。他的悲劇性在于他所依附的世界已經(jīng)消失,給予他生命意義的世界已不復(fù)存在,但他還活著”[13]。史蒂文斯的悲劇性確實受到社會歷史變遷的沉重影響,但石黑一雄賦予了其對未來的希冀和新的生命意義。勇于揭開過去的傷口,正視經(jīng)歷與傷痛,并完成自我的心理重建。正如小說《長日留痕》的名字一樣,漫漫長日已然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但史蒂文斯能做的是對往事回憶的反思、對自我的重構(gòu)和對生命意義的探索,卸下傷痛與悔恨,期待來日方長。
4 結(jié)束語
《長日留痕》用回憶的方式,對小說主人公所經(jīng)歷的事件進行了碎片化處理和選擇性闡述。石黑一雄借用一位“杰出”管家的視角審視著20世紀上半葉英國社會的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探討了尊嚴、職業(yè)倫理與個人道德判斷等一系列具有共同性的人類生存議題。石黑一雄用既幽默卻又傷感的筆調(diào),再現(xiàn)了現(xiàn)代社會對個體的壓制及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的疏離,也在批判著個人主體身份的缺失、家庭關(guān)系的不和諧及戰(zhàn)爭對平民造成的傷害等諸多現(xiàn)實問題,以獨特的創(chuàng)作和批判視角書寫著石黑一雄本人對創(chuàng)傷群體的同情與悲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