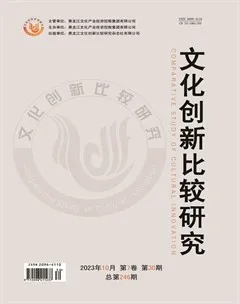中國近現代歷史教育研究的基本問題探析
高詩博,劉洋
(遼寧師范大學,遼寧大連 116000)
眾所周知,我國有著五千多年的悠久歷史,人類社會經歷了漫長的由古代到近現代的變遷,同時也在不斷進行著以歷史學為基礎的傳播活動和教育活動。中國近現代史歷史教育基本問題研究以歷史教育概念、研究對象為切入點,探析歷史教育所涉及的兩大場域及其問題。為此,本文先闡述歷史教育的概念及其所發揮的作用,再對中國近現代史歷史教育的研究對象加以分析,最后探析歷史教育所涉及的兩大場域及其問題。
1 歷史教育的概念以及歷史教育所發揮的作用
歷史教育從廣義上來說,就是以歷史為主要內容的各種學術研究活動,其對象包含社會各類群體。從狹義上來說,歷史教育是以學生為主要對象,由教師對學生采取的歷史內容為主的教育活動。歷史教育通過傳播歷史知識,開展歷史教育活動,對小至個人、大至一個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社會均有著積極的教育作用。對個人來說,能豐富知識,促進深思,提升人文素養,并以史為鑒,聯系現實,認清和實現自我,更好地實現人生價值。對民族來說,歷史教育涉及愛國主義教育,能強化民族意識,增強全民族人民的凝聚力,服務好社會及國家。對人類社會而言,既能傳承歷史,又有助于延續文明,汲取前人的經驗教訓與智慧,做具有全球意識的“地球公民”,造福人類。
2 中國近現代史歷史教育研究對象分析
歷史知識生產機制與過程,知識產品形態,歷史知識的傳播主體、傳播渠道。傳播形式及傳播受眾等內容均是中國近現代史歷史教育所要研究的對象[1]。以下從兩個方面(歷史知識生產與傳播)對歷史教育研究對象加以分析
2.1 歷史知識生產
2.1.1 生產主體
歷史知識生產經歷了從古代史官、修著史書的史家到近現代學院職業史家等生產主體變遷的過程,上述生產主體均有著職業史家這一共同點。此外,在歷史知識生產的過程中,來自社會群體中的一些非職業史家也參與其中,使職業史家不再壟斷歷史知識的生產。
2.1.2 生產機制及其過程
在古代主要通過兩種方式(官方與私人)來進行歷史知識生產,其中官方的集體修史或者是詔令修纂均以史官和官方修史機構為依托,以史學目標和官方意識形態為指導思想來進行,從而官方有著歷史知識生產的權威解釋權。私人修纂則有所不同,其主要指導思想為史學思想,主要參考依據和標準為史學、史識和史才,有更強烈的個性。發展到近代,主要生產方式演變為學院式和社會式。學院式生產追求科學性,主要依托的機構為學術機構和研究機構,表現樣態為專業論著,生產主體則是職業史家,通過專業學術刊物進行傳播,讓歷史知識的生產兼具科學性與系統性。社會式生產追求商業化、大眾化,主要依托于社會媒體如文化團體、出版機構等,知識樣態包括影視、藝術、通俗讀物等,生產主體為社會群體中的非職業史家,傳播渠道多元化,有時還會質疑和挑戰官方及學院派的權威觀點,從而推動歷史知識與觀念領域的變革[2]。由于社會生產群體存在流動性,形成了多元化的社會歷史教育。
2.1.3 產品形態
歷史知識產品以史書、簡牘、金石、劇作、影像、畫卷、雕塑等不同材質的歷史文物及不同形式的歷史文獻為其外在表現形態,以歷史事實與歷史解釋為基礎所建立的各種歷史理論與歷史觀念為其內在表現形態,這些歷史知識產品不僅發揮著傳承歷史文化的重要作用,同時還是歷史知識的象征。
2.2 歷史知識的傳播
2.2.1 傳播主體介紹
歷史知識的傳播路徑是多元化的,不僅可以通過政府部門、文化機構,也可以通過商業機構和企業及個人等不同的主體來傳播[3]。而在上述傳播主體中,國家對歷史知識的傳播具有全局性的影響,一方面國家通過修史書、頒行官及官方修史機構的設立,行使著其主導修史權,以闡釋其修史的合法性,并對國民進行歷史教育,以強化其國家意識和政治認同。而史家作為歷史知識的傳播者,滿懷熱情的傳播歷史知識,但傳播動機和意圖因時、因人、因地而異。其他傳播主體的動機則大多是因為利益、責任或者愛好。
2.2.2 傳播渠道與形式介紹
歷史知識的傳播渠道是非常廣泛的,傳播的形式也是五花八門。一方面,歷史知識會通過社會的發展推動其主動傳承,具體的傳播形式有刻史、修史等,通過這個路徑去傳播和再生產[4];另一方面,歷史知識會通過其他社會人士或者機構進行社會性廣泛傳播,其傳播的途徑和形式多種多樣,比如,文士論史、官學講史、書坊刻史、政者修史、民間說史、戲劇演史等,相對而言,其傳播范圍更為廣泛。到了近代,歷史知識的傳播渠道則主要以學校和社會為主。學校從中學開始就設置專門的歷史學科,從古代到近代,從國外到國內,建立了系統的教學體系,內容深度也是由淺到深,讓不同年齡段的學生都能接受歷史教育,這種傳播方式是最基礎的,同時也是最系統、最科學、最持久的[5]。社會傳播則伴隨各種融媒體的出現了新的傳播形式,隨著電視、廣播、視頻的出現而不斷發展,不僅傳播效率高,而且能很好地吸引受眾[6]。互聯網時代的今天,網絡融媒體迅速火爆,一躍為傳播歷史知識的新寵,以其通俗化、平民化等特點深受國民喜愛,讓職業史家的傳播不再具壟斷性。課題研究、學術活動、史學刊物、史學團體等渠道的歷史知識傳播范圍較廣,其傳播渠道更廣,傳播的內容更深奧。這種傳播形式兼具了學校和社會兩種渠道。
2.2.3 傳播受眾
歷史知識受眾層次多,其傳播受眾有著分層化需求的特點。在古代,社會層級分化明顯,上到以帝王為統治的政治中心,下到各級官員、文人士子,再到普通大眾、販夫走卒、尋常百姓,對于歷史知識均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受眾分層化特點明顯。近代,由于人類分工的不同,社會階層依然存在,歷史知識的傳播仍然存在分層化,但同時又與古代不同,其傳播內容和形式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所以說在不同的時代,是根據不同階層受眾群體的實際需求,選取不同的傳播內容,以及受眾最感興趣的傳播方式傳播歷史知識的[7]。史家雖然是歷史知識的傳播者,但同樣也是傳播受眾,既要完成歷史知識的傳播,又要不斷實現自身知識的更新換代。
3 歷史教育所涉及的兩大場域及其問題
3.1 學校歷史教育
近代隨著歷史學學科的開設,建立了學校歷史教育體制,并形成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并存而分立的格局。
3.1.1 基礎歷史教育
近代,基礎歷史教育以中小學校為主要陣地,從小學到初中至高中階段,都有不同的課程大綱與歷史相關,內容也有從淺到深的過渡,這種教育模式以教師和教材為主要傳播主題,學生為傳播對象,這種模式最初是清末時期基礎歷史教育學制改革的產物。育才是基礎歷史教育的目的,旨在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歷史觀,促進其全面發展。基礎歷史教育涉及學制、課程兩大重要問題。從20世紀初開始,我國學制經歷了模仿美國、日本等國家的基礎歷史教育到我國自主探索的過程。我國通過多年研究實踐,逐漸形成了一套獨屬于我國的歷史課程教育體系,其內容包含了世界的古代史、近代史,以及中國的古代史和近代史,也就是現今的歷史學科基礎教育體制。而歷史課程標準的制訂自晚清到目前已歷經百余年,高達近30 種,為基礎歷史教育提供指導并成為綱領性文件[8]。歷史學科基礎教育的落實,最終是以教科書的形式來體現,因此與教科書相關的編纂機制、編纂群體、編纂模式、編纂內容都應該受到高度重視。與此同時,相應的教學手段和方法是對歷史學科教學認知水平的直接反映,關系到歷史教育的質量[9]。而歷史教師的教學水平、素養、教學態度、教師來源,則對基礎歷史教育質量和效果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縱觀我國的基礎歷史教育經驗,進一步證實要想搞好歷史知識傳播,專業的教師是重要保障,所以必須想辦法提升歷史教師的教學技能和知識儲備,而要完成這點,關鍵在于歷史教師的師范教育,只有強化歷史學師范教育,才是固本之舉,才能讓基礎歷史教育質量得到提高。
3.1.2 高等歷史教育
現代高等歷史教育的框架最初設計于清末學制改革時期,并設置有歷史學科,逐漸演變為現代的依托于歷史學專業機構,由學院化職業史家擔任教育主體,教育的對象主要是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內容更加深入,甚至還帶一些研究的課題[10]。高等歷史教育秉承育才與育學并舉的宗旨。歷史專業人才的培養從晚清培養預備官僚的忠君達德,經民國至今高深人才和合格公民的專門培養,形成了職業化與社會性均能兼顧到的高等歷史教育人才培養目標。所謂育學其核心是科學歷史學的建立,各史學流派對于科學歷史學的建設均希望以自己的理念來進行,也就導致了歷史學科的格局出現了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多元并存現象[11]。要想達成高等歷史教育宗旨,實現歷史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學科建設是依托。通過一流的大師級師資團隊、專業化的歷史課程設置、良好的教學氛圍和機制、明晰的教學目標和理念、高質高效的研究成果等多方面協同配合,來完善學科建設內容。但同時,也必須認識到開展這些學科建設的中心是培育專業優質的人才。高等歷史教育相對于普通的歷史教育來說,需要迎接更多來自史家與史學社會化的挑戰,而職業史家的研究重點則更偏向于歷史知識的專業化生產及傳播,所以歷史教育其實更多的還是集中于學院,社會歷史教育相對比較欠缺[12]。
3.2 社會歷史教育
社會歷史教育呈現出復雜多變的格局。歷史的演變過程本身就是復雜的,因此其涉及的相關知識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復雜性和交叉性,這對于現代社會歷史教育的機制、渠道和方式都是巨大的挑戰,同時也要重點關注由社會、國家、學者這些因素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一大矛盾存在于國家主流意識與多元社會訴求相互間。國家一直是歷史教育的主導力量,對于歷史教育有絕對的話語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同時又不得不兼顧社會的多元訴求,把控好教育的方向,以保證國家主流意識形態能夠貫徹[13]。但社會歷史教育參與主體眾多,各主體訴求不僅客觀存在,而且多元化,需加強對社會力量的引導,以使國家與各方力量間的矛盾和沖突得到妥善解決[14]。
另一大矛盾存在于社會市場化需求與學者科學性要求之間。學者們認為科學的歷史知識是受史家素養和史學規范所限的,且自身文化優越感和精英意識強烈,對非專業人士批評,以突出自身的專業權威,因此難以為非專業受眾所接受和喜歡,這樣一來便令其處于尷尬的境地,需要積極反思,在文化上樹立平民意識,以大眾化、平民化的方式、專業化的水準來進行歷史知識的傳播[15]。
4 結束語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各種信息的交流和傳播更加便捷,網絡也成為社會歷史教育傳播的主要渠道,這對于社會歷史的繁榮發展是有促進作用的,但同時也降低了門檻,讓普通人也能夠參與到歷史教育研究中來。因此,在社會歷史教育研究中,還需要注意甄別信息的價值,在遵循和諧、包容、共存原則的同時,也要盡量屏蔽一些負面的、不準確的歷史知識。社會歷史教育主體和相關史學專業學者也應該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做好積極正面的引導和宣傳,多方力量共同努力,為社會歷史教育質量達到理想狀態提供保障。要想實現上述目標,也需要重視公共史學發展。公共史學不僅參與多元主體,而且主張各方力量和諧共進,并以滿足社會大眾的多層需求為目標,科學合理地發展歷史教育,完成歷史教育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