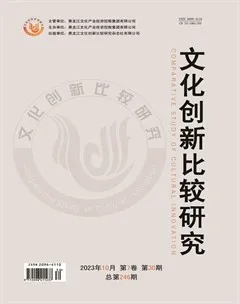中國傳統美學對游戲美術設計的價值和影響
邵逸璇,陳元
(淮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安徽淮北 235000)
游戲美術是指在游戲制作過程中負責游戲畫面、角色、場景、特效等視覺元素的設計和制作工作。20世紀70 至80年代,由于計算機技術的限制,早期的游戲美術元素通常以像素風的形式呈現在電子游戲當中,雖然這種像素風的游戲美術設計自問世以來廣受好評,但由于受到早期家用紅白機色域和分辨率的制約,這種像素風的游戲在這一時期的呈現內容顯得十分單調。不過,21世紀以來,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游戲美術迎來了空前的盛世——顯卡的更迭打破了畫面和色彩的桎梏、3D 技術的出現突破了畫面動態效果的藩籬,衍生出一系列諸如《魔獸世界》《劍俠奇緣》《最終幻想》等優秀游戲作品。而如今,AI 和虛擬現實技術的發展則使得游戲內容的呈現得到了極大的解放,游戲表現形式不再受到技術的制約,而游戲美術設計也在智能化時代的背景下迎來了進一步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認識中國傳統美學對游戲美術設計的價值和影響,如何巧妙地將中國傳統美學應用于游戲設計中,對于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提升公眾美學修養及塑造青少年核心價值觀有著舉足輕重的現實意義。
1 中國傳統美學特征與審美心理
長期以來,學界對于中國傳統美學的起點各執一詞,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傳統美學起源于《老子》[1],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傳統美學是以儒學為主體,儒、釋、道三種哲學思想相互補充、相互制約、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有機整體[2],并且這一有機整體具有鮮明的政治倫理色彩,承接了文藝為政治倫理的教化服務的重要任務。雖然上述兩種觀點針鋒相對,不過,就中國傳統美學的“意象化”特征來看,雙方的爭議僅局限于中國傳統美學的起源和主體,二者并不否認老子的“意象說”對于中國傳統美學發展的深遠影響。老子認為“道”是宇宙萬物的生命和本體,是有無虛實的有機統一。因此,在老子哲學思想的影響之下,中國古代藝術家并不過分注重對具體事物的逼真刻畫,他們更多追求的是“意中之象”。例如,“成竹在胸”就是在強調藝術家對“竹”這一客觀事物的意象化構造。鄭燮說:“胸中之竹,并非眼中之竹。”他所強調的“意中之象”就是“竹”這一客觀事物從“具體的竹”意象化為“審美的竹”這一構造過程。也就是說,“意中之象” 就是審美主體的審美意識和審美客體的美學特征之間形成的統一整體。在中國傳統美學的這種“意象化”背景之下,中國傳統美學的審美活動呈現出一種形而上的體悟化特征。明代王廷相說:“言征實則寡余味也,情直至而難動物也,故示以意象。”他所強調的就是“美”是難以通過邏輯語言來表達的,“美在意象”,“美”只能通過喻示和象征來為人所體悟,這也是禪宗所言“神似”的另一種表達。
道家強調淡薄樸素,禪宗主張妙悟神似,儒家遵循倫理教化,三者相輔相成,共同融合而形成了如今“美在意象”的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的哲學命題,使中國傳統美學在僅圍繞“意象” 的基礎上形成了兼具儒、釋、道三種哲學思想的獨特美學特征。
2 中國傳統美學在游戲美術設計中的現實困境
2.1 元素形式與歷史真實的割裂
縱觀當下,雖然我國對于游戲美術設計的制作和教學流程已相對成熟,但對于其內在價值的開發卻淺嘗輒止,以近年來廣為市場所青睞的“新國潮”游戲為例,盡管這些“新國潮”游戲在設計和制作過程中充分考慮到了民族元素、水墨元素等中國傳統美術元素,其游戲性也可圈可點。但是這類游戲卻時常給人帶來一種割裂感和違和感。比如,某國戰類游戲為了突出諸葛亮“多智而近妖”,將諸葛亮的形象刻畫為某種具有“法術”的“妖士”,這類刻畫從審美的要求來看并無不妥,然而這種刻畫方式卻讓人不免對諸葛亮這一中國傳統人物有了流于形式的刻板印象,并進一步導致玩家對于真實歷史認同感的割裂。
實際上,諸葛亮身上凝聚了中國人的處事態度、理想抱負和道德品質,諸葛亮這一符號已經在歷史的變遷中逐漸成了中國人民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識和中國社會的文化現象[3]。我們推崇諸葛亮,并非單純地為政治倫理背書,并非單純地推崇其“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我們實際上所推崇的是一種“抵抗精神”。孫周興認為:“生命就是抵抗。”這句話就是對“抵抗”精神的完美詮釋。宋元時期,社會動蕩不安,這一時期中國先民對諸葛亮的推崇達到了極致,這也是《三國演義》成書的基礎。南宋時期岳飛揮淚走筆在武侯祠內寫下了自己精忠報國的崇高理想;元代宋時,漢人則仰慕諸葛亮“躬耕于隴畝”的隱居生活。后來,那些郁郁不得志的中國傳統藝術家又在諸葛亮的身上得到了靈魂的寄托與慰藉。因此,我們實際上所推崇的是那個遙遠而又近在咫尺的自己,我們在現實的悲劇和歷史的悲劇中,逐漸地和諸葛亮這一文化符號的身影合為一體。當我們開始與這些具有“抵抗精神”和“悲劇色彩”的人物符號產生共情時,這一刻,我們可以是岳飛,也可以是諸葛亮,我們在這種憐憫的愛意與惋惜中獲得了崇高的正義與力量。
在理解了以諸葛亮為代表的歷史文化人物的內在核心之后,就很好理解我們為什么會對游戲中所塑造出現的人物形象產生割裂,正是因為游戲的塑造僅停留在人物最表層的形象上,沒有深入人物真實的歷史環境中去,也就不可能接觸到作為歷史人物諸葛亮的形象對于后世之人的重大精神意義。而這種精神意義,才應該是中國傳統美學的核心理念和價值要求,然而部分“新國潮”游戲卻落入商業化窠臼,對此淺嘗輒止。
2.2 標簽化的形式與內容
其實,“新國潮” 游戲中這種重表征輕內在的現象并非個例,造成這種感官的核心在于游戲的構造,形式與內容都流于了標簽化的表現。以近年來廣受好評的中國風恐怖游戲《紙嫁衣》為例,與西方“驚嚇與野獸” 的恐怖不同的是中式恐怖往往充斥著崇高與對立的心理暗示。在中式恐怖游戲《紙嫁衣》中,游戲將極具現代性的主角置身于民族的傳統性當中,營造出一種二元對立的違和氣氛。游戲將民俗元素巧妙地應用于畫面之中,使玩家在參與游戲的過程中產生出對主角命運的心理暗示,這種心理暗示在玩家的內心形成了一種“移情”的美感。這種“移情”的美感并非來源于民俗畫面帶來的感官刺激,而是來源于神秘主義和唯物主義經驗的對立和沖突[4]。例如:“下班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一位老太蹲坐在街邊燒紙,我漸漸走近,卻發現今天是我的頭七。”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這種語句沒有華麗的辭藻,卻可以在我們心中營造出一種含蓄的恐怖氛圍,正如某些評論者所言:“看來只有中國人知道怎么嚇中國人”。
但是,盡管《紙嫁衣》等中式恐怖游戲對民俗元素的應用極為巧妙,但依然未能實現對中國傳統美學的融會貫通。這種觀點并非我們刻意為難,我們所評判的標準來源于這類游戲的作品本身。例如,《紙嫁衣》 中作者希望通過一個一個故事將角色塑造為現實的“犧牲品”,最終卻和其他中式恐怖游戲一樣,逐漸淪為“玄幻題材”。一個又一個模塊化、形式化的劇情構造與類似的人物情節使得一部一部接連出現的紙人,也逐漸流于形式,不可避免地使得玩家陷入了審美疲勞。雖然每部《紙嫁衣》都被冠以“中式恐怖”的標簽,但似乎除了第一部外,后續作品最為玩家所關注的卻是角色之間的“凄美” 的現代愛情故事,這無疑是對于內容的把握失衡所導致的,過于注重形式帶來的感官刺激而忽視了內容核心的重要性,這種尷尬境地實際上是多數“新國潮”游戲所必然會經歷的現狀。當下游戲主流玩家的生活經歷本身就是二元割裂的,他們經歷著社會的巨變,他們在父輩的身影中感受著民俗,自身又身處于唯物的現代社會之中。當這種民俗符號第一次出現于他們的游戲經歷中時,他們所體會的新奇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這種新奇感是流于形式的,脫離了民俗環境而失于內容。然而,這類符號的頻繁出現卻忽略了其具有的“時代性”特征,這意味著雖然中式恐怖游戲實現了對民俗符號的深入挖掘,卻并未能使得玩家獲得對“時代性”的體悟。玩家沒有辦法感受到那個過去時代真實的樣貌及身處其中的人們的真實情感,可以說這種“時代性”本質上是一種批判與接納[5],接納其存在的時代背景,才能獲得對中國傳統美學的深刻體驗。
3 中國傳統美學在游戲美術設計中的應用策略
3.1 挖掘神韻
中國傳統美學在歷史發展變遷的過程中已經逐漸形成了極具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獨特風格,中國傳統美學始終強調構造的“神韻俱佳” 和“形神兼備”。在游戲美術的設計和制作過程中,游戲美術設計者應更加注重對游戲角色神韻的挖掘。例如,在對歷史人物的塑造過程中,游戲美術設計者應當從文獻古籍中搜尋足夠的歷史記錄作為設計參考。當下時代的信息洪流使得很多信息都失去其原本的意義,被誤讀的情況時有發生,只有回到原始文獻當中才能發現歷史的本真。此外,游戲美術設計者應當具有良好的文化意識,應從二次文獻的加工和處理中形成對歷史人物的深刻和全面認識,以避免對歷史人物的塑造陷入“扁平化”的窠臼。中國文化的古籍博大又繁復,其思想內容更是復雜多樣,對同一人物的觀點和認知多有爭議是為常態。故而游戲的設計者不僅要會讀古籍,還要通過自身的文化素養辨別古籍的內容與范式,只有這樣,才能使游戲為受眾帶來一種獨特的生命力和深刻的體悟,做出有思想內涵的內容,受眾才可以通過游戲設計者為其提供的藝術形象來了解歷史人物背后蘊含的深刻精神氣質和文化氣質,而非僅僅是流于形式的模塊化構建,這也是“神韻”的基本內涵。
3.2 構造虛實結合的場景
虛實結合的場景構造是“新國潮”游戲美術設計靈魂。法國哲學家波德里亞在其“虛擬論”中指出,視覺技術和媒介技術的高度發展導致現如今流行的法則不再是藝術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藝術[6]。所以在游戲的設計中,也要做到生活與藝術的虛實結合。中國傳統山水畫藝術作品通常強調在“虛實”中營造一種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中國傳統藝術家通常利用這種獨特的場景構造來傳達出他們自身的情感意識和審美心理。雖然這種紙面的構造是二維的、平面的,卻是三維游戲不可或缺的思想核心。在“新國潮”游戲的設計中,要巧妙地將二維的平面轉化為三維的立體構造,以透視的手法為基準,營造情景交融、虛實共生的意象之美,要做到從二維的平面中凝練出三維的空間感,就不能局限于平面化的視覺感受,而是要將其升格為立體的、綜合的感官享受[7]。在形象的塑造、元素的搭配、空間的營造、色彩的運用上都要做到先以虛運實,再虛實結合,這樣才能呈現出游戲美術設計的動態效果與悠長的意境之美[8]。
3.3 體現“張力”
游戲美術的場景設計不僅要考慮到其美觀程度,還應重視玩家的操作舒適度,使其能夠體現出中國傳統美學所蘊含的“張力”特征,這種“張弛有度”的美感也是道家思想的重要體現[9]。游戲美術設計中不僅需要規則的幾何界面,也需要虛實結合的不規則界面,這種“張力”是游戲場景功能性與操作性的直觀體現,能夠使受眾擁有更為良好的游戲體驗,也能在游戲的體驗過程中感受到中國傳統美學的 “忘我與無我”的飄逸的美學特征[10]。
4 結束語
中國傳統美學是儒、釋、道三種哲學思想相互融合、相互補充而形成的具有鮮明政治倫理色彩的倫理型美學。在“新國潮”游戲設計中融入中國傳統美學,一方面應當對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的重要意義和影響性問題具備深刻的認識,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避免“新國潮”游戲美術設計中時常會出現的同質化問題。游戲美術設計者應當注重中國傳統美學元素與游戲角色設計、場景設計、動態效果設計等多方面的深度融合,追求“神韻”和“意象”以及必要的“張力”,虛實相生相映,在游戲美術設計中充分發揮中國傳統美學元素的價值和作用,從而提升游戲美術設計的質量,增強我國游戲產業的文化傳播力和影響力。
而另一方面,游戲美術設計也不應僅局限于對中國傳統美學元素的挖掘,更應注重對中國傳統美學的審美心理和深刻內涵的體悟,應當深刻地意識到中國傳統美學所具有的鮮明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特征,加強對中國傳統美學的升華機制的深刻認識,從而創作出更為優秀的“新國潮”游戲美術設計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