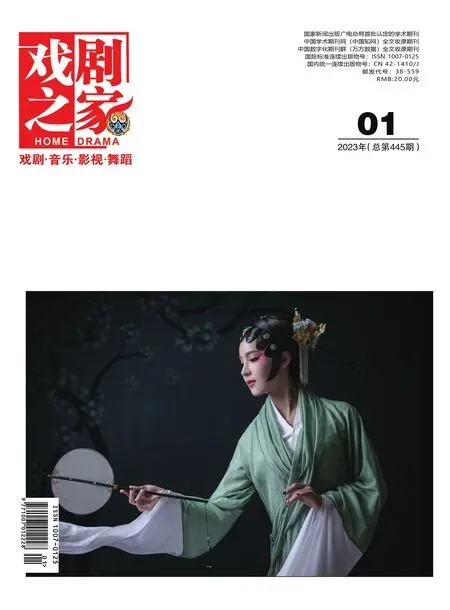現代化背景下侗族音樂文化生態的重塑分析
黃玉翔
(凱里學院 音樂與舞蹈學院,貴州 凱里 556011)
侗族音樂文化涵蓋了侗族戲劇、侗族歌唱活動、侗族音樂種類、侗族樂器等,屬于我國民族音樂中現存的音樂文化涵蓋較廣、保存比較完好的音樂文化體系。侗族音樂中,“侗族大歌”傳播度和影響力最高,“侗族大歌”的民間傳承也最為完整,這就決定了關于“侗族大歌”的“文化生態”研究最為完整。但是,“侗族大歌”僅僅是侗族音樂中的一種類別,而“侗族大歌”文化也只是侗族音樂文化體系中的一小部分。因此,要想完成對侗族音樂文化體系的整體研究、搞清楚侗族音樂“文化生態”,單純依靠對“侗族大歌”的“文化生態”研究是遠遠不夠的。而且,現代化背景之下,音樂形式紛繁多樣、音樂文化傳播渠道不斷發展、網絡媒介不斷普及,侗族人的生活模式、生產模式、思想觀念等均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尤其是現代化背景之下“遷徙”活動不斷發生,侗族音樂文化也必然發生變化。因此,在現代化背景下侗族音樂變化過程中,侗族音樂“文化生態”如何進行“傳承保護”“發展保護”“拓展創新”,進而完成侗族音樂“文化生態”的重塑,加固侗族音樂的藝術價值和音樂價值,是侗族音樂文化傳承和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課題。
一、侗族音樂的“文化生態”概念和現狀
(一)侗族音樂的“文化生態”概念
“文化生態”的概念最早產生于20世紀的西方,概念產生之初主要用于探索文化和自然環境的關系,即對文化與環境的辯證關系解讀。“文化生態學”概念的提出,推動了關于藝術文化的生態問題研究的發展,重點研究的是藝術創造、藝術發展和藝術傳承等藝術活動過程中社會因素、文化因素、民風民俗等的影響。具體到音樂“文化生態”方面,主要是對音樂文化發展、傳播、傳承等過程與地理環境、社會變化規律、地域文化的辯證解釋[1]。所以,侗族音樂的“文化生態”主要是對侗族音樂文化的傳承、發展、創新、保護過程中侗族家族、侗族村落、侗族民風民俗、侗族活動區域、侗族生活習俗、侗族音樂傳承空間、侗族音樂保護途徑等的綜合分析,并基于此,建立侗族音樂長久發展、永葆生命、傳承傳播的體系。同時,侗族音樂的“文化生態”還涵蓋了侗族文化的理論探索、侗族音樂文化發展對侗族民族生活區域生物多樣性研究等的影響。比如,侗族音樂根據侗族語言分區又劃分為不同的種類,即侗族聚集地南部方言區的侗族音樂和侗族聚集地北部方言區的侗族音樂。南、北方言區的音樂形式、音樂形態、音樂表達形式均打上了“侗族烙印”,但是因為生活方式、生產特征、區域特點等,在音樂形式、音樂形態、音樂特性和音樂演奏特征等方面又存在細微差別,南、北方侗族音樂是侗族音樂的組成部分,而南、北方侗族音樂的產生、發展、傳承所受到的一系列影響,又是侗族音樂“文化生態”的整合和重組[2]。
(二)侗族音樂的“文化生態”現狀
侗族音樂傳承發展多年,自身具備了龐雜多樣的種類,侗族民歌、侗族民樂、侗族歌舞、侗族曲藝、侗族樂舞等構成了侗族音樂特有的體系[3]。這些不同的音樂體系元素與侗族生活區域自然環境、侗族社會發展、侗族歷史變遷、侗族生活方式等存在必然關聯,而這種關聯就是侗族音樂文化的系統、動態、活態的體現,也是民族特質和音樂文化的解讀。現代化背景之下,社會生活方式、社會生產方式、社會經濟發展模式都在產生變化,而這種社會變革在一定程度上讓侗族的發展走向了新方向,多元文化融入、民族聚集地遷徙、生態環境變化等都對侗族音樂文化產生了影響[4]。尤其是現代科技的發展,使得音樂創作形式、音樂融合模式、文化發展更新對侗族音樂的傳承、發展、創新產生深遠影響。比如,傳統侗族音樂的審美和創作根植于侗族生活區和侗族生活模式,但是社會變革和社會價值觀變化,使得侗族音樂的歌曲內涵、情感表達也隨之變化;侗族人千百年來生活在山水交融的地理環境之中,侗族音樂寄情于山水之間、表達的是原生態的內涵,“西南獨秀”“音樂如清泉般閃亮”“民間支聲復調音樂代表”等美譽是侗族音樂的傳統特征。但是,現代旅游業的發展、網絡電視媒體的崛起,導致侗族原生態生活環境發生變化,趨于商業化的生活場景阻礙了侗族音樂的發展和創新。傳統侗族人“夜夜聽大歌”“月月追侗戲”的習慣也被電視節目、電影等沖擊。此外,受到社會經濟發展趨勢的影響,無論是南方言片區還是北方言片區的侗族人,很多都伴隨著“打工潮”走出了侗族村寨。這樣,侗族音樂文化的傳承和發展面臨著“斷代”風險[5]。
另一方面,侗族音樂“文化生態”中,侗族音樂活動等對于侗族音樂“文化生態”的穩定性極其重要。但是,部分侗族村寨隨著“社會大遷徙”“民族大融合”的實現,傳統的侗族節慶活動、侗族音樂活動逐漸消失。因此,侗族音樂“文化生態”已經“瀕臨破碎”,一些優秀的侗族音樂文化面臨著發展困境和傳承挑戰。
二、現代化背景下侗族音樂“文化生態”的重塑價值
現代化背景之下侗族音樂“文化生態”的重塑就是侗族人音樂創作、傳承和發展過程與現代化環境、現代化社會之間的相互磨合、相互調整、相互適應,并讓侗族音樂逐漸在現代化背景之下通過“文化生態”重塑獲得現代化發展意義,不至于讓侗族音樂文化的傳承斷代,也不讓侗族音樂發展“蔽塞”。具體來說,現代化背景下侗族音樂文化的持續發展和文化傳承需要調整和適配整個侗族音樂“文化生態”,不僅需要滿足侗族音樂“文化生態”的內部要素調整,也要實現對侗族音樂“文化生態”的外部結構優化。侗族音樂的發展不應當是“排外”的,這是侗族音樂文化體系發展和傳承的基礎,更是侗族音樂演變、創作、發展的根基。另一方面,現代化背景之下,侗族人處于接受新鮮事物、適應現代發展并保留自身傳統文化的過程,他們對于新生事物、現代發展帶有“包容心”[6]。所以,侗族音樂不僅存在于侗族村寨,也通過網絡媒體、廣播電視等傳播到了不同地域和不同場合。當然,侗族人也能通過網絡媒體、廣播電視學習其他民族的音樂文化,拓展音樂創作視野,進而創造出更具有豐富性、差異性和現代性的侗族音樂。最終,通過現代化背景下侗族音樂“文化生態”的重塑,侗族音樂就能走出完全依賴原始環境、原始生態、原始生活的模式,尋找侗族生活、侗族社會、侗族生產在整個現代化發展環境中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并依托這種價值和意義進行侗族音樂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實現侗族音樂的“可持續發展”[7]。
三、現代化背景下侗族音樂“文化生態”的重塑策略
(一)尋找文化土壤
侗族音樂根植于侗族人生活的土壤、發展于侗族人生活的環境、傳承于侗族人生活的社會。在現代化背景之下,侗族人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發生了不可避免的變化,侗族人音樂“文化生態”體系中的土壤也受到了影響,尋找屬于侗族音樂“文化生態”體系中的文化土壤,就成為重塑侗族音樂“文化生態”的必然策略。具體來說,現代化背景下尋找侗族音樂文化的土壤,首先需要將侗族社會和侗族村寨恢復到“原始”狀態和“適應侗族音樂創作”狀態,保證侗族音樂“文化生態”的土壤“環境”與現代發展相適宜,既凸顯侗族文化特征、侗族音樂形態、侗族生活環境,又展現侗族音樂文化的“凝聚力”和現代音樂的審美認同[8]。這樣,具備侗族人現代審美認同、侗族特有民風民俗、開放包容和諧共生的侗族音樂文化土壤就得以形成,推動了侗族音樂“文化生態”的人文與自然、現代與傳統的“共生”。這樣,現代化背景之下侗族音樂就不會因為環境變化、語言變化、傳承人變化而發生變化,實現了侗族音樂“文化生態”的穩固發展。
(二)發展文化產業
發展侗族文化特色產業,推動侗族音樂文化的傳承和傳播,是現代化背景下侗族音樂“文化生態”重塑的重要途徑,是侗族音樂文化傳播、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的協調發展,也是通過文化產業和文化生產力推動侗族音樂文化“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近些年來,侗族文化旅游產業不斷發展,侗族音樂憑借著媒體宣傳得到了良好的傳播,以“侗族大歌”“侗笛情歌”“侗族蘆笙”“侗戲”等為特色的音樂表演藝術活動取得了良好的發展勢頭。此外,針對“侗族大歌”“侗族蘆笙”“侗戲”等侗族音樂文化的研究也在不斷深入。所以,以侗族特色音樂文化為核心的文化產業取得了良好的發展優勢,侗族音樂文化也作為“國粹”之一展示于世間[9]。這樣,依托文化產業的發展,侗族區域經濟發展、侗族文化發展、侗族社會發展都得到了推動,產生的社會效應、科研效益和經濟效益等又為侗族音樂文化的傳播和傳承注入了“強心劑”,推動了侗族音樂“文化生態”的重塑。比如,侗族聚集地的地方政府近些年來積極開展了以“侗族文化傳播”“侗族文化傳承”“侗族音樂藝術表演”為主題的文化節日活動,帶動了侗族文化產業發展,實現了侗族民族音樂的傳播和發展。反之,侗族音樂的傳播和發展、侗族文化產業發展,又給侗族文化創作和發展帶來了契機,實現了侗族音樂“文化生態”重塑的多維度空間。
(三)打造文化品牌
文化品牌是品牌宣傳、品牌傳播、品牌價值創造、品牌影響力提升的關鍵。對于侗族音樂“文化生態”體系而言,文化品牌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和可利用資源,打造侗族音樂文化品牌可以賦予侗族音樂文化更高價值和更高內涵,讓侗族音樂文化“走出侗族”“走出侗鄉”“走出國門”,并逐漸與現代化背景實現“文化生態”的協調和適配[10]。比如,“侗族大歌”作為最具代表性的侗族音樂類型,經過“侗族歌師”的多年傳承和多年發展已經具備了很大影響力,打造文化品牌進行文化宣傳和文化推廣具有良好基礎。侗族文化品牌的打造以“侗族大歌”為切入點,無論是侗族文化資源展示、侗族文化旅游活動、侗族文藝表演都可以嵌入“侗族大歌”的內容,讓“侗族大歌”逐漸成為一種特色、一種產品、一種文化,最終成為一個侗族文化音樂品牌,進而成為侗族音樂“文化生態”重塑的核心要素。
四、結束語
侗族音樂“文化生態”在現代化背景之下是受到各種因素、各種力量、各種文化干擾的,但侗族音樂“文化生態”也在進行資源拓展、整體發展、文化傳播、文化交融,并憑借著其文化價值和文化功能參與了現代社會發展。因此,現代化背景下重塑侗族音樂“文化生態”對于侗族音樂“文化生態”的內在機理、“文化生態”的制衡、“文化生態”的適應等有著重要價值,能有效推動侗族音樂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實現侗族音樂文化的傳承、發揚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