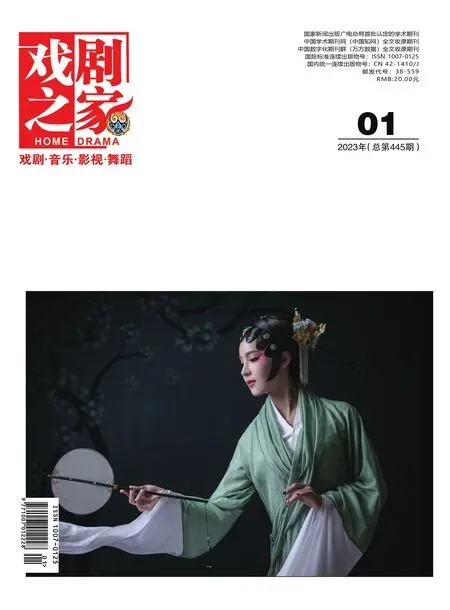新時代語境下王光祈國樂觀對音樂創作的現實意義
潘孝玉
(四川音樂學院 四川 成都 610021)
王光祈是一位愛國主義者,他懷著救國的赤誠之心來到德國留學。他旅居德國的十七年中,致力于中西方音樂交流,翻譯了大量音樂論著。在音樂領域,他的成就斐然,他將比較音樂學介紹到中國、開創性地提出“世界三大樂系”,而他的國樂思想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頁。要真正了解王光祈的國樂思想,也必須回到其特定的時代去揭曉答案。
一、王光祈國樂思想的提出——獨特的時代背景
王光祈出生于晚清,成長于民國,成熟于西歐。王光祈所處的時代是中國社會政治迅速變革、各種思潮激烈交鋒的時代。無數能人志士在探索救國的道路,王光祈也時刻將自身前途與國家命運相聯系。他的成長與中國革命的發展合拍共振,主要表現在王光祈先后發起和參加少年中國學會、工讀互助團,但無一例外,這些實踐均失敗了。
為尋找救亡圖存的道路,王光祈赴德留學,開眼界,學真知,其目的在于考察德國社會經濟的復興及背后的原因。在德國,他接觸到了德國的人文、藝術,尤其是德國的音樂。他在《東西樂制研究》中提出:“蓋中華民族者,系以音樂立國之民族也…。”[1]王光祈從德國的戰后重建中看到音樂與詩歌對德意志民族的重要作用,開始反思新文化運動中的一系列主張,從此改學音樂。而面對中國音樂當時在西方音樂的排斥之下的艱難處境,王光祈也立志于重構復興中華民族的樂種、樂器和民族音樂。
二、王光祈“新國樂”思想的含義
20世紀20年代,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中國的文化雖古老但式微,讓中國人意識到自身音樂內容和結構的不足,并從中反思如何創造中國的音樂文化。音樂家們產生了關于中國音樂與西方音樂的激烈討論,有人認為應全盤西化,有人堅持國粹主義。而許多音樂學家不約而同地提出了國樂思想。蕭友梅認為,僅僅用中國古老的樂器和較為成熟的音樂體系所創作的音樂是“舊樂”并非“國樂”,應該合理借鑒西方的樂器和音樂技法,但只要是表現中國精神的音樂就是“國樂”[2];楊蔭瀏主張用開放溫和的眼光看待西方音樂文化進入中國的現狀,極力主張國樂前途及其研究與西方音樂文化充分融合交流和公開比較之后形成真正的國樂;劉天華則主張改進中國的國樂,劉天華認為不應該用片面的眼光來對待中西音樂,而要全面討論中西方音樂的差別,西方音樂雖然目前完全成熟,但不能夠強加在中國人的意識性格之間,作為一個中國的音樂學家,要守住中華民族的傳統,把中國音樂的優點發揚光大[3]。
王光祈在《歐洲音樂調式進化表》一文展開描述了國樂的標準。一是代表民族特性;二是發揮民族美德;三是舒暢民族感情。[4]王光祈所主張的國樂是,一種具有一定審美趣味的音樂,一種能夠代表中華民族的文化特色的音樂,一種能夠振奮民族精神的音樂。國樂首先是能夠喚醒民眾低沉精神的音樂,他強調了音樂救國的重要性,利用國樂達到“救人”—“救族”—“救國”的目的。
三、新時代語境下文藝觀與王光祈國樂觀的聯系
新時代文藝觀是我國文藝發展的風向標,新時代文藝觀是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通過對比研究,不難發現,新時代語境下的文藝觀與王光祈國樂觀有一定的聯系。
一是兩者的時代背景有相似之處,都產生于大變革大發展的時代。新時代機遇挑戰并存,國際文化交流變得日益頻繁,與此同時,伴隨著文化的交鋒。王光祈國樂觀產生于民國時期,正值中西方文化交流之際,中國為了實現救亡圖存,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科技等。
二是兩者對待中西方文化的態度有相似之處,即兼容并包的文化態度。新時代的文藝觀面對中西方文化的差異,要合理地看待西方文化。王光祈的國樂觀既沒有忽視音樂的世界性,又堅持了我國音樂的民族性。
三是兩者的最終目的相契合,兩者最終的目的都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新時代是文化繁榮的時代,在實現自身文化繁榮的同時促進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王光祈創立國樂觀的最終目的是實現音樂救國的偉大理想。在繼承中華優秀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基礎上,合理借鑒西方文化,改造我國的音樂,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國樂,達到音樂育人的目的,最終實現我國文化富強的使命。
四、王光祈國樂觀對當代音樂創作的現實意義
音樂創作是指作曲者在學習音樂理論和創作技法的基礎上,通過腦力勞動寫下具有一定美感的樂曲。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音樂在曲譜創作、演奏技法、表現力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進入21世紀,文化市場呈現多元化趨勢,移動終端迅速擊敗唱片,隨著音樂媒介的變化,流量藝人出現并受到了年輕人的追捧。然而,他們所產出的音樂大多數稱不上是“國樂”。
而王光祈的國樂觀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從音樂創作的國別來講,音樂創作應堅持中華民族特有的民族性;從音樂創作的質量來講,強調音樂的審美性;從音樂創作的對象來講,音樂創作應注重人民性。
(一)音樂創作應立足民族性
首先,新時代的音樂創作者應注意到,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音樂,音樂是民族獨特性最好的表達。王光祈所堅持中國文化之魂,即“和諧主義”,這對新時代的音樂創作者有啟示意義。王光祈在《歐洲音樂進化論》中提到:“什么是‘中華民族特性’?簡單來說,便是一種“協和態度”,是我們生存大地的根本條件,也是我們將來感化人類的最大使命,這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唯一特性,我們應該使之發揚光大。”王光祈認為中華民族的唯一的“民族特性”,歸根到底是一種“和諧”精神,來源于孔子的“禮樂觀”。孔子強調樂的教化功能,其核心內容是通過強調社會秩序上的和諧,達到社會秩序的穩定。王光祈批判繼承了孔子的禮樂思想,試圖從中找到音樂救國的方法。“和諧”態度在中國音樂中可以窺測一二,整體體現為含蓄內斂表達情感、沒有夸張奔放的音樂語言。“和諧”在音樂上則表現為聲音的高低、大小、音色、曲調的和諧統一,從形式上達到韻律的和諧。而新時代的音樂創作者是中華優秀文化的傳遞者,應該從自我做起。新時代的音樂創作者應表達一個國家的集體記憶和共同理想,讓音樂作品最終實現由一件普通的藝術作品到大眾化的藝術再到民族化身的轉變。
其次,新時代的音樂創作者要正確處理國樂與西方音樂的關系。王光祈前輩對此持中庸態度,他認為應在立足本民族優秀傳統音樂的基礎之上,借鑒西方先進的音樂技法、體系等,來改造現有的中國音樂,從而創造出“國樂”。目前正有無數的音樂家,在這條道路上探索著。例如,鋼琴曲《平湖秋月》,旋律流暢,音調婉轉,獨具中國之韻。新時代的音樂工作者應該平等地對待中西方文化的特色,深刻認識到任何一個民族的民族特性并沒有好壞之分,也沒有先進和落后之分。
(二)音樂創作應立足人民性
王光祈認為:“舒暢民族感情,是舒暢民眾的感情,不是一部分知識階級的感情…。”[5]他強調國樂的大眾性,來源于大眾,服務于大眾。王光祈強調國樂具有大眾性,國樂的受眾要廣泛,抒發民眾的感情。藝術創作者扎根生活,提煉人民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精華,創作出反映人民精神風貌的優秀藝術作品。人民群眾是廣大音樂創作者的創作對象,群眾生活是廣大創作者的創作源泉。
人民性是藝術作品評判的標準,優秀的作品要符合人民的審美觀。音樂創作應注重人民性,一是由于音樂創作的來源是人及人的生活,如歌曲《Yesterday once more》以人的回憶為中心,深深地打動了聽眾。二是音樂創作中要表現人的精神狀態,阿炳從自身的現實生活出發,創作出《二泉映月》,其中凄涼而哀怨的旋律,表現人對貧困的無奈和生活的無助,聽者無不動容,給人以強大的精神共鳴。音樂創作是音樂家從生活中觀察而得到靈感,進行藝術加工并賦予豐富的情感,用于表現音樂家所思所想,而音樂創作的源泉正是人民的生活現狀和情感。
音樂成果由人民共享。音樂創作者應深刻認識到,完成一首好作品不僅是為了實現個人的人生價值,還應該認識到音樂創作的最終目的是助力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三)音樂創作應立足審美性
王光祈認為國樂必須是發揮積極向上精神的音樂,他說:“如蘇州的灘簧,京津的時調,誠然是代表我們中華民族的生活,但只是一部分墮落社會的生活,亦不能稱為我們的國樂。[6]學者葉潔純在《少年中國與國樂建構:王光祈音樂民族主義思想探析》一文中指出:王光祈重建禮樂的根本目的在于音樂,他把音樂當做改造國民生活的工具,而看重的是音樂對國民的感情和精神所發揮的作用,因此他反對音樂的娛樂功能,強調的是音樂的道德教化功能。[7]學者席格認為王光祈的這一論述,創建國樂采取美善并重的標準,可謂既繼承了禮樂傳統,又符合音樂藝術的發展潮流。[8]由此可見,王光祈主要在強調音樂的積極作用,追求美與善的統一。這種美是指音樂所具有的節奏美、內容美。善則是指音樂所起到的社會作用應該是積極的作用。而目前音樂創作仍然存在著許多問題。比如:突出的具有代表性的音樂作品不多。在新時代的音樂創作中,真正能夠留下歷史足跡的音樂作品少之又少。而大多數的音樂作品僅僅是為了跟隨社會熱點,部分音樂作品缺乏精神內涵和人文價值,勢必會被歷史所淘汰,被人們所遺忘。目前市場上的音樂作品大多異曲同工,缺乏鮮明的個人特色。而王光祈的國樂創作思想對解決以上問題具有指導作用。
五、結語
面對西方音樂知識傳入中國的現實環境,王光祈受古代儒家思想的影響,他創造性地提出“國樂”思想,堅持在西方音樂技術的指導下,發掘出優秀中國音樂。在新的歷史背景下,本文重新分析王光祈的音樂思想并審視其現實意義,簡要論述王光祈國樂觀,根據當今的現實情況,多方面、多角度探析王光祈的思想對音樂創作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