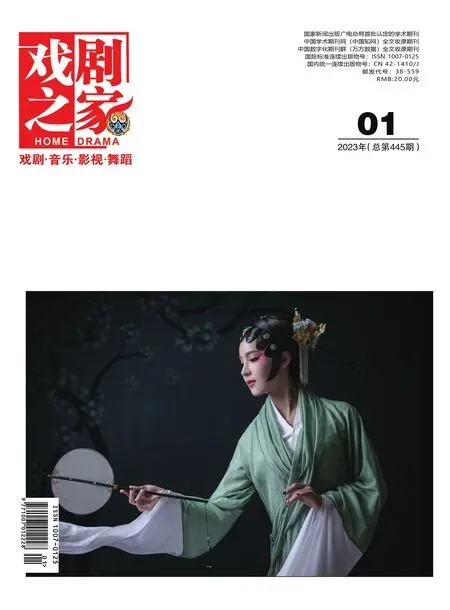平凡溫暖訴人生
——以電視劇《人世間》為例
趙曉霞
(中央戲劇學院 北京 100000)
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騰訊影業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等數家影視文化傳播方聯合出品的當代現實主義題材大劇《人世間》于2022年1月28日在央視綜合頻道首播,在愛奇藝等網絡平臺同步上映。開播后,該劇收視率創下央視近8年新高[1],引發各平臺熱議,成為2022年開年的爆款影視作品。其實,近幾年來,這一題材的高質量的電視劇有不少,比如《山海情》《大江大河》等。但像《人世間》受眾面如此之廣的電視劇并不多見——其受眾囊括了40后、50后甚至10后,涵蓋了不同圈層和不同年齡的群體。這部融歷史、民族、國家、家庭、個人于一體的年代大劇所傳遞出來的正能量的價值觀和有歷史文化積淀的精神在當下社會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同時,這也說明該劇題材的深刻性和稀缺性。該劇導演李路曾說:“《人世間》展示了這50年中國大的變化,深情謳歌了改革開放和熱血燃情,這也正是我最看重的一點。”[2]
《人世間》以順時的線性結構鋪開,敘事的主要場景轉向宏大的敘事空間,融時代敘事、家庭敘事、個體敘事于時代洪流的龐大敘事之中。該劇沒有一味地呈現激烈的矛盾沖突,也沒有陷入“悲劇”“悲情”的敘事模式,而是以一種熟悉、溫情的方式緩緩展開,以溫暖現實主義的表現形式給予觀眾心靈上的撫慰和真善美的價值導向。對于人物的塑造,該劇雖然以周家三兄妹的成長經歷為主線,但人物群像的建構沒有出現臉譜同質化的問題,人物形象生動豐滿、性格鮮明、立得住,把平凡普通的平民子弟在社會洪流中跌宕起伏的人生融于日常生活敘事的“生活流”中,以此呈現跨越50年的中國普通大眾的現實生活的真實面目,真實還原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傳遞出一代平凡大眾堅韌拼搏、秉承初心,為實現美好生活積極奮斗的光輝力量。正如該劇編劇王海鸰所說:我們的電視劇《人世間》是溫暖的。
本文擬以此為基點分析電視劇《人世間》的敘事策略,探析該劇如何以溫暖現實的表現方式與觀眾產生真切共鳴。
一、立足歷史 超越歷史
電視劇《人世間》作為一部現實主義的史詩大劇,不僅要再現還原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50年的表象真實,也要呈現這段歷史的本質真實,以此引發觀眾的真切情感共鳴,提供審視、思考社會現實的場域。蘇珊·朗格在敘事學研究中提到,藝術作品中的諸多元素都是由不同的藝術符碼構成的具有特殊含義的符號體系。影視作品中的人物、道具、場景等都是符號體系的組成部分。
電視劇《人世間》改編自梁曉聲獲茅盾文學獎的同名小說,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電視劇的改編具備基底夯實的文本基礎。把115萬字的小說濃縮成58集的電視劇,涉及大大小小一百多個人物和50年的歷史跨度,要想原汁原味還原這50年的真實感,表現人物命運的起伏、掙扎、走向,需要特別強的整合能力。為了重現吉春這個東北老工業城市的面貌,尤其是“光子片”居民區,劇組在東北三省尋覓實景未果后,決定搭建一個“光子片”。4萬平方米的景,數十輛超大車廂內裝滿了搭景用燈、掛歷、自行車、家具等,孩子們玩的沙包、橡皮筋等都是按照電視劇的年代真實照搬過來的,甚至地面上的黑土都是從別的地方運來的……這一切都真實完美呈現了一個20世紀60年代的老工業城市的居民區。可以說,劇中的道具、布景、化妝、服飾等都表現了那個年代普通大眾生活表象的真實。
《人世間》真實把握了50年歷史跨度的縱深走向,再現了社會真實。這50年涵蓋了這個歷史階段中國真實發生的重大社會歷史事件。上山下鄉、大三線建設、推薦上大學、改革開放、下海潮、出國熱、老工業區搬遷改造等。從東北老工業區到最早進行改革開放的珠三角,再到云貴川……這部電視劇不僅從時間維度把握了中國這一階段的幾個重大社會熱點,也在空間維度上給觀眾呈現了當時中國發展的基本面貌。
夯實、接地氣的劇情,充滿生活氣息的場景,貫穿始終的重大社會歷史事件,可以說,《人世間》在還原呈現這50年的歷史表象方面做得很好,該劇立足于歷史,讓觀眾感受歷史細節的真實,因此,很多觀眾評論說從中可以看到自己或父母過去生活的影子,但這并不是作者創作這部現代史詩大劇的根本目的。
電視劇《人世間》把一群真實、鮮活、具有代表性的大小人物跌宕起伏的命運掙扎軌跡融入50年的時代洪流中。這組群像的設置也有區分,比如,家庭環境不同、成長經歷不同、經濟境況不同、與家人和朋友的相處之道不同。每一個個體都有自己獨特的成長生活經歷和不盡相同的困難和坎坷。雖然這部劇沒有特別激烈的矛盾沖突,但劇中也設置了諸多情節來展現人物之間的矛盾。其中,周家小兒子周秉昆與父親周志剛的爭執、周家大兒媳也就是省長千金郝冬梅被郝母怒打一巴掌等情節算是該劇比較大的沖突。但該劇所呈現出的矛盾在劇中以一種溫情的方式獲得了化解,在理解、成長與包容中,該劇的思想深度得到升華。每個人都在經歷著不同的苦難,比如,以周秉義為代表的黨的領導干部面臨的類似“光子片”改造的困難和阻力,以周秉昆、肖國慶、孫趕超等為代表的始終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所面臨的下崗、就業等困難。每個人在面對生活的坎坷和困難時,依舊會懷著樂觀積極的態度往前奔,盡最大努力以相對理想的方式去化解那些看似難以解決的問題。劇中的每個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無論在幾個家庭中還是在朋友間,他們在遇到矛盾與問題時都敢于反思、敢于面對,他們都不是孤立的個體與生命,而是融進暖暖的人間煙火氣中,融于中國傳統的家文化中,融于中國人吃苦耐勞、堅韌不拔的傳統美德中。
“電視劇的最終訴求就是以作品中蘊含的正確價值導向幫助現實中的人們走出困境,而要實現這種訴求就不得不提到認同心理的作用。認同心理一旦產生,觀眾就會設身處地投入作品中去感受、領會角色本身的喜怒哀樂,從而不自覺地對角色產生強烈的移情反應。”[3]
電視劇《人世間》透過這段真實的歷史再現,不僅表現了這段歷史的表象真實,更呈現了這段歷史表象真實背后的可以撫慰人心、引起共鳴、呈現生活、引領時代、展現中國人巨大生命力的精神追求。這才是作者創作這部溫暖的現實主義題材大劇的根本目的,同時,這也是這部現實主義題材大劇超越歷史的現實性內涵所在。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電視劇《人世間》是值得肯定和褒贊的。
二、有情有義 溫暖扎實地塑造人物
電視劇是塑造“人”的藝術。“人物作為基本的敘述動力元素,在電視劇敘事中有著十分重要的美學功能,眾多人物不僅構建了敘事中復雜的關系網絡,而且,人物本身作為視覺形象,就是一個電視劇敘事藝術的情感符號,一個蘊含著思想和意義的‘象征體’。”[4]
電視劇《人世間》放棄了年代劇、史詩劇的傳奇性,以最樸實、最平凡的普通人的生活為底本,把這種家長里短的“生活流”真實地融入時代洪流,把這群人在酸甜苦辣中的向陽而生真實地融于這“人世間”,這應該是這部劇最具吸引力的地方。真實、溫暖、向陽而生、生生不息,這應該是觀眾最熟悉的“人世間”,也是這部劇最令觀眾“破防”,可以吸引各個年齡層的觀眾的重要原因。
“敘事核心離不開對人物的塑造。在一部電視劇作品中,藝術思想是靈魂,人物則是創造與接受的主體。”[5]電視劇《人世間》以周家人為核心,周家人與“光子片”的“六小君子”的交映成為這部劇的敘事主體。他們這群溫暖、可親的形象真實普通得如同我們身邊的人,他們亦是可以折射出我們每個人的鏡子,傳達著有情有義的真善美,彰顯了這部現實主義史詩大劇的藝術高度。
這部劇善于從細碎的尋常生活中展現細膩的人物情感。這部劇所塑造的人物很難用“好”或者“壞”去做簡單的定義。導演李路曾說:“《人世間》的故事發展并不是靠情節去推動,而是靠生活中的點滴堆積。在宏大的背景下,圍繞著周家五口人的情感牽絆最打動人心。”[6]
周志剛作為周家的一家之主,也是新中國參與大三線建設的最普通的工人代表,他常年在外,與家人聚少離多。在他帶著三兄妹于春節拜訪親朋好友時,他的臉上和內心無比驕傲,他讓我們看到了一名老工人望子成龍的欣喜與炫耀。他與小兒子周秉昆在火車站的爭吵又呈現了他中國式家長的專制與獨斷。當他放棄休假跋山涉水去貴州看望“私奔”的女兒,當他為了迎接親家的到來放棄例行的拍全家福,當他與秉坤和解時……我們看到了一個立體、豐滿、有溫度、有缺點但敢于反思、敢于面對的普通大眾最熟悉的中國父親形象。
周家三兄妹在父親要做一個“好人”的教育下,呈現出三種不同的人生軌跡——黨的領導干部、高級知識分子、普通工人階級。周秉義是一個集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于一體的干部形象。初入岳父岳母家的他因為出身于工人階級而處處小心,但也是有理有節。他忠于自己的愛情,面臨金錢的誘惑他堅守黨的原則,因此獲得了岳父岳母的真心認可。作為黨的干部中的高級知識分子,他既有修身治國平天下的志向,也有面對困難迎難而上的決心和毅力,最終他成功成為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的好干部。電視劇對周蓉的塑造應該是這部劇為數不多的引發批評的地方。小說中的周蓉是一個極具浪漫主義色彩的女性,她不食人間煙火。在電視劇中,觀眾從她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霸道、清高、自私、獨斷、自我。為了追求自己心目中的愛情,她不顧及父母,不顧及兄弟姐妹,一切以自我為中心。即便后來成為大學教授,成為一名高級知識分子,她依然會清高地把丈夫、摯友送去的禮物要回,不顧及身邊人的感受。身為母親,她對自己的孩子也有很強的控制欲。但隨著孩子對她的冷漠態度和丈夫的離去,好友蔡曉光對她的關愛讓她一步步成長與反思,她努力與自己和解,與孩子和解,最終成長為一個柔軟的女性和春風化雨般的母親。
周秉昆應該是這部劇中人物刻畫的重中之重。劇中的人物關系網,包括父子、母子、夫妻、朋友,都由他發散開來,又交織在一起。他普通得就像我們身邊的人,他沒有哥哥姐姐那樣有出息,身為家里最小的“老疙瘩”,他始終陪伴在父母身邊,照顧著家人。他是一個最普通、最底層的工人,苦難仿佛成了他的生活最主要的底色,但他從來沒有改變善良、積極樂觀、真誠的本色。他是普通的,既要養家糊口又要顧及身邊的難兄難友。他是憨厚的,無論經營書店還是管理飯店,他都是踏踏實實、本本分分的。他是溫暖的,老母親醒過來時他喜極而泣,與父親和解時他感到釋然,自己的生活困難重重但依然對好朋友施以援手。同時,他也是笨拙的,不愛說話,總覺得自己不夠優秀,很倔地想向父親證明自己……。但他一直秉承著善良、真誠的原則,始終沒有偏離父親的教育所說的“要做一個好人”。
鄭娟也是該劇著力刻畫的人物。她賢惠善良,有時候有些懦弱。出身不好,沒有工作,但她用自己的善良和真心守護了周家的老小。很多觀眾感覺,她比較類似《渴望》中的劉慧芳,她們都具有中國女人尊老愛幼、默默付出的傳統美德,但鄭娟卻隨著生活和社會的發展,活出了與劉慧芳不一樣的堅韌與堅強。一直以來,鄭娟都是周秉昆背后溫暖的存在,但隨著秉昆入獄,二人的角色定位逐漸模糊,她開始像秉昆一樣負責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在接受幫助的時候,她也沒忘力所能及地幫助別人。在秉昆出獄后,面對發展飛速的社會,她有些頹喪,此時,二人的角色定位發生了反轉,二人形成了“錯位”搭配,她不再是他背后溫暖的、默默無聞的存在,而是堅強有力地開導秉坤,站在秉昆身邊保護陪伴著他。這種“錯位”互補的人物設定,使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立體、有血有肉。
電視劇還刻畫了周秉義的岳父岳母及曲書記等一批黨的高級干部,“光子片”的“六小君子”,商人駱士賓、彭心生等,這些人物有著各自的人生追求和價值體現,其中,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壞人”,他們的人生都體現著中國某個時代的歷史印記,他們都在時代發展中努力向前,生生不息。
劇中的每一個人都在過著平凡人的生活,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酸、甜、苦、辣、咸,他們積極樂觀地向陽而生。觀眾可以從一個個小家的成長與進步看到中國的發展,看到普通人的頑強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溫暖著我們每一個人。平凡最有力量,這或許是這部劇最成功的地方,這也是對現實主義題材作品品格的最好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