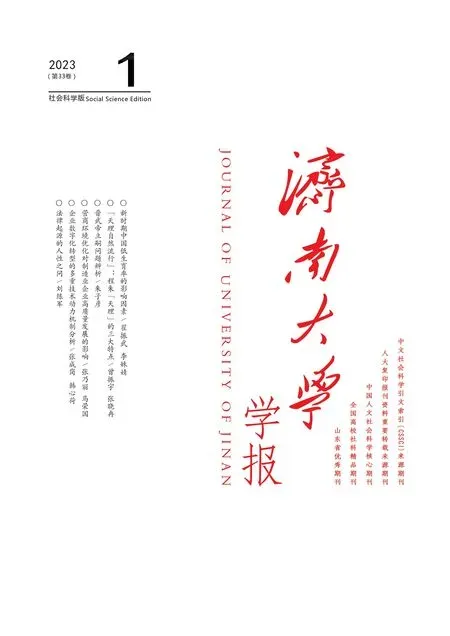出土文物與傳世文獻中半人半獸形象的演化及文化探原
張 兵,趙賢蓮
(1.濟南大學 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022;2.山東省出土文獻與文學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 250022)
半人半獸是出土文物中常見的藝術形象,在歷代傳世文獻中亦數見不鮮。關于此類人與獸組合而成的異獸形象的文化起源、心理根源及功用屬性,學界至今聚訟紛紜,未有定論。概而言之,大致有以下幾種觀點。關于其文化起源,其一,以圖騰理論釋之。一是認為半人半獸之神是由圖騰演化的圖騰神或圖騰祖先,獸即為原來的圖騰動物。二是認為半人半獸的實質是“半獸”圖騰,也即動物肢體圖騰,它的起源與人以動物肢體為飾有直接關系。三是認為半人半獸是人類社會由圖騰制轉向氏族制時,意識形態隨之轉變的結果,為氏族酋長與圖騰崇拜的復合體。四是認為半人半獸是按照圖騰祖先形象進行的“人的擬獸化”,人們繼而根據自己的模樣擬想始祖,造成“獸的擬人化”。其二,以“部落中心主義”釋之,認為半人半獸是古人受“部落中心主義”觀念的支配而產生的,對遠方民族荒唐想象習慣下的產物。關于其產生的心理根源,其一,認為“崇拜圖騰是導致半人半獸神產生的宗教心理根源,半人半獸是人與獸經過主體分解、組合創造的,是以人為主人獸結合的新觀念”(1)李景江:《論半人半獸神的心理根源》,《民族文學研究》,1987年第5期。。其二,認為半人半獸是“野性思維”調和“自然—文化”秩序過程的產物(2)韓鼎:《女媧“人首蛇身”形象的結構分析》,《廣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其三,認為半人半獸是一種心理投射,是在現實臨界意識的支配下塑造的非現實的神話人物(3)石峰:《臨界與神秘:神話中“半人”形象生成研究》,《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3期。。
此外,對于出土文物中某個或某類半人半獸形象,學界亦多有討論。如仰韶文化的人面魚紋、良渚文化的神人獸面紋、人面獸身的鎮墓獸、獸首人身的生肖俑等等的具象研究,觀點多樣,不勝枚舉。如楚式鎮墓獸,從其象征的神怪看,有山神、土伯、方相氏、宛奇、龍神、鹿神、死神、靈獸、巫覡、靈魂看守者、生命之神等說;從其作用看,有鎮墓辟邪、生命轉化、引魂升天、鎮攝人鬼等論;從其來源看,有楚人圖騰、楚人崇拜、楚人傳說、楚人巫術、楚人鬼神信仰等說。討論之熱烈,可見一斑。但目前學界對半人半獸的考察多為零篇散帙,大多集中于對《山海經》或單個出土器物的闡釋,未能將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緊密結合,對照比較,互為印證。此外,對于半人半獸藝術形象的萌芽、形成、發展、定型等演變過程亦缺乏系統性、條理性地整理和闡述。實際上,中國出土文物和傳世文獻中的半人半獸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呈現出了不同的造型方式和文化意蘊。探討其間經歷的傳承、變化和消失,對研究原始神話、原始宗教和原始心理及某些民間文學形式都有重要意義。
一、史前時代圖騰制的瓦解與半人半獸形象之萌芽
史前時代是指夏商周以前的未有文字記錄的原始社會。
(一)史前遺址中半人半獸的形象特征——由寫實到抽象
半人半獸的形象萌芽于新石器時代中晚期,這一階段中,半人半獸主要表現為人面與動物形軀的組合,紋樣簡單。分布地域從甘陜一帶延伸至余杭地區,不同區域發現的半人半獸在構形上存在明顯差異,種類和樣式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呈現出寫實到抽象的演化。
甘陜一帶半人半獸中的動物紋基本與日常生活相關,富于寫實,虛幻元素幾不可見。根據目前的考古資料,中國半人半獸的藝術形象最早出現于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的彩陶陶畫中。其形象表現為人面與魚紋合并在一起,人面作圓形或橢圓形,以魚飾口部或雙耳兩側,頂部為尖錐狀的簡化魚形。最先出土于距今約5600~6700年的西安半坡遺址,其后在臨潼姜寨遺址、寶雞北首嶺遺址、西鄉何家灣遺址的陶器圖案上都有發現。就目前刊布的材料統計,共出土半坡類型仰韶文化人面魚紋圖案12例(圖一)。新石器時代彩繪的半人半獸形象,除半坡類型的人面魚紋外,甘肅省武山縣西坪和傅家門遺址各出土一件人面鯢魚瓶,人首鯢魚身,張嘴露齒,左右胳膊伸出且四指張開,軀干呈“C”字形鋪展(圖二)。(4)甘肅省博物館:《甘肅古文化遺存》,《考古學報》,1960年第2期。湯池:《黃河流域的原始彩陶藝術》,《美術研究》,1982年第3期。此外,彩塑和陶塑類的半人半獸藝術形象亦有所發現,如陜西銅川前峁遺址出土的人首壁虎紋褐陶罐,人面五官剔刺而成,身似壁虎,上肢向上,下肢下彎,攀附于陶罐之上(圖三)(5)尚友德:《銅川前峁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報告》,《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2期。。以及甘肅寧定半山遺址出土的人首蛇身陶塑(圖四)和青海樂都柳灣遺址出土的陶塑人像和蟾蜍紋陶罐(圖五)(6)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灣——樂都柳灣原始社會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彩版二。。這些圖案中的紋樣基本為生活中常見的魚類或小型爬行動物,可見甘陜地區人獸結合的動物種類寫實傾向。
然在東南地區出土的半人半獸,其構形方式不再是人面紋與某一種寫實動物紋的簡單拼合,反而趨近程式化和抽象化。距今約4500~5200年的石家河文化遺址主要分布于長江中下游地區,出土玉器中的半人半獸以猛獸和禽鳥類多見。其寫實特征逐漸弱化、抽象特征逐漸凸顯,人面獸牙和鷹人合體等半人半獸的刻畫方式已傾向于抽象動物紋。如湖北省荊門市肖家屋脊遺址出土的齒民羽冠玉雕像,梭形眼,寬鼻梁,鼻尖向外突出,口的兩側各有一對獠牙,頭兩側上方有彎角形裝飾,角下方有兩道略向上卷的飛棱(圖六)。人面獸牙羽冠的刻畫運用平直纖細簡單的線條來勾勒,人面與獸面的界線模糊不清,二者渾然一體,使得其具有一定的抽象性(7)荊州博物館:《石家河文化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頁。。距今約4000~5000年的良渚文化遺址主要分布于浙江及周邊地區,出土了數量眾多的神人獸面紋樣。如余杭反山遺址出土的“琮王”神人獸面紋(圖七)、瑤山祭壇墓地出土的玉狀冠飾(圖八)、反山良渚墓地出土的玉璜和玉鉞(圖九)等。琮王神人的臉作倒梯形在上,頂部為放射狀羽冠,胸部以下既是神人應具的軀體,同時也是一種獸面(8)王明達:《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1期。。該獸形圖案以卷云紋和長短弧線刻畫而成,雖明顯具獠牙和趾爪等猛獸的特征,卻無法確認為何種動物的造像,故而整個圖案呈現出一種抽象感。

圖一 半坡類型仰韶文化人面魚紋圖案1-5、 西安半坡遺址出土 6-10、臨潼姜寨遺址出土 11、寶雞北首嶺遺址出土 12、西鄉何家灣遺址出土

圖二 人面鯢魚紋瓶1、武山縣西坪人面鯢魚紋瓶 2、武山傅家門人面鯢魚紋瓶

圖三 銅川前峁遺址紅陶罐浮雕人首壁虎身塑像

圖四 甘肅寧定半山遺址人首蛇身陶塑

圖五 青海樂都柳灣遺址陶塑人像和蟾蜍紋陶罐

圖六 湖北荊門肖家屋脊遺址齒民羽冠玉雕像

圖七 余杭反山遺址“琮王”神人獸面紋

圖八 瑤山“祭壇”墓地玉冠狀飾

圖九 反山良渚墓地1、玉璜 2、玉鉞
(二)史前半人半獸形象的功能意蘊——由紋飾審美到鎮墓安魂
史前文化遺址出土的與半人半獸有關的諸多文物表明,在上古文化信仰體系中,以人獸結合為母題的藝術形象在制度化的喪葬中已形成較為穩定、系統的組合主題。關于其功能意蘊,半人半獸在產生初期,當與史前陶器中常見的動植物紋、幾何紋一樣,是出于審美需要產生的藝術裝飾。
殉葬器一般是模仿實用器具的,原始社會人們基本上以日用器具殉葬。半人半獸的圖案多發現于陶盆、陶瓶、陶罐等生活用具之中,而日用器具上的紋飾最初是起裝飾作用的。在新石器時代早期,人們制作的陶器十分簡單粗糙,器身繪有紋飾的日用器具較為少見。如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距今約14000年)、陜西西鄉李家村文化遺址(距今7000年以上)、河南新鄭裴李崗文化遺址(距今約8000年)等出土的陶器,大多未見紋飾或少量有劃紋、繩紋、指甲紋、乳釘紋等簡單紋飾。隨著原始人思維的不斷發展,以及對自然的認知和理解的加深,審美意識逐漸萌生,人們開始有意識、有規則地在陶器表面刻畫、繪制紋飾。陶器開始出現寫實紋樣和簡單的線條紋飾,如魚紋、鳥紋、蛙紋、葉紋、水波紋等。而后在寫實紋樣的基礎之上,人們將動物紋、植物紋、編織紋變化為抽象的幾何形紋(圖十)。如在半坡類型的彩陶中,菱紋中對角十字方形圖案是魚頭的變化;黑白相間菱形十字紋、對向三角燕尾紋,是魚身的變化。此類幾何形紋還有:曲折紋、圓點紋、個字形紋、梯形鋸齒形紋、直線組合、顛倒的三角形組合等等。“彩陶作為人類史前時代最系統、最完整的物質文化創造,除了實用功能以外,可以說是一種最具有審美意識的創造。”(9)程金城:《遠古神韻:中國彩陶藝術論綱》,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4頁。史前陶器紋飾逐步發展的過程,說明原始社會日用器具上的圖案和紋樣最初是人們審美需要下的裝飾藝術。所以,半人半獸作為日用器具上的一種紋飾,在產生初期是一類單純的審美圖案,鮮明地反映著原始先民的美學追求。

裴李崗文化遺址的素陶 彩陶中的動物紋舉例 半坡彩陶中的幾何紋舉例圖十 史前陶器紋樣發展演示圖
隨著原始人在不同場合對彩陶的使用,半人半獸的紋飾逐漸由單一的審美圖案轉化為具有社會功用的文化符號。半人半獸在墓葬和祭壇遺址中的頻頻出現,也說明在原始時代,半人半獸的形象顯然不單是審美需要下的藝術裝飾,還是當時部落群體的一種象征符號,與當時人們的精神世界有著特殊的聯系。巴贊曾說,“先在宗教中繼而在藝術中給動物以重要的地位,是另一個特性,它將最早的文明與史前時代聯結起來。在原始人看來,獸的力量是神的力量之標志”(10)[法]巴贊(G.Bain):《藝術史 史前至現代》,劉明毅譯,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頁。。所以半人半獸應當象征著神靈。值得注意的是,半人半獸的圖案除在一般隨葬明器中出現外,半坡人面魚紋彩陶盆還作為覆蓋在兒童甕棺口上的葬具。當時人們在罐底和盆蓋中央都鉆有讓小孩靈魂出入的小孔,這表明半坡仰韶居民具有人死后靈魂不滅的觀念。他們很可能認為未成年的孩童靈魂較為弱小,無法對抗其他強大的惡靈,故而以具有神性的半人半獸圖案鎮壓可能危害死者靈魂的野鬼惡魂,同時安撫墓主靈魂,以免其滋生怨氣而為害生人。作為隨葬明器上的圖案,半人半獸的功能意蘊已由日用器具上的審美紋飾演化為墓葬之中鎮墓安魂的圖案。半人半獸的形象逐漸成為一種普遍意義上具有鎮墓安魂作用的明器紋飾,從而以不同形象廣泛運用于墓葬之中。史前時代,半人半獸在墓葬之中具有鎮墓安魂的作用基本成為共識,且在后來的發展中一直延續。
(三)史前半人半獸形象的文化探原——由圖騰信仰到人本初覺
關于中國史前文化的研究,對于其聚落形態、器物類型、生產方式、社會結構、埋葬習俗、物質文化等等,學界都有了相當深入的了解,但我們對史前的宗教觀念卻知之甚少。所以對于史前文化遺址中半人半獸組合的來源和含義,學界至今未有定論。考之西方學者關于原始社會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推知,半人半獸是原始信仰下的神祇,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圖騰崇拜瓦解的象征遺跡。人們在對自然具有一定的認識和支配能力之后,自我意識逐漸覺醒,從而創造了以人為主體的半人半獸這種由獸形神向人形神的過渡形式。
19世紀英國人類學家泰勒在研究原始文化現象時,提出了至今尚被許多學者所稱道并在一定范圍內沿用的“萬物有靈觀(Animism)”。他認為“萬物有靈觀既構成了蒙昧人的哲學基礎,同樣也構成了文明民族的哲學基礎”(11)[英]愛德華·泰勒:《原始文化》,連樹聲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49頁,第349-350頁。。萬物有靈觀的理論可以分解為兩個信條,“其中的第一條,包括各個生物的靈魂,這靈魂在肉體死亡或消滅之后能夠繼續存在;另一條則包括各個精靈本身,上升到威力強大的諸神行列,人們認為神靈影響或控制著物質世界的現象和人的今生和來世的生活,并且認為神靈和人是相通,人的一舉一動都可以引起神靈的高興或不悅;于是對他們存在的信仰就或早或晚自然地甚至可以說不可免地導致對它們的實際崇拜或希望得到它們的憐憫。這樣一來,充分發展起來的萬物有靈觀就包括了信奉靈魂和未來生活,信奉主管神和附屬神,這些信奉在實踐中化為某種實際的崇拜。”(12)[英]愛德華·泰勒:《原始文化》,連樹聲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49頁,第349-350頁。而人類所信奉的最初的神,就是被當作圖騰的動物。他們不僅相信自己與某一種類的動物之間存在著血緣關系,而且認為這種動物能給予這個氏族成員一切保護。“圖騰”本是美洲印第安奧吉布瓦的一個方言詞匯,意為“親屬”。圖騰崇拜的最主要特點是蒙昧部落認為自己與某一種動植物存在血緣聯系,部族成員禁止宰殺及傷害圖騰動植物,否則圖騰動物會向殺害它的同族血親——人——進行殘酷的報復。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方式從狩獵生產過渡到農耕與畜牧時代,人們對自然的控制能力加強,對周圍世界的看法也發生了改變。
人與動物關系的改變不僅促使了圖騰崇拜觀念的瓦解,而且推動了神的擬人化。當人們控制自然的能力加強,并意識到自我的優越性時,他們逐漸幻想過往那些使他們驚異的自然現象是由人的意識所引起的。他們把自己從動物中分化出來并擺在動物之上,另一方面原始人崇拜動物的心理圖式并未完全清除,仍存在借助動物威力加強自身力量的心理要求。這種以人為主體同時獲取動物威力的心理結構在想象領域重現,便創造出了半人半獸之形的神祇。歸根結底,是生產方式的改變導致了人與動物關系的改變,進而產生了以人為主人獸結合的半人半獸之神。半人半獸神不能等同于圖騰,圖騰是一個部落將某種動植物視為自己的血緣親屬,是一種血緣聯合體下對動植物的無條件崇拜。半人半獸之神則是出于對人的主體意識的肯定和對獲得動物威力下的神祇構想。
所以,史前文化遺址出土的半人半獸可以斷為先民圖騰信仰瓦解下產生的過渡性神祇,故而祭壇遺址中出現大量的半人半獸紋飾,亦在情理之中。而作為隨葬明器上的圖案,加之遠古先民靈魂不滅的生死觀,其在埋葬習俗中多半為守護神一類的角色,對于死亡的人具有鎮墓、安魂、護魂和超度的作用。
二、早期文化載體中神祇的構擬與半人半獸形象之發展
早期文化載體主要是指夏商周以來至秦漢時期的出土文獻、傳世文獻、出土文物等中涉及半人半獸形象的文化載體。
(一)早期文化載體中半人半獸的形象特征——由板滯到生動
隨著史前原始氏族公社階段的結束,中國進入有史可稽的文明時期。除傳世文獻中關于半人半獸的記載屢見不鮮外,半人半獸的形象在青銅器、玉器、陶器、木制漆器、壁畫、畫像石、畫像磚等出土實物中也屢有發現。商周和春秋戰國時期主要是青銅器和玉器、石器、陶器等性質的小型立體雕塑作品,其中有很多是禮器,有的是儀仗兵器。這一時期,半人半獸以人面與鳥、龍、蛇、虎、鹿等動物的組合為主。而秦漢時期的半人半獸多以平面圖像的方式呈現,在細節處理和紋飾上又常將多種不同動物的特征綜合于一體,使之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較之夏商周和春秋戰國時期的半人半獸形象作品遠為生動。其人體形貌與動物特征結合的自然、合理,充分顯示出秦漢時期藝術工匠非凡的藝術想象力和創造性。
在以半人半獸形象為題材的雕塑性質作品中,比較突出的一件是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所藏的安陽出土商代人面龍身盉(13)馬承源:《中國古代青銅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頁,第68頁。。盉的蓋子是一個浮雕的人面,額頭上有三道皺紋,頭頂兩側生有瓶形角。蓋、器紋飾相連,自人頭頂背后成為龍軀,盤繞于器腹,雙爪自兩側前伸,抱住盉的管狀流。在紋飾空隙處,填以夔龍紋。整個器物最為突出的是作為盉蓋的人面,其下頜與雙角突出于盉口之外,仰面朝天,面部表情呆滯,造型頗為呆板,缺乏生動的氣韻(圖十一)。類似的半人半獸造型的青銅器作品還有該館所收藏的商代鳥獸紋四足觥,其后足作饕餮食人的形象,人的下身作蛇軀,有鱗甲。以及湖南寧鄉黃村出土的禾大方鼎(圖十二)(14)馬承源:《中國古代青銅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頁,第68頁。和四川廣漢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兩件人首鳥身青銅像(圖十三)(1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頁、231頁。等。禾大方鼎四面以寫實的浮雕人面為裝飾,額左右有角,腮側有爪,雙目凝視,神態嚴肅。而諸如玉器、木制漆器類的半人半獸則有河南安陽婦好墓出土的人面蛇身紋玉人(圖十四)(16)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173頁。、陜西韓城梁帶村遺址M27墓室人龍合體佩(圖十五)(17)孫秉君,程蕊萍等:《陜西韓城梁帶村遺址M27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7年第6期。、黃君孟夫婦墓出土的人首蛇身環形玉飾(18)歐潭生:《春秋早期黃君孟夫婦墓發掘報告》,《考古》,1984年第4期。及已出土400余件的楚式鎮墓獸(圖十六)等等。雖然這些半人半獸形象的塑造已經具備粗輪廓的描繪,但對面部表情的塑造較為簡單,缺乏動態刻畫,精神面貌比較呆板,沒有生氣,給人以滯重僵硬的感覺。

圖十一 人面龍身盉

圖十二 禾大方鼎

圖十三 三星堆人首鳥身青銅像

圖十四 河南安陽婦好墓人面蛇身紋玉人

圖十五 陜西韓城梁帶村遺址M27墓室人龍合體佩

圖十六 江陵雨臺山楚墓楚式鎮墓獸
隨著雕塑和繪畫技藝的發展,秦漢時期半人半獸的塑造變得生動而富有活力,尤其是漢代祠堂和墓室的壁畫、畫像石、畫像磚上刻畫的半人半獸,形象簡潔精練,線條婉轉流暢,造型動態生動。如山東嘉祥武氏祠前室第二石第一層描繪的神話人物(19)朱錫祿:《武氏祠漢畫像石》,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頁。,居中的西王母肩生雙翼,盤腿而坐;圍繞在其身側各種姿態的羽人,人首、牛角、蛇身、有翼,或雙人首共一蛇身,或單人首雙蛇身(圖十七)。圖像采用上遠下近的等距離鳥瞰透視構圖法表現,將視點提高,沿縱深空間整齊排列同類事物的側面輪廓線,從而使畫面的三維空間得到更明確的體現。物象雖紛繁眾多,但其布局結構錯落有致、層次分明,給人紊而不亂,錯而不雜的感覺。此外,由于各部分恰當的比例以及弧線、直線的合理搭配,半人半獸的外形輪廓簡潔而不草率,單純而不刻板。因為在石頭上作畫,要表現人物面部的細微表情有一定的困難,所以工匠們著力于半人半獸的動態描繪,強調半人半獸的活動姿勢和速度。如沂南畫像石中的羽人(20)曾昭燏,蔣寶庚,黎忠義:《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北京: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出版,1956年版,第42-46頁。,騰空而飛,衣袂飄揚,即使是靜態的畫像,仍能使人感到其騰空飛翔之姿態(圖十八)。舉規的女媧、持矩的伏羲(圖十九)、手拿劍盾的人魚(圖二十),全都具有一種動勢和速度,各有一種動態的美、力量的美,加強了畫面的生動感。

圖十七 嘉祥武氏祠前室第二石(局部)

圖十八 沂南畫像石18幅

圖十九 嘉祥武氏祠左右室第四石伏羲女媧

圖二十 嘉祥武氏祠后石室第一石海神出戰
(二)早期文化載體中半人半獸形象的功能意蘊——由辟邪祈福到升天成仙
根據文獻資料記載,先秦時期半人半獸形象的屬性大多是神祇,諸如地域山神、天界神祇、四方神、月令之神等。《山海經》中稱“神”而為半人半獸的有46處,其中一部分為“其十神者,皆人面馬身”等統稱之語,故實際上半人半獸神共計有308個。《山海經》中共出現神祇384個,其中對其形貌有所描述的計有371個,所以《山海經》中形貌可知的神祇中半人半獸約占83%。半人半獸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中是神人的神異特征,那些造型為半人半獸的器物則是神權的象征。
上古先民將半人半獸的青銅器、玉雕、漆器置于墓葬中,旨在求得神靈佑護,開路辟邪,祛除惡鬼穢物,保護死者的靈魂不受侵擾,祈求平安幸福。在先秦的古籍文獻中,喪葬儀式中以半人半獸驅疫辟邪、送魂安魄,禮書記載甚詳。《周禮·夏官·方相氏》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驅疫。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驅方良。”鄭玄注曰:“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驅疫癘之鬼,如今魌頭。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兇惡也。”(21)(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851頁。方相氏身披熊皮,頭戴黃金四目面具,上著玄色,下穿紅裳,手持戈盾。簡而言之,即人面熊身,與半人半獸的形象極為相似。方相氏率領眾隸,索室驅疫。《釋名》云:“疫,役也。言有鬼行役。”(22)任繼昉:《釋名匯校》,濟南:齊魯書社, 2006年版,第37頁。所以疫指的是癘鬼。方相氏在墓室中以戈擊四隅,從而驅逐癘鬼、除祟祓邪。雕刻或繪有半人半獸的器物應當與方相氏一樣,皆是模擬或塑造半人半獸神的形貌以震懾惡鬼、驅疫辟邪。如楚式鎮墓獸,早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學者水野清一已考證其為“山神像”,或稱“鎮墓獸”,作用為鎮墓辟邪。(23)高崇文:《楚“鎮墓獸”為“祖重”解》,《文物》,2008年第9期。張正明先生在《楚文化志》中也說:“其意當為死者除惡辟邪以保佑其靈魂。”(24)張正明:《楚文化志》,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頁。所以先秦時期墓室中半人半獸的功用主要在于辟邪祈福。
戰國中期,《山海經》神話傳說中半人半獸的羽民、西王母等神祇逐漸演變為神仙信仰的仙人,成為仙界的一員。《楚辭·遠游》云:“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注曰:“《山海經》言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25)(漢)王逸撰,黃靈庚點校:《楚辭章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年版,第154頁。羽人儼然成了長生不老、生命永恒的仙人。秦漢之際,神仙方術盛行,半人半獸由神祇之狀過渡為仙人的形貌特征。王充在《論衡·無形》中說:“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為翼,行于云則增矣,千歲不死。”(26)(漢)王充著,張宗祥校注,鄭紹昌標點:《論衡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頁。認為仙人應當是全身長滿羽毛,雙臂變得像飛行的鳥翼。西漢時期,西王母融入了昆侖仙話系統,最終成為昆侖的主人。西王母和昆侖的結合體現了永生追求的象征意義。除其自身長壽、使人長壽的基本功能外,她還具有消除災難、保佑平安、繁衍子孫、獲取財富,甚至幫助死者靈魂升天的功能。這些功能在《漢書》《易林》及大量的銅鏡銘文中均有反映。如漢中平四年的銅鏡銘文有:“……早作明竟,買者大富,長宜子孫,延年命長,上如王父,西王母兮,大樂未央,長生大吉……”(27)劉俊艷:《試論古人樸素宇宙觀的形成過程》,《遺產與保護研究》,2018年第3卷第8期。所以漢代墓室中出現了大量以西王母為中心、以仙禽神獸為眷屬的導引升仙圖。以西王母為代表的半人半獸既保護著陰間的墓主,又成為其靈魂升天的引導者。
顧頡剛先生曾指出“古史往往是層累地造成的”,同理,半人半獸所具有的功能意蘊也是層累地形成的。其衍化出升天成仙這一功能不意味著鎮墓辟邪功用的失去,漢代墓室中的半人半獸既有與神仙信仰有關的仙人,也有鎮墓辟邪的守護神靈。
(三)早期文化載體中半人半獸形象的文化探原——祖先崇拜與仙神信仰
商代半人半獸造型的青銅器、玉器主要出自王陵和貴族的墓葬及祭祀坑遺址,同時埋入的還有數以百計的人牲和殉人。商代的宗教觀念,正如《禮記·表記》所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先罰而后賞,尊而不親。”(28)(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吳友仁整理:《禮記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8頁。在尊神重鬼觀念的影響下,對于日月星辰、風雨雷電、山川土地諸神和祖先神的崇拜和祭祀活動,成為商周及春秋戰國時期宗教的重要內容,是“國之大事”。對于祖先神的崇拜和祭祀,是維系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統治集團內部穩定所必須的心理支柱,特別為統治者所重視,對不同對象規定了不同的、名目繁多的祭祀禮儀形式。半人半獸形象即是古人祖先崇拜觀念的反映。
祖先崇拜觀念所內含的實質性關系,在于古人與今人、死人與活人、活人與活人之間的關系。(29)錢杭:《周代宗法制度史》,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頁。甲骨卜辭中常有“咸賓于帝”之語,可知死去的先王、先妣也能賓于帝所,成為人間統治者與天帝的中介。在殷人看來,祖先既然孕育了子孫,那么出于血緣的聯結,子孫將會受到祖先神靈的保佑。但保佑不是完全受今人和活人控制的、對他們的愿望百依百順的、并抹煞祖先任何自主性的外在力量,也表現為對偏離宗族原則的言行進行譴告和懲罰。比如“先后丕降與汝罪疾……自上其罰汝”(30)李民,王健:《尚書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頁,第149頁。,甚至“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天毒降災荒殷邦”(31)李民,王健:《尚書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頁,第149頁。。這種類似“反向制約”的保佑,是人們對祖先神權的威力更切實的認識。換言之,由于祖先崇拜而興盛的“鬼治主義”,在某種程度上使死人掌握了活人的命運。所以統治者在碰到需要做出抉擇的事情,都要通過甲骨占卜,請示上帝和先王后,才能做出符合權威的相應決策。同時需要按時舉行各種祭祀儀式,才能求得祖先神靈的佑護。而半人半獸作為隨葬明器和祭祀禮器中象征神祇的器物,是先民在祖先崇拜心理之下產生的辟邪祈福之物。一是在喪葬中驅逐癘鬼、除祟祓邪,使祖先死后能居于舒適祥和的幽冥世界;二是在前者的基礎上,祈求祖先護佑。半人半獸中祖先崇拜的特質還體現于對遠古始祖的尊崇,如漢代墓室中廣泛出現的伏羲女媧圖像。
仙神信仰也是早期社會一個重要特征。商代人們由多神信仰發展至對于至上神——天帝的崇拜,而仙人世界是在戰國中期才開始出現、到西漢晚期才終于確立起來的宇宙觀念。在古代特別是在漢代人的觀念中,“仙”與“神”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存在。根據《說文解字》的解釋,“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32)(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頁,第165頁。。也就是說住在天上世界的上帝和諸神,不僅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也是宇宙秩序的管理者和主宰者。對人類來說,上帝和諸神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是超越時間和空間的、無始無終的終極存在。而仙人,卻與“神”有著本質的區別。在《說文解字》中,“仙”字有“仚”和“僊”兩種寫法,“仚,人在山上”,“僊,長生僊去”(33)(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頁,第165頁。。《釋名·釋長幼》解釋說:“老而不死謂之仙,仙,遷也,遷入山也。”(34)任繼昉:《釋名匯校》,第152頁。從這些漢代人的解釋,可以知道當時人們的觀念中,所謂仙人,是同時具有超越時間和空間的不死不老的神性和人的肉體的永恒存在,其住處不是天上世界,而是高高聳立在現實人間世界的仙山。生活在凡間的人,盡管不能升天與諸神齊壽,但卻能以“死”的形式擺脫苦難的現實世界,暫時棲身到地下的鬼魂世界,在那里獲得升仙資格后,飛升到昆侖仙界,在那里長生不老,永遠過著無憂無慮的幸福生活。
所以,在天帝崇拜的宗教觀念下,《山海經》《國語》《墨子》等文獻中記載的半人半獸的屬性多為供天帝驅使的四方神、地域山神和氣象之神等,是墓葬中鎮墓辟邪的守護神。然而隨著仙人世界的建立,半人半獸逐漸演變為升仙信仰中的仙人,成為幫助死者靈魂升天的引導者。這說明半人半獸的性質和功用與當時人們的宗教信仰和宇宙觀念密切相關。
三、中期多元宗教信仰下妖精鬼怪的塑造與半人半獸形象之變化
中期是指魏晉南北朝時期。
(一)中期文獻及墓葬中半人半獸的形象特征——祥和與獰厲
魏晉南北朝之際,各地區的壁畫墓、畫像石墓、畫像磚墓(35)下文敘述著重于墓葬中的半人半獸形象,對其載體方式不做細究。因而據鄭巖《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所述取“壁畫”廣義,指各種形式的壁面裝飾,如磚雕、模印磚、線刻畫、彩繪畫像等包括在內統稱為壁畫。及敦煌石窟中皆出現了大量的半人半獸形象。中原戰亂頻仍,國力疲弊,曹魏以下各代明令葬事從簡,故而中原地區這一時期壁畫墓資料不多。屬于魏晉時期的壁畫墓較多地發現于甘肅東起永昌西至敦煌的河西走廊中西部,主要有嘉峪關新城墓群、酒泉干骨崖古墓群、單墩子灘墓群、果園鄉西溝墓群、佘家壩墓群、崔家灣墓群、丁家閘墓群、佛爺廟灣古墓群等(36)鄭巖:《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39頁。。這些墓葬中有的繪有通壁的大幅壁畫,有的為彩繪畫像磚,還有極少量單繪墨線而不著色的畫像磚。
墓室壁畫中半人半獸的形象不在少數,大多線條纖細流暢,色彩豐富和諧,圖像精美細膩。造型講究氣韻生動和以形寫神,突出強調半人半獸的形態特征和氣韻。如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中描繪的雞首人身像和牛首人身像(37)甘肅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頁。,牛首南向,張口,雞首西向,皆身著圓領袍服,雙手執笏。雙目炯然,生動傳神,面部神態刻畫細微,服飾以數道弧線刻畫出拱手之狀(圖二十一)。整塊畫像磚中部為仿木門楣,周邊描以云氣紋,將半人半獸呈現為靈隱神俊、藹然和善之態。其他諸如羽人(圖二十二)、人面龍身神獸和熊面人身力士(圖二十三)等皆以流暢準確的細線條表現其飄雋或雄健,畫面生趣盎然而不失祥和之感。敦煌石窟壁畫中半人半獸的繪畫技法更趨成熟多樣,造型自由奔放,重色塊輕線條。多以土紅色線條進行構圖起稿,上色后再以墨線勾勒出外輪廓,線條行云流水,波蕩起伏。在色彩應用和表現手法上多用同一顏色不同純度的色彩進行暈染,以表現面部的立體感及形體的凹凸,色彩對比鮮明,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黃、赤、藍等暖色的大面積渲染,及三維立體的空間布局,使半人半獸給人祥和寧靜的感覺。如西魏249窟的千秋鳥(圖二十四)、烏獲(圖二十五)、開明神獸(圖二十六)等等(38)吳健:《中國敦煌壁畫全集》(西魏卷),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年版,第78-87頁。,千秋鳥人首鳥身,展翅飛翔,雙翼和尾羽的線條秀麗瀟灑,周邊繪有從下往上流動的云氣,為千秋鳥飛翔時的動態感平添傳神之筆。加之面目從容祥和,整體色調單純溫暖,給人美好祥和之感。

圖二十一 雞首人身、牛首人身

圖二十二 羽人

圖二十三 熊面人身

圖二十四 西魏-249窟千秋鳥

圖二十五 西魏-249窟烏獲

圖二十六 西魏-249窟開明神獸
中原地區雖然壁畫墓的資料不多,但在墓葬中卻發現了大量半人半獸的人面鎮墓獸陶俑。與壁畫中半人半獸所呈現的祥和安寧不同,人面鎮墓獸給人的感受是獰厲、神秘和嚴冷。人面鎮墓獸往往面部猙獰可怖,獸身的塑造集多種動物特征于一體,整體顯得怪異詭譎。人面鎮墓獸根據體態姿勢的不同可以分為蹲坐狀、四足直立狀和伏臥狀三式,這三類的造型皆為兇惡可怖之狀。如洛陽北魏元邵墓出土的人面鎮墓獸,呈蹲坐狀,有底座,面部兇惡猙獰,頭生獨角,背脊豎有三撮鬃毛,前肢上部兩側長毛卷曲,上繪紅彩(圖二十七)(39)黃明蘭:《洛陽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第4期。。山西大同云波路北魏墓M10出土的人面鎮墓獸為四足直立的姿態,頭部略下垂,頭戴小黑帽,大耳,彎眉,鼻子高闊,“八”字胡,臉部涂紅,腹部中空,背有長方形孔應為插鬃毛之孔,長尾從后方繞起搭在獸脊背上,尾端分叉,獸身先涂白,繪黑線,后紅色彩繪,形象詭怪(40)張志忠、古順芳等:《山西大同云波路北魏墓(M10)發掘簡報》,《文物》,2017年第11期。。至于伏臥狀,西安南郊的北魏墓M4、M5,北周墓M3,以及西魏吐谷渾公主與茹茹大將軍合葬墓等等,均出土了伏臥狀的人面鎮墓獸。西魏吐谷渾公主與茹茹大將軍墓中的人面獸身鎮墓獸,一件雙目圓睜,怒視前方,四腿粗壯勁健,曲折前伸著地,原均涂白彩,再施紅彩,多已脫落;一件闊口獠牙,仰面朝天,顴骨高凸,額上獨角已殘斷,脊背有櫛齒狀鬃毛后斜刺(圖三十)(41)劉呆運,程旭等:《陜西西安西魏吐谷渾公主與茹茹大將軍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9年第4期。。其神情獰厲可怖之狀和色彩強烈對比所形成的詭怪氛圍,令人感到精神上無名的壓迫感。
(二)中期文獻及墓葬中半人半獸形象的功能意蘊——導引升仙與執守冥界
魏晉南北朝時期,墓葬中以西王母主題為依托的半人半獸圖像組合比之漢代漸趨衰落。但以羽人、千秋鳥為代表的半人半獸仍是神仙體系中的仙人,《神仙傳·彭祖傳》說:“仙人者,或竦身入云,無翅而飛,或駕龍乘云,上造天階,或化為鳥獸,浮游青云,……或隱身于草野之間,面生異骨,體有奇毛,……。”(42)(東晉)葛洪:《神仙傳》,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6頁。,面有異骨,體有奇毛,即指仙人的形貌不同于凡人。《抱樸子·對俗》中描述:“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43)(東晉)葛洪:《抱樸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頁,第11頁。壁畫墓中的羽人即身生羽翼,而人身獸首、頭頂牛角、雙肩生翼的烏獲,九首人面獸身的開明獸等半人半獸形象顯然更是異于常人之形,所以壁畫墓中祥和的半人半獸當是仙官或仙禽神獸一類。

圖二十七 洛陽北魏元邵墓人面鎮墓獸

圖二十八 山西太原北齊婁叡墓人面鎮墓獸

圖二十九 山西大同云波路北魏墓M10人面鎮墓獸

圖三十 陜西西安西魏吐谷渾公主與茹茹大將軍合葬墓人面鎮墓獸
人們在墓室中繪制此類半人半獸,目的在于希望這些仙人能夠迎接墓主前往仙界,升天成仙,獲得長生。根據文獻資料記載,這一時期人們的修仙途徑大致可以分為服食煉丹、修煉道術、仙人指點、積善濟世四類。當修成得道之后,最終或飛升登仙,或隱化仙去,或尸解成仙。葛洪在《抱樸子·論仙》中明確提出:“上士舉行升虛,謂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蛻,謂之尸解仙。”(44)(東晉)葛洪:《抱樸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頁,第11頁。可知成仙模式中以飛升成仙為上品,而飛升的方式又可分為或只憑己力白日飛升,或乘云駕龍、騎虎化鶴,或由仙官相迎、奇禽異獸開路。在壁畫中繪制羽人、熊面人身力士、開明獸等半人半獸,即是希望通過仙人迎接、神獸開道的方式引導墓主升天成仙。《神仙傳·茅君》描寫茅君升天時的情景云:“明日迎官來至,文官則朱衣紫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旌旗,器仗耀日,千余人。茅君乃與父母宗親辭別,乃登羽蓋車而去,麾幛幡蓋,旌節旄鉞,如帝王也,驂駕龍虎麒麟白鶴獅子,奇獸異禽,不可名識。飛鳥數萬,翔覆其上。流云彩霞霏霏,統其左右。去家十余里,忽然不見,觀者莫不嘆息。”(45)(東晉)葛洪:《神仙傳》,第67頁。可見茅君升仙的方式是由仙人迎接引渡到仙界,瑞氣祥云,聲勢浩大,與墓葬壁畫中所繪之景極為相似,故而墓室中描繪的也是仙人迎接墓主升仙的景象。

(三)中期文獻及墓葬中半人半獸形象的文化探原——民族融合與多元宗教信仰
在魏晉南北朝墓葬體系中,祥和的半人半獸圖像和獰厲的人面鎮墓獸陶俑并非兩個完全對立的文化對象。如太原南郊金勝村第一熱電廠北齊壁畫墓,不僅四壁繪制的導引升仙圖中有羽人、千秋萬歲鳥等祥瑞的半人半獸,還出土了一件人首獸身的鎮墓獸陶俑。這兩類看似矛盾的半人半獸的出現既與當時多民族融合的社會現實直接相關,同時也是儒、玄、道、佛等多元宗教信仰交相滲透與影響的結果。
隨著以鮮卑、匈奴、羯、氐、羌為主的北方少數民族不斷大規模向內地遷徙,各民族文化在沖突中不斷融合。前文已提及人面鎮墓獸最早是以圖像的形式出現在北魏早期的鮮卑破多羅氏墓中,“由于這種陶俑和鎮墓獸共出且只見于鮮卑政權控制下的關中地區,我們懷疑這種鎮墓獸的形象源自鮮卑民族特色,后來由北魏掌握的關中漢人工匠生產為陶俑。”(48)韋正、劉繹一:《中古北方地區鎮墓神物的文化構成和變化機制》,《考古與文物》,2020年第3期。已有考古資料證明,鮮卑族原本沒有隨葬鎮墓俑獸的習俗,北魏建立初期其喪葬習俗以鮮卑族自身特點和對其影響較大的匈奴的特點為主。(49)金愛秀:《北魏喪葬制度探討》,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隨著鮮卑族漢化程度的加深,其墓葬中逐漸出現鎮墓獸陶俑。而將陶俑殉葬以鎮墓的葬俗源自華夏,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孟子》《禮記》中就已出現了關于俑的明確記載。如《禮記·檀弓》云:“涂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小仁’。”鄭玄注曰:“俑,偶人也,有面目肌發,有似于生人。”(50)(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吳友仁整理:《禮記正義》,第377頁。由此看來,拓跋鮮卑等少數民族利用漢文化構建自己的墓葬文化體系,從而形成了此類半人半獸的人面鎮墓獸陶俑。此外,許多人面鎮墓獸的人面為胡人形象,高目深鼻,面部多胡須,具有典型的胡人特點(圖二十八)。均說明此時墓葬中的人面鎮墓獸,應當是拓跋鮮卑族群與漢文化密切接觸、磨合在喪葬文化方面的表現。
由于戰亂不斷,朝代更替頻繁,社會動蕩不安,上至權貴名士,下至平民百姓,皆追求長生升仙之道。《魏書·釋老志》記載,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天興中,儀曹郎董謐因獻服食仙經數十篇,于是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煉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51)(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049頁。可見人們求仙愿望之強烈。人們不僅夢想生時成仙,更希望死后能進入仙界。魏晉南北朝的神仙信仰比漢代復雜化,一是其開始以道教的形式出現,形成了以仙神信仰為核心,參雜陰陽五行思想、巫術行為、佛教儀式的神仙道教;二是神仙信仰開始滲入儒家的仁義忠孝、天命觀和佛教的輪回報應觀等觀念。所以作為仙府祥瑞的四神、飛仙等符號和獅紋、寶相花等佛教元素開始混雜,反映在同一墓葬或圖像之中。如敦煌石窟中千秋鳥和九頭人面開明獸的人首皆為光頭,雙耳較大,顯為佛教人物的特征;太原南郊北齊壁畫墓中導引升仙圖的空隙處以寶相花作點綴,皆表明此時的升仙信仰已演變為多元宗教雜糅。
另外,至魏晉時期,人們對死后世界的構想也更為立體明晰,據葛洪《枕中書》描述:“鮑靚為地下主者,帶潛山真人。蔡郁壘為東方鬼帝,治桃止山。張衡、楊云為北方鬼帝,治羅酆山。杜子仁為南方鬼帝,治羅浮山。周乞、嵇康為中央鬼帝,治抱犢山。趙文和、趙真人為西方鬼帝,治潘冢山。”(52)(東晉)葛洪:《枕中書》,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5頁。五鬼帝的建構和佛教的十八層地獄、十殿閻王等觀念讓人們相信人死后會以鬼魂的形式繼續在另一個世界生活。為了讓死者在冥界不為邪祟厲鬼所害,人們便將獰厲的鎮墓獸置于墓室守護墓主,震懾惡鬼。
四、后世堪輿術盛行下的明器神煞與半人半獸之定型
后世是指隋唐五代至南宋末期。
(一)后世文獻及墓葬中半人半獸的形象特征——由兇惡到謙恭
據歷史文獻記載,隋朝建立后創制的禮儀制度與北朝存在著明顯的承繼關系。《隋書·禮儀志》云:“開皇初,高祖思定典禮。……弘因奏征學者,撰儀禮百卷。悉用東齊《儀注》以為準,亦微采王儉禮。修畢,上之,詔遂班天下,咸使遵用焉。”(53)(唐)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版,1973年版,第156頁。此已確鑿載明,隋朝各種制度禮儀,是承襲北齊與梁的。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隋朝墓葬中半人半獸的形象不可避免地保留了北齊與梁人面鎮墓獸的造型特征。
隋唐時期,兩京地區、華北地區、長江中游和新疆吐魯番等區域均出土了大量人面鎮墓獸陶俑。造型大體沿用北朝的樣式,同時又有新的發展。一是主體造型上的演變,包括整體姿態、頭部、足部的變化。如四足直立和伏臥狀的人面鎮墓獸已不見,基本為蹲坐狀,盛唐時期出現弓步狀。二是附屬裝飾的變化,包括角、戟形飾、鬃毛、肩部羽翼、火焰等等。隋到盛唐人面鎮墓獸頭部、肩部、背部的裝飾由簡單到復雜,中晚唐又回歸相對簡略的造型。雖然不同時期和地域的人面鎮墓獸在造型上或有細微的差別,但其風格均為兇惡可怖、面目猙獰。或濃眉大眼,顴骨突出,嘴角下咧,神情兇神惡煞;或突目高鼻,獠牙外露,表情兇狠。如合肥西郊隋墓出土的人面鎮墓獸,“呈蹲坐狀,頭戴圓形小冠,頂有三小孔,為插裝飾的殘跡。豎眉圓鼻,高鼻梁獅形鼻,兩腮肌肉凸起,嘴角下斜,構成一副兇氣逼人的面孔。”(圖三十二)(54)胡悅謙:《合肥西郊隋墓》,《考古》,1976年第2期。又如西安郊區隋唐墓V型人面鎮墓獸,雙目圓瞪,闊嘴獠牙,面容兇悍,張牙舞爪,弓步站立,手中握蛇,腳踩怪獸,整個形態顯得更為兇猛(圖三十三)。

圖三十一 安陽隋張盛墓

圖三十二 合肥西郊隋墓

圖三十三 西安郊區隋唐墓V型人面鎮墓獸
隋唐至宋末,墓葬中出現的半人半獸還有獸首人身型的生肖俑、雙人首蛇身俑、人魚俑、人鳥俑、人首龍身俑、人首鱉身俑等等。這些半人半獸不同于人面鎮墓獸的猙獰可怖,反而皆面目平和,姿態謙恭。如湖南長沙成嘉湖唐墓出土的生肖俑,均為禽獸首人身,身穿寬邊披大袖服,昂頭平視,表情溫和,雙手執笏盤膝而坐,恭而有禮(圖三十四)(55)熊傳新,陳慰民:《湖南長沙成嘉湖唐墓發掘簡報》,《考古》,1980年第6期。。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出土的人鳥俑,上身作人形,神情親切,頭束高髻,身著對襟闊袖衣,揖手于胸前,謙遜恭敬;下身為鳥形,有羽毛,尾上翹,下連圓形座(圖三十六)(56)辛明偉,李振奇:《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文物》,1993年第6期。。南唐李璟墓出土的人魚俑作伏臥狀,延頸昂首,光頭,臉龐豐滿,注目前視,抿嘴斂唇,嘴角內凹,表情和善;自頸以下為魚身,周身布滿淺刻的圓形鱗片,脊鰭聳立,魚翅明顯,胸鰭向兩側張開,臀鰭后收,給人一種恭敬虔誠的感覺(圖三十八)(57)南京博物院:《南唐二陵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年版,第72頁,第74頁。。江蘇南京南唐烈祖李昪欽陵出土的雙人首蛇身俑,呈雙體相背臥伏纏繞狀,兩人首皆髡發,光頭相背昂起,隆額圓臉,曲眉大眼,闊鼻抿嘴,眼含笑意(圖三十九)(58)南京博物院:《南唐二陵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年版,第72頁,第74頁。。“于南唐烈祖李昪欽陵的這件雙體人首蛇身的墓龍俑,雖然奇異,面目卻是一副善相,并不令人望而生畏,反倒感到和藹可親,富有人情味。”(59)曹者祉,孫秉根:《中國古代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頁。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此類半人半獸俑或許因時地不同而形制有所差異,但其神態基本為謙恭之狀。

圖三十五 遼寧朝陽黃河路唐墓生肖俑

圖三十六 河北南和唐郭祥墓人鳥俑

圖三十七 湖南長沙牛角塘唐墓M1雙人首蛇身俑

圖三十八 南唐李璟墓人魚俑

圖三十九 南唐李昪墓雙人首蛇身俑
(二)后世文獻及墓葬中半人半獸的功能意蘊——由鎮守門戶到福佑子孫
隋唐時期,人面鎮墓獸的造型和擺放形制與北朝一致,均是放于墓門兩側,故而其在墓葬中的功用亦是作為保護神,為墓主鎮守門戶,驅鬼除邪,確保墓室的安寧。《舊唐書·玄宗紀上》記載:“然則魂魄歸天,明精誠之已遠;卜宅於地,蓋思慕之所存。古者不封,未為非達。且墓為真宅,自有便房。今乃別造田園,名為下帳。又明器等物,皆競驕侈。”(60)(后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74頁。可知在人們對陰間世界的構想中,墓室被視作真宅或陰宅。人死后靈魂不滅,繼續在陰間世界生活。而在古人心目中,始終不可避免地對陰間世界存在恐畏心理,害怕陰間各種鬼魅惡邪作祟于死者。因此,人們將人面鎮墓獸放置在墓葬中,以期對地下的惡鬼妖怪加以鎮壓避邪,起到護衛的作用。唐人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羊虎”條記載:“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馬之屬,人臣墓則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屬,皆所以表飾墳壟,如生前之儀衛耳。”書中又引《風俗通》說:“墓上樹柏,路頭石虎,《周禮》‘方相氏葬曰入壙,驅魍象’,魍象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側以禁御之,而魍象畏虎與柏,故墓前立虎與柏。”(61)(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2-83頁。這段記載將古人畏魍象等鬼怪危害死者,而以驅鬼除邪之物立于墓側護衛墓主的心理講述得十分清楚,鎮墓獸的作用據此可明。
關于唐宋時期葬俗的理論書籍并不鮮見,《新唐書·藝文志》中和喪葬直接相關的書目多達幾十卷,如《葬經》《葬書地脈經》《墓書五陰經》等。這些書籍大多亡佚,目前能見到的是成書于金元時期而被《永樂大典》收錄的《大漢原陵秘葬經》。該書假托授自婁敬而冠以“大漢”之名,實則記錄的是宋金元時期的葬俗。雖未將唐收錄其中,但唐宋相似,據宋也可窺見其神煞制度之端倪。徐蘋芳先生根據《秘葬經》所記各種明器,指出人魚俑即儀魚,人鳥俑即觀風鳥,雙人首蛇身俑即墓龍。面對陰間世界的各種神靈鬼怪,人們一方面要對地下的惡鬼妖怪加以鎮壓避兇,一方面力圖祥瑞求吉,得到神靈的庇佑,為死者攘災解禍,祝生人吉利,子孫得福。唐宋墓葬中一套完整的十二生肖俑,加上人魚俑、人鳥俑、雙人首蛇身俑、人首龍身俑、鱉形俑、朱雀、玄武、青龍、白虎等等,正好是一套伴隨著道教盛行而出現的明器神煞,旨在為逝者解謫、為生者除殃,福佑子孫。
關于這些明器神煞俑的功用,《秘葬經》中有明確記載,書序云:“頃余因暇日,述斯文五十四篇,分為十卷。備陳奧旨直說,內為萬代之樞機,作后人之明鏡。吉兇征驗,祥究皆知。官祿貧窮,三陽內顯,子孫多少,高低興旺,造化修展。”又言:“凡大葬后,墓內不立盟器神煞,亡靈不安,天曹不管,地府不收,恍惚不定,生人不吉,大殃咎也。”(62)(明)解縉等:《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828-3829頁。由此可知,明器神煞的放置不僅關系死者亡靈的安寧,還會影響后代子孫的吉兇禍福。所以人們在墓葬中置放各式明器神煞,以構造藏風納氣的吉葬格局,聚斂生氣滋養先人魂神,從而使墓葬趨吉避邪,致福子孫。此類用明器布局墓室風水以求吉招福的做法,在出土文物的石刻文字中有詳細的記載。如四川彭縣發現的宋墓中有兩塊鎮墓石,置于腰坑之上,其一曰:“趙公明,字都□,□□□□之中,鎮壓壽堂之內。□禁□忌,五土之精。轉禍為福,改災為祥。伏祈□佑男生胡□壽堂遐齡,兼附亡室杜氏道喜娘子幽室一所,各引旺氣入穴。一枕來崗,永遠千福。□外邦于他方,納吉祥□□□。”(63)徐蘋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秘葬經〉札記》,《考古》,1963年第2期。這段文字直接言明鎮墓石的作用在于引旺氣入穴,求吉納福,利及子孫,明器神煞俑大抵亦是如此。
(三)后世文獻及墓葬中半人半獸形象的文化探原——禮樂文化與堪輿方術
唐宋時期,隨著儒學的發展,儒學道統得以確立,禮樂文化得到重視。在儒家的禮樂文化中,禮是社會等級的劃分原則。《禮記·曲禮》云:“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64)(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吳友仁整理:《禮記正義》,第13頁,第6-7頁。無“別”,則無秩序。故而不同等級的喪葬活動要嚴格按照禮的規定進行,不允許僭越。器以藏禮,死者入葬時所用的明器,須依生前的品級而有所不同。《唐會要》卷三十八葬葬條記載:“(元和)六年十二月條流文武官及庶人喪葬,三品以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五品以上明器六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九品以上明器四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以前明器并用瓦木為之,四神不得過一尺,余人物不得過七寸。……庶人明器一十五事……四神十二時各儀,請不置,所造明器并令用瓦,不得高七寸。”(65)(宋)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814頁。可見品級不同的官員或庶人,其所隨葬的半人半獸俑的數量和尺寸大小皆各不相同。對此,筆者亦有“唐宋墓葬中半人半獸形象出土信息一覽表”為證,另有撰文刊出。
儒家認為,有禮必有敬。恭敬是禮所傳達的基本精神,是禮應有之義。《禮記·曲禮》開篇即云:“毋不敬,”鄭玄注:“禮主于敬。”孔穎達疏:“然五禮皆以拜為敬禮,則‘祭極敬’、主人拜尸之類,是吉禮須敬也。‘拜而后稽顙’之類,是兇禮須敬也。‘主人拜迎賓’之類,是賓禮須敬也。軍中之拜、肅拜之類,是軍禮須敬也。冠、昏、飲酒,皆有賓主拜答之類,是嘉禮須敬也。”(66)(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吳友仁整理:《禮記正義》,第13頁,第6-7頁。“敬”是行禮者行為和心態的統一,行禮要敬重、謙恭。在心態上,儒家強調恭敬必須是發自內心的真實情感,若僅僅是流于禮儀形式,就不算恭敬。在行為上,禮是“治躬”的,它教人“正容體,齊顏色”,一舉一動都要符合禮義道德的規范,在行動和外貌上做到“莊敬恭順”。宋代呂祖謙麗澤書院學規為:“會講之容,端而肅;群居之容,和而莊。(箕踞、跛倚,喧嘩、擁并,謂之不肅;狎侮、戲謔,謂之不莊。)”(67)(宋)呂祖謙:《呂東萊文集》第四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247頁。可知唐宋時期人們極為注重儀態的端莊有禮。在這種文化環境的影響下,墓葬中的半人半獸也表現出禮樂文化所倡導的恭敬謙遜、敦睦親和,多為謙恭之態,以示對死者的敬重。
唐宋時期,堪輿之術、風水地理之說大為流行,對葬俗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百姓,無不熱衷于風水相墓之術。《舊唐書·呂才傳》曾記載“暨乎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生死。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兇,拘而多忌。”(68)(后晉)劉昫等:《舊唐書》,第2725頁。可見唐代葬書之盛、風水之興。堪輿術家認為陽宅和陰宅風水的好壞,均關乎生人的吉兇休咎。早期的相地術,以觀察地形為主,占卜吉兇為輔。至陰陽五行學說盛行,相地術與天體運行相聯系,產生了“黃道”“太歲”“月建”等宜忌。同時,出現了陰宅位置關乎子孫后代命運的觀念。堪輿術除承襲陰陽五行、天人感應諸法外,尤其講究審視山川形勢和墓穴、宮勢的方位、向背及排列結構,葬地的選擇越來越受重視。晉代托名郭璞的《葬書》,明確提出“乘生氣”之說,認為死者的骸骨可通過土中的“生氣”勃勃與在世的子孫產生感應,從而左右他們的命運。(69)鄭謐注釋;吳澄刪定:《劉江東家藏善本葬書》,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2-5頁。其說為唐宋術家所尊奉,附會出極為復雜的理論體系,助長了厚葬的習俗。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隨葬俑的放置顯得尤為重要,術家根據陰陽五行將其置于墓葬之中以合于墓室方位與墓主氣場,構造斂氣之風水,從而使“生氣”生生不息,福佑子孫。
在儒家禮樂文化、道教風水堪輿之外,佛教的文化元素在唐宋墓葬的半人半獸中亦頗為常見,如人面鎮墓獸手中握蛇、腳踩怪獸、弓步站立的造型來自佛教天王,南唐李璟墓出土的人魚俑、李昪墓中的雙人首蛇身俑均為光頭,皆是佛教文化在唐宋墓葬中的反映。
至元明清時期,由于葬俗的變化和紙扎明器的流行,墓葬中曾盛極一時的半人半獸形象消失不見,從史前時代一直延續至宋代的半人半獸形象至此戛然而止,其藝術形象、文化屬性亦定格于此。
結語
中國出土文物與傳世文獻中半人半獸形象的特征、功能意蘊、文化內涵隨時而變,與中華文明的發展脈絡息息相關,不僅展現了古代社會葬俗的變遷,也反映了人們對宇宙層次構建的逐漸豐富,以及先民審美觀念的流變。而其所體現的本土信仰、異域宗教和各區域、各民族文化的融合碰撞,展現了中華文化兼容并包的特性。因而,半人半獸形象的歷史意義、思想史價值和文化史價值值得深入研究。
魏晉南北朝和唐宋時期傳世文獻中半人半獸的特點與出土文物基本一致,由于受篇幅所限,文中未作詳細論述。在宋元之后的出土文物與傳世文獻中,半人半獸的形象幾不可見,此種變化的緣由,特別是其背后所反映的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值得深挖。在我國現代剪紙、刺繡、泥人等民間工藝,以及部分少數民族的神話傳說中,半人半獸的形象指不勝屈;國外出土文物、神話體系和民族學資料中涉及的半人半獸亦不在少數。這些半人半獸和中國古人觀念中的半人半獸有著怎樣的共性與差異,皆有待我們進一步探究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