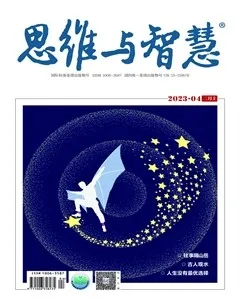古人的“漫游”
江舟

古代交通不便,如果需要遠行,大多是出于某種目的、某種需要,甚至是迫不得已而為之,多少帶有點無奈的性質。但是有些文人,卻在顛沛流離的旅途“漫游”中領略到全新的人生體驗,置身異鄉,廣見洽聞,過一地即覽一地之人情,經一方則睹一方之勝概,而且食所未食,嘗所欲嘗,甚至留下了千古名篇。所有這些新奇的人生體驗,使得古人“漫游”的旅途本身也充滿了魅力。
古代旅游,沒有現在所謂的導游,所以古代文人在旅游時更注重自己的感受、體驗和發現。清代沈復,游歷三十年,自稱“天下所未到者,蜀中、黔中與滇南耳”。沈復不作人云亦云之言,在《浮生六記·浪游快記》中,將一些受人推崇的景觀說得一無可取。“余凡事喜獨出己見,不屑隨人是非,即論詩品畫,莫不存人珍我棄、人棄我取之意;故名勝所在貴乎心得,有名勝而不覺其佳者,有非名勝而自以為妙者。”旅游途中,如果讓人在一邊指指點點,說那塊石頭像坐著的老僧,這塊石頭像蹲著的猴子,再附會上一兩個傳說故事,那只能讓人覺得索然無味。
晉代王子猷居住山陰時,有一次正值大雪,夜里他未能入眠,便小酌一番。當時月光雪色,一片皎然,王子猷吟誦著左思的《招隱詩》,忽然想起好朋友戴安道。那時戴安道在剡,王子猷連夜乘小船前往。船行了一夜,到了戴安道的住所,王子猷不入其內,而是掉頭返回。人們覺得奇怪,王子猷說:“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世說新語》中的這則故事歷來被人所津津樂道。雖然說的是訪友,然而也完全可以用來表示對“游”的態度:以適情為宗旨。王子猷沒見到戴安道,但在途中的感悟與體驗已使其精神得以安頓。
所以古代士人之游,崇尚沒有時間、路線限制,全憑興之所至,盡興而返。在旅游途中,則無所牽掛,忘卻一切俗務。
林語堂深得這種漫游的情趣。他說:“一個真正的旅行家必是個流浪者,經驗著流浪的快樂、誘惑和探險意念……旅行的要點在于無責任、無定時、無來往信札、無嚅嚅好問的鄰人、無來客和無目的地。一個好的旅行家決不知道他往哪里去,更好甚至不知道從何處而來。他甚至忘卻了自己的姓名。”
這一連串的“無”與“不知道”,實際上便是暫時割斷自己的所有社會關系,以一個自然人的身份,投身于大自然母親的懷抱,“朝友麋鹿,暮猿與棲”,領略“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那種微妙的自然變幻。
在現代社會中,日益豐富的物質生活越來越將人們束縛在一個狹小的生活圈子中,與自然日益擴大的疏遠感,使人感覺鈍化,從而導致了部分人性的迷失。旅游作為親近自然的最佳途徑,能使人們重新獲得一個豐富而充實的人生。
(編輯 大江/圖 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