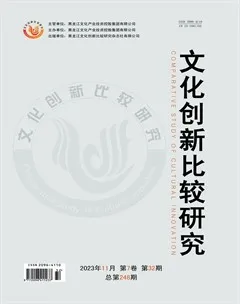關于博厄斯和薩丕爾對語言、思維及文化關系研究的比較分析與啟示
馬維伯
(四川外國語大學 西方語言文化學院,重慶 400031)
在探索人類認知和行為的過程中,語言、思維和文化三者之間的關系一直是人類學、心理學和語言學等學科的核心議題。這個議題涉及人們如何理解世界,如何構建知識體系,如何表達思想,以及社會和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其中,人類學家弗朗茨·博厄斯和語言學家愛德華·薩丕爾的思想和研究在這個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博厄斯的研究專注于人類文化和語言的相對性,強調文化和語言在形塑人們對世界的理解中的重要作用。薩丕爾則強調了語言對人類思維方式的影響,并提出了語言和文化相互作用的觀點。他們的理論雖然各有側重,但都強調了語言、思維和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本文從博厄斯和薩丕爾的視角出發,探討語言、思維和文化之間的關系,對他們的主要觀點和理論進行詳細分析和比較,探索他們對于這個問題的理解和研究。本文還提出新的假設,從新的視角來理解和探討語言、思維和文化之間的關系,加深對三者之間關系的理解,以期為這個領域的研究提供新的啟示和思考。
1 博厄斯觀點分析
弗朗茨·博厄斯是繼摩根之后美國現代人類學和民族學的創始人,享有“文化人類學之父” 和“美國人類學之父” 的美譽。博厄斯的人類學研究成就斐然。在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方面,他提出了人類學的目的和任務,堅持歷史特殊主義、文化相對主義的文化觀和反種族主義的社會和政治觀。他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和人類學的其他分支學科。
本文重點分析博厄斯《原始人的心智》中的論點。根據博厄斯[1]的觀點,文化不是單一民族的產物,而是在不同民族之間傳播和融合的過程中形成的。不同文明的發展模式不一定相同,所以不能用發展階段的不同步性來證明特定種族和文化的優越性。基于這樣的判斷和邏輯,博斯提出了文化相對主義理論。郭丹丹[2]認為,各個民族的文化是不同的,也是復雜的,很難用絕對的評價標準做出客觀的分析,在這種情況下,應當把自己從基于自身文化的判斷價值標準中解放出來,深入到每個民族的文化深處,深入到每個民族的思想深處,才能得出真正科學的結論。張今杰和林艷[3]強調,博厄斯的文化相對主義證明了種族平等和文化平等思想的合理性,在他看來,文化本身是一種塑造物質和心理世界的能動力量。博厄斯的文化相對主義理論使得人們對于不同文化的價值有了全新的看法,并引導人們嘗試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獨特性。
在《原始人的心智》的第四部分,博厄斯表達了原始部落人和現代社會人在思維能力上具有一致性的觀點。他認為語言能力是人類獨有的,并且不存在語言之間的高低貴賤。在這部分,博厄斯反駁了某些認為原始人缺乏邏輯思維能力和難以控制自己情緒的觀點。當時的一些學者認為,原始人做出決策的過程,受到強烈的情緒和信仰因素的影響,基本不存在邏輯與理性。然而這樣的觀點來源現代社會的思維邏輯和文化,并沒有把原始人的行為和他們獨特的社會風俗文化聯系起來。因此,這樣的判斷并不客觀。博厄斯認為,如果充分考慮原始部落成員的生活方式、日常活動和風俗習慣,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在這個基礎上,博厄斯在長期的原始部落實地考察中確認了原始部落成員和現代社會的人一樣有能力進行邏輯推理和情緒控制。原始部落的人在智力上基本上與文明世界的人處于同一水平。現代人腦的主要功能,如語言能力、邏輯思維、情緒控制和主觀意識,都是人類所共有的。
在《原始人的心智》的第五部分,博厄斯從語言學的角度論證了原始部落人的語言和文明社會的語言具有基本一致的功能和特點。他還從語言學的角度展示了一些關于種族劃分的理論。首先,博厄斯認為人種、語言和文化類型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并不密切,有證據表明,一些人群的語言和文化曾發生過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種變化并沒有從本質上改變他們所屬的人種。例如,非裔美國人在移民后完全接受了英語和當地的文化,但這并不會改變他們是非裔人種的事實。此外,博厄斯還舉了其他的例子,例如美洲原住民在逐漸散居后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即便它們來源同一種語言,這些方言與原來的語言相比有明顯的變化。部分阿拉伯人遷徙到北非后,與當地人種通婚,但阿拉伯語在他們的后代中保留了下來。此外,隨著歐洲文明的繁榮,歐洲語言也傳播到其他大陸。不同的民族和國家接受了這些來自歐洲的語言和文化,但這些國家和民族并不一定與歐洲白人有血緣關系。根據大量的觀察和對比,博厄斯認為,目前還無法證明特定語言或文化的形成與特定種族有直接關系。即使在最早的人類社會中,不同的部落也是相對孤立的,同一部落中也可能產生不同的語言和文化習俗。總之,沒有證據表明某種語言的形成發展,以及其所具有的基本功能和人種的屬性有直接的關系。
此外,博厄斯認為,語言并不是一個完全統一的整體,因為語言的語音、語法和詞匯并不是完全綁定在一起的。不同語言之間存在著相互同化和吸收的現象,進而會產生類似的特點。某些傳統刻板的觀點認為原始部落人使用的語言缺乏語音區分、邏輯分類和抽象的能力。但博厄斯認為事實并非如此。所有語言的基本特征是它們產生的音節組合能夠表達人們的思想,每種組合都有自己固定的含義,在不同語言當中,音節和音節組合的用法也不同。每種語言中能使用的有意義的音節組合是有限的,只有這樣才能將人們腦海中的想法快速、準確地進行傳遞。原始部落人使用的語言同樣有這樣的基本特征和功能組合。博厄斯還認為,由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體驗和經歷,所以為了描述類似的經驗和感受,便于交流,人們使用有限的詞根來描述不同類型的感覺經驗。這是人類思維的分類和總結歸納能力在語言中的體現,也是所有語言中的共同現象。這些音節需要通過一些常用發音器官的肌肉運動來表達。人們可以不假思索地聯想到發音所指向的事物和感受。即使是原始部落人使用的語言也與文明社會的語言具有相同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的語言中,這種語言內部的分類特點也與特定民族的生活習俗有關,例如因紐特人就有豐富的關于雪的詞匯和表達儲備。
杜秀[4]認為,人類文化的發展沒有普適的原則,每種文化都有自己的價值,每個民族都有自己值得尊重的價值觀。博厄斯的理論對人類學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有助于人們理解語言、文化和思維之間的關系。他的觀點挑戰了當時的主流思想,為研究人類的行為和認知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2 薩丕爾觀點分析
愛德華·薩丕爾是20 世紀初期最杰出的語言學家和人類學家之一。他的研究對語言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許多理論和觀點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薩丕爾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開創者和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研究興趣不僅局限于單一的語言或語族,而且涉獵廣泛,他的研究對象包括印第安語、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語言、塞米特語、印歐語等。他的跨語言和跨文化的研究方法為后來的比較語言學和人類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薩丕爾的代表作《語言論》于1921 年首次出版。該書是最早全面介紹語言學研究的著作之一,至今仍被廣泛視為該領域的開創性著作。
薩丕爾[5]認為,語言不僅是人們用以交流的媒介,也是一種復雜的文化現象,與人類的思想、行為和文化交織在一起。他探討了語言如何塑造人思考世界的方式,以及語言如何反映一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觀和信仰。薩丕爾也是 “薩丕爾—沃爾夫假說” 的提出者,這個假說又被稱為 “語言決定論”。他認為,人的思維方式和世界觀受其使用的語言的影響。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和概念體系,這些差異會導致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對同一種事物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釋。這個觀點對于人類學、心理學和認知科學等學科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于語言與思維關系的爭論由來已久。例如,柏拉圖認為思想是一種無聲的語言,而亞里士多德則認為思想的范疇決定了語言的范疇,語言只是思想的象征。薩丕爾和沃爾夫并沒有為他們的理論和觀點命名,后來美國語言學家卡羅爾首先將其命名為“薩丕爾—沃爾夫假說”。張雪梅[6]提到,自 “薩丕爾—沃爾夫假說” 問世的半個多世紀以來,人們爭論的焦點大多集中在該假說的正確與否上。許多學者對這一假說進行了不同的解釋。例如,趙世開[7]認為世界的概念是由語言塑造的。胡壯麟[8]強調語言塑造了人們的思維模式。劉潤清[9]認為語言的形式決定了使用者的思維和對世界的感知。多年來,語言學家和認知科學家對 “薩丕爾—沃爾夫假說” 一直爭論不休,至今仍未達成明確共識。根據孫洋和鮑文[10]的說法,學術界一般將 “薩丕爾—沃爾夫假說” 分為兩類:強類型和弱類型。持強類型觀點的學派認同語言的決定論,即語言決定思維、信仰、態度等,語言的形式決定了語言使用者的世界觀。持弱類型觀點的學派支持語言相對論,即語言反映思維、信仰、態度等,思維模式隨語言的變化而變化,不同民族的語言差異同樣反映在他們的思維方式上。
薩丕爾在《語言論》中指出,語言和文化深深地交織在一起。語言不僅是一種交際手段,也是使用社會文化和思維習慣的體現。語言是一個動態系統,是不斷發展和變化的,它是由使用這種語言的社會和文化背景所塑造的。他認為,語言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一個自然而重要的特征。語言研究需要跨學科的方法,需要在更廣泛的社會、文化和歷史背景下進行動態的語言研究。他認為語言研究需要借鑒人類學、心理學和其他領域的見解。
薩丕爾還對文化和社會的研究有著深遠的影響。在文化方面,薩丕爾的觀點是開創性的。他認為文化是一種復雜的符號系統,是一種社會的表達,而這種表達是通過語言、習俗、藝術和儀式等各種形式實現的。文化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而是決定人們如何理解世界、如何與他人互動、如何定義自我身份的關鍵因素。薩丕爾的貢獻不僅在于他的理論和發現,他的方法和研究態度同樣重要。他以開放的眼光和尊重的態度對待所有的語言和文化,他的工作展示了一種對人類多樣性的深入理解和欣賞。
總的來說,薩丕爾的研究和觀點對于理解語言、思維和文化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他的理念和研究方法也成為理解和尊重人類語言、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框架。
3 博厄斯與薩丕爾觀點的比較
3.1 相同點
在理論上,博厄斯和薩丕爾都是文化相對主義的倡導者,他們都強烈認同語言、文化和思維的相互關系。他們都認為語言不僅是一種溝通工具,而是影響人思維方式、世界觀和價值觀的重要因素。語言和文化在他們看來是緊密相連的,每一種語言都攜帶了其文化的獨特信息。他們都反對種族優越論,并強調了多樣性的重要性。他們認為,不同的人類群體和文化擁有獨特的語言和表達方式,并且這些差異并不意味著某一種語言或文化的優越或劣勢。此外,他們都相信語言的變化與社會、文化的變遷密切相關。在研究方法上,博厄斯和薩丕爾都高度重視實證研究,尤其是田野調查。他們致力于收集語言和文化的實際數據,并基于這些數據進行理論建構。他們的研究方法都非常具有實證主義特征,強調觀察和記錄,而不是僅依賴于理論推理。
3.2 不同點
3.2.1 在理論構建方面
博厄斯強調具體的語言現象和文化現象,他關注的是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他的工作致力于理解和描述特定的語言和文化群體,他的理論往往基于深入的田野調查和詳細的數據分析。相比之下,薩丕爾的理論框架更加宏觀和抽象,他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語言的系統性和結構性。他認為語言不僅是一種社會現象,也是一種心理現象,語言的結構反映了人類思維的結構。他的研究往往關注語言的普遍性質,比如語音變化的規律,詞匯和語法的系統性等。
3.2.2 在研究方法上
盡管博厄斯和薩丕爾都倡導田野調查,但他們在實踐中有著不同的重心。博厄斯更傾向于深入的田野調查和文化研究,他嘗試通過收集大量的實證數據來理解和解釋特定的語言和文化現象,他的方法強調的是翔實、深入和全面。薩丕爾的研究方法則更加注重理論分析和綜合,他通過收集和分析語言數據,試圖揭示語言的普遍性質和規律。他的方法更偏向于對數據進行系統的整理和分析,以此來驗證和構建理論。
總的來說,盡管博厄斯和薩丕爾有很多共同的觀點和方法,他們在理論構建和研究方法上還是存在一些重要的差異。他們的工作各有側重,但都為語言學和人類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4 啟示與新的思考
博厄斯和薩丕爾的觀點和理論是人們理解語言、文化和思維之間關系的重要基石。他們強調語言、思維和文化是密切相關的。他們的研究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框架,可以通過這個框架探索和理解不同的文化和語言現象。這不僅對于語言學和人類學的研究者具有重要意義,對于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例如社會學、心理學和哲學等,也提供了一種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
4.1 博厄斯和薩丕爾的理論挑戰了語言和文化的普遍性和絕對性
他們強調語言和文化的相對性和動態性,認為語言和文化都是社會和歷史條件的產物,是不斷變化和發展的。這對于理解和接納文化和語言的多樣性,提供了重要的思考角度。人們不應該以自己的語言和文化為標準,去評判其他的語言和文化。相反,應該以開放和理解的態度,去接納和欣賞文化和語言的多樣性。
4.2 博厄斯和薩丕爾的理論強調了語言對于思維和文化的影響
他們認為語言不僅是一種溝通工具,而是影響人思維方式、世界觀和價值觀的重要因素。這對于理解和評估語言的重要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應該重視語言教育和語言保護,因為語言的喪失不僅是語言本身的喪失,也是文化和思維方式的喪失。
在博厄斯和薩丕爾理論的基礎上,也對語言、思維和文化之間的關系有新的思考和探索。例如,可以提出這樣的假設:語言和文化最初都來源人類的思維能力,語言和文化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語言和文化成為客觀實在誕生之后,便反過來對人類的思維和理解世界的方式產生了重要影響。這個假設將人類的思維能力作為語言和文化的起源,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解角度。根據這個假設,語言和文化不僅是社會和歷史條件的產物,也是人類思維能力的產物。語言和文化最初誕生于人類的思維能力,然后又反過來影響和塑造了人類的思維方式和世界觀。
此假設與博厄斯和薩丕爾的理論并不矛盾,而是在他們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新的理解和解釋,而且強調了人類思維能力的重要性和創造性,同時也認同了語言和文化對于人類思維的影響和塑造作用。這也是一種可以用來探索和研究語言、文化和思維之間關系的視角和研究方法。
5 結束語
綜上所述,博厄斯和薩丕爾的觀點和理論為人類提供了理解語言、文化和思維之間關系的理論框架和思考方式。同時,他們的理論也激發了新的思考和探索。通過理解、應用并發展他們的理論,可以更好地解釋語言、文化和思維的關系,也可以更深入地探索和研究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