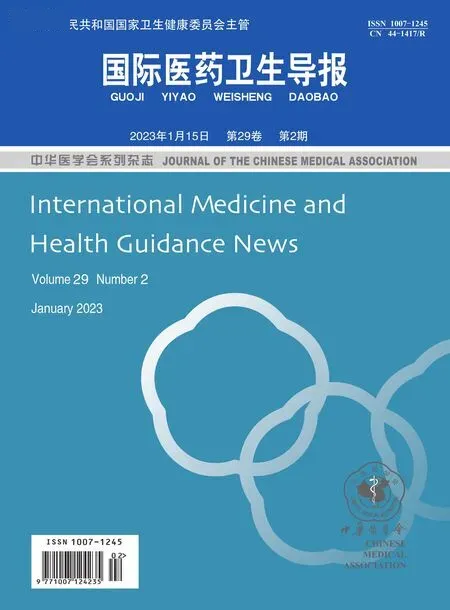以腹部巨大包塊為特殊表現的系統性紅斑狼瘡1例并文獻復習
崔凱悅 彭揚 趙培慶 蘭永廷
1濱州醫學院,濱州 256603;2濰坊醫學院,濰坊 261902;3淄博市中心醫院轉化醫學中心,淄博 255020;4淄博市中心醫院消化內科,淄博 255020
系統性紅斑狼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種累及全身多臟器多系統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SLE病因復雜,目前尚未完全清楚,好發于女性,不加以治療會造成受累臟器的不可逆損害,最終導致患者死亡,是影響我國女性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之一。隨著當今醫學診治水平的不斷提高及臨床醫師對其認知的增加,SLE 患者的生存率大幅度提高,SLE 已由既往的急性、高致死性疾病轉為慢性、可控性疾病[1]。但是,SLE可出現多種并發癥(包括疾病的并發癥和治療相關的不良事件,例如SLE 患者冠狀動脈疾病的發病率較正常人高出至少2 倍,而在年輕患者中發病率更高[2])。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會明顯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延緩并發癥的發生。SLE 的發病形式、臨床特點因人而異,其中以不典型臨床表現為首發表現不在少數。本文旨在分析出現腹部包塊這一不典型臨床表現的病例1例,并對相關文獻進行回顧復習。
病例資料
患者,女,29 歲,因“反復發熱2 個月,再發伴惡心、嘔吐3 d”入院。患者2 個月前無明顯誘因出現發熱,體溫峰值39 ℃,多于夜間體溫升高,并伴胸痛、乏力,就診于外院,CT 示胸膜炎、胸腔積液,血沉>100 mm∕h,經抗感染、對癥治療(具體不詳)后患者未再胸痛及發熱,復查CT 示胸腔積液較前無明顯變化,因此懷疑為肺結核,結核感染T 細胞檢測(-),血沉74 mm∕h,痰集菌未查到抗酸桿菌,予以經驗性抗結核治療2 周后體溫恢復正常出院。在院外繼續服用抗結核藥物過程中仍舊反復高熱,伴有周身酸痛,再次于外院就診,復查血常規無明顯異常,C反應蛋白18.38 mg∕L,CT示右肺條索樣改變、雙側胸膜增厚,在抗結核藥物治療基礎上加用左氧氟沙星及奧司他韋治療后,患者仍反復發熱并伴惡心、嘔吐,并逐漸出現乏力、胸悶、腹痛、周身瘙癢、皮疹、結膜充血等癥狀,再次復查血常規及生化常規均無異常,復查C 反應蛋白32.62 mg∕L,CT 示左腎結石;左側腹腔內多發占位性病變并淋巴結腫大;雙側胸腔少量積液;盆腔積液,遂來淄博市中心醫院就診。既往史:“結膜炎”2 個月余,未治療。個人史及家族史無特殊。入院體格檢查:體溫38.6 ℃,血壓108∕84 mmHg(1 mmHg=0.133 kPa),脈 搏113 次∕min,呼吸20 次∕min。右側頸部可觸及直徑0.3~0.5 cm 淋巴結,有輕壓痛。眼瞼水腫,結膜充血,左側胸壁壓痛,腹部平坦,左側腹部可見陳舊性瘢痕,腹肌柔軟,劍突下及右下腹壓痛,全腹反跳痛,左上腹可觸及直徑約3 cm 的包塊,無搏動感,質韌,無明顯壓痛,活動度差。肝、脾肋下未觸及,Murphy 氏征陰性。腹部叩診呈鼓音,肝腎區無叩擊痛,無移動性濁音,腸鳴音4 次∕min,雙手掌大、小魚際可見紅斑。實驗室檢查:血小板計數32×109∕L,白 蛋白22.7 g∕L,K+3.46 mmol∕L,Na+128.9 mmol∕L,尿蛋白(+),大便潛血試驗(+);凝血系列: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42.1 s,凝血酶時間21.7 s;C 反應蛋白19.26 mg∕L;血沉67.00 mm∕h;補體C3、C4 測定:C3 0.35 g∕L,C4 0.02 g∕L;抗核抗體(+);抗U1-nRNP 抗體(+);AnuA(+);AHA(+);抗線粒體抗體(+);抗雙鏈(天然)DNA 抗體(+);抗Ro-52 抗體(+);磷脂綜合癥抗體(+)。肺部CT:雙肺下葉炎癥改變,右側葉間胸膜增厚,雙側胸腔積液,縱膈、雙腋窩下、雙鎖骨下多發腫大淋巴結。腹部彩超:腹腔內探及多發低回聲包塊,較大者為65 mm×37 mm、55 mm×39 mm,邊界清晰,回聲欠均質;彩色多普勒血流顯像:其內見少量血流信號(圖1A)。經多學科會診討論,患者SLE 診斷明確,同時根據狼瘡疾病活動性指數(SLE-DAI)評分標準,患者補體C3、C4 均下降低于正常值,體溫>38 ℃,胸膜炎伴胸痛,血小板減少,總分6分不考慮疾病活動期,但患者腹部巨大包塊性質不明確,不能確定是否與SLE 有關。入院后給予糖皮質激素治療(甲潑尼龍琥珀酸鈉60 mg∕qd)、免疫抑制劑、調節骨代謝、調節免疫、利尿消腫、補充人血白蛋白、糾正電解質紊亂等治療,患者體溫逐漸恢復正常,全身乏力、口干癥狀消失,雙眼瞼及面部浮腫明顯減輕,仍訴有輕微膝關節疼痛,治療14 d 后,輔助檢查回報:T細胞斑點檢測(-);C反應蛋白+血常規:紅細胞計數3.46×1012∕L,血紅蛋白109 g∕L,血小板計數431×109∕L,C 反應蛋白0.71 mg∕L;血沉28.00 mm∕h;補體C3、C4 測定:C4 0.02 g∕L;生化常規:白蛋白36.6 g∕L;抗雙鏈(天然)DNA抗體測定(定量):563.0 IU∕ml(患者應用激素前后血液檢驗主要指標變化情況見表1)。此后,調整甲潑尼龍琥珀酸鈉用量為40 mg∕qd,并加用來氟米特控制病情,再次治療3 d后,患者無發熱,雙眼瞼及面部浮腫消失,通知患者出院,院外繼續服用醋酸潑尼松、阿法骨化醇軟膠囊、珍牡腎骨膠囊、羥氯喹片、腎安膠囊、來氟米特片、葡醛內酯等藥物,病情平穩,口服藥物4 個月后患者再次入淄博市中心醫院復診,查體未捫及淺表腫大淋巴結,復查彩超示腹腔包塊消失(圖1B)。

圖1 1 例以腹部巨大包塊為特殊表現的系統性紅斑狼瘡患者初次入院與出院4 個月后腹部彩超情況對比。A:腹部彩超(初次入院),腹腔內探及多發低回聲包塊,較大者為65 mm×37 mm,55 mm×39 mm,邊界清晰,回聲欠均質,彩色多普勒血流顯像見少量血流信號;B:腹部彩超(出院4 個月后)未見明顯異常回聲包塊

表1 1例以腹部巨大包塊為特殊表現的系統性紅斑狼瘡患者應用糖皮質激素前后血液化驗重要指標變化情況
討論
SLE 好發于育齡女性,是由自身免疫介導,可侵犯多系統、多器官,臨床表現多樣的慢性彌漫性結締組織病。由于SLE 早期癥狀不典型,為提高患者的生存及生活質量,早期診斷和綜合治療尤為重要。本例患者以發熱為主要表現,伴有惡心、嘔吐等消化道癥狀,最初輔助檢查僅提示胸膜炎、胸腔積液,血沉明顯增快,但多次查血常規、生化常規等均無明顯異常,初期診斷較為困難,隨著病情進展,患者漸漸出現周身酸痛、乏力、胸悶、腹痛、周身瘙癢、皮疹、結膜充血等癥狀,同時輔助檢查結果,如血常規、生化常規、尿常規也出現明顯異常,表現為血小板減少、白蛋白降低、尿蛋白增高等,腹部CT 亦提示腹部多發占位病變、多發淋巴結腫大及多發漿膜腔積液,經多學科會診,診斷考慮免疫性疾病可能性大,進一步完善相關檢查發現患者存在免疫學指標多項異常。根據美國風濕病協會(ACR)1997年SLE 分類標準,如符合11 項中的至少4 項,在除外感染、腫瘤和其他結締組織病后可診斷為SLE。本例患者雙側胸膜積液(漿膜炎)、血小板減少(血液學疾病)、抗雙鏈DNA 抗體陽性及磷脂綜合癥抗體陽性(免疫學異常)、ANA 陽性,符合SLE分類標準中的4 項。此外,患者入院前反復檢查已經排除感染及腫瘤性疾病,結合多學科會診意見,患者最終診斷為系統性紅斑狼瘡并多臟器受累(血液系統、腎臟、肺臟、漿膜腔積液、電解質紊亂)。本例患者疑診之處在于腹部包塊性質不明確,盡管腹部超聲提示可能為腫大的淋巴結,但SLE 合并巨大腹腔淋巴結臨床少見,故腹部包塊初診尚不能確定是否與SLE有關。
在臨床上,腹腔淋巴結腫大的病因復雜多樣。宋豐前等[3]對131例腹部腫大淋巴結進行了病因分析,結果提示病因以惡性腫瘤居多,其次是腹腔淋巴結結核、淋巴瘤等。
當SLE 合并淋巴瘤時兩者臨床表現相似,鑒別困難,當患者出現發熱、淋巴結腫大、血細胞減少時,應當引起重視,警惕淋巴瘤的可能,避免延誤病情。良性腹腔淋巴結腫大病因多是反應性增生,如細菌感染、病毒感染、結締組織疾病[4]等。
目前普遍認可的腹部淋巴結正常大小為短徑在5~10 mm之間,即使腫大后淋巴結通常也比較小,患者多難以察覺。本例包塊經查體及超聲檢查均提示為巨大包塊,經驗上考慮包塊性質為腫大的腹腔淋巴結可能性較小,而考慮淋巴結結核、淋巴瘤、轉移瘤等其他疾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在SLE 中,淋巴結腫大是病情活動的一種反映,病情活動時患者可能在單個或多個部位呈現淋巴結腫大,最常見的部位是頸部、下頜、腋窩等部位,一般為輕度或中度腫大,很少出現原發性淋巴系統疾病淋巴結重度腫大的情況[5],尤其出現腹腔淋巴結腫大的概率不高,其中多數患者經糖皮質激素治療后腫大淋巴結可以縮小甚至恢復正常。徐婧梅等[6]對17例經臨床確診為SLE并且累及消化道患者進行研究發現,僅1 例出現腹膜后淋巴結腫大,提示SLE 累及消化道對淋巴系統影響較小。從病理學角度來看,SLE 的淋巴結病變特點是不同程度的凝固性壞死伴蘇木紫小體或反應性濾泡增生,前一種組織學是SLE 特有的[7]。因為多數患者可以通過年齡、臨床表現、體格檢查及血清學檢查等就可以診斷SLE,所以在臨床上很少有SLE 患者做淋巴結活檢[7]。本例患者亦未進行淋巴結活檢,在確診SLE 后,給予糖皮質激素及免疫抑制劑等綜合治療后腹部包塊消失,充分佐證了該包塊性質即為SLE所致的高度腫大的腹腔淋巴結。
在SLE 患者中,除了腹部包塊為特殊表現的,少數病例會以腋下淋巴結[8]、腹痛腹瀉[9-10]、膽汁淤積性肝炎[11]、急性肝衰竭[12]為首發癥狀。研究表明,SLE 患者在疾病活動期有25%~60%的可能性表現為肝功能異常[13]。遇到上述情況,應高度警惕SLE 的不典型臨床表現,避免因主觀臆斷造成誤診[14]。從另一方面來講,這也提醒臨床醫師,當面對特殊疑難病例時,及時完善免疫學、影像學等一系列檢查甚至提請多學科會診對于明確診斷是非常必要的。
對于SLE 的治療,應根據疾病活動度、受累器官等,制定個體化的治療方案。目前,糖皮質激素加免疫抑制劑依然是主流方案,一些新興治療方法[15]如生物制劑、血漿置換、免疫吸附、干細胞移植等醫療支出較大,且長期臨床療效缺乏臨床循證醫學證據,因此在臨床上的應用受到限制。SLE 經合理治療后多數病例可達到長期緩解,但腎臟受累患者預后較差,其10 年病死率可高達12.5%[16]。治療原則應根據病情是否在活動期而有所變化,急性活動期需積極用藥控制病情惡化,緩解期則應調整用藥減少臟器損害。在治療SLE 患者過程中,應密切關注患者病情變化,以免發展成重癥SLE 及狼瘡危象等。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表明,SLE 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礙,其中以抑郁、焦慮、敵對、恐怖、偏執最為顯著;婚姻狀況、就業情況、激素用量、病情活動評分是心理健康的重要影響因素[17]。治療SLE 的同時,無論是SLE 本身還是應用糖皮質激素和免疫抑制劑的不良反應都會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所以非藥物治療也很重要。在一項研究中,納入研究的1 萬余例SLE 患者中,重度抑郁癥和焦慮癥的患病率分別為24%和37%[18];在另外一項對SLE 住院患者的研究中總共有34.4%的SLE 患者有自殺意念[19],然而目前臨床醫生和患者對SLE 伴抑郁等精神癥狀不夠重視,臨床上接受治療的患者很少[20]。此外,中度至重度抑郁情緒的SLE 患者也增加了藥物不依從性的可能性[21],由此可見關心患者的心理動態,耐心傾聽,及時給予心理干預,也有助于疾病本身的治療和病情的緩解[22]。對本例患者,在制訂治療方案時,我們充分考慮上述因素,及時給予糖皮質激素、免疫抑制劑、補充白蛋白、營養支持、心理疏導等綜合治療,此外,本例患者加用了瑞舒伐他汀鈣片治療。臨床試驗研究表明,他汀類藥物不僅可以預防SLE 患者心血管系統并發癥的進展,還可以調節免疫[23]。最終患者多系統損害癥狀好轉,相關指標逐漸恢復正常,出院后4 個月復查腹部包塊消失。該患者一直予以密切隨訪,隨訪中患者未再出現腹部包塊癥狀,無明顯不適感,病情穩定。
綜上所述,對于SLE 伴隨腹部包塊或其他不典型臨床癥狀時,在鑒別診斷中應格外注意,應該進一步提高對SLE的認知,做到早期識別、診斷。當患者出現多發漿膜腔積液、多發淋巴結腫大、低蛋白血癥或多系統受累的臨床表現時,若不能用單一系統疾病解釋相關癥狀和體征,應考慮結締組織病尤其SLE,繼而精準治療,改善患者預后[24]。盡管SLE 無法徹底治愈,但早期診斷、合理用藥可以促使病情盡快達到臨床緩解,同時也可以避免由于誤診而導致不可逆的臟器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