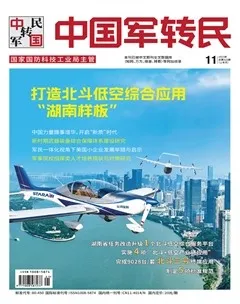1895—1945年日本的臺灣文化觀光政策探究
【摘要】1895—1945年,日本殖民者為進一步尋求對中國臺灣殖民統治的“必要性”與“合理性”,激發日本國內民眾赴臺進行文化“墾殖”的熱情,實現日本帝國的“海外雄飛論”,日本殖民政府通過官方和非官方的形式,積極組織、招攬日本文化界、藝術界以個人或團體的名義赴臺旅行觀光,進行殖民地旅行書寫。其本質是近代日本“皇化”臺灣的一部分,服務于殖民擴張,其目的是為日本的進一步對外侵略擴張服務。
【關鍵詞】1895—1945年∣近代日本∣臺灣文化觀光∣侵略擴張
1895年,日本殖民者通過不平等的《馬關條約》,侵占了中國臺灣,在臺灣民眾掙扎著承受日本殖民統治的同時,日本國內上下卻滿懷著新鮮、獵奇、探險、征服等諸多心理前往臺灣進行文化旅行觀光,探尋“南方島嶼”——殖民地臺灣的秘密。這些旅臺或居臺的日本組織和個人將在臺的所見所聞所感行諸筆端,留下了大量反映臺灣社會現狀、風土人情、名勝古跡、逸聞奇事的文字,體裁廣泛涉及游記、紀行、日記、小說、詩歌、隨筆、戲劇等形式,展示了其對臺灣進行殖民統治的歷史軌跡。這些日本人對的臺灣書寫,固然有個人經歷、文化身份以及在臺體驗等因素的主導,其實也是日本官方積極倡導和策劃的海外觀光文化政策直接促成的。本文結合相關作家文本的分析,系統梳理1895—1945年日本在中國臺灣的最高殖民統治機構——臺灣總督府積極倡導日本國內民眾尤其是文化藝術界名人赴臺旅行觀光背后的殖民企圖和帝國權力欲望,以期揭示日本殖民統治中國臺灣的歷史真相,為我們正確處理中日關系和早日實現海峽兩岸統一提供歷史借鑒。
一、鼓動“海外雄飛論”——文化觀光政策緣起
“殖民表述的最重要載體之一,就是殖民者對旅行的狂熱和大量游記作品。周游世界的記錄是數世紀以來帝國抒寫的特征。”[1]澳大利亞學者比爾?阿希克洛夫特等在《逆寫帝國》中對旅游游記與帝國抒寫的關系進行了理論闡述,從中可以看到,在帝國時代,旅游所帶來的異國風情色彩,不僅極大地滿足了帝國民眾對異域的獵奇體驗,也極大地激起了殖民主體對“未開墾”殖民地的征服欲望和臣服心理。殖民地旅游,對于帝國民眾來說,是欣賞異域風情,滿足獵奇欲望;對于帝國官方而言,是最直接的宣傳鼓動帝國民眾進行海外殖民擴張以及移民的方式。旅行寫作作為歐洲帝國知識生產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曾在歐洲的民族觀念、領土觀念、世界觀念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建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樣,對于積極模仿歐洲殖民主義發展模式,急切期盼躋身歐洲殖民主義國家之列的近代日本來說,旅行書寫對其殖民主義擴展和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建構發揮著不可估量的作用。這是日本殖民統治臺灣五十年期間,日本民間時有人赴臺旅行,日本官方經常組織觀光團赴臺旅游觀光、臺灣總督府極力鼓動日本文化藝術界人士赴臺旅游觀光的根本目的。
明治初年,以太平洋場域和海洋思想為主導的“南進論”成為日本國家發展的主導思想,“南進論”者提倡打開國門自由貿易的通商富國政策,并鼓動日本政府應領有太平洋領域制海權,向“海洋國家”發展。日本政府擬通過西方大航海時期海外觀光探險的形式,激發日本人的海外殖民欲望,被日本侵占的第一個海外殖民地——中國臺灣自然而然地成為其推行海外觀光的主場地和實現帝國殖民意識形態建構的“試驗場”。日本政府一方面積極吸引日本國內民眾到臺灣觀光旅游、探險,通過觀光客的視角,強化臺灣蒙昧、野蠻的形象,積極宣揚日本對臺殖民的“必要性”“合理性”及“文化墾殖”的成績;一方面凸顯臺灣的富饒與未開墾,觸發日本民眾對臺灣異域風情的浪漫憧憬,激發赴臺“墾殖”的熱情并以此來宣揚鼓動日本的“海外雄飛論”。臺灣學者高嘉勵說:“幾百年帝國的旅行者因各種目的,經過長時間的跨海旅程,來到與母國社會文化不同的殖民地……旅行使得國家、文化、種族的疆界不斷被跨越,挑戰原本受限制或固定化的自我。”[2]如他所言,旅行讓日本帝國處于不斷變化、不斷拓展的更新狀態,刺激著帝國的海外擴張野心和民眾的對外殖民的熱情,日本作家書寫殖民地臺灣,企圖為日本的殖民意識形態建構增添“浪漫唯美”的一筆。
事實上,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最初十年間,其對臺殖民政策以武力鎮壓為主。到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中期,也就是1910年后,日本通過軍事手段全面控制了臺灣大部分地區。為更穩固、更長久、更深入、一勞永逸地占有臺灣這個“南進基地”和“資源寶庫”,日本當局逐漸采取了懷柔的措施對臺殖民,即采用非軍事化、政治或官方的商貿和旅游文化舉措殖民臺灣。1920年左右是日本國內海外觀光風潮盛行之時,臺灣總督府順應這股“海外旅游風”,以臺灣為基地,積極發展近代觀光業,制定宣傳策略以招攬日本國內文人赴臺觀光,一方面激發日本人的海外“淘金”欲望與“殖民開墾”熱情,另一方面宣揚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成績”。
二、招攬文化名人旅臺——文化觀光政策的實施途徑
作家佐藤春夫是最早獲得日本官方支持赴臺旅游的知名文化人士。1920年夏天,佐藤春夫因個人感情的挫折,在臺灣友人的再三邀請下赴臺旅行。起初他只打算在臺灣停留十幾天,但當他踏上臺灣的土地,在當地官民友人的極力促成下,在臺灣停留了三個多月,先后游覽了臺北、高雄、臺南、嘉義、日月潭、霧社、鹿港等地,并以此次赴臺旅行為背景相繼創作了《女誡扇綺譚》《殖民地之旅》《霧社》等數篇游記和小說,開啟了日本作家旅行書寫殖民地臺灣的先河。值得一提的是,佐藤春夫的此次臺灣之旅,受到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下村海南和臺北博物館代理館長森丙牛的熱情招待。他們為其舉辦歡迎宴,擬定了完美的旅程表,專門派遣秘書兼向導一路為其“保駕通行”,令佐藤春夫數月的臺灣之旅十分愉快。他在其作品《旅人》中寫到:“長官指令,要對我好生款待。……可憐人們雖不知文學家為何物,既然是長官的命令,且不論是什么小人物,都盡心竭力地接待我。”[3]
最終佐藤春夫不負臺灣總督府的殷切希望,他創作的小說《女誡扇綺譚》得到下村海南的贊賞:“為致力于宣傳朝鮮和臺灣,通過宣傳手冊、電影等形式之外,還邀請觀光團前來,或是在日本內地的展銷會進行各種宣傳,但都顯得隆重有余、親民不足。我記得當時《每日新聞》上連載的高濱虛子的《朝鮮》,于是想到能否也以這種形式進行宣傳,在臺灣時也曾拜托兩三位知名文士,均未果。正巧佐藤先生來了,想必我的愿望轉達到了先生那里。”[3] p8佐藤春夫的小說《女誡扇綺譚》終不負囑托,成為日本官方求之不得的臺灣宣傳范本。下村海南將佐藤春夫的小說《女誡扇綺譚》定位為宣揚殖民統治成績的標桿,這正應了臺灣學者高嘉勵所言:“即使文學作品創作指出,并不一定是為了政治宣傳,但在帝國殖民的架構下,文學作品不但無法完全與殖民統治切割,而且可能被吸納成為政治政策和文化意識形態的一環。曾任總務長官的下村以《女誡扇綺譚》為標桿,期待未來臺灣相關創作的出現,即顯示這部作品隱含某種后續的政經效應。”[2]
除去臺灣總督府有目的地組織和招攬日本知名文藝界人士赴臺旅行考察觀光外,赴臺旅游的另一主體是個人短期旅臺觀光。1939年,中村地平受到佐藤春夫旅臺作品《女誡扇綺譚》的“南方憧憬”誘惑踏上臺灣土地旅行,創作了《南方的郵信》《長耳國漂流記》和《熱帶柳的種子》等一系列滿懷“南方憧憬”的作品。本來中村地平的赴臺旅行只是他為收集小說題材實施的個人計劃,但當臺灣總督府得悉中村地平的赴臺計劃后,也給予其“特別照顧”,以高規格優渥待遇給予他各種方便和優待,讓在文壇初露頭角的中村地平受寵若驚,他在隨筆《旅人之眼》中這樣寫到:“我是一介文學書生,卻在各方面受到臺灣總督府超過應用待遇的許多方便。有火車、巴士的免費搭乘,大部分地方的官廳也借汽車給我,甚至在有需要做視察的場合,還特別派人做導游。我此行是舒適的,或簡直可說是感動得無以言語。”[4]中村地平此時在日本還是一名籍籍無名的“文學書生”,其在各方面受到“超過應該有待遇的許多方便”,并非他在文學界的聲名顯赫,主要是因為他是以創作臺灣題材作品而登上文壇的新人,臺灣是培育他的文學基地,對于臺灣總督府來說,促成他在臺灣文學方面的成績,亦是在為日本對臺殖民統治培育“宣傳后備軍”。
日本官方組織旅游團,主要是由臺灣總督府定期組織,其構成主要為日本政界、軍界人士和文化界名人,其目的是為日本海外殖民侵略進一步尋求支持,使之成為“政治正確”的見證人和殖民開墾的“鼓動者”“宣傳旗手”,以掩蓋其侵略的罪惡本質。日本每年大量平民甚至是無業游民涌入臺灣,或觀光漫游、或懷抱“淘金夢”、或自我放逐、或逃避現實,或尋找發展新機遇。無論是哪一種,來自殖民宗主國的日本民眾進入臺灣,都有來自殖民者身份的天然優勢,都能在臺灣獲得比日本國內多一些的地位、尊嚴、榮耀。這些流浪臺灣的日本普通民眾,以“鍍金顯達”的身份回歸日本現身說法,口耳相傳臺灣的異域風情、臺灣生活的異彩斑斕,不僅客觀上轉移了日本的國內矛盾,而且極大地誤導并鼓動了日本民眾對海外殖民的認可和熱情。
三、服務于殖民擴張——文化觀光政策實質
“對東方主義結構以及更為復雜的殖民互動交往的研究中,游記必定成為重要的并且不斷壯大的領域。”[1]游記是殖民主體凝視殖民地、抒寫殖民地生活、體現殖民主體最主要最直接的文學樣式之一,而旅游觀光則是催生游記的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方式策略。賽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認為:“如康拉德很強烈地認識到那樣,維系帝國的存在取決于‘建立帝國這樣一個概念。一切準備工作都是在文化中做的。反之,帝國主義又在文化中獲得了一種協調一致,一套經驗,還得到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5]通過臺灣總督府實施的一系列優待日本文人名士赴臺旅游觀光的文化政策,日本殖民者為其在臺建立長久、穩固的殖民統治機制培植了大批的“宣傳后備軍”和“戰時旗手”,并借助這些文人對臺殖民“合情合理”和海外擴張“大有可為”進行渲染美化與大力宣揚,為日本帝國的海外殖民和對外侵略積累了雄厚的國內民意基礎,獲得了輿論支持。借由旅游觀光文化的渲染與鼓動,日本帝國主義的海外殖民擴張與侵略政策深入人心,這也是近現代歷史上,日本帝國主義一路猖狂囂張、強盛發展的文化誘因之一。
日本學者鶴見俊輔在其著作《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序言中,對戰爭時期日本國民的精神力量和文化信心曾有過這樣一針見血的論述:“自一八六七年明治新政府成立以來,約莫四十年間,日本國民都生活在必須攀登文明的階梯——如果說真有這種東西的話——這類虛構之物,相信只要身為‘國民,不管身處何國,都可感受其存在;并且,我們可以說這類虛構之物,長期以來,在國民的想象力中不斷地發揮作用。因此可以這樣說,從明治時代開始,‘文明階梯此一虛構物,對日本國民的想象力始終發揮著重大作用。”[6]
他認為日本國內鼓吹的“文明階梯”是虛構想象之物,是日本進行對外擴張的一大借口。“在這個時代,所謂文明階梯的思想,在日本國內對政治有興趣的人的想象中,時常作為一種實體的觀念發揮著作用。參加政治活動的人——不管是右翼或是左翼都相信,要強制朝鮮進一步登上文明的階梯,就算使用暴力亦未嘗不可。這是基于他們政治上篤定的信念。”[6]當然,對朝鮮的殖民如此,對中國臺灣的殖民亦是如此,日本人篤定地認為自己的權力擴展和暴力統治,皆是“文明進步”的必然要求,是對“落后文明”之代表的朝鮮和中國的“文明教化”之使命感,對中國臺灣的殖民統治也是其實現“現代文化啟蒙和教化”的現實教材。
根據日本學者鶴見俊輔對日本國民精神和“文明階梯”思想的論述可知,日本政府組織官方的赴臺旅游是“文化殖民”的一部分,是“皇化”臺灣的一部分,也是其“文明階梯”這一帝國精神虛構物的現實體現。其實質是將殖民臺灣當作是日本近代化文化“優勢性”的例證,借助文化的渲染鼓動效應鞏固日本帝國主義海外殖民的民意與輿論支撐基礎,激發日本民眾一致對外殖民擴張的欲望。通過日本殖民當局對赴臺旅游觀光文化的積極倡導,日本作家經歷了對臺灣“旅行之眼”到“帝國之眼”的轉化演繹,參與了近代日本殖民意識形態的建構。這形象地印證了薩義德所論述的,帝國建立的一切準備工作都是在文化中做的,也印證了臺灣學者高嘉勵對殖民地旅行書寫與殖民政治意識形態建構不可分割關系的闡述,即使文學作品創作本身并不是必然指向政治宣傳,但在帝國殖民的架構下,對于殖民地的旅行書寫無論如何也無法擺脫殖民統治及殖民意識形態建構的環繞。可見日據臺灣時期日本作家的臺灣旅行書寫是在帝國意識形態的強力環繞下進行的,其筆下的臺灣形象也是具有強烈意識形態傾向,帶有濃烈的帝國殖民霸權意識色彩。
四、結語
通過厘清近代日本的臺灣旅游觀光文化政策與對臺殖民統治事業的關系可知,日本近代實施的海外觀光旅游遠非當下我們熟知的民族之間、國家之間平等友好地雙向文化互通交流,而是有著侵略者與被侵略者、支配者與被支配者、霸凌者與被霸凌者的絕對區別,它是單向的、強制的,也是霸凌的、建構的。通過對近代日本侵略中國臺灣文化誘因的剖析,為我們客觀認識近代中國臺灣與日本的關系,反對以蔡英文為首的“親日派”“臺獨派”的丑惡行徑提供了歷史佐證,也為正確處理和對待中日關系、促進海峽兩岸早日統一提供了歷史借鑒。
參考文獻
[1]比爾·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倫·蒂芬.逆寫帝國:后殖民的理論與實踐[M].任一鳴,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196-197.
[2]高嘉勵.書寫熱帶島嶼:帝國、旅行與想像[M].臺北: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16:15-71.
[3]佐藤春夫.定本佐藤春夫全集:第5卷[M].京都:日本臨川書店,1998:5-8.
[4]河源功.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M].莫素微,譯.臺北:臺北全華科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37.
[5]愛德華·W.賽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M].李琨,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12.
[6]鶴見俊輔.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M].邱振瑞,譯.臺北: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5:13-114.
【基金項目:本文系2021年度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后期資助項目)“1895-1945年日本作家對臺灣的凝視研究”(編號:2021281)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徐莉,博士,武昌工學院國際教育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作者單位:武昌工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