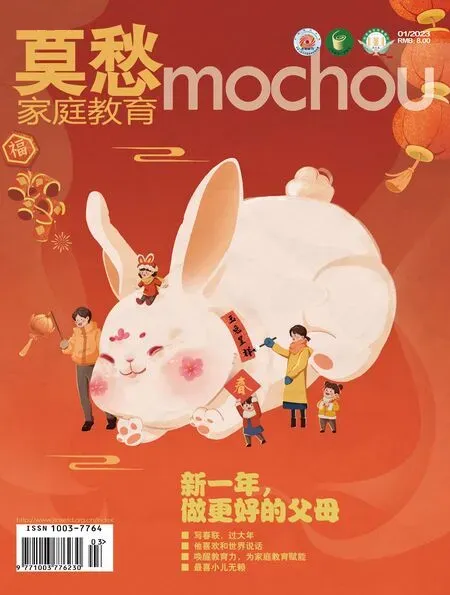鄉下的鳥窩
文 孫陳建

1
小車駛離了高速口,碾進了鄉間公路。車道窄了,車流量明顯增加,車速減慢了很多,路兩邊的樹木突兀凋零,農田里麥苗長勢喜人、油綠發亮,給鄉野的冬渲染出春的色彩。
“快到爸爸的老家啦。”我輕輕地松了一口氣,提醒車后座上昏昏欲睡的孩子。
“噢,快到爺爺家啦,快見到奶奶啦。”女兒剛才還一副睡意,猛然間,長途的疲勞消散殆盡,像小馬駒一樣神氣活現起來。
“快看,路邊樹上掛著足球。”我指著一只碩大的鳥窩。
“真是鳥窩,好大的鳥窩啊!”孩子更加興奮了。
“媽媽,我們來數鳥窩吧。你數你那邊的,我數我這邊的,看誰數得多。”孩子推推暈車中的媽媽。
我關掉音樂,留出耳朵聽孩子數鳥窩。
“1、2、3……10、11……”
“快看,那棵樹上有2個鳥窩,一大一小。”
“快看,快看,4 個,這棵樹上有4 個鳥窩,1 個鳥的家族呢。這是我看到的鳥窩最多的樹了。”
“我數到59啦,媽媽數到64啦,總共是123個。”
車子拐進了家門口,輕輕摁了聲喇叭,老父母從瓦屋里應聲而出,打開車門和后備廂,抱出孩子,取下行李。
2
從除夕到正月初三,孩子玩得特別歡,時間過得特別快,一會兒跟著爺爺,在屋東邊的河邊,挖了二十來個三角河蚌、一籃子的紅皮荸薺和粉白慈姑;一會兒追著奶奶,在屋前油菜田里挖喜菜(薺菜)和香菜(芫荽);一會兒蹲在田頭畦間摘豌豆苗尖,鏟包扎得結結實實的大白菜。累了,她用鏟子挖泥潭,說是幫狗刨坑等天水喝,省得老狗阿黃自己用爪子刨。
耍夠了這些鄉野活動,孩子又牽著我的手玩起數鳥窩的游戲來。爺爺家屋后有3 個鳥窩,屋前唐奶奶家杉樹上有2 個鳥窩,河北邊的馬爺爺家桑樹上有1 個鳥窩。唐奶奶獨身守寡多年,一年養一頭肥豬送給城里的兒子;馬爺爺老夫妻辭世才一周年,老屋大門緊閉著,墻根處枯草齊膝,要是二老在世,一定還會樂呵呵地端出糖果花生招待我們。
“為什么有的鳥窩有足球那般大,有的鳥窩只有我的拳頭那樣小呢?”
“為什么有的樹上有鳥窩,有的樹上沒有呢?”
“為什么有的鳥窩密不透風,有的鳥窩可以看見縫隙呢?”
這些看似簡單的問題,還真是不好回答。
“鄉下的鳥窩真多啊。怎么鳥窩里見不到鳥呢,出去找食了嗎,還是去了南方?鳥兒們還記得自己的家嗎?”孩子感慨著,擔憂著,自問自答著。
初四是晴天,父母親開始幫我們準備返城的食物。蔬菜有豌豆頭、荸薺、慈姑、大白菜和菠菜,葷菜有香腸、豬排骨和白切羊肉,還有赤豆、綠豆、紅皮花生米和新機的大米。
孩子認真地說:“奶奶,你這是讓我們去開農家飯店啊。”一句話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正月初五,從凌晨零時起,爆竹聲在四鄉八野此起彼伏、回聲不絕,到了上午八九點進入了高潮。今天,我們的財神爺在萬眾的熱烈擁戴下登天了,大地上勤勞的人們也將開始新的勞作了。
八九點起床后,一碗炒米茶、三塊糯米糕下肚便覺得飽了。一包包行李已經被父母在車后放妥。
車子七拐八拐地從村路上了鄉路,眨幾眼的工夫,父母的身影在車后越來越遠,老宅小得酷似一個加了蓋兒的鳥窠了。
“媽媽,我們繼續來數鳥窩吧。我數這邊,你數那邊,看誰數得多?”
“1、2、3……”
娘倆又興致勃勃地數起了鳥窩。
“媽媽,是什么樣的力量讓鳥媽媽鳥爸爸編織出這么大的鳥窩呢?一個如此精致而又溫暖的鳥窩,一定要銜成千上萬根樹枝和毛發吧。”
“真是令人驚嘆的愛心工程。”
“爸爸,我們明年還回老家數鳥窩,好嗎?”
3
我們多像是鳥兒啊,從老窩遷徙到城里,在城里蓋新窩,父母于是成了老家的守巢人。只有在秋冬初春時節,落葉紛紛,我們才會感覺到鳥窩的存在;只有在拋卻工作的煩擾,靜心凝神,才能夠感受到鳥窩的溫暖,在春節長假里回家光顧老鳥窩。
回城后的正月里,孩子也經常會在小區、公園的樹上東瞅瞅、西瞧瞧,若是發現了鳥窩,會歡喜上老半天。
我給孩子講了自己小時候的故事。那時候不懂事,就是個頑劣的鄉下孩子,喜歡和小伙伴一起爬樹掏鳥蛋、抓小鳥,用木棍捅鳥窩。記得有位老先生拿白居易的詩句教育我們:“誰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勸君莫打枝頭鳥,子在巢中望母歸。”隨著年齡增長,我慢慢地感受到詩人盼望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美好愿望。時過境遷,在一千多年后的春節里,鳥兒們用嘴巴編織出的偉大藝術品帶給我另一番感悟:勸君莫戀他鄉好,勸君莫嫌返程累。四季守巢月月盼,母在老家望兒歸。欲孝須趁親猶在,得有閑暇快快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