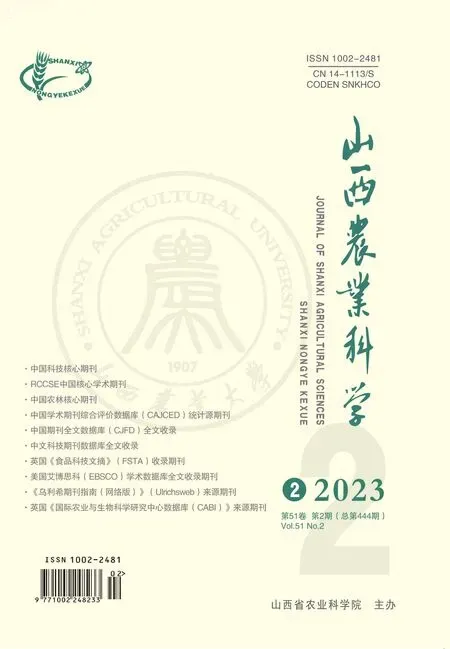魔芋病毒病研究進展
劉 歡,何 斐,李 川
(安康學院 現代農業與生物科技學院,陜西 安康 725000)
魔芋(Amorphophallus rivieri)屬于天南星科(Araceae)魔芋屬(AmorphophallusBlume)多年生草本植物,因其能提供大量的葡甘聚糖,且含有多種人體必需的微量元素,廣泛應用于食品、藥品、農業化工等領域,被譽為“長壽食品”,具有很好的保健功效[1]。我國是魔芋栽培大國,面積和產量均居世界首位。傳統的魔芋稀疏種植在樹陰下,病害較少,隨著魔芋規模化種植的推廣,栽培面積不斷擴大,為病害的發生和流行提供了有利條件。國內外魔芋主產區的真菌、細菌和病毒病害發生普遍[2]。相對于真菌和細菌病害,魔芋病毒病研究最為薄弱,而無性繁殖對于魔芋栽培非常重要,因此,病毒傳播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久而久之導致病毒積累,種性退化;另外,因魔芋長期受各種病毒侵染,導致自身抗性降低,加劇了白絹病、軟腐病和一些生理病害的發生流行,最終導致產量降低、品質下降,一些地塊甚至絕收,嚴重制約了魔芋種植業乃至整個產業的發展[3]。
本研究對現階段魔芋病毒病害的研究現狀進行了分析,從病原學、發生情況、檢測技術等方面進行歸納,并提出病毒病控制方法,分析魔芋病毒病研究中急需探明的科學問題,指出下一步研究方向,倡導重視魔芋病毒病害的發生蔓延,旨在為魔芋病毒病的深入研究提供參考依據。
1 魔芋病毒病病原種類和發生情況
1.1 魔芋花葉病毒(Dasheen mosaic virus,DsMV)
DsMV是馬鈴薯Y病毒科(Potyvirus)馬鈴薯Y病毒屬(Potyviridae)成員,基因組為正義單鏈RNA(+ssRNA),全長約10 kb,僅編碼一個大的多聚蛋白,通過自身編碼的蛋白酶將多聚蛋白加工成P1、HC-PRO、P3、6K1、CI、6K2、Via-VPg、Nia-Pro、NIB和CP等10個具有功能的蛋白[4]。病毒全基因組序列是開展其致病機理、病毒與寄主相互作用、基因功能和致病性等相關研究的基礎信息,然而,GenBank中DsMV全基因組序列大多來自同科植物馬蹄蓮和芋頭,DsMV魔芋分離物全基因組信息卻鮮有報道。
DsMV主要侵染天南星科植物,也是天南星科植物最重要的病毒病,其侵染對作物并不是致命的,但會延緩農作物生長并降低產量,DsMV發生嚴重時,可能會導致某些天南星科植物50%的產量損失[5]。對于魔芋來說,DsMV主要依靠種芋進行遠距離傳播,而在田間主要由蚜蟲以非持久性方式傳播給健康植株,傳播速度非常快,此外,汁液摩擦也可以傳毒[6]。
日本是全球魔芋種植的第二大國,對魔芋病毒病的研究起步較早,日本學者20世紀70年代在表現為花葉癥狀的魔芋植株中檢測到DsMV[7]。隨后到90年代,巴西科學家發現魔芋病毒病,受害葉片表現出花葉和畸形癥狀,有些植株塊莖變小,經過宿主范圍、形態學、細胞病理學和血清學特征鑒定,確定病原為DsMV,這也是DsMV浸染巴西魔芋的首次報道[8]。
國內學者陳集雙等[9]于20世紀90年代在杭州栽培的魔芋上檢測到DsMV,并對其組織病變進行了研究,結果在電子顯微鏡下發現細胞中存在較多的風輪狀內涵體(pinwheel inclusion body,PW),而這一特征在感染DsMV的植物體內是普遍存在的。2007年,胡曉等[10]在湖北恩施自治州栽培的魔芋中檢測到DsMV,其葉片表現出皺縮、褪綠和斑紋癥狀。之后到2008年,在安徽六安市各縣區栽培的魔芋中通過血清學檢測到DsMV,10份葉片樣品中病毒感染率達70%[11];同年,云南省昆明市嵩明縣栽培的花魔芋中發現一些植株葉片表現出典型的病毒病癥狀,且發生率較高,羅延青等[12]分離得到一個病毒分離物YN80,植株葉片癥狀為花葉、畸形和皺縮,經形態學和細胞病理切片觀察到明顯的PW,屬于典型的Potyvirus成員,后經血清學、RTPCR和基因測序分析,最終將YN80確定為DsMV的一個分離物。2021年,筆者在陜南秦巴山區采集了多份魔芋葉片樣品,通過RT-PCR檢測到DsMV,結果發現,DsMV在安康各魔芋栽培區廣泛發生,受害植株葉片表現為嚴重的褪綠斑塊、黃化、畸形和卷葉癥狀(圖1)。

圖1 受DsMV感染的魔芋植株癥狀Fig.1 Symptoms of konjac plants infected with DsMV
1.2 魔芋花葉病毒(Konjak mosaic virus,KoMV)
KoMV分類地位與DsMV一致,均屬于馬鈴薯Y病毒科(Potyvirus)馬鈴薯Y病毒屬(Potyviridae)成員,但二者沒有明顯的血清學關系。20世紀90年代,KoMV首次在日本群馬栽培的魔芋中分離到,能夠引起魔芋花葉癥狀[13]。隨后,日本學者測定了KoMV魔芋分離物全基因組序列,并對其生物學特性進行了初步研究,結果發現,KoMV病毒粒子為彎曲棒狀,長800~900 nm、寬13 nm。通過汁液摩擦接種至5科17種植物中,僅有3種天南星科植物感染了該病毒,這表明KoMV的寄主范圍很窄。同時該研究發現,KoMV可通過棉蚜以非持久性的方式通過傳播,亦可通過魔芋球莖進行傳播[14]。
2000年,方琦等[15]在云南曲靖、玉溪、楚雄等地采集了大量魔芋樣品,使用負染法在一些樣品中觀察到類似于KoMV的病毒粒子形態,但沒有經過分子檢測鑒定,在GenBank中也沒有發現KoMV中國魔芋分離物序列信息,僅有來自中國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區的KoMV當歸分離物全基因組序列(Accession number:MK770338)。由于 KoMV 在魔芋中的研究報道非常有限,尚不清楚KoMV侵染對魔芋品質和產量造成的影響。
1.3 黃瓜花葉病毒(Cucumber mosaic virus,CMV)
CMV是雀麥花葉病毒科(Bromoviridae)黃瓜花葉病毒屬(Cucumovirus)的典型成員[16]。基因組包括3個單鏈正義基因組RNA(RNA1、RNA2和RNA3),共編碼 5個蛋白(1a、2a、2b、MP 和 CP)。其中,1a蛋白由RNA1編碼,是病毒重要的復制酶組分,具備RNA依賴RNA聚合酶(RdRp)的活性,也是影響寄主癥狀的重要因子;2a蛋白由RNA2編碼,與1a蛋白共同完成病毒的復制,同時影響寄主癥狀的發展;2b蛋白是一個基因沉默抑制子,由RNA2的亞基因組RNA4A編碼;MP由病毒的RNA3編碼,負責病毒在細胞間的移動以及長距離運輸;CP由病毒來源于RNA3的亞基因組編碼,在病毒的包裹、復制、細胞間移動以及長距離運輸中都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同時也是病毒最重要的癥狀決定因子[17]。有些CMV 除基因組RNA以外還攜帶非編碼的衛星RNA(satellite RNA,satRNA),CMV的衛星RNA可以顯著地改變CMV致病性,加重或減弱寄主癥狀,這取決于衛星RNA和宿主物種[18]。CMV在密歇根州和紐約首次被發現,之后世界各國相繼報道,CMV侵染不同寄主植物,并已確定為幾種病毒病流行的致病因子[19]。其寄主范圍超過1 100種植物,造成的經濟影響非常大,CMV被列入“十大植物病毒”,排名第4[20]。CMV往往能在寄主植物上產生嚴重癥狀,多表現為花葉、矮化或畸形等[21]。由于CMV多侵染作物,且大多數作物種質中缺乏抗性基因,因此也是目前研究較廣的植物病毒之一[22]。
20世紀90年代,日本學者通過免疫擴散法首次在魔芋中檢測到CMV,受害植株生長遲緩,同時表現為小葉壞死和葉柄矮小癥狀,病毒可通過蚜蟲和機械接種傳播,但不能通過魔芋球莖傳播,日本科學家建議將該病命名為魔芋壞死性矮小癥(konjak necrotic stunt disease),隨后通過病害調查發現,CMV和KoMV是日本魔芋栽培中的主要病毒病原[23]。
我國自2000年開始,在云南魔芋主栽區進行了病毒病調查鑒定研究,通過電子顯微鏡檢測到直徑28 nm的球形病毒粒子,樣品經負染色后觀察到電子致密中心結構,屬于典型的CMV病毒粒子特征[24],受害植株葉片表現為黃化和花葉癥狀[15]。2015年,盛佳婧等[25]研究發現,可將CMV辣椒分離物通過機械摩擦接種至魔芋,接種7 d后,魔芋植株出現卷葉癥狀,并通過RT-qPCR檢測確認,但相對于其他寄主,CMV在魔芋中病毒含量較低。
1.4 番茄斑萎病毒(Tomato spotted wilt virus,TSWV)
TSWV是布尼亞病毒科(Bunyaviridae)番茄斑萎病毒屬(Tospovirus)的典型成員,病毒粒子為扁球狀,在80~120 nm[26]。基因組由3個單鏈RNA組成,其中L基因組為負義RNA,編碼RNA依賴的RNA聚合酶,與病毒復制相關[27];M基因組為雙義RNA,病毒鏈編碼一個參與細胞間運動的非結構蛋白(NSm),病毒互補鏈編碼2個糖蛋白(GPs)的前體[28];S基因組同為雙義RNA,病毒鏈編碼一個具有基因沉默抑制因子功能的非結構蛋白(NSs),而病毒互補鏈編碼核衣殼蛋白(N)[29]。
TSWV于1915年在澳大利亞首次被發現,現已蔓延至多個國家,1989年傳入我國廣州[30],主要由薊馬持久傳播,目前至少發現9種薊馬可傳播該病毒,少數情況下,TSWV也可通過汁液傳播[31]。TSWV能引起寄主植物各種癥狀,包括葉片、莖和果實上的局部壞死和斑點,致使果實失去商品價值[32]。據統計,全世界每年因TSWV侵染農作物導致的損失估計超過10億美元[33]。因其分布在世界各地、具有廣泛的寄主(>800種植物)、侵染作物導致重大經濟損失以及難以控制的蟲傳介體等特征[34-35],被列在十大植物病毒中,排名第2。在其報告近1個世紀后,全球經過30余年的科研攻關,TSWV仍然是最具經濟破壞性和科學挑戰性的植物病毒之一[20]。
魔芋中TSWV的報道非常少,僅我國學者通過制作超薄切片,利用電子顯微鏡在魔芋植株中觀察到典型的TSWV病毒粒子分布,該樣品來自云南,受害植株葉片表現為墨綠色[15]。
1.5 其他潛在的病毒
2005年6—9月,吳祝平[36]在湖北一些地區開展了魔芋病害調查研究,共發現了12種病害,其中包含病毒病,受病毒侵染的魔芋植株表現為矮化、葉片畸形;2016年,杞和平[37]在云南大姚縣發現魔芋病毒病,感病植株有矮化現象,且葉片初期表現為褪綠,后期逐漸黃化,但均未報道具體的病毒種類,由于植物病毒侵染引起的寄主癥狀往往比較相似,僅通過癥狀表現很難判斷具體是哪一種病毒感染。近期,筆者在陜南秦巴山區發現魔芋栽培區病毒病的發生非常嚴重,植株癥狀表現各異,主要有葉邊緣褪綠、花葉、黃化、卷葉、窄葉和畸形等(圖2),相關病毒正在進一步鑒定中。

圖2 魔芋病毒病癥狀Fig.2 Symptoms of konjac viral disease
魔芋地理分布廣泛,種芋在不同地區進行頻繁運輸交換,導致病毒的廣泛傳播和地理分化,隨著魔芋產業快速發展,加之天南星科植物病毒種類繁多,某些科目病毒檢測和鑒定又非常復雜,在后續科研攻關中將會有更多侵染魔芋的新病毒種類被發現。
2 魔芋病毒病檢測技術
植物病毒及其所致病害對各種農園作物的為害日趨嚴重且防治困難。病毒病大多為系統性侵染,魔芋一旦感病便會蔓延到全株,這就帶來了防治上的困難。多年來,人們針對不同病害進行了許多探索,但是,對大多數病毒病還很難防治,也沒有一個或一套通用、有效的方法。為了確保魔芋能進行持續穩定生產,無毒種苗與植物組織脫毒技術成為預防病毒病的關鍵方法,而魔芋病毒的檢測技術是防治病毒病最基本的前提。隨著分子實驗技術的不斷完善,魔芋病毒病的檢測方法越來越趨于快速、高效。
2.1 電子顯微鏡檢測
電子顯微鏡的誕生促進了植物病毒學的研究,德國科學家利用電鏡證實了煙草花葉病毒(Tobacco mosaic virus,TMV)的桿狀形態[38]。之后,生命科學領域開始廣泛應用電子顯微鏡技術,電鏡的應用為病毒形態與結構的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開創了病毒形態與結構研究的嶄新局面,用電鏡可直接看到病毒粒體的外形、大小及內外表面的構造[39]。
由于電鏡技術對操作人員的專業要求很高,而且儀器昂貴,檢測周期長和檢測樣本的數量有限等問題,在植物病毒的檢測應用中并不廣泛,取而代之的是血清學和分子檢測。但這并不意味著電子顯微鏡不具有應用價值,隨著現代化農業種植結構的不斷優化,新的病毒不斷被發現,對于新病毒的存在與病毒粒子的直觀性觀察,電子顯微鏡發揮的作用仍然是其他檢測技術不可替代的[40]。
2.2 生物學檢測
生物學方法是植物病毒檢測的傳統方法,操作簡單。我國很多學者曾利用生物學檢測方法對天南星科植物病毒進行初步鑒定。魔芋病毒可通過一些草本指示植物鑒定,比如利用黃瓜、西方煙、本氏煙等草本植物鑒定DsMV和CMV,將病組織通過汁液摩擦接種至草本寄主,大約13 d后,指示植物葉片出現褪綠點,葉片皺縮等癥狀[41];利用矮牽牛、三生煙也可以鑒別TSWV,病毒汁液接種矮牽牛后葉片出現褐色斑點,接種三生煙則顯示為葉片局部壞死點并伴有系統癥狀[42]。生物學檢測方法雖然耗時長,但它作為植物病毒學研究中的最經典、常用的實驗方法,在運用其他病毒檢測方法前先利用生物學檢測進行初步篩選鑒定,可以減少工作量。
2.3 血清學檢測
在20世紀60年代就有了血清學檢測病毒的報道,隨著植物病毒學和生物化學研究技術的不斷完善,這種方法已經成為檢測鑒定病毒病的基礎方法。DsMV、KoMV、CMV和TSWV這4種侵染魔芋的病毒早已制備出抗血清,對于田間魔芋病毒病大面積普查具有重大意義。中國學者基于血清學原理已經制備出DsMV和CMV檢測試劑盒[43],可對大量樣品進行檢測,具有高效率、簡便、無需大型儀器設備等優點。基于血清學檢測TSWV更快速方便,潘慧等[44]制備了TSWV多克隆抗體,可用于田間病株的病害診斷,具有一定的應用開發前景。由于KoMV在中國報道較少,在國內尚未發現KoMV血清學檢測應用,但其作為日本魔芋栽培中的常發病毒,KoMV抗血清在當地的應用也較為普遍[14]。相對于傳統的生物學檢測和電鏡檢測,血清學技術簡化了檢測流程,具有快速、易操作等特點,雖然檢測靈敏度相比分子檢測略低,對于病害的分布與大范圍調查研究,血清學的應用最為廣泛。
2.4 分子生物學檢測
分子生物學技術是以DNA或RNA為研究基礎,對植物病毒進行檢測鑒定的方法。分子檢測取樣方便,在受害作物任何部分收集樣品,均可以通過分子方法準確檢測。以4種魔芋病毒外殼蛋白(Coat protein,CP)為靶標基因,通過多重比對,在cp基因保守區設計用于RT-PCR檢測的引物,為魔芋病毒病的準確檢測鑒定提供了技術支持[45-46];針對DsMV、CMV和TSWV這3種病毒,RT-qPCR檢測體系也非常成熟[47-48],通常比普通RTPCR靈敏度高10~100倍。此外,可根據魔芋生長的不同時間、不同部位采取高效的分子生物學檢測方法。在植物病毒檢測方面,分子生物學是不可或缺的核心技術。對于病原的檢測,除了我們常用到的傳統PCR技術,目前已有很多新的技術基于常規PCR優化而來,如核酸酶保護試驗(Ribonuclease protection assay,RPA),環 介 導 等 溫 擴 增 技 術(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LAMP)以及多重PCR(multiplex PCR)等技術,在協助檢測鑒定魔芋病毒病害方面有一定的應用潛力。
3 魔芋病毒病防控建議
對于病毒病目前防治較難,主要體現在作物一旦發生病毒病便終身帶毒,另外魔芋主要依靠無性繁殖,病毒易通過種芋不斷積累傳播,加之多種病害復合侵染,為魔芋產業帶來嚴重的威脅。病毒病防控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第一,從正規經銷商購買種芋,確保種芋健康,避免病毒遠距離傳播,是最有效的防治方法。第二,倡導魔芋保健栽培,合理的水肥管理以及田間規劃,可以提高植株自身抗逆性。第三,在蚜蟲和薊馬盛發前期,選擇高效殺蟲劑殺滅可能的傳毒介體,阻斷病毒在田間交叉傳播感染。常用殺蟲劑有吡蚜酮、啶蟲脒、高效氯氟氰菊酯、苦參堿等,推薦化學農藥+生物農藥組合施藥,避免長期單一用藥;有條件的地塊也可以懸掛黃板或藍板對蟲傳介體進行誘殺,根據魔芋栽培面積和種植密度,合理規劃誘蟲板懸掛高度和田間布局。第四,對于田間魔芋表現出輕度花葉、褪綠、卷葉等病毒病癥狀的可以予以抗病毒治療,常用的植物免疫調節劑可選擇寧南霉素、香菇多糖、氨基寡糖素等藥劑,按照藥劑推薦濃度進行防治,可以減輕由病毒侵染導致的產量和質量損失。如果發現嚴重的植株矮化、黃化、畸形等,建議清除病株,帶出田間集中深埋處理。
4 魔芋病毒病研究中急需解決的問題
魔芋病毒病仍處于初步研究階段,根據研究現狀,其在生物學特性、發生規律和防控技術上有很多工作需要進一步完善:第一,導致魔芋病毒病害間歇性發生流行的侵染來源和關鍵因子尚不清楚,防治上缺乏針對性措施;第二,中國魔芋主栽區從未有過系統取樣調查研究,各個主栽區主要病毒株系類型、變異動態和發生消長規律缺乏系統監測,給預測預報和抗病育種工作帶來很大的盲目性;第三,主要病毒群體尚不明確,病毒長期潛伏侵染或多種病毒復合侵染導致魔芋自身抗性降低,進一步加重“兩病”的病情指數和發病程度,導致防治難、危害損失嚴重;第四,配套的防控技術體系尚不成熟,對于田間可能存在的病毒傳播介體、傳播規律尚不清楚;第五,當前魔芋品種對侵染魔芋的主要病毒的抗性不清楚,需開展系統的抗性評價,為抗病育種提供參考依據。
5 總結與展望
近年來,隨著葡甘露聚糖不斷被開發應用,魔芋在食品、醫療、化工及保健品市場上的占有量逐年擴大,隨之而來的是種植面積不斷增加,品種更替加快,被稱為“植物癌癥”的各種病毒病逐漸成為制約魔芋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由于魔芋栽培主要集中在中國和日本,有關魔芋病毒病害的研究在國際上鮮有報道。為確保魔芋能進行優質、豐產、持續性的生產與提高,必須重視并做好魔芋病毒病相關研究,為病毒病的治理提供新方法,新思路。未來研究可以從這幾個方面予以考慮:第一,天南星科作物病毒病種類繁多,造成的損失嚴重,魔芋病毒病種類應該遠不止已報道的這4種,可以利用新一代測序技術,系統鑒定魔芋病毒種類;第二,在已報道的4種病毒中,除KoMV研究較少,暫不清楚其為害特性,TSWV、CMV和DsMV已經在天南星科其他作物中造成嚴重為害,發生地塊農作物損失嚴重,摸清魔芋主栽區優勢病毒的分布、發生率,確定關鍵病毒已刻不容緩,對關鍵病毒分子致病機制開展科研攻關,為抗病毒育種提供重要依據;第三,由于一些常規檢測技術很難準確檢測低豐度病毒樣本(如休眠種芋),需要建立高靈敏度魔芋病毒檢測技術,對阻止病毒隨繁殖材料遠距離傳播有重要意義;第四,對魔芋主要病毒生物學特性、傳播途徑、群體遺傳結構、株系分化等開展持續性研究,有助于建立病害預測預報模型,推動魔芋病毒病防治工作;第五,利用植物組織脫毒技術對魔芋病毒進行清除,建立無毒種苗基地,同時也可對目前已有的魔芋品種開展抗病毒檢測鑒定,挖掘抗病毒品種和資源,可以很好地解決或降低由病毒感染帶來的品質和產量損失。
魔芋已成為我國云南、湖北、四川、貴州和陜西山區經濟發展、村民增收的支柱產業,積極做好魔芋病毒病科學研究和技術攻關,為決勝脫貧攻堅、同步全面小康、推進鄉村振興作出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