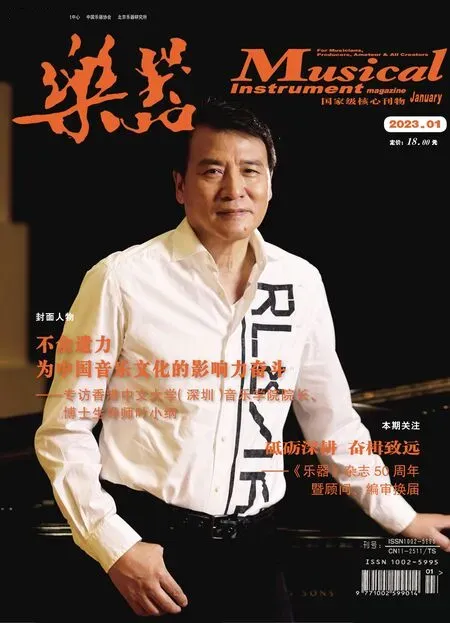融合和突破:新時代下缶的重構與傳播
文/吳 寬
一、缶的起源——古缶
據考證,缶被認為是中原漢族地區的一種古老樂器,但是在一開始,缶并不是直接作為大家娛樂的樂器出現的,而是一種陶制器皿,一般是用來盛水或者盛酒的,或者是作為一種祭器使用,所以缶的形狀一般類似于瓦罐或是小缸[1]。
著名的“擊缶”典故出自《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2]:“‘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于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于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從中就可以看出來缶作為樂器出現的原因其實是存在著一定的巧合性的,無論是秦王擊缶還是民間人們在喝酒助興的時候想要演奏,剛好面前有盛著酒的缶就隨手拍了起來,結果發現聲音清脆悅耳,并且根據其中盛酒量的不同,發出的聲音大小也不一樣,非常新穎有趣,受到了人們的關注。

圖1
不過缶作為樂器并沒有在當今過于流行,許多人其實在一開始的奧運會開幕式上看到這個樂器的時候大都是不知道它的名字的。所以這么看來大部分人們對于缶的了解是有所不足的,那么也就說明缶作為一個文化符號或者音樂符號在人們的記憶中存在著缺失。人們一開始了解這個器具的時候大都應該是在某某博物館中看到過(圖1),它是作為一種生活器皿來展示,對于缶的歷史發展并沒有去過多了解,也就導致了人們在傳播認識上一直偏向于認為缶是一種家用品,這也就導致了缶作為樂器的功能被一直塵封在博物館之中。人們對于缶的記憶或者說對于這種符號的記憶也就停留在了博物館中,人們僅僅是作為一個瀏覽文物的欣賞者一樣去觀賞缶這個器物,使得缶作為樂器這一部分產生了認知錯誤,人們對這一部分也就產生了思維誤區,認為既然是古物應該好好保管,就算是樂器也不能用來敲擊,畢竟也是文物,這樣也就使得缶還是在古代的氣味中得以溫存,并沒有完全融入到我們的生活中,就像是一位從古代走來的旁觀者,冰冷而無言。如果沒有在現在這個時代再一次展現屬于它的光輝,這對于一件完全具備音樂功能的樂器來說是非常遺憾的。
二、缶的新生——今缶
盡管在古代,缶的造型在現在人們看來都比較土氣,并不是可以讓很多人去接受它作為一種樂器來進行敲打。不過缶在2008年奧運會和2022年冬奧會中的兩次出現,也使得這件神秘的樂器一次次走入人們的視野中,可以說是以一種新的姿態走入到世人的世界,但又沒有流失屬于缶的古老韻味,是一種古代與現代交融的融洽感。當然也會有人說在開幕式上出現的樂器缶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樂器缶,是一種人為改造過的樂器。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件樂器的本體還是缶,并且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重塑,造型參考的是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銅冰鑒缶(圖2),這種缶的雙層結構就可以看出其的耐用性和敲擊的清脆感,看上去也非常的端莊大氣,不再是人們印象中的那種一用力敲就可能碎的陶瓷缶的刻板形象。在時代的發展中,不妨也會發現許多古物也在漸漸淡出人們的生活,如果想要再次走進人們的視野中,勢必要作出相應的改變和突破,以此來順應新時代的發展趨勢。在奧運會中進行千人表演的缶,肯定也是有著人們對古缶的一些繼承和創新的,以此來適應這種場合下的表演。隨著時代的發展,缶要融入進來,它的造型、材質、音質和表演等方面肯定都會有所變化,但是從兩個開幕式中的展現來看都是相當成功的。在這兩個開幕式中,都是以缶陣的形式來呈現(圖3),場面非常振奮人心,人們整齊劃一的擊缶動作,鏗鏘有力的聲音仿佛可以穿透人心,再加上開幕式上的缶都進行了現代化的改良與裝扮,采用了根據聲音大小變化的聲光燈等一些現代技術,這也就使得人們在缶陣中的表演更加磅礴大氣,恢弘壯麗,令人久久不能忘懷。這兩次的缶陣表演將現代的氣息融入到了這些古樸的器樂中,使得這些器樂重新擁有了鮮活的生命,不再像擺在博物館中的那些一樣死氣沉沉。當然在運用缶陣方面也要有所考慮,要保持好應有的節奏,因為缶既是一件樂器,同時也是中國的優秀文物,其中飽含著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要讓現在的人們能夠有更多正確的認識和了解,然后將之不斷地繼承并傳播下去。
三、缶的重構特色及視覺呈現
在人們看來,奧運缶(圖4)的形象是非常古典大氣的,和人們潛意識里認為的古老的缶器是有所差距的。當然,奧運缶是經歷過現代氣息和古代氣息的碰撞所形成的產物,可以認為是一種繼承與發展。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中,其實遠古的缶就像上面所提到的一樣,一般是指一種瓦盆或者是瓦罐,因此古代人們所說的擊缶其實也就是去敲打瓦盆或是瓦罐,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一些節奏感和韻律感,成為了一種樂器。這么看來與奧運會上出現的缶形象來比可謂是天差地別,一個平平無奇,一個氣勢磅礴。雖然話這么說,但是奧運缶結合的古缶的元素還是比較多的,還是以缶這個符號作為本體,但是在外形上做出了現代化的創新和古老化的結合。由于造型參考的是青銅冰鑒缶,這種缶顧名思義,帶冰字又具有缶存儲物品的功能,其實就是古代人們的小冰箱,因為其周邊有夾層是可以放入冰的,所以可以有效的貯存食物,從這我們也可以看出我們的祖先所掌握的精湛的青銅鑄造技術[3]。

圖2

圖3

圖4
奧運缶造型上雕刻的各種花紋和動物造型也是有參考中華傳統文化的。通體以一種暗色調為主,大體上使用黃色為主,主要是為了宣揚出我們是偉大的炎黃子孫。通體的色澤上呈現出金屬的質感,周身雕刻裝飾有象征著中國元素的古老傳統紋樣,紋樣多以黃色和黑色為主。再加上奧運缶是一個雙層組合結構,為了貼近奧運會節儉的理念,外層使用的都是雕刻缶,內層使用的都是貼面缶,雖然外觀方面有所相似,但是各有風格。外層的雕刻花紋大多都是瑞獸的圖文,宣揚的是祥瑞之風,缶身各部分的支撐也都是瑞獸形狀,體現了缶的正氣凌然。同時在擊缶的那一面的兩側是有兩個隱藏鼓槌的地方,這里是有一個小機關的,可以起到一個彈出鼓槌的作用,方便演奏者去展示。過后來為了減少失誤取消了這個環節,不過這個小機關卻保留了下來,成為了一個擺放鼓槌的地方,非常的精妙。還有就是奧運缶四周的支腳都是龍形的,也是在表現我們中國人民是龍的傳人,龍同樣也是古老中國元素的一種象征符號。雖然黑金的配色使得奧運缶看上去充滿著尊貴的氣息,但是多種淳樸的中國紋樣在上面的勾勒使得奧運缶整體看上去非常的融洽,仿佛渾然天成,既有尊貴典雅的氣息又帶有質樸古老的氣韻,據說每個奧運缶都是有著屬于它的獨特并且唯一的編號,這更加體現了奧運缶的神秘感。奧運缶讓人驚嘆的設計并不止于此,它還有著更加震撼人們心靈的設計,那就是在奧運缶的面板上還鑲嵌有許多像米粒大小一樣的小燈,隨著演奏的開始,眾人進行擊打的時候,奧運缶的面板上就會隨之出現一種閃爍的狀態,就像是天上一閃一閃亮晶晶的星星一樣,非常的唯美。借助缶面上多個LED燈的排列,隨著眾人的表演,缶陣也會展現出各種不一樣的圖案,就像兩次奧運會上時間的倒計時一樣,這樣仿佛神來之筆的設計不僅給世人傳達出來一種中國發展到如今的光陰變化之感,也給世人在視聽感受上展現出一種別樣的風采(圖5)。
這樣一種結合了聲光電三位一體的現代科技的缶,對世人充滿著強烈的吸引力,也再一次向世人展現出中國祖先的高超智慧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設計之美。奧運缶的設計使其仿佛是從遠古一直走到現代的一名戰士,眾人在奧運會上的演奏也仿佛使人們再一次夢回古代,見證了一場具備現代氣息的古代樂隊的演奏。這也同樣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一種變化和方向,也是中國一個重要的歷史象征符號。奧運缶的設計可以說是古代神韻和現代科技完美融合的結晶,無論是要去展現奧運精神,還是說要去傳播中國的傳統理念,又或者是要傳達中國人民熱情好客的習慣,都已經在磅礴大氣、氣勢豪邁的擊缶表演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所以無論是奧運缶的設計還是擊缶的表演方式,都讓人們真實地感覺到缶作為樂器的力量和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和擁抱世界的精神。
四、古缶傳神 今缶傳情

圖5

圖6
在開幕式中的缶陣表演令許多人過目不忘,其實從缶陣中表達出來的情感也是異常豐富的。首先,在兩次開幕式中擊缶,一方面是為了展現古代中國人民的智慧和中華民族的的燦爛文化,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展現我們中國人民的精氣神是昂揚向上的,傳播出來的是中國人民自強不息的精神,以及隨著擊缶聲音的越高越快,也是在表達奧運健兒們在后面的比賽中要更快更強,展現屬于他們的光輝。其次,在開幕式上擊缶也是一個迎賓的儀式(圖6),中國是禮樂之邦,擊缶而歌也是為了展現中國人民的熱情好客,以及對于在開幕式上的缶都是四平八方的,也是寓意著迎八方客,表達的是中國人民對世界人們的熱情和大型賽事即將開始的激動心情。最后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眾人擊缶也是擊出存在于歷史中的回響,里面有著人們振興古代樂器的期盼和中國古代樂器走向世界的愿望。同時這次擊缶也是將華夏禮樂的傳承蘊含在其中,想要抒發的是中國人民的恢弘氣勢但又不失禮儀,也是將中國富強偉岸的國家形象表達了出來。同時在擊缶的時候,燈光隨之舞動,人影在其中交匯相映,場景美輪美奐,給人們氣勢宏大的感受。擊缶的震撼表演給人們的視覺沖擊還是非常大的,在開幕式中擊缶也讓人們看到了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遠流長,人們在聽缶的時候也是在領略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民族歷史的厚重,在缶聲中漸漸感受中國文化的積淀以及在其中閃閃發光的藝術神彩。
兩次奧運會都是人類體壇上的圣典,兩個開幕式上的“擊缶而歌”可以說只是從華夏豐富的文明大餐中閃出的一小扇貝,同樣也只是陶瓷文化、青銅文化的一次簡短折射[4]。但作為古代陶瓷器文明成果之一的缶卻通過這兩次開幕式向世界發出了自己的真切情感。雖然在如今具體的實物都已無處找尋,大多也都陳列在博物館,但在現在人們對于缶的繼承與創新的認可,也使得缶擺脫了世俗的束縛,以一種新穎、創新、獨特的造型出現在世人面前。如今結合著生活實用和藝術裝飾,新的設計思維已經使得缶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陶缶所蘊含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和古樸莊重的人文精神,尤其是“陶缶之勇”更應當成為激勵我們愛國主義思想,并成為我們在藝術領域勇于突破藩籬、勇于創新的精神指南,如今的“缶”依然是我們學習、研究和創新的重要對象和典范。
所以無論是古缶還是今缶,都有自己存在的價值,各自傳承著屬于它們的文化意義和時代精神。對于古缶創新突破得到的今缶,其中也飽含著人們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期盼,不希望中國古老的文化被人們所遺忘。在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中,今缶并沒有拋棄自己的本質,反而像是一種特向的發展,今缶的設計使其更加貼合表演的形式,彌補了前身沒有盡情表演的遺憾。而古缶在古代更偏向于盛水的器皿,作為樂器的價值并沒有在當時得到完全的發揮,反而在現代有了更進一步的突破。今缶與古缶遙遙相望,也正是中華文化傳承的繼承與發展,透露著人們對于振興中華傳統文化的堅定決心。
五、新時代缶的傳播及意義
到這里我們不禁就會想到為什么開幕式中會突然去使用缶陣來演奏呢?相比較其他一些著名的古代樂器來說,缶遠遠沒有像它們那么出名。像是古琴和編鐘這類的器樂莊重大氣,一眼就可以體會到其中蘊含的磅礴華夏氣息,而且相對于缶來說,古琴和編鐘更為人們所了解,傳播的也更為廣泛,不過這些當然也是經過了仔細考慮的,缶在這里的出現是蘊含著深意的。
首先,中國上下五千年是擁有著豐富的文化底蘊的,有許多底蘊或者文物人們需要去發掘,去傳播,不能一直把目光放在著名的事物上,而忽略了其它一些在這個時刻更加需要人們去傳播的事物,它們也有屬于它們的光彩,不能讓它們慢慢離開人們的視野。這兩次開幕式中缶陣的表演也讓人們重新開始認識到這件古代樂器,使人們開始對這件樂器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這何嘗不是一種對中國文物的保護和傳播;這何嘗不是一種對中華文化的繼承發揚和傳播;這何嘗不是對中國古代樂器的一種完善以及人們對中華文化認同感的提升。
其次,其實古琴和編鐘的氣勢并不適合于在開幕式上進行大型的震撼表演,在這種熱情洋溢的場景下需要一種振奮人心的感情渲染和文化傳播,而古琴眾所周知是一種文雅的樂器,適合在一些靜怡的場景中進行彈奏,讓聽者慢慢沉浸在清雅的音樂中,顯然與奧運會的熱情奮斗是有所不符的。而對于編鐘來說,雖然編鐘演奏效果非常獨特,能夠吸引世人的目光,音樂也比較清脆悅耳,具有非常經典的東方色彩,但是編鐘所體現的厚重感在這一個普天同慶、熱情奔放的場景下似乎也不能夠完全融入進來,營造不出那種磅礴的氣勢以及不能夠傳遞一種中華民族的頂天立地、磅礴大氣的氣勢,所以缶以及缶陣的出現就巧妙契合了這個場景。缶作為一件民間器物具有的是雙重身份,缶在中國音樂史中是一直隨著民間音樂在發展的,所宣揚傳播的也是人們內心最為真切的情感,所以對于缶來說,它的民俗根基和人們對它的繼承是它在歷史上得以延續的動因。雖然還有許多人不知道這件樂器,但是在開幕式中的表演已經使它從遠古走來,帶著嶄新的面貌在生活中進行音樂文化的傳播,再加上奧運會的舉辦也是符合了民俗文化的意義,這里的缶陣也有著象征意義,象征著人們團結一致、擁護和平、保持友誼的精神實質,使奧運會能夠圓滿舉辦下去,在這里缶就化身為一種精神,擊缶也是為了使這些精神傳播并且傳承下去,同時也是讓世人知道缶的中華民族特色。
最后,在開幕式中使用缶陣是為了和閉幕式中的鼓陣形成呼應,兩種打擊樂器充滿力量的聲音,何嘗不是在傳播一種激情,在這種普天同慶的場景下,人們也會被擊缶而歌的氣勢所感染。
新時代下缶的傳播,也是對中國文化符號的傳播。通過人們的視覺和聽覺,人們在缶身上看到并感受到了許多能夠代表中國文化氣息的符號,雖然在眾人的表演下可能看得不夠真切,但是通過表演者的氣勢和情緒仍然可以打動很多人的心靈。因為中華文化的傳播并不是只靠視聽傳播就可以了,在如今這個日新月異的時代,惟有振奮人心、感染他人的文化才能更好地被人們所記住并傳承下去。在缶陣表演的這一場景中,眾人可以說是一體的,在情緒方面的體驗也會使他們產生情感上的共鳴,就像目光所至,皆是華夏這種感受一樣。所以在這種場景下,缶承載著華夏人民的激情和華夏文明的深厚,通過擊缶正是把這種情感和文化傳播給人們,使他們深深沉浸其中,體會華夏文明的奧秘和深厚,也使得中國人民對于中華文化的歸屬感有了更加深厚的體驗,文化認同感也更加強烈。
中國在世人面前進行的缶陣表演也使得缶活了過來,從缶中人們也可以感受到一股人們的激昂和歡樂在流動,人們也會感受到中國是一個深刻秉持著傳播文化和為文化傳承負責的大國,中國的國家形象在擊缶的聲音中也慢慢從被人們所感知到被人們所接受,從而得到了一定的提升。缶陣的成功演出也使缶這件樂器受到了許多關注,使得缶這種樂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經傳播出來了,而擊缶所傳播的熱情、歡迎和激昂等多種情感也在聲聲缶聲中傳播到了每一個人的心靈里。
六、結語
擊缶而歌不知道喚起了多少人心中的熱情,每個人的心仿佛是隨著缶聲舞動的。缶作為中國古老的樂器之一凝聚著中國古人的智慧在其中,奧運會和冬奧會中的缶陣表演就像是神來之筆,其獨特的魅力已經久久停留在人們心中,久久不能忘懷。缶這件樂器經過了近千年的滄桑的發展,是北京奧運會和冬奧會把它從塵封的博物館中喚醒,讓全世界的人民認識了它,使它在如今以一種新的姿態呈現在眾人面前,這不僅是對傳統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和未來的展望和相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