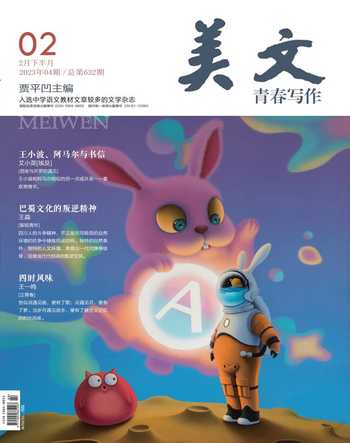清風徐來
靳小倡
生于陜南靈秀小鎮繞溪鎮。本職醫生,偶爾寫字,常常發呆。作品見于《河北林業》《海河文學》《參花》《合瀾海》《河北日報》《錢塘江文藝》等。
如今,都市里大街小巷新式理發店五花八門,工作流程、設備都與過去的有天壤之別。新式理發店大都裝了空調,用電動工具,給一位男性顧客單純理發往往只需三五分鐘。
不過,快是快了,顧客卻談不上享受了。
俗話說“敲鑼賣糖,各干各行”,講的就是老行當。老行當中的理發師,過去叫剃頭匠。開店經營的叫剃頭鋪,流動理發的叫剃頭挑子。所謂“剃頭挑子一頭熱”,就是說剃頭匠一頭挑著火爐與銅盆,一頭挑著供顧客落座的方凳,走街串巷。
童年時我家住在紫陽縣繞溪鄉,附近就有一家剃頭鋪。鋪面不大,只有倆座位。店主父子倆還收了兩個小徒弟。別看店小,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在當地很是聞名。
那時顧客到剃頭鋪里剃頭,只需往老式靠背椅上一躺,白大圍裙一披,微閉雙眼,就可以睡眼惺忪地任由剃頭師傅擺弄。
剃頭師傅先用手推剪子剪發,再一刀一刀地修發;接下來是用剃刀刮臉、修眉毛。這個過程中,師傅還時不時地將剃刀在一小塊油浸布上“嚓嚓”地反復磨礪,以使其鋒利免銹而不傷皮膚。熱烘烘的毛巾鋪在顧客臉上,取下后再涂上皂角泡沫。剃頭師傅輕輕地刮著,幾乎讓你感覺不到刀鋒在皮膚上游走。從臉部刮到嘴沿、下巴,再刮到鬢角。然后刮脖頸,刮耳輪。最后的幾刀是高超的技術——修眼眶。溫潤的刀角在眼眶內轉動著,刀鋒飄過,眼角雜質瞬間消除。刮完臉,師傅又拿出一套小件工具,為顧客剪鼻毛、剪耳毛,并用小耳勺、小鑷子取出耳中耵聹等物。然后用一只小毛球伸進耳中,輕輕轉動著清掃耳膛,一種酥麻感頓時從耳膜附近放射到全身,舒坦感一時無以言表。
那時剃頭常常要花一個多小時,孩童剃頭的時間則較短。那些幼童幾乎都是在父母的押送下來到店里,一個個被按坐在老式靠背椅上,一邊號啕大哭或抽泣不止,一邊接受著剃頭師傅的擺弄。等到被父母牽出店時,幼童一個個都成了漂亮的“鍋鏟頭”——前鏟子后柄子,那尾柄就像是一條微小的馬尾,在微風中輕輕飄動……
剃光頭,最能考驗剃頭匠的手藝了。我家附近那家剃頭鋪師傅剃光頭的手藝,堪稱一絕:無論怎樣的頭型,剃完后無論你怎樣摸,都是光溜溜,沒有絲毫發茬的感覺。
那時店里沒有空調,也沒有電風扇、電暖爐之類。可是店里自有辦法。冬天,店里燃起兩盆炭火,顧客躺在老式靠背椅上,周身暖暖和和的。到了夏天,剃頭堂屋上方則掛起一塊厚厚的長方形大紙板。紙板表面用白紙包裹并粘貼牢固,上書“清風徐來”四個大字,紙板上方用繩索固定在樓板橫梁上,然后安上滑輪,再拴上一條長長的繩子,一個老式大風扇便安裝完畢。有顧客進店剃頭,一個小徒弟便蹲在堂屋后墻根下,一下又一下拉動繩子,那紙板大風扇便在空中來回不停地蕩著秋千,攪動著空氣,送來陣陣涼風。
兩個小徒弟是老師傅鄉下遠房親戚,學徒是為了到鄉下當流動剃頭匠。那時,學剃頭很不容易。學徒三年的頭一年,徒弟只能端水、遞毛巾、洗頭,或者夏天牽拉“清風徐來”紙板大風扇。到后來,老師傅就拿出個冬瓜,讓徒弟們練習用剃刀剃瓜皮。等到徒弟真正學會了十六般技藝:剃、刮、梳、編、掏、剪、剔、染、捏、拿、捶、掰、接、活、舒、補,才夠資格當剃頭匠。
20多年過去了,老家的老式剃頭鋪早已不見蹤影。時代在發展,老行當剃頭匠漸行漸遠,老式剃頭鋪也難逃被時代淘汰的宿命。其實,又豈止剃頭匠與剃頭鋪,許多老行當,如篾匠鋪、鐵匠鋪、老式茶房等,在很多城市已經看不到了。想想,真有點惋惜。
前些日子,路過南昌時,在紅谷灘新區贛江邊,忽見路旁一組精美的銅質雕塑——那是一組老行當的塑像。那尊老式剃頭匠塑像,讓我癡迷了一會兒。我似乎又看到了在那家老式剃頭鋪里,老師傅正瞇著眼細心地為顧客理發;似乎又感受到了那塊“清風徐來”老式大風扇,此時正蕩起陣陣清風……
哦,老行當——我國各地的傳統手工藝絕活,但愿能夠永久地保留下去,而不僅僅是只留下一組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