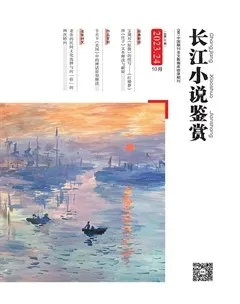從存在主義女性主義視角解讀《蝲蛄吟唱的地方》主人公基婭的成長歷程
陳思余 胡戈
[摘? 要] 《蝲蛄吟唱的地方》是美國當代作家迪莉婭·歐文斯于2018年發(fā)表的長篇小說,講述了自幼就生活在濕地的基婭·克拉克從一無所有的小女孩成長為生物學家的故事。本文從存在主義女性主義視角出發(fā),分析小說主人公基婭所面臨的生存困境、自我覺醒與超越、實現(xiàn)自由解放三個成長階段,解讀主人公基婭作為男性和資本主義父權制度影響下的“他者”是如何通過自我選擇和反抗,擺脫“他者”身份,最終成為一名生物學家,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
[關鍵詞] 《蝲蛄吟唱的地方》? 存在主義女性主義? 他者? 自由解放
[中圖分類號] I06?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3)24-0054-04
《蝲蛄吟唱的地方》以一樁1969年發(fā)生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濕地的謀殺案為主線,串聯(lián)起了兩條時間線的故事情節(jié)發(fā)展。隨著調查的逐漸深入,主人公基婭的故事被慢慢揭開,案件的真相也逐漸浮出水面。基婭自出生起就與父母和哥哥姐姐們生活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海濱的濕地中,一家人過著簡樸的生活。然而,隨著父親的酗酒問題日益嚴重,他的家暴行為也變得越來越頻繁。基婭6歲時,母親和哥哥姐姐們因為父親的暴行相繼離開了這個家,再也沒回來過。后來,父親也離開了家,從此杳無音信。年紀尚小的基婭開始獨自面對這個陌生的世界,生存危機以及來自各方面的壓力接踵而至。即便如此,基婭也沒有陷入悲怨的泥淖中,而是選擇了覺醒與反抗,她克服重重阻礙,最終找到人生的意義。
西蒙·波伏娃運用存在主義哲學的觀點對女性主義進行了闡述,其著作《第二性》成為現(xiàn)代女性主義理論的重要來源之一。同時,存在主義女性主義也是女權主義運動第一次高潮時期的重要流派之一,其主要觀點對后來女性主義的發(fā)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存在主義女性主義強調對所謂的女性‘內在性的超越,企圖擺脫‘他者和‘他性狀態(tài),使女性主體意識得以樹立,使女性成為一個自由的主體,實現(xiàn)自身的價值。”[1] 從存在主義女性主義視角對小說《蝲蛄吟唱的地方》的主人公基婭進行解讀,可以更深入地對其成長歷程進行把握,剖析基婭遭受的壓迫和生存困境的根源,即男性和資本主義父系社會所賦予的“他者”身份和“內在性”特質,見證她為克服這些困境和尋求自我解放所做出的努力。
一、“濕地女孩”的生存困境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寫道:“定義和區(qū)分女人的參照物是男人,而定義和區(qū)分男人的參照物卻不是女人。她是附屬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對立的次要者。他是主體、是絕對,而她則是他者。”[2]基婭在成長過程中深受由男性定義的“他者”身份的影響,被身邊的男性視為可以隨時被拋棄掉的、附屬者般的存在。男性“主要者”們一步步地剝奪基婭的主體性和生存空間,使她面臨著多種生存困境。
首先給基婭帶來這種影響的是她的父親,這也是導致基婭生存困境的開端。基婭父親作為一家之主,擁有絕對的話語權。在他眼里,自己是整個家庭的權威,而其他人都是依附于他的存在。他成天沉浸在酒精中,忽視妻子和孩子們的需求。一旦出現(xiàn)不滿意的地方,或是有違背他意愿的情況,他就會以暴力回應。有一次,妻子勇敢站出來進行反抗,結果被他打得血肉模糊。他的暴行最終導致妻子等人的出走。經此一事,基婭父親的暴行有所收斂,偶爾還會帶著基婭去鎮(zhèn)上玩耍,或外出捕魚,但他仍把基婭當作一種可有可無的依附,沒能肩負起父親的責任。他從不關心基婭是否吃飽穿暖,甚至把做飯的重任拋給了年紀尚小的基婭。捕魚時,他不允許基婭跟其他同齡人說話。基婭母親來信詢問基婭近況并打算接走基婭時,他憤怒地把信燒掉,并回信告訴她這輩子都別想再見到基婭。他依舊沉溺于酒精中,常常因此好幾天不回家。某次外出喝酒后,他再也沒有回來,只留下基婭一個人。從基婭的童年經歷來看,她和母親都成為絕對權威父親影響下的“他者”,她們沒有話語權,沒有反抗的機會。最終,基婭母親雖出走,但她因受到丈夫阻撓無法再次見到基婭而患上精神疾病早早離世,而基婭則因父親的暴行失去了母親的關懷,從此獨自一人面臨生存危機。
將基婭視作“他者”看待的還有同她交往過的兩位男性泰特和蔡斯。泰特是基婭在潟湖遇見的男孩,基婭當時迷了路,正在捕魚的泰特見狀后幫助她回到了家。從那一刻起,遭到親人拋棄的基婭被泰特的溫柔所打動,“她第一次呼吸時不再感到痛苦,還感受到了傷痛之外的東西”[3]。父親離家出走后,兩人間的互動日漸頻繁,關系也變得更加親密。泰特教基婭認字和讀書,兩人在濕地間嬉戲,互表愛意。后來,泰特考上了外地的大學。為了讓基婭放心,臨走前他向基婭保證自己會經常回來看她。然而到了約定見面的日子,基婭什么都沒等來,泰特也從此失去聯(lián)系。大學的經歷使泰特的想法發(fā)生了轉變,他想要追逐自己的研究夢想,害怕基婭會阻礙自己的腳步。除此之外,他認為自己跟基婭早已不是同一個世界的人,覺得基婭很難融入他的圈子,因此他選擇在沉默中拋棄基婭。在泰特心里,基婭無形中成為“他者”的角色,即使對方是自己曾許下承諾的愛人,泰特也從未真正將對方納入自己未來的規(guī)劃中。“從童年開始,男性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去追求和享受自己的事業(yè),從來不會有人告訴他們,他們想追求的事業(yè)會和自己作為情人、丈夫以及父親的幸福相沖突,他們的成功從來不會降低他們被愛的可能性。”[2]當“他者”基婭可能成為泰特前行路上的阻礙時,他便草率地將其拋棄,甚至不愿當面向對方表達自己的想法,獨留基婭一人在濕地等待。
后來,基婭遇見了蔡斯,對方是小鎮(zhèn)上的富二代。兩人相遇于濕地,并在相處一段時間后確定了戀人關系。蔡斯向基婭承諾自己會跟她結婚,但現(xiàn)在還不是時候,希望她能夠再等等。基婭以為自己終于找到了那個不會再拋棄自己的人,于是開始期盼著和對方結婚。但是,后來發(fā)生的一切讓她的希望再次幻滅。蔡斯其實是一個花花公子,他跟基婭的感情只不過是他尋歡作樂的一部分。他不尊重基婭對于濕地的熱愛,認為她對濕地生物的了解沒有任何意義。蔡斯跟他人談起基婭時,仿佛是在討論某種玩物。有一次,基婭在小鎮(zhèn)遇到蔡斯,他的旁邊站著一位妝容精致、打扮時髦的女性。打完招呼后,這位女性直接宣告了她的身份——蔡斯的未婚妻。得知此事的基婭憤然離去,并在這之后向蔡斯提出分手。這一行為直接讓蔡斯暴露出真面目,他以暴力威脅基婭,并企圖強暴她,傷痕累累的基婭從此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小鎮(zhèn)的警察也被家境顯赫的蔡斯收買,對于基婭的求助不予理睬。對于蔡斯而言,基婭就是滿足他尋歡作樂的附屬品。他通過精神控制等手段將基婭牢牢困在自己身邊,當自己的意圖被揭露后便開始訴諸暴力,并通過自己的權勢向其施壓,為的就是宣誓自己作為“主要者”的主體地位,而基婭則在這種強壓下艱難生存。
二、困境之下的覺醒與超越
“他們拋棄了她,留她獨自生存,獨自掙扎。”[3]基婭父親的酗酒和暴力行為導致家庭破碎,初戀泰特的冷漠拋棄以及花花公子泰特的始亂終棄,使得“他者”基婭反復地沉浸在被拋棄和背叛的痛苦中,一次又一次地尋找存在的意義。但是,這些壓迫并沒有熄滅基婭心中的那團火焰,而是讓她一次次地成長并逐漸擺脫“他者”身份所帶來的困境,實現(xiàn)了自我覺醒。波伏娃認為女性所處的“他者”地位深受其“內在性”的影響。“‘內在性描述的是一種沒完沒了地重復著對歷史不會產生影響的工作的處境,在這種處境中女性處于封閉、被動而無所作為的生存狀態(tài)。其外在表現(xiàn)最直觀的就是女性在經濟上、文化上對男性的依賴。”[1]女性如果要擺脫“他者”身份的桎梏,就必須從“內在性”入手,實現(xiàn)經濟上的獨立和文化上的超越,以消除“內在性”的影響。
父親離開家后,基婭失去了一切經濟和生活來源,身邊只有這個僅剩空殼的家和一艘船。但是,年僅10歲的基婭沒有因此而喪失求生的意志,她強忍著被拋棄的痛苦以及獨自面對世界的恐懼,開始為生存而努力。基婭通過捕獵和在海灘挖貽貝的方式獲得食物。父親帶她乘船捕魚的經歷使她學會了駕駛那艘船,她每次都會挖出多余的貽貝,然后駕船前往小鎮(zhèn)碼頭與商販進行交易。商販一開始以已經有了貨源為由拒絕了基婭的交易,但基婭努力爭取,向對方承諾自己每次都會比其他人來得早,最終說服商販并達成合作。自此,基婭每次都會趕在天亮之前挖好貽貝,然后早早趕往商販處進行售賣以換取錢財、食物和汽油。
雖然身邊沒有至親的關懷,但濕地早已成為基婭心中母親的角色。濕地養(yǎng)育了基婭,為她提供食物,教她人生哲理,更重要的是,濕地永遠不會拋棄她。基婭從小就對濕地生物充滿興趣,得益于濕地豐富的物種資源以及奇特的自然風貌,她每天都能接觸到各種各樣的濕地生物。她觀察它們的生活習性,收集鳥類的羽毛,并用手中的畫筆記錄下她所觀察到的一切。后來,在泰特的幫助下,基婭學會了識字,并接觸到有關生物學的各種書籍。她開始通過文字了解與自己朝夕相伴的濕地生物,書中是如何描述它們的,又有哪些物種和特征是書中尚未提及的。出于對濕地的熱愛,基婭不斷積累生物學相關知識,并開始借閱更加專業(yè)的書籍。
在泰特食言并失去聯(lián)系后,基婭再次經歷了內心的折磨與痛苦,她不明白人為什么要拋棄同自己最親密的人,親人如此,愛人也是如此。后來蔡斯的始亂終棄更是給了基婭沉重的一擊,但是,一次次的打擊并沒有擊垮基婭,濕地總會在她需要的時候聽她傾訴并治愈她,而她在汲取了濕地的能量后又會變得更加堅強。之后,基婭將自己全身心投入到沼澤生物的研究當中。她游走于濕地的各個區(qū)域,收集并制作生物標本,然后再在標本下方添加相應的筆記,詳細描述這些生物的特征和習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基婭的標本手冊日漸充實,里面的圖畫比現(xiàn)有的書籍更生動,描述更加細致,收錄的物種也更為豐富。她試著將這些標本和文本寄給一家出版社,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夠被認可,同時也希望世人能夠通過它們更加了解濕地和濕地生物,以回報從小養(yǎng)育自己的濕地。基婭很快就收到出版社的回信,對方表示打算將基婭的成果制作成書并進行出版,同時向她支付版權費用。出版后,書籍受到大眾的青睞,基婭也從中獲得了收益。她還與出版社達成進一步的合作,將制作和出版更多的標本書籍。自此,基婭再也不必以挖貽貝和捕獵謀生,實現(xiàn)了財富上的獨立。
在此期間,地產開發(fā)商曾到訪基婭家并聲稱打算在此處新建一家酒店。基婭到小鎮(zhèn)政府詢問后才得知,自己的爺爺雖曾買下這塊地,但由于拖欠了多年的稅金,政府打算把它的所屬權移交到能夠付清這筆稅金的人。弄清事情的原委后,基婭向政府證明了自己與爺爺?shù)挠H屬關系,然后用自己剛得到的版權費和其他積蓄付清了稅金,將這片濕地的所屬權掌握在自己手上。再后來,基婭成為年輕有為的生物學家,她積極參與學術活動,擁有眾多出版成果,贏得了世人的稱贊和尊重。“擺脫女性的‘內在性關鍵在于她必須在作為‘人的意義上重新確立自己的主體地位,并在此基礎上構筑新的觀念體系,組織新的行為系統(tǒng)”[1]。如果說過去的基婭是依附于父親、泰特和蔡斯的“他者”,思想和行為處處受到他們的限制和影響,那么蛻變后的基婭則是更為強大的存在。在經濟方面,她不依賴于男性的給予,通過出版圖書實現(xiàn)了經濟獨立,并從開發(fā)商手中拯救了這片濕地,獲得了它的歸屬權。而在文化方面,基婭突破了資本主義父系社會為女性設下的刻板角色和行為,在生物學界成為獨當一面的存在。由此,基婭擺脫了“內在性”對于女性的束縛,在獨立人格和主體意識的指引下,完成了自我覺醒與救贖。
三、尋求落葉歸根的自由與解放
在歷經磨難后,基婭終于通過自身的努力擺脫了“他者”身份帶來的壓迫與生存困境,實現(xiàn)了對自己人生的掌控。成為生物學家后,基婭仍然決定留在濕地,并將接下來的人生都投入到濕地生物的研究中。她不愿移居到小鎮(zhèn)去過所謂的社區(qū)生活,因為她的一切源自濕地,她的根就在這里,她不會像拋棄她的人那樣拋棄濕地,更何況小鎮(zhèn)也曾給基婭帶去了噩夢般的體驗。從基婭的經歷來看,整個小鎮(zhèn)就是資本主義父權制度和父權意識的縮影,小鎮(zhèn)居民將跟自己不同的人和處于社會邊緣地帶的人視為“他者”,他們在彰顯自身的優(yōu)越性的同時力求排除異己,而來自濕地的基婭則從小就成了他們眼中的完美“他者”。小時候基婭跟父親去鎮(zhèn)上時,鎮(zhèn)里的小孩會盯著她滿是泥濘的衣物看,而其他居民則嫌她臟,躲得遠遠的。餐廳不歡迎她的到來,同時也不允許婦女和黑人到餐廳用餐。七歲那年,基婭到鎮(zhèn)上的學校上學,班里的很多孩子都排擠她,罵她是“濕地女孩”和“濕地垃圾”。這種惡意迫使第一天上學的基婭難過地跑回了家,從此再也沒有去過學校。自那以后,小鎮(zhèn)居民就將“濕地女孩”的標簽固定在基婭身上,更有人說她是半人半猿的結合體。基婭在受到蔡斯暴力對待時,小鎮(zhèn)的警官也無視她的求助,只因他們不想得罪這位小鎮(zhèn)的富二代。基婭在“濕地女孩”等“他者”化標簽下,一直受到小鎮(zhèn)居民的不公對待。他們不愿去認真了解基婭,更不會給她自證的機會,只會將她視作異己,然后趕出小鎮(zhèn)。直到基婭的出版物大獲成功,小鎮(zhèn)居民才開始改變態(tài)度。對于基婭而言,小鎮(zhèn)從來都不是她的選擇,只有濕地才是她永遠的家。所以,她義無反顧地選擇將余下的人生都投入到濕地當中,以追求身體和心靈上的解放。她想讓自己的身體在離世后回歸到濕地,然后成為濕地的一部分。
在對待伴侶和婚姻上,基婭也遵從著自己的內心。泰特在博士畢業(yè)后回到濕地,他主動跟基婭見面,并就多年前的食言和消失行為進行道歉,希望兩人能夠重歸于好。其實基婭心中也還保留著當年的那份感情,再加上泰特真心悔過,一直陪伴在她的身邊,鼓勵她出版標本并提供幫助,基婭最終原諒了泰特。當所有的事情塵埃落定后,泰特向基婭提出求婚,但她拒絕了。她認為兩人現(xiàn)在所處的狀態(tài)已經足夠了,不需要結婚這一形式來證明他們的關系。泰特尊重她的決定,他們沒有結婚,也沒有后代,兩人互相為伴,在濕地度過余生。對于婚姻,波伏娃在《歲月的力量》中寫道:“婚姻使兩個人遭受更多家庭的束縛以及社會的勞役。相反,為追尋自身的獨立而受的困擾遠不及此沉重;對我來說,在空洞中尋找自由是如此的做作,因為這種自由僅僅存在于我的頭腦與心靈。”[4]波伏娃以此為由拒絕薩特的求婚,通過締結口頭婚約的形式,與薩特成為彼此的終身伴侶。潛在的社會屬性和分工使女性在社會婚姻制度中更易于遭受不平等的待遇,而婚姻所帶來的女性刻板角色則會加重“內在性”對于女性的影響,使其最終淪為婚姻關系中的“他者”。當然,波伏娃也并非主張將女性和男性割裂開來,而是認為“婦女解放的目標和理想結果是在承認男女差異的基礎上實現(xiàn)兩性的完全平等并和諧共處,共同創(chuàng)造兩性組成的世界的美好未來”[1]。基婭選擇拒絕婚姻帶來的束縛,并和泰特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終身為伴,一同在濕地的烏托邦里追尋精神的自由和靈魂的解放。
四、結語
小說中故事的時代背景是在二戰(zhàn)后的二三十年,那個年代世界局勢還沒有迎來相對穩(wěn)定的局面,全球仍處于動蕩不安的狀態(tài),各國人民也處在二戰(zhàn)余波的影響中,過著艱苦的生活。在美國國內,由于資本主義父權制度的統(tǒng)治,性別歧視、種族歧視、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不斷滋生,女性、黑人以及社會底層人士被視作“他者”,在壓迫當中艱難生存。“濕地女孩”基婭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誕生,她是男性眼中的“他者”,是小鎮(zhèn)居民眼中的異端,一個接一個的生存困境使得她喘不過氣來。本文通過對《蝲蛄吟唱的地方》中主人公基婭的成長歷程進行解讀,得以窺見二戰(zhàn)后女性謀求自我超越和性別平等的努力。她們在壓迫和困境之下覺醒,努力謀求經濟獨立,敢于挑戰(zhàn)和超越父權文化,最終實現(xiàn)了自身的價值。
參考文獻
[1] 劉慧敏.存在主義女性主義與女性的自由與解放——淺析波伏娃的《第二性》[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3).
[2]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陶鐵柱,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
[3] 迪莉婭·歐文斯.蝲蛄吟唱的地方[M].王澤林,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9.
[4] 西蒙·波伏娃.歲月的力量[M]. 黃葒,等譯.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