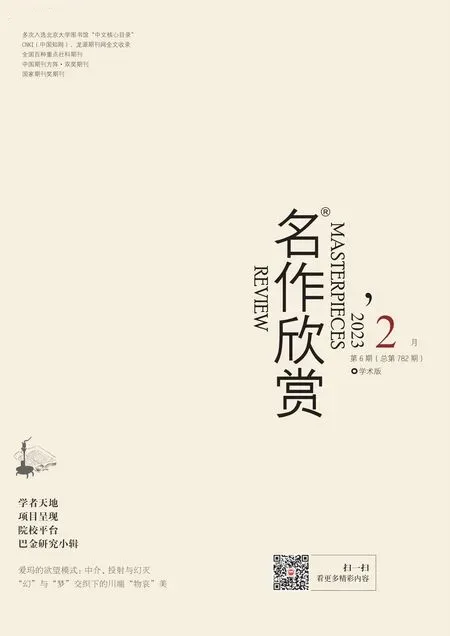愛瑪的欲望模式:中介、投射與幻滅
——基拉爾“三角欲望”視域下的《包法利夫人》解讀
⊙杜超逸[蘇州大學唐文治書院,江蘇 蘇州 215121]
一、欲望三角模型:愛瑪的欲望構成
勒內·基拉爾提出以“欲望三角”為中心的“模仿欲望觀”,這一理論認為“模仿欲望是對他者欲望的抄襲,是模仿他者欲望的欲望”,這是最強的欲望,也是唯一真正的欲望。浪漫的謊言就在于強調欲望的“自發性”,將對欲望的唯我論定義投射到小說的真實——對模仿欲望的揭露上。①
“欲望三角”的基本模式如圖1 所示,基拉爾將我們崇拜并希望與之相像的“楷模”稱為“欲望介體”,追求客體,歸根結底就是追求介體。主體通過介體選擇其欲望的對象,這種欲望是既以他者為原因,又以他者為目標的。介體對主體的影響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使得主體喪失對現實事物的感覺和判斷力;
(2)使主體混淆欲望和保持自我的意志;
(3)主體借助欲望選擇“模式”;
(4)造成兩個相互競爭的欲望,也即產生“模仿競爭”。

圖1 三角欲望模型
本文主要涉及前三個方面,因為在《包法利夫人》中,介體外在于主人公的世界,由于介體與主體之間不存在競爭的關系,這種介體被稱為“外中介”,介體和主體各居中心的兩個能量場的距離較大,彼此不接觸。與此相對的另一種介體則是“內中介”,兩個場距離較小,彼此相互滲透。這就是對以“愛情”為中心的三角欲望結構的說明。
《包法利夫人》以文本形式的獨特性和闡釋空間的多元性著稱于世。愛瑪想象現實和世界的方式被法國評論家于勒·德·戈爾蒂埃(Juleo de Gaultier)稱為“包法利主義”②,即幻想脫離現實條件而進入小說般的夢幻世界,“小說”是學界探討愛瑪欲望模式的核心之一。
盡管此前的討論充分關注到文學作品對愛瑪欲望的影響,但多數論者側重強調欲望主體的主動性,強調其自身的虛偽、自私、拜金等因素對其文學選擇的影響,對愛瑪模仿欲望的過程重視不夠,或忽視了愛瑪欲望的復合特質,從而使得對愛瑪這一人物的分析落入道德說教的窠臼,同時也脫離了愛瑪與塑造她的特定時代之間的有機聯系。
本文認為,愛瑪的欲望應該放在主體、介體、客體三個要素共同作用的整體中考量,她的欲望符合勒內·基拉爾提出的“欲望三角”模式。基拉爾將我們崇拜并希望與之相像的“楷模”稱為“欲望介體”,追求客體,歸根結底就是追求介體。主體通過介體選擇其欲望的對象,介體為欲望建立模式。③基拉爾將欲望介體看作一個具體的對象,如具體的人。但介體可以是抽象的,如觀念、認知,或由它們復合而成。愛瑪所想象的舞會上的“子爵”,其實是她將小說情節中的主人公所具有的特質賦予他并經過想象的結果,現實中并不存在這樣的“子爵”。
有學者指出,介體建立的模式,也即概念,可以表現在廣告里,也可以是書籍、報刊的信息,通行的觀念,流行的敘述,或某種文化、某個意識形態。④本文認為這種界定是比較合理的。愛瑪所閱讀的小說及其情節、人物,代表資本主義庸俗精神的奢侈品等都是構成愛瑪欲望介體的原料。基拉爾批評了浪漫主義小說所宣揚的直線欲望,認為要“破除人的自主性神話”,“堅持對自我的定義不能摒棄自我與他人的關系”⑤,這為我們探索愛瑪的欲望提供了嶄新的視角。
當然,對文學淺薄幼稚的理解并不能全然歸咎于愛瑪自身,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將愛瑪的病癥稱為民主式幻想,在社會和政治維度上解構了愛瑪的欲望。民主社會的到來打破了不同階層各安其分的秩序,使得平民也開始追求不曾有過的精神刺激,并渴望將其變為現實,混淆文學和生活的界限,這就是“日常生活的美學化”,也是“愛瑪的不赦之罪”。⑥這一論點的意義在于,它不僅點明了愛瑪浪漫幻想的病灶,而且強調了文學與社會的有機聯系,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了愛瑪作為欲望主體的普遍性。正如福樓拜所言:“就在此刻,我可憐的包法利夫人,正同時在法蘭西二十個村落里受苦、哭泣。”
基拉爾的三角欲望模型充分考慮了主體、介體和客體之間的距離問題,并凸顯介體的地位。本文將在上述觀點的基礎上探究愛瑪欲望生成、投射,及至幻滅的過程。愛瑪的天性與后天的環境,感受、探索生活與賦予生活意義,愛情與金錢的張力隱藏在福樓拜微妙的反諷和對細節精妙的設計之中,這正是《包法利夫人》作為經典的魅力。
二、文學與自我想象:愛瑪的欲望介體
基拉爾認為,“愛瑪·包法利也依著年輕時飽讀的那些情感小說編織自己的欲望”。他指出,文學在這里具有“種子”的功能,她的欲望來自浪漫主義小說的女性人物,這些平庸的作品摧毀了她的自發性。⑦
本文認為,將愛瑪的欲望介體歸結于任何具體的人或事物都是不全面的,從小說中獲取的資產階級的金錢觀和愛情觀塑造了她庸俗、混亂、不切實際的欲望介體,即對“完美丈夫”的幻想。這使她不再“感覺”這個世界,而是讓實際的感情機械地模仿已有的感情,將她對生活意義的想象投射給現實。
在愛瑪所看的故事中,愛情無一不體現為女性對男性的依附:“書中的男子個個勇猛如獅子,溫柔如羔羊,人品世間少有,衣著考究華麗,哭起來淚如泉涌。”⑧在愛瑪構建的欲望模式中,一個強有力的、可依附的,同時兼有名利的男性是必不可少的。此外,這些完美的男性沒有任何私利似的投入愛情,是與資產階級社會中被金錢腐蝕的人際交往現實相對立的,愛瑪主觀上有忽視這種對立的傾向。她看小說的目的是“在想象中滿足自己的貪欲”;她會選擇性地看見巴黎中符合她想象的“兩三種場景,卻遮蔽了其他的場景,讓她覺著這就是整個人生”;她看小說時看到的不是其中女性的獨立精神,而永遠只有華貴的裝飾和地位(如瑪麗·斯圖亞特)。將“美”“高貴”等詞語與擁有更多的財富簡單相等的粗淺認識已經侵入她的意識深處,對此,小說中描寫資產階級和貴族糜爛生活的片段難辭其咎。
愛瑪的欲望介體似乎是她自發選擇的結果,但這一由她自發選擇的介體反而使愛瑪喪失了自己的“自發性”,這種喪失反映在現實與小說的混雜之中。在愛瑪那里,現實與小說的秩序是混亂的,閱讀小說是在經歷現實,經歷現實也成為她“閱讀”的一部分,她隨時準備將閱讀到的東西轉化成觀念存放在介體之中。后文中,她在侯爵的宴會上所關注的,都是小說中那些庸俗的東西。敘述者在暗中將現實與愛瑪的想象對置,暗示愛瑪已經將現實也當作小說閱讀:
他這一生從未安生過,荒淫放蕩成性,不是決斗賭博,就是誘騙女人,家產被他肆意揮霍,家人為他擔驚受怕。
愛瑪……仿佛在看意見非常稀罕的,令人敬畏的東西。他居然在宮廷里生活過,還在王后的床上睡過。
小說與現實形成互文關系,愛瑪經歷現實的目的是弄清“歡愉、激情、陶醉這些字眼,在生活中究竟指的是什么”,而她從書中得來的對欲望模式的認識,已經給她一種價值預設:財富、名利、激情才是人生的終極意義,荒淫、賭博等低級趣味,誘騙、揮霍家產、不顧家人等違背道德的行為是無足輕重的。對于愛瑪而言,思想先于經歷,對感情的想法先于感情,在實際存在之前,想象中已經多次經歷“幸運的隨大流的感情”,實際感情就模仿已有的感情。⑨這就導致她的生活并非感覺、經歷的過程,而是不斷上演先驗存在的意義和目的的過程,她清楚地知道“她的氣質不是藝術型的,而是多愁善感的,她尋求的是情感,而不是景物”。正如朗西埃所言,“狂熱從今以后似乎要和生活本身共享實體,正是通過其盲目的推動,生活抓住了所有文字和所有形象,以便不斷建造欲望的客體”⑩。雖然表面上看,愛瑪賦予意義的過程是一個自發的過程,但愛瑪顯然沒有意識到,她所認為的求索過程其實是賦予過程,是將她所認為的意義賦予這些詞匯,并投射在屬于現實的人身上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愛瑪的自發性其實是被介體褫奪的。
我們可以用李健吾先生的觀點總結愛瑪的欲望介體:“她(愛瑪)給自己臆造了一個自我,一切全集中在這想象的自我,擴延起來,隔絕她和人世的接近。這想象的自我,完全建筑在她的情感上面。”?這正符合愛瑪的內心獨白:“按照書本上的描寫去想象愛情,那種感情多么妙不可言,多么令她神往呵。”愛瑪欲望介體的本質正是一種“自我想象”和“隔絕”,她在腦中預先想象一個欲望“模式”,將從文學作品中讀到的奢華享受的生活、不切實際的愛情,現實中“閱讀”到的風景混雜在其中,并堅定地將這種在想象中經歷的情感模式投射到生活中。在這個過程中,意義變成先驗的東西,本是用來感受、尋覓的生活世界被愛瑪以“藝術化”方式想象的欲望中介侵占了,然而現實世界有其真實的秩序,愛瑪的欲望最終在這個秩序中走向幻滅,本文將在下一部分討論這個問題。
三、欲望的投射與幻滅:現實·小布爾喬亞·子爵的幻影
本文在前一部分認為:愛瑪的欲望介體是一個混雜的愛情模式,她希望讓介體變成現實。在現實的愛情中,她應該是文學作品中聲名顯赫、高貴富有的少女或貴婦,她欲望的最終對象應該是“未知的丈夫”——舞會上的子爵,紳士而浪漫,為愛情不顧一切。愛瑪“把她賦予子爵的優點轉而賦予她實際的情人”?,并“賦予感受和神秘形象一種具體外形,讓其體現在真實的物品和人物中”?。這就是欲望投射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愛瑪逐漸被欲望介體徹底支配的過程。現實秩序在這個過程中阻礙并最終宣告欲望投射的失敗和欲望的幻滅。這個過程有兩個轉折點,分別發生在向羅多爾夫發出“你愛我嗎?”之問和最終發現萊昂的平庸之后。這兩個轉折點使得原本還有一些農民質樸務實天性的愛瑪完全放棄貞潔和操守,變成她曾厭惡的庸俗而乏味的人,形成了反諷效果。而當她的欲望投射觸及堅硬的現實——資產階級社會中狡詐的欺騙和利益至上的原則時,她才不得不從精神麻醉中醒悟過來,欲望也隨之幻滅。本文接下來就試圖對愛瑪投射自己欲望的兩個對象進行分析。
萊昂身上所具有的浪漫氣質與愛瑪類似,在永鎮的第一次會面上,他們的談話合如符契:“落日”“大海”“冰川瀑布”“懸崖邊的小木屋”“對著壯麗景色彈琴的鋼琴家”,這與愛瑪想象的“無比明凈的原始生活”“林中的陰影”恰好形成某種對位,前者宏大,后者雅致?,然而背后的空洞和浪漫幻想是一致的。無論拯救公主的白馬王子還是面對冰川彈琴的藝術家,在現實中都幾乎不可能出現。他們都喜歡沉浸于小說中的“冒險故事”“淋漓盡致的細節描寫”,兩個庸人在討論平庸的時候成為“知己”,這是小說隱含的一層反諷,愛瑪的欲望由此生長。此時,愛瑪雖然受到欲望介體的影響,按照她欲望介體的要求尋找情人,但她仍然保持她的貞操。她想要私奔,但她“心頭驟然出現黑黢黢望不見底的深淵”,“愛瑪愈是意識到這份愛情,她就愈是后退,一心想別讓它冒頭,想讓它的來勢減弱些”。
然而羅多爾夫是一個屬于現實的人,與和愛瑪一樣富有浪漫幻想的萊昂不同,羅多爾夫始終知道愛瑪只是一個“漂亮的情婦”,為了滿足他原始的性欲,他準確地識別出愛瑪的欲望介體,利用她的虛榮心,并用浪漫的陳詞濫調欺騙她:
責任是什么!當然是去感受高尚的情感,去珍愛美好的事物,而不是去接受社會的種種陳規陋習,以及它強加于我們的恥辱。
英雄氣概的源泉,創作靈感的源泉,詩歌,音樂,藝術乃至一切事物的源泉,難道不正是激情嗎?
我無時無刻不在想念您!……一想起您我就悲痛欲絕。
愛瑪卻以為她找到了真正的愛情,她“回憶起從前看過的書里的女主人公,這群與人私通的癡情女子……圓了少年時代久久縈繞心頭的夢”。她以為羅多爾夫是書中的那個在陰暗森林中拯救女子的男子,會愛憐她,聽她哭訴生活中的煩悶;她覺得她就是小說中那個落難的女子,區別只在于她的苦難是婚姻,是那個平庸而不懂浪漫的丈夫查理。
為了配得上這個她想象中的“子爵”,她要把自己打造成小說故事中的那個貴婦,她精心穿戴昂貴的衣飾,并覺得只要有奢華的物件就能獲得想象中的愛情。然而羅多爾夫真實的想法與她的設想大相徑庭,對于她送的馬鞭和印章,他只是覺得她專橫,將她的欲望強加于他。在她的想象中,她的戀人不僅是專一的,而且愿為愛一個人而奮不顧身,付出一切代價和激情。當她向羅多爾夫詢問他是否只愛她一個人時,他的回答是否定的,這讓愛瑪悲痛欲絕,幾近癲狂:“我知道怎樣刻骨銘心的愛!我是你的女仆,你的情婦!你是我的國王,我的偶像!你心地好!你模樣俊!你聰明!你了不起!”
本文認為這是愛瑪徹底被欲望介體支配的第一個轉折點,她希望羅多爾夫能遵循她的欲望模式,表現出夢中子爵的模樣。小說是這樣標界的:“習慣成了自然,包法利夫人的舉止做派完全變了。”她變得浪蕩、隨便,道德觀念讓位于欲望。她渴望這位“子爵”的化身將她救出婚姻,遠走高飛,她已經開始想象旅途中美妙的夜晚,遠方的沙灘、懸崖和海洋。但她不知道的是,無論她如何打扮,如何深情,都不能改變羅多爾夫對她的厭倦和輕浮的態度,她只是他用完即棄的玩具:“他把她調教成一個又柔順又放縱的尤物”,“她的打扮讓他覺得挺做作,那種暗送秋波的眼神更是俗不可耐”。
羅多爾夫是屬于現實的,他知道愛瑪的情感是荒誕的,他不可能放棄個人的幸福,拖著一個在他看來僅是長得更漂亮些的情婦和她的孩子去受苦受難。愛瑪認為愛情只是去追求“快樂”“激情”“陶醉”這種詞形容的生活?,她不知道的是,愛情不等于激情,紅顏終會老去,她讀的小說只告訴她最浪漫的愛情,卻沒告訴她浪漫背后的物質基礎和情感支撐,或者她忽略了這些珍貴的啟示?。羅多爾夫作為布爾喬亞的庸俗性就表現在,他放任愛瑪進入“癡愚”的深淵,他知道愛瑪無法辨別現實和想象,卻任由她越陷越深,只為滿足自己征服、玩弄一個人的粗鄙愿望。他一開始就在欺騙愛瑪,利用愛瑪的介體掌控她。對愛瑪最終的陷落,他負有和那些小說一樣的責任。
被羅多爾夫拋棄之后,愛瑪在一場大病之后將她的欲望轉向超驗的事物,隨后一場演出將她重新與萊昂聯系在一起。這次,兩人的行為都變得更加放蕩,愛瑪短暫地表現了猶疑,她發問:“這樣做很不妥當,您知道嗎?”在感情上一向懦弱的萊昂卻從容地說:“在巴黎都這樣。”愛瑪在偷情中感受到了成為小說女主人公的快感,認為自己正在成為上流社會的女人。同時,由于不能和他時刻在一起,愛瑪要將宣泄欲望時的感受固定下來,換成華貴的新東西,地毯、新套子,只有這些才配得上她的欲望模式。
與羅多爾夫不同,萊昂在愛瑪的欲望中始終占據被支配的地位,當愛瑪告訴他,她曾經愛過另一個人時,他的反應不是生氣,而是覺得“可以抬高自己的身價”,他“感受到自己地位的卑微”,他懦弱、自卑、優柔寡斷,當那欲望介體的幻影閃過,“騎馬在樹林里漫游,與子爵跳的華爾茲,還有拉加迪的演唱”,“萊昂在愛瑪眼里變得像旁人一樣遙遠了”。萊昂的“布爾喬亞式”性格比羅多爾夫更為顯著,他缺乏獨立自主性,想法受到母親掣肘。在激情過后,他剩下的只是厭倦,而沒有責任,他更不可能成為愛瑪想象中的白馬王子。他為了事業和名利而放棄愛瑪,并且絲毫不以此為恥,敘述者對這種性格的概括是很準確的:
每個布爾喬亞,在特別容易沖動的青春時代,總有那么個時期,會自以為渾身都充滿了激情,自以為能成就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
愛瑪最終發現,想和布爾喬亞產生她欲望介體中的浪漫愛情是不可能的,“愛瑪在私情中又嘗到了結婚的全部平庸和乏味”,這是愛瑪徹底被欲望介體支配的第二個轉折點。雖然愛瑪認識到萊昂不可能成為她想象中的子爵,但她已經上癮了,“她再怎么感受到這種幸福的卑鄙恥辱,也是枉然,她已經離不開它了,這是習慣使然,要么就是墮落使然”,這是欲望介體強力作用的結果。在寫書信的時候,她清晰地感受到她的欲望介體,敘述者在這里暗示了我們,愛瑪現在追求的不是萊昂,而是那個“子爵”的幻影:
可是她一邊寫著,一邊依稀看見另一個男人的身影,這是一個由激情澎湃的回憶、無比美妙的閱讀、貪得無厭的欲念生成的幻影,他最后變得如此真實,如此貼近。
這個轉折點成為愛瑪被現實秩序吞噬的開端,即使她知道萊昂不是那個幻影,她也要拼命留住他,她已經進入精神錯亂的狀態,如果無法找到那個目的,那就把那個目的或先驗的生活意義強加給欲望對象的客體,“賦予客體一種虛幻的價值”?。假想欲望的投射在現實中獲得了徹底的成功,她加大花銷,找最好的旅店,透支自己的消費,這是愛瑪的欲望徹底庸俗化的時刻。萊昂在這里真正地被肉身化,只是愛瑪肉欲的對象,是形而上學的替代品,而那些美好的特質都是愛瑪自我麻醉的結果。
然而,愛瑪的自我麻醉和假想無法改變她借貸欠下的債務,這是她追求本就虛空的欲望介體的代價。愛瑪混淆了文學與生活,不只是文學中的白馬王子在這個被無能、庸俗的小布爾喬亞支配的時代不存在,那種揮霍無度而又不付出任何代價的奢華生活不存在,嬌滴滴的公主與小姐在這個時代也不存在,即使存在,也不可能是愛瑪這種出身的人。文學可以不告知讀者故事中的人物是如何獲取那些金銀財寶,如何認識她的白馬王子,而生活不行,這就是文學與生活的最大區別,沒有空穴來風的生活,也沒有未經過程就可先行獲得的生活意義,想將這目的、意義強加給生活,那就只有自我麻醉,自我欺騙。正如愛瑪最后發現萊昂的平庸一樣,她也知道她大量購買奢侈品和小商品的代價:
一個人窮到這地步,就不會在槍柄上嵌銀絲!就不會去買鑲玳瑁的掛鐘!……也不會給馬鞭配上鍍金的銀哨子……
她不是沒有想過要算賬,只是數額太大,她只能“撇在一邊,不去想它了”;愛瑪知道窮到一定地步就不應該再買奢侈品,但她為了支撐自己虛妄的愛情,為了得到自己夢想中的“子爵”,哪怕是將一個完全沒有“子爵”品質的人想象、包裝成“子爵”也在所不惜,她覺得麻醉自己就可以永久地擁有對子爵的愛。只有當現實中的債務逼上前來,她才終于知道這種麻醉失敗了,他們都不是夢中那個為女主人公付出一切的“子爵”:“你從來沒有愛過我!你跟別的男人是一路貨色。”其實她的兩個情夫一直都是那路貨色,他們一直是平庸、放蕩、自私的小布爾喬亞,和查理一樣,愛瑪天真的地方不在于不能察覺出他們的平庸,而在于用自我麻醉的方式去想象平庸,認為在想象中可以把夢變成現實。“愛情會經受陣陣寒風,而金錢上的要求風力最猛,能把愛情連根拔除”,而當債務無情摧毀她欲望的物質基礎時,她只能帶著她的欲望——關于“子爵”的夢服毒自殺。
愛瑪欲望投射的過程是一個不得不承認“文學僅僅是文學”?的過程,在現實生活中,唯一恒久存在的不是愛情,而是厭倦。愛瑪討厭查理的平庸,厭倦查理不能給她帶來新的幸福;羅多爾夫厭倦愛瑪的陳詞濫調,萊昂厭倦愛瑪用金錢收買人心的乖戾舉止,這些厭倦在本質上是一致的。“生活,就是從變化到變化、穿越一系列平庸單調的經歷”,“厭倦、愛、享受、依賴、又是厭倦,這就是指揮福樓拜著作的深沉節拍”?。在這之中只有查理這一個例外,盡管他平庸,但他容易滿足,他為擁有愛瑪這個妻子而驕傲,從未感到厭倦。他資質平庸,但他那有點呆板卻真誠的愛是不平庸的。所以愛瑪唯在一點上遵循了現實,那便是以世俗的價值定義平庸。這就決定了她不可能在世俗的世界中找到真正的“不平庸”,而只能自我欺騙,最終走向滅亡。
四、結語
在基拉爾發現的基礎上,本文認為:第一,愛瑪的欲望中介是觀念的混雜,是從生活、書本中“閱讀”而得到的各種碎片拼接而成的“幻影”——子爵;第二,愛瑪的欲望就是將在腦海中已經上演過的理想愛情投射到現實中去,現實與這種想象的錯位使得愛瑪不得不麻醉自己,把那個目的或先驗的生活意義強加給欲望對象的客體,現實秩序最終證明了這種強加的意義的荒唐,并摧毀了愛瑪的欲望;第三,愛瑪并非自始而是經歷了兩個轉折之后才被欲望介體支配,這在作品中有明確的標界。
本文將上述發現融入愛瑪的整個欲望過程,并做如下概括:
(1)介體生成:文學閱讀與修道院經歷(在農村成長的過程與這些經歷對比,起到了加強介體的作用,現實條件的匱乏既是愛瑪幻想產生的源頭,也是摧毀愛瑪幻想的“兇手”)。
(2)投射欲望:愛瑪追求萊昂、羅多爾夫的過程(主體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變化,逐漸放棄貞操變得放蕩,被介體支配)。
(3)欲望幻滅:現實的債務,或者說再也沒有辦法獲得的愛逼迫愛瑪自殺。
最后,《包法利夫人》給我們最深刻的啟示之一就是:“文學中的現實主義承認物質世界獨立于我們的希望和欲望而存在。我們也不總是控制我們的身體和思想。”?福樓拜借愛瑪深刻地展現了欲望對人的負面驅動,這種驅動有時是無意識的。如果經由欲望介體達成欲望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正確地認識自己的欲望介體并讓它為我們所用,而不是被它支配是可以進一步思考的。
①③⑦? 〔法〕勒內·基拉爾:《浪漫的謊言與小說的真實》,羅芃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版,第1、3、4、10、15、16、17、24、25、43頁,第1—166頁,第2、12頁,第68—72頁。
② See Jules de Gaultier,Le Bovarysme:La psychologie dans l’oeuvre de Flaubert,2007.
④〔美〕童明:《現代性賦格:19 世紀歐洲文學名著啟示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版,第93頁。
⑤ 陶艷柯:《基拉爾“模仿欲望”概念的回溯及辨析》,《復旦外國語言文學論叢》2016年第2期,第43頁。
⑥⑩?? 〔法〕雅克·朗西埃:《文學的政治》,張新木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67—99頁,第93頁,第79頁,第92頁。
⑧〔法〕居斯塔夫·福樓拜:《包法利夫人》,周克希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頁。(本文有關該書引文均出自此譯本,后文不再另行標注)
⑨?? 〔法〕讓·皮埃爾·理查:《文學與感覺:司湯達與福樓拜》,顧嘉琛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296—298頁,第300頁,第220頁。
?? 李健吾:《福樓拜評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0頁,第106頁。
?〔美〕納博科夫:《文學講稿》,申慧輝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168頁。納博科夫對這種方法的命名是“多聲部配合法”。
? 據原文可知,愛瑪所看的小說中不乏真正具有獨立精神的女性,如瑪麗·斯圖亞特等;也不缺少優秀的作品,如巴爾扎克、司各特的作品。
? Laurence M.Porter,Eugene F.Gray.Gustave Flaubert’s Madame Bovary:A Reference Guide,New York:Greenwood Press,2002:p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