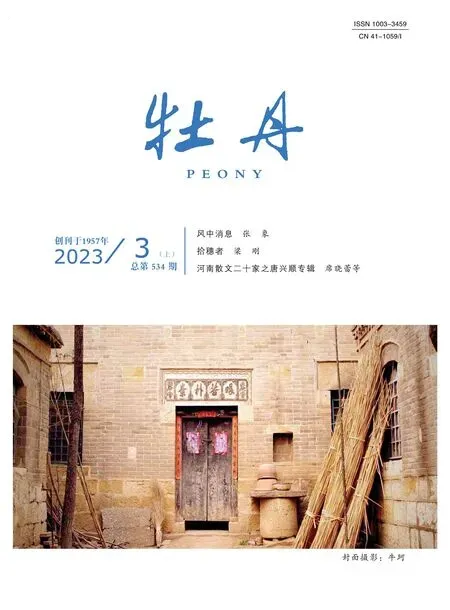發小
李為民
1987 年的夏天,嚴澍跑到我們市委范羅山的大院里找到我,語氣有些詭異地說,龐微的高考錄取書拿到手了,我當時正睡午覺,揉著惺忪的眼睛說,考上了有什么了不起呢?嚴澍見我揉著惺忪的眼睛就不再吭氣了。那一年我們幾個發小都參加了高考,嚴澍上了省城的財會學校,龐微被中科大錄取了,我通過招干進了青弋江邊的一個小學校教書。
嚴澍心里清楚我暗戀龐微,本想讓我心死,因為龐微上了名牌大學,可能就要出國,前程似錦,其實我心里也沒有失落感,只是覺得龐微長得比較好看,說話輕聲細語,她還有一個優雅的愛好,喜歡拉小提琴。
既然她考取了大學,我找了個機會溜到她家,她家住在范羅山的組織部的大院里,我小心翼翼地站在院子門口,望著龐微佇立在窗前拉小提琴,她沉浸在自己的旋律里,神態安然,我有些恍惚。
見我來了,她認真地盯著我,張淼,我要走了,以后你得照顧好我干媽。她的干媽就是我的母親,我們的父母都來自部隊,大軍渡江的時候,我的母親救過她母親的命,我父親過世后,母親也長年生病住院。
我岔開話題,你為什么選擇化學專業呢?龐微細聲細語地解釋,只有在化學的世界里,你才能理解太陽為什么白得那么耀眼,天空為什么那么湛藍好看。
她詩一樣的語言讓我有些迷戀她,她上大學去了,沒過些日子,龐微的母親因為身體里的槍傷發作,器官衰竭,死在醫院的病床上。龐微從學校跑回來,辦完喪事,她又跑到我母親的病房里,拉著我母親的手,眼圈慢慢變紅,聲音很低,穿透力卻很強,干媽,您要多保重,您身體也受過傷。我的老母親白發蒼蒼,氣息奄奄地說,孩子,你很懂事,我們這一輩人經歷的事情太多了,所有的痛苦我們都能忍受。
龐微鄭重地點點頭。
龐微后來飛往美國攻讀化學碩士專業,臨行前和我告別,我去了她家,她家的院子很大,還有一棵粗壯的槐樹,我走進院子,龐微拎著行李箱,手里還握著一把古銅色的小提琴,笑意盈盈地望著我,她伸出手把小提琴遞給我,我搖搖頭,這是你喜歡的東西,我不能要。
龐微細聲細語地說,那好吧,以后送給你。
龐微走出了我的生活,不過她幫了我和嚴澍一個忙,托在省里工作的父親找關系,把我弄到了市刑警隊,她看我長得高大健碩,這個工作適合我,還打了個越洋電話祝賀我,依然細聲細語地對我說,我還有個發小叫石衛平,也在市刑警隊,今后,我們這些發小可要團結啊。嚴澍先在銀行當了會計,因為挪用公款被除名后,跑到外貿公司當了報關員,又覺得不滿意,找到龐微,最后跳槽跑到遠洋輪上當了一名船員。
我在刑警隊干了不到半年,為了執行任務,我和石衛平跑到外貿碼頭的理貨公司當了臥底,摸查船員進口舊家電的走私線索,我們經常登嚴澍的定期班輪,為船員辦理聯合年檢手續。嚴澍已經當了管事,成了高級船員,每次我上船辦理手續,嚴澍都要招待我和石衛平。
有次登輪是個傍晚,嚴澍見我們來了,從冰箱里取出牛肉、雞翅、火腿腸、魚丸和日本方便面,擺了滿滿一小方桌,艙間里飄著香味,嚴澍端起酒杯,我們仨連著干了好幾杯,石衛平是個急性子,眼睛死死盯著嚴澍,老兄,我也不藏著掖著了,我發現你們船員的登記冊上,有不少船員的登記本是假的。
嚴澍笑了笑,慢悠悠地說,既然大家都是發小,我就實話實說,這條班輪有四個水手和一個大廚,在泰國下了錨地后,就一直沒有上船。
我漫不經心地問,他們干什么呢?嚴澍笑了笑,他們幾個倒騰泰國大米,因為我們跑的是泰國定期班輪,所以你倆看著辦吧。
我和石衛平面面相覷,沒有再吭氣了,夜色漸漸濃稠,站在船尾的甲板上,我倆看到不遠處的中江塔四周縹縹緲緲地升起了毛茸茸的霧,霧或濃或淡,借著貨艙尾燈的光影,石衛平嘴里噴著酒氣問我怎么辦,我嘿嘿一聲,兄弟,你看前面的中江塔,咱倆要立功了。
話音剛落,船尾的警示燈又亮了,燈亮那一刻,霧氣散淡,嚴澍三步兩步從底艙爬上甲板,拉著我倆從船尾的軟梯下到青弋江的大埂上,又大步流星地領著我倆來到了霧氣散淡的中江塔前,他從懷里掏出一把鉗絲鉗,嫻熟地撬開塔門,不聲不響地把領我倆進了石門,打開手電,我倆看到堆得像小山一樣的舊家電。
嚴澍語氣平靜地說,這里面的玩意兒都是從日本的大阪淘來的,現在都歸你倆,你倆就是萬元戶了,船上的幾個兄弟弄來了這些舊家電送給我,他們想倒騰進口泰國大米,互惠互利,就這么簡單。
嚴澍伸開雙臂,摟了一下我倆的肩膀,輕聲說,放心,這兒有人看著,只要你倆保持沉默,錢會存到你倆的工資卡上。
那天是冬至,從中江塔里鉆出來,無風的夜空下,卻感到很溫暖,不遠處的大埂邊上,長著一排古杏樹,樹杈上掛著一輪黃黃的殘月,嚴澍鄭重地對我倆說,下一趟我們一起去泰國吧。
石衛平遲疑地望了我一眼,我微笑地點點頭。
這艘定期班輪是半個月后停靠在泰國港的。那天傍晚,我們幾個下了錨地后直奔巴蓬街,那條街喧嘩熱鬧,霓虹燈閃著耀眼的光芒,酒吧一家挨著一家,我們找了一個酒吧坐下,一邊喝啤酒,一邊看表演,忽然聽到一陣小提琴的旋律,我不由自主地往酒吧的另一角望去,還真的看到一個拉小提琴的女孩,她的肩膀瘦削,背朝著我和石衛平。
石衛平湊近我的耳朵,拉小提琴的是我們的人,叫伊姍,然后我倆悄悄鉆進街邊的一個小巷子,走了不到五十米,周圍一片寂靜漆黑,我們的雙腳踩進了清涼的水里,發出了水花濺起的聲音,再往前挪動腳步,眼前出現一片微弱的燈光,鼻孔里鉆進一股濃稠的稻米香味,夾雜著低沉的馬達轟鳴聲,走進那片大棚,石衛平像早有準備似的喊了幾嗓子泰語,幾個正在加工稻米的泰國佬,松松垮垮地抬起頭,望了我們一眼,又埋頭干活了。
石衛平老練地摸了一下別在后腰上的槍,警覺地望了我一眼,檢查一下帶的家伙吧,嚴澍干的這單買賣不小。
話音未落,一個中年胖子帶著嚴澍迎面走近我倆,我下意識地將手伸進褲兜里,摸了摸家伙。那個胖中年人脖子臉黑紅,他左看看,右看看,裝成一個迷路的人,嚴澍滿不在乎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都是我們的人,古船長。
嚴澍環顧四周,碾米機的轟鳴聲又漸漸地響起來,嚴澍微笑地對我倆說,這兒有一千多噸的稻米,加工完了會運到三號碼頭,古船長已經安排了船上幾個兄弟接應我們。
古船長咧開嘴沖我倆笑笑,拱手說,大家發財。
忽然我們聽到槍聲,古船長愣怔了一下,猛地拉著嚴澍朝碼頭方向跑,我和石衛平同時掏出槍,黑暗中我們聽到了不遠處一陣汽車發動的轟鳴聲,一輛吉普車閃電般地駛向嚴澍和那個船長逃跑的方向,巨大的車燈光柱猶如一條巨蟒,正蜿蜒地沖著兩個一瘸一拐的身影射去。
我聽到幾聲像爆竹似的沉悶聲音,應該是從吉普車里射出的子彈,嚴澍晃了一下身體,撲通一聲栽倒在泥濘的地上。
我的心一下子就跳亂了節奏,石衛平反應比我快,他幾乎追上了那輛吉普車,我又聽到了一聲爆竹的炸響,石衛平踉蹌了一下,撲倒在地上,我有些被激怒了,閃電般地沖向吉普車,一道電筒光向我射來,光影下,我隱約地看到吉普車里一個瘦削的女孩正沖我抿嘴笑,她的眼眶中有暗示的意味,我忽然心里生出一絲沖動,我舉槍瞄準她,可胳膊抬不起來,我竟然有些薄醉,鼻孔里鉆進的依然是淡淡的稻米氣味。
我暈厥過去,醒來后,我發現躺在當地醫院的病床上,坐在我身邊的竟然還是那個瘦削的女孩,我吃力地睜大眼睛,她卻望著我淡淡地笑了笑,主動地伸出手和我握了一下,我叫伊姍,省公安廳的,這個案子本來破了,有點兒可惜,嚴澍的腿被打瘸了,不過和那個古船長還是跑了。
我艱難地問,石衛平呢?
伊姍向我解釋,吉普車里的人都是泰國籍的走私船員,后來都被我們收拾了,有個家伙混亂中抵抗,沖石衛平的后腦勺開了一槍,而我是被一種泰國產的麻醉中樞神經的迷香藥給弄暈了,嚴澍和古船長逃回到定期班輪上,后來船開跑了。
回國后,省廳召開案情分析會,我才得知那條裝運泰國大米的班輪改變了航線,穿越大西洋駛向巴西港,可這條船遇到了16 級臺風,當時船上的三臺發電機全部啟動,意外還是發生了,整個船體在排山倒海的搖晃顛簸之后,終于傾斜下沉,風暴之后,整個海面又平靜下來,嚴澍下落不明。
這件事雖然過去了,可石衛平腦部受到了嚴重的損傷,身體恢復后退出了公安,我找到伊姍,給他辦了低保,龐微打越洋電話,叮囑我和伊姍騰出范羅山的大院子給石衛平,給他開了一家煙酒店,又寄給我一個大哥大,讓我有事和她聯系。
生活又恢復了平靜,我依然在刑警隊,而伊姍卻調到了市局宣傳科,工作清閑下來,一有空就到范羅山照顧石衛平,有一次我和伊姍去了一趟范羅山,看到石衛平靠在躺椅里,睜著空洞失神的眼睛,望著不遠處的山巒和樹林,伊姍眼圈發紅,輕輕地走過去,抱住石衛平的頭,他嘟囔了一聲,閉上眼睛,再也不吭氣了。
伊姍后來向我透露了個秘密,是她對石衛平開了槍,因為石衛平一個心眼要活捉嚴澍,龐微事先叮囑伊姍要保護好嚴澍,因為嚴澍一直在為龐微做一樁生意,至于什么生意,伊姍沒有告訴我。
我沒料到,一年后伊姍和石衛平結婚了,又過了大半年生下一個兒子,我那段時間一直在青弋江邊瞎折騰,整天圍著臭氣熏天的沼澤地轉悠,因為那兒一直埋藏著許多隱秘的案件線索。
我記得那是一個傍晚,我神情緊張,身邊的小年輕們滿身淤泥,拎著一只新皮箱遞給我,站在大埂上,小年輕們打開沾滿淤泥的皮箱,里面擺放著一副仕女圖,保存得完好,畫面里的人物明媚香艷,我仔細盯著那幅畫,腦海里晃出了龐微的影子,那還是上高中的時候,她穿著粉紅色的連衣裙,綠色的長絲巾飄在腦后,長而粗的發辮垂到了胸前,兩條秀頎的腿被連衣裙遮去了一半,我有點兒發呆。
我掏出煙遞給身邊的幾個小年輕,自己點燃了一根,猛吸了幾口,彎下腰,小心翼翼地托起那幅畫,畫的下面居然是一把古銅色的小提琴,那么眼熟,我的心臟猛地一沉,我站起身,裝作若無其事地對身邊的幾個小年輕說,這個破玩意兒交給我吧,可能和幾年前古玩市場的那件失竊案有關。我胡謅了幾句,臉一熱,頭低了下去,我自己都感覺這個謊扯得不地道。幾個年輕后生很識趣地沖我擺擺手散了。
我孤零零地站在大埂上,褲兜里的大哥大響了,我聽到了龐微的聲音,她依然是細聲細語地問我是不是發現了一只小皮箱,我含混不清地說是的,我腦子有點兒亂。
龐微柔和地對我說,箱子里的小提琴里面有些藥品,是我干媽需要的,電話掛斷了。
我嗓子有點兒干澀,說不出話來,拎著皮箱徑直去了母親的病房,母親渾身插著管子,已經不能開口說話了,護士輕聲地叮囑我,老太太不能受過多的刺激。
我輕輕點頭,不管不顧地站在母親的床頭,打開了那只皮箱。
母親滿臉驚愕和譴責地望著我,不一會兒死死地盯著那只皮箱,我將那只古銅色的小提琴在母親眼前晃了一下,又找護士要了藥棉將小提琴消毒擦洗了一會兒,我讓護士出去,關上病房的門,剛轉身,母親猛地掙扎了一下,身體幾乎要碾壓到那把小提琴上。
悲哀的是老人渾身動彈不得,用盡了全身的力氣,胸口起伏,慢慢地閉上眼睛,感覺到身體里那撕裂的疼痛還在蔓延,深陷的眼睛里有淚,喉頭哽咽,她嘟囔了一聲。
我拎著那把小提琴,端詳了一會兒,敏銳地感到小提琴有些沉重,晃了一下,咕咚咕咚,我居然聽到琴肚子里好像裝了什么東西。我警覺地朝病房的門口窗戶望了望,樓道很安靜,我稍稍放心了。
那天晚上,我給母親用了藥,是從小提琴里面取出來的藥,母親睡得很安詳,第二天早晨,醫生查房告訴我,母親服用了大量的麻醉劑,已經沒有了呼吸,她的肝部一直埋著兩個子彈頭,常年的病痛誘發了肝癌,我沒有過多的悲傷,拎著舊皮箱毫無表情地走出了病房,我意識到該來的事情躲不掉了。
幾天后,我又接到了龐微的電話,我開車去了機場,機場的廣播里不停地播放各個航班飛機的最新信息,我的目光漸漸清晰起來,龐微從國際出口處向我緩緩走來,她拎著一只和在青弋江里找到的一模一樣的皮箱,臉上掛著微笑,輕輕地揚起手,無名指上的婚戒在燈光的映射下分外耀眼。
我不自然地抬起頭,笑了笑,龐微展臂自然地抱住了我,我們是在彼此的懷抱里了,我聞著她身上柔和的茉莉香氣,臉靠著她瘦削的肩膀,感受著她那柔和細密的長發質地,那一刻我的心情很復雜。
我開車送她回范羅山老家,龐微坐在我身邊,面孔顯得有些委屈,問我這些年為什么不和她聯系,我說我干了刑警,有些事只能咽到肚子里,或許我們之間還有什么誤會呢。
我也希望是誤會,可恰恰我倆沒有什么誤會呀,除了我沒有告訴你伊姍是我表妹以外,你現在的日子不正過得有滋有味的嗎,龐微狡黠地望了我一眼。
可她偏偏嫁給了一個殘疾人,伊姍讓我想起了你,我明白我配不上你。
龐微仰起臉,望著窗外,天空從未有過的蔚藍和清爽,張淼,你太自私了,石衛平的父母和我父母曾經是戰友,他父母不在了,他父母什么都沒給他留下,除了他的姓名之外,所以我促成了表妹和他的婚姻。
我和龐微遠遠地站在院子外,望著躺椅里躺著的石衛平,面孔呆滯,嘴角涎著口水,像個癡呆兒。
院里有一棵高大的槐樹,站在槐樹邊,龐微打開皮箱,我又看到了一把古銅色的小提琴,龐微關上皮箱,又將箱子很自然地遞給我,她心無旁騖地沖我笑了笑,我知道你的眼睛不會騙人,它們常常讓你看起來溫順,你希望你也是你母親眼中的乖巧的兒子,雖然你知道你不是,但你希望你母親認為你是,龐微踮起腳,用她纖細的手指拂了下我的額頭,說這下好了,我們幾個發小又走到了一起。
龐微,我能不能問你一下,這算不算最后一次走私藥品的買賣,石衛平是怎么受傷的呢?我們應該記住教訓,誰搞的鬼誰心里清楚。
龐微微笑地說,我不清楚,但伊姍嫁給了他,這就是回報,他們現在有了兒子,有了家庭,只是你心里還沒翻過這一頁,因為嚴澍沒有死,我嫁給了他,而你卻一無所有,還在為我們干活,你覺得委屈,對吧?
我深深嘆了口氣,轉身要走,龐微在我身后幽幽地來了一句,我要報答你。
我徑直走進院子,蓬松的毯子覆蓋在石衛平的身上,他靠在躺椅里,我聞到了一些陽光的味道,石衛平除了行動不便外,大腦是清醒的,他艱難地爬起來,抻了抻佝僂太久的腰背,含混不清地對我說,走吧,兄弟,走得越遠越好,我已經沒有父母了,我好不容易才有一個完整的家,有了兒子,可我還得為我老婆干活呢。
他拄著雙拐,蹣跚著腳步來來回回,顯得有點兒焦躁,他一定是沒有看到院子外還站著龐微。
我輕聲說,老兄,我要保護你,保護你的家。
我拎著龐微給我的那只皮箱,走出院子,龐微已經不在了,我開車去了朱家橋碼頭,那兒一片繁忙。我跨進理貨公司的大門,找到伊姍,她有些驚訝,不由自主地拉著我的胳膊,走到江邊,清涼的江水拍打著水面,發出了濺起水花的聲音。伊姍有些抱怨地對我說,你不清楚這個公司有嚴澍的股份嗎?這個航次古船長還得跑一趟泰國。
我有些玩世不恭,揚了一下手里的皮箱,龐微回來了,我警告她,這是最后一次了,老子不干了。
伊姍用一種古怪的眼神望著我,剛要開口,我卻聽到了一個渾厚的男中音,張淼,我和龐微是假結婚,是為了在泰國注冊一家公司,我們只是名義上的夫妻。
我轉過身,嚴澍緊緊地摟住我,魁偉的身形和微卷的頭發,讓我的心一下子就跳亂了節奏。
兄弟,好久不見了。
嚴澍歪著腦袋細細地看著我,臉上的微笑有了一種會意,我勉強咧開嘴,那一瞬間,我內心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我看著停靠在不遠處的定期班輪,望著定期班輪上掛著的舷梯,依然生硬地說,如果你還要活著,就不要再逼迫我了,我已經向龐微表明了我的態度。
伊姍忽然插進來,張淼,你不大氣,你為什么不從龐微的角度考慮呢,她就想多賺點兒錢,以后帶著你遠走高飛。
我平靜地說,你也干過公安,你難道忘記了我們曾經許下的誓言嗎?如果都按他們的意思做下去,那就不是生活了。
那什么樣是生活呢?日出東方催人醒,不及晚霞懂我心,龐微曾把這句話送給我,現在我再送給你,嚴澍依然微笑地看著我,他來回在江邊踱步,江水依然不急不慢地拍打著岸邊的礁石。
你現在已經是這個樣子了,我認為生活就是跟著緣分跑,伊姍瞪了我一眼。
嚴澍輕輕將伊姍拉到一邊,張淼是我們的人,你回去吧,好好照顧石衛平,他雖然啥也干不了,可他是一副道具,能掩護我們。
我內心忽然一陣沖動,揮拳砸向嚴澍,他猝不及防,重重地摔了個四仰八叉,好在這兒是江邊,我恨恨地低吼一聲,兔崽子,別看我們是發小,從一開始,老子就被你算計了,你把我們都拉下水了。
嚴澍緩緩地從地上爬起來,擦了下嘴角的血水,兄弟,不要把誤會變成包袱,你的誤會會讓你變得偏執,別忘了,我們這么干有些原因,是因為你母親的病痛,龐微留學選擇化工專業,也是因為你母親,因為我們的父輩,他們經歷的痛苦太多了。
別冠冕堂皇地找理由,你們犯罪還顯得這么溫和得體,呸!
嚴澍踉蹌了一步,伸手摟了下伊姍的腰,我看見伊姍緊緊依偎著嚴澍,一副小鳥依人的模樣,臉上的笑容恬淡而遙遠,放心吧,咱們的兒子長得壯實著呢。
我的心臟一陣抽搐,可我找不到合適的詞語,眼前金星亂冒,我沉默了半天,嘴唇囁嚅,騙局啊,伊姍,我其實不在乎你懷了嚴澍的孩子,我就是覺得對不起石衛平,他是個孤兒,天底下有這樣的報復嗎?別忘了,嚴澍不在的日子,是我一天天看著你的肚子隆起,是我替石衛平把嬰兒抱出了產房,是我看著孩子睜開眼睛,看著這個世界,看著藍天,看著星星,他只有在石衛平的懷里睡得最香最甜,石衛平就是他爸爸。
我的語調變得有些顫抖。
嚴澍擺擺手和伊姍低語了幾聲,伊姍面色倉皇,低下頭匆匆地走了,嚴澍轉過臉,親切和藹地對我說,張淼,那次沉船前,我被泰國理貨公司的直升機吊起來的那一剎那,我意識到是龐微救了我,我曾當她面發誓要報答她,可她拒絕了我,她說她喜歡你,她要給我自由,可自由真的來了,我又舍不得哥幾個,我怕見不到你們,心里難受,只好還得干這樣的活,我清楚,我欠你們的太多。
我沒有搭理嚴澍,他依然微笑地盯著我手里的皮箱說,發小,你看著辦吧,他不急不慌地穿過邊防執勤的卡口,掏出一個小本子亮了一下,又爬上舷梯,我的心臟在顫抖,我感覺手里拎著的皮箱異常沉重。
夜幕降臨,碼頭燈火輝煌,巨大的江面將燈光反射向夜空,一切亮得刺眼,我拎著皮箱,穿過邊檢的卡口,爬上了舷梯,鉆進底艙的一個輪機房里,我強迫自己調勻呼吸,我心里充盈著一種奇異的感受,混雜著巨大的恐懼。
那個輪機房是我們臥底的一個蹲點,組織上早就給我準備好了吃喝的日用品,又過了幾天,船在海上漂著,我透過小圓窗俯瞰大海,船體再次遇到了臺風,那兒是太平洋的深溝,最大深度一萬多米,黑白顛倒的兩天后,風力增強到十四級,我緩緩地從輪機艙爬到了駕駛臺,暈眩感愈發強烈,耳朵像被棉花堵住了一樣,什么也聽不見,周遭的一切開始劇烈抖動,像受損的影像般不停倒轉,碎裂,重組,撕扯又彌合,循環往復。
我拎著皮箱,跌跌撞撞地爬到船長室,還沒推開門,腳底一滑,重重地摔倒在甲板上,我的眼前一片虛幻,忽然有一股力量將我卷起,抱到船長室里,我看到了嚴澍。
張淼,其實你的活已經干完了,你不應該跟著我,他微笑著拍了拍我的肩膀,接過我手里的小皮箱,別擔心,我們這條船還有兩個多小時就會離開臺風眼,一切都會風平浪靜的。
嚴澍將小皮箱扔到海綿床上,吧嗒一聲帶上門出去了,我艱難地從海綿床上爬起來,眼前又看到了另外一幅景象,龐微坐在固定的椅子里,她很安靜,微笑地看著我,眼神里充滿理解和憐愛,她輕輕站起身,身體搖晃著抱住我,她摩挲著我濕漉漉的頭發,一圈又一圈,我忽然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感受,覺得身邊一切物體都不再清晰,變得毛茸茸,一切都在搖晃,變形。
我躺在她的懷里,她低聲向我訴說這些年在外面的感受,周圍依然搖晃,我靜靜傾聽,偶爾垂下頭,艙房里的燈光閃爍著金屬的光澤,我們彼此赤身裸體擁抱著,望著窗外無盡的黑色海面,我們不再像剛開始那樣激烈,而是變得繾綣。
我低沉地說,龐微,你回來也好,省得我見不到你,心里怪別扭的。
龐微低頭沉默,過了一會兒,我匆匆地穿上皮大衣,跳下海綿床,我要去找嚴澍,艙房的門被推開了,一切就像設計好似的,嚴澍鉆了進來,依然親切地替我整了整衣領,再忍耐兩天,船就會靠到泰國港。
我平靜地望著嚴澍,當年我告訴過你,龐微是我的。
嚴澍耐心地拍了下我的肩膀,張淼,龐微就算不是我的,她也不是你的,她是她自己的,只是我倆都瞎了眼,她策劃了一切。
我從皮大衣里掏出了一副手銬默默地遞給嚴澍,如果我和龐微走到一起,你不會介意吧?
嚴澍沒有吭氣,猛地揮拳砸到我的臉上,這個女人是什么東西,你到現在還不清楚嗎?我踉蹌了一下,再次摔倒在甲板上,我大口喘息著,渾身無法動彈,周圍的一切依然在搖晃,我看到龐微穿著先前的套裝,臉上掛著溫和得體的微笑,手里握著一把九二式手槍,對準嚴澍,我忽然清醒,那是我的槍。
龐微習慣性地甩了一下額前的碎發,細聲細語地說,老朋友,咱們合作了這么多年,你應該清楚,我翻臉比翻書還快。
我聽到了槍聲,嚴澍先是低下頭,然后滿臉驚愕地望著我倆,撲通一聲跪在甲板上,他的額頭在冒血,他居然又微笑了,帶著不屑的口氣,艱難地低吼,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后來發生的事情我記不清楚了,應該是我和龐微用白色的床單,裹住了嚴澍的尸體扔到了海里。船靠港后,龐微拎著皮箱消失了,我的槍也消失了。回到老家,我被判了刑。
幾年后,我被放了出來,我清楚地記得,伊姍開著一輛黑色的轎車把我從牢改農場接了回來,還拉著我去青弋江邊的小酒館給我接風。
坐在酒館里,我看到廣場上的噴泉隨著音樂聲時起時伏,幾輛轎車零星地停在廣場上,其中一輛墨綠色的大吉普的發動機依然在抖動,像是輕輕地喘息著,訴說著曖昧和疲憊。伊姍給我開了瓶洋酒,我悶著頭連干了幾杯,感覺全身放松下來。
伊姍笑意盈盈地對我說,我現在做房地產生意,以后你就跟著我干吧,你看前面的音樂廣場,是我們集團的作品,你知道是誰贊助的嗎?
我腦袋一時反應不過來,睜著一雙醉眼,盯著廣場的右前方,那兒居然擺著一個餛飩攤,一個花白駝背的中年人正低頭忙活著,我使勁睜大眼睛,感覺那個身影很熟悉。
伊姍優雅地點燃一支煙,饒有興趣地望著我說,張淼,你既然出來了,我就不繞圈子了,我和石衛平分手了,孩子歸他,我承擔撫養費。
我似乎清醒了不少,說,石衛平很可憐,一直生活在謊言之中,他是生活在別人給他編織的謊言之中,可他自己的感受是幸福的。
伊姍淡淡地笑了一下,既然嚴澍已經不在了,我覺得要一個孩子有什么意義呢?我和石衛平其實是在慘淡經營一個空殼,這是個悲劇,是龐微造成的。
龐微在哪兒呢?
她是我們集團的董事長,你能這么快的出來,也和她有關,伊姍意味深長地望了我一眼。
我又回到了范羅山的半山腰,我依然向往那個院子和磚瓦房,我想躲在那個院子里,站在那個小煙酒店的柜臺邊,那兒有一張石衛平躺過的椅子,沒事的時候,我可以躺在椅子里,看著不遠處青弋江邊的晚霞和中江塔,我心里踏實。
伊姍找過我幾次,讓我跟著她干,我靠在躺椅里搖搖頭,你找石衛平跟你干吧,反正我們都是發小嘛。
伊姍愣怔了一下,也不再勉強我了,只是淡淡地解釋,她已經幫石衛平在青弋江的街道辦事處謀了一份小差事,至于是什么差事我沒問。
我不愿多問石衛平的事情,我覺得我和他一樣,都是可憐的人。
那是一個夏天的午后,四周蟬鳴,我靠在椅子里瞇縫著眼,忽然聽到一個女人的聲音,可以給我一瓶礦泉水嗎?我光著汗津津的肩膀,從躺椅里緩緩站起來,從櫥柜里拿了一瓶礦泉水放在柜臺上,我似乎感覺那個女人的眼睛在盯著我,眼神柔和,我覺得眼前變得有些虛幻,像踏空之后即將跌落到恐慌和暈眩中,我扶著躺椅,穩了穩神。
龐微顯得有些富態,穿著考究,她端起礦泉水杯喝了一口水,我看見她把右手食指搭在塑料瓶口上,開始繞圈,一圈,兩圈……塑料瓶口在她的輕揉之下,發出一種嗡嗡聲,我的眩暈感愈發強烈。
我艱難地睜大眼睛望著她。
龐微將礦泉水瓶扔到一邊,又從自己隨身帶的包里掏出一個用報紙包裹的東西遞給我,張淼,物歸原主,如果當年不把槍帶走,你可能還是一名英勇的公安干警,原諒我吧,我也有難處。
我不停地吸氣呼氣,心里充盈著一種復雜的感覺。
我懷里揣著那個報紙包裹,像一個木偶被龐微牽引著,上了一輛墨綠色的越野車,我打算把那個東西還給龐微,我覺得它危險。
我看到伊姍緊握方向盤坐在車里,我忽然意識到這輛車可能就是我在廣場上見到的那輛車,看來伊姍沒有撒謊,龐微一直在家鄉,不過我已經無所謂了。
車里后排的皮椅里,躺著一個熟睡的六七歲小男孩,皮膚白皙,頭發蓬松柔軟,龐微輕輕地揉了揉孩子的臉蛋,將毛巾被覆蓋在孩子的身上,我聞到了一股淡淡的清香。
龐微顯得慵懶和漫不經心,她示意我坐在她的身邊,語氣有些冷峻,伊姍,把冷風開大些。
伊姍點點頭,會意地沖我微笑了一下,點火,腳踩油門,越野車沿著半山腰的山路蕩來蕩去,龐微坐在我身邊,腦袋卻靠在我聳起的肩膀上,讓我感到極其不舒服,我轉過臉,眼前的視野開始搖擺,越野車朝著山頂搖搖晃晃地駛去。
到了山頂,陽光在茂盛的樹蔭里跳躍閃爍,眼前的青弋江像一條玉帶,緩緩地流向寬廣的長江,龐微的臉上有了些喜色,沉默了許久,她喃喃自語,來這兒逛逛,還是老樣子,以前我和張淼經常來這里玩兒。
我沒有搭理龐微,懷里抱著那個報紙包裹,故意走到伊姍跟前,我盤算著要讓她也意識到我手里有這么個家伙,因為她畢竟和我一樣也干過公安,伊姍目光脧了一眼我懷里的東西,她意識到了,不過面無表情。我這么暗示伊姍,是不希望在這里發生什么意外,因為我禁不起再折騰了。
見我不吭氣,龐微岔開話題,沖伊姍說,這男男女女都一樣,一旦分手之后,舊愛就像我家院子里的那棵槐樹,別看這棵樹平時給不了你擋風,可一旦有人砍了這棵樹,你心里的滋味一定不好受,對吧?
伊姍平靜地問,龐微,你是拿槐樹比喻石衛平嗎?
龐微反問,你說呢?
伊姍輕嘆一口氣,是該了結了,她走到我面前,從我懷里拿過那個報紙包裹,輕輕地撫弄,其實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龐微,如果你一定要這么認定我,我也不在意,因為我的命運曾經被你操控過,嚴澍死了,我的丈夫死了,這讓我覺得我必須承擔一切痛苦。
伊姍撕開報紙,咔嚓咔嚓,推槍上膛,輕輕地將槍口對準龐微,語氣和藹,你真心細,里面還有子彈。
我的腿有些抖,心臟怦怦亂跳。
龐微面色紅潤,轉過臉對我說,張淼,如果我不在了,車里的孩子你得替我照顧好,那是咱倆的,你可以說我是自私的,其實每個人都是自私的,當年我拿走了你的槍,我不想離開你,我要讓你有一個落魄的下場,就像石衛平不知道他的孩子是嚴澍的,他永遠是幸福的,因為他生活在別人為他編織的謊言里。
我渾身哆嗦,龐微,你毀掉了我,你想過沒有,你生活在哪一種謊言里呢?你怎么就那么自信?自私是人之常情,但兇殘就會天誅地滅。
伊姍舉槍逼近龐微,你說什么做什么我都不在意了,因為我們都是發小,可你殺了嚴澍,同樣也毀了我,那我就很在意了。
那天我發現龐微穿得雖然很考究,可緊身的真絲T恤被她穿得松松垮垮,倒顯得格外性感,她轉過臉柔情地望著我,充滿了濃烈的眷戀,她抱著胳膊撲哧一聲笑了,盡管槍口頂著她的腦門,她依然帶著欣賞的目光環顧寂靜的山林,然后慢慢地走到我身邊,輕輕依偎在我的懷里。
我踉蹌了一下,渾身依然戰栗,可我偷偷聞到了她長發的清香,她的頭發有些單薄,還帶點兒亞麻色,我把它束在自己的手心里,我明確感覺到我的手指滑過她的后頸,是絲滑而冰涼的感覺,子彈從她的太陽穴嵌入她的腦袋,她戰栗了一下,柔軟的身體癱在我的懷里,陽光依然躲在樹蔭的縫隙里閃耀,我感受到她身上散發出的溫暖和曖昧混雜的氣息。
伊姍被判了死緩。
冬天來了,我溜達到音樂噴泉廣場,找到餛飩攤,那兒熱氣騰騰,石衛平佝僂著腰正在忙活,有兩個一大一小的男孩圍在他的身邊轉,他見我來了,也不吭氣,我剛要開口,音樂噴泉里飄出一陣小提琴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