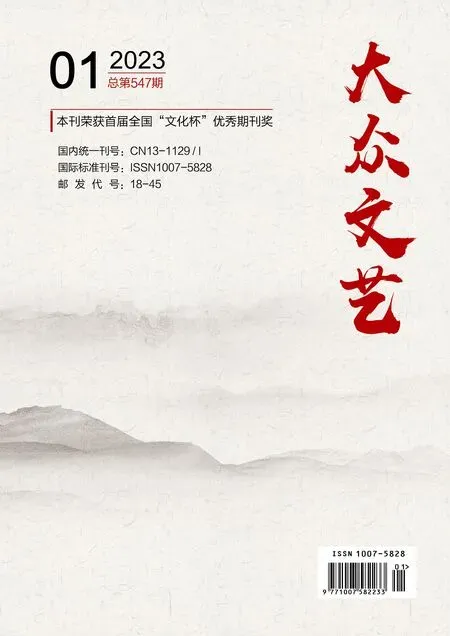論《刀鋒》中拉里的倫理困境與倫理選擇
史紅利
(青島大學(xué),山東青島 266000)
《刀鋒》是英國現(xiàn)代著名小說家和劇作家威廉·薩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晚期最知名的小說。他自1915年發(fā)表代表作《人性的枷鎖》,當(dāng)時已活躍于英美文壇三十余年,以許多具有異國風(fēng)采的短篇故事與膾炙人口的劇作聞名于英語世界。“刀鋒”一詞出自印度教圣典《迦托·奧義書》:“悟道之途艱辛,如同跨越刀鋒,越過刀鋒實(shí)屬不易,因而智者常言救贖之道艱辛”[1]。毛姆自己也從不諱言他小說中的人物是從真實(shí)生活取材的,《刀鋒》可以說是一幅兩次大戰(zhàn)之間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畫卷。細(xì)讀《刀鋒》可以發(fā)現(xiàn),這本長篇小說傾注了毛姆晚年對人生終極意義的倫理思考。
目前,國內(nèi)外學(xué)者對毛姆作品的研究多集中于《月亮與六便士》《面紗》《人性的枷鎖》和其短篇小說上,對《刀鋒》的先行研究相對較少。總的來看,對《刀鋒》的研究集中于探討主人公拉里的精神危機(jī)及其自我救贖和療愈、毛姆作品與東方宗教(尤其是印度宗教)的對話、《刀鋒》獨(dú)特的寫作手法和技巧和《刀鋒》中的女性形象等等。但鮮少有人從文學(xué)倫理學(xué)批評的角度出發(fā),對《刀鋒》進(jìn)行解讀和評析。文學(xué)倫理學(xué)批評理論主張文學(xué)在本質(zhì)上是關(guān)于倫理的藝術(shù),其立場和最終目的是發(fā)現(xiàn)文學(xué)的倫理價值。以文學(xué)倫理學(xué)批評為鑒,《刀鋒》中關(guān)鍵人物拉里在小說特定倫理環(huán)境下產(chǎn)生的倫理困惑及其作出的不同倫理選擇,為探求毛姆筆下的倫理機(jī)制與倫理訴求、挖掘《刀鋒》文本背后所蘊(yùn)含的倫理價值提供了有益參考。
一、拉里面臨的倫理困境及成因
倫理困境是文學(xué)倫理學(xué)批評理論的核心術(shù)語之一,是指“文學(xué)文本中由于倫理混亂而給人物帶來的難以解決的矛盾與沖突”①[2]。并且,一般來說“倫理兩難是倫理困境的主要表現(xiàn)之一。倫理兩難是難以做出選擇的,一旦做出選擇,就往往導(dǎo)致悲劇”[2]。《刀鋒》中幾個主要人物,包括拉里、伊莎貝爾、索菲和艾略特等等,都面臨著不同程度的倫理困境。進(jìn)一步探討這些倫理困境的成因則需要回歸當(dāng)時的倫理環(huán)境。聶珍釗認(rèn)為“對文學(xué)的理解必須讓文學(xué)回歸到屬于它的倫理環(huán)境中去,這是理解文學(xué)的一個前提”[2]。毛姆在《刀鋒》中刻畫了許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看似經(jīng)常游離于故事之外的拉里”[3]尤為讓人印象深刻。從文學(xué)倫理學(xué)批評的視角來看,拉里作為《刀鋒》的主人公,一直面臨著某種倫理困境。
毛姆作為一戰(zhàn)的親歷者,對戰(zhàn)爭的殘酷及其帶來的創(chuàng)傷有著深刻的感悟。晚年的毛姆對戰(zhàn)爭、對人性、對整個西方文明都加以了深刻的反思,并訴諸筆端,寫成了《刀鋒》這部長篇小說。毛姆通過對拉里這一人物的刻畫巧妙地在《刀鋒》中展現(xiàn)了創(chuàng)傷人物的心理困惑,以表達(dá)自己對“人性的反思和對西方現(xiàn)代性的批判”[4]。拉里從一開始就面臨著維持世俗生活和進(jìn)行精神探索的倫理困境。現(xiàn)代化帶來了經(jīng)濟(jì)發(fā)展,但戰(zhàn)爭帶來的痛苦、悲傷、無助也引發(fā)了“現(xiàn)代性語境下的創(chuàng)傷體驗(yàn)”[4]。經(jīng)歷一戰(zhàn)后,拉里拒絕了馬圖林先生提供的穩(wěn)定高薪的工作、丟下了未婚妻,一心想要弄明白為什么這個世界上會有邪惡,人生的終極意義又是為何。拉里對伊莎貝爾是這樣解釋的:“你知道,我有個看法,覺得我這一生還可以做許多事情,這比賣股票有意義得多”②[5]。在拉里眼中,追逐名利的世俗生活是一種枷鎖,一種精神的枷鎖,人生的意義應(yīng)該在于不懈的精神追求和滿足。后來,拉里又對未婚妻伊莎貝爾坦白:“我想弄清楚上帝究竟是有還是沒有,我想弄清楚為什么世界上會存在著邪惡,我想要知道人的靈魂是不是不滅,還是人死后一切就沒有了”。可以說,維持世俗生活和進(jìn)行精神探索的倫理困境始終貫穿于這部長篇小說看似混亂的敘事主線,同時也成為主人公拉里生存發(fā)展的重要突破點(diǎn)。
回歸《刀鋒》的倫理環(huán)境進(jìn)一步探討拉里面臨的倫理困境的成因,可以發(fā)現(xiàn)其實(shí)是內(nèi)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共同導(dǎo)致了這種倫理兩難。一方面,拉里在一戰(zhàn)中目睹愛爾蘭好友犧牲的個人經(jīng)歷促進(jìn)了他自我意識的覺醒,使得他開始探求人生的意義:“人生究竟是為了什么,又到底意義何在,人生是否就是一出盲目的、糊里糊涂的、由命運(yùn)造就的悲劇?”。這種哈姆雷特式的關(guān)乎人生終極意義的發(fā)問首先揭示了主人公拉里內(nèi)在自我的精神覺醒。拉里對人類生存狀態(tài)及意義的終極思考引發(fā)了其自我身份認(rèn)同的危機(jī),他在此刻意識到了人生歸于荒誕和虛無的可能性,這與哲學(xué)家薩特的存在主義不謀而合。這種倫理困境同時又作為一種催化劑,裹挾著主人公拉里不斷進(jìn)行自我和精神的探求,從而不斷成長,最終走向?yàn)⒚摵妥杂伞A硪环矫妫饭P下的《刀鋒》所處的時期,也就是一戰(zhàn)到二戰(zhàn)期間,美國大發(fā)戰(zhàn)爭橫財,經(jīng)濟(jì)迅速蓬勃發(fā)展,與此同時傳統(tǒng)價值觀不斷受到?jīng)_擊和挑戰(zhàn),物質(zhì)主義和功利主義風(fēng)靡一時。這一點(diǎn)毛姆在書中多次提及,在刻畫馬圖林一家的富有時更是大肆渲染這種物欲橫流的社會風(fēng)氣:“格雷才二十五歲,每年已經(jīng)能進(jìn)賬五萬美元,而且這只是開始。美國真是個遍地財富的國家。這不是短期利益,而是一個偉大國家蓬勃興起的必然勢頭”。一戰(zhàn)后美國物欲橫流的社會背景,使得擁有一份穩(wěn)定且高薪的工作成為評判一個青年成功與否的標(biāo)志之一。這也是為什么拉里的好友格雷要拜托父親給拉里安排一份好工作,而伊莎貝爾迫切地希望拉里接受的原因。然而,這樣復(fù)雜的社會環(huán)境也會促使拉里更加關(guān)注自我,開始思索人生。這就使得拉里一開始處于世俗生活和精神追求的倫理兩難之中。
二、拉里的倫理選擇及倫理教誨
倫理選擇也是文學(xué)倫理學(xué)批評理論的核心概念。聶珍釗認(rèn)為“在人類文明發(fā)展史上,人類在作出第一次生物性選擇即獲得人的形式之后,還經(jīng)歷了第二次選擇即倫理選擇……人是通過倫理選擇才真正把自己同獸區(qū)別開來的”。也就是說,人只有通過倫理選擇才能把自己從獸中解放出來,而“倫理選擇是人擇善棄惡而做一個有道德的人的途徑”。毛姆筆下的拉里在面臨上述倫理困境時作出了自己的倫理選擇。
毛姆在《刀鋒》中創(chuàng)造了一個近似烏托邦式的人物——拉里。小說中拉里身處20世紀(jì)30年代的美國,此時的美國大發(fā)戰(zhàn)爭橫財,正處于一個急速膨脹的時期;國內(nèi)實(shí)用主義盛行一時,金錢至上蔚然成風(fēng)。而拉里在面對物質(zhì)誘惑和精神追求的倫理兩難時一直執(zhí)著于對精神的探索和追尋。《刀鋒》中其他人物也為拉里的這種烏托邦式的追求提供了有力參照。伊莎貝爾雖然愛著拉里,卻最終出于拉里的游手好閑而和他解除婚約,嫁給了多金的格雷,從此過上了紙醉金迷的生活。格雷破產(chǎn)后,伊莎貝爾又來到巴黎投奔其舅父艾略特,繼續(xù)這種物質(zhì)的享受;書中的艾略特更是一個貪慕虛榮、趨炎附勢的勢利鬼;作者本人扮演的“我”更是坦陳對金錢的追捧——“錢能夠給我?guī)砣耸郎献钭顚氋F的東西——不求人。一想到現(xiàn)在只要我愿意,我就能夠罵任何人滾他媽的蛋,真是開心之至,你懂嗎?”。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拉里對外在物質(zhì)的輕視和對內(nèi)在精神的不懈追求。拉里一直試圖在對精神的探求中進(jìn)行靈魂的自我救贖。基于此,更有學(xué)者認(rèn)為《刀鋒》是“毛姆竭力探索靈魂(Atman)的產(chǎn)物,是關(guān)于神秘思想的論文”[6]。值得注意的是,拉里的精神探求所面臨的倫理選擇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的拉里剛經(jīng)歷過一戰(zhàn)的創(chuàng)傷,面對物質(zhì)主義帶來的沖擊,拉里選擇沉入知識的海洋,希望能從知識中找到人生的答案。這一時期,他主要求助于深奧的心理學(xué)和哲學(xué)著作,后來逐漸擴(kuò)展到所有書籍和知識,包括各種語言。小說前半部分有這樣一個情節(jié):拉里和伊莎貝爾等人在酒吧度過一夜后,沒有像其他人一樣選擇回去補(bǔ)覺,而是早早地到閱覽室,渴望在書籍中解答內(nèi)心的迷惘,尋求人生的答案。毛姆是這樣描述在閱覽室的拉里的:“我看了看,原來是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學(xué)原理》。這當(dāng)然是部名著,在心理學(xué)史上很重要,而且書寫得極其流暢……我絕沒有想到他手里會有這樣一本書”。而拉里自述:“我的知識太淺了”。毛姆筆下的拉里從小就是個藏書家,在伊莎貝爾和其他孩子去參加聚會尋歡作樂的時候,拉里和索菲則常常在家里讀詩。在拉里看來,書籍是幾代人智慧和知識的結(jié)晶,這也是為什么在經(jīng)歷了戰(zhàn)爭給他帶來的巨大創(chuàng)傷后,拉里的第一選擇是轉(zhuǎn)向書籍,而書籍也確實(shí)是他的一劑良藥,盡管沒有徹底解決他面臨的精神困境,這些書籍也深化了他對那些關(guān)乎人生的哲學(xué)問題的思考。遺憾的是,哲學(xué)、文學(xué)和藝術(shù)都無法最終解決他心中對人類生存的困惑,更無法滿足他對精神和靈魂的探索。
拉里在伊莎貝爾決定和格雷結(jié)婚后,決定從書籍中解放出來,去法國北部的一個煤礦從事體力勞動,這是拉里倫理選擇的第二個階段。拉里是這樣解釋他的這一行為的:“我認(rèn)為從事幾個月體力勞動對我有好處;這會使我有時間把自己的思想理理清楚,使自己平靜下來”。可見,在拉里眼中,從事體力勞動和之前閱讀書籍的行為在本質(zhì)上都是為了進(jìn)行精神的探索,都是為了獲得精神的滿足。這聽起來像一個悖論,然而拉里的確在這場體力勞動中收獲頗豐。他在法國煤礦的這一段生活不僅讓他以一種國際視角更深切地體驗(yàn)和見證了這個世界,而且遇到了來自形形色色的來自不同階級的獨(dú)特個體,并意識到生命對每個人都是苦難重重。采礦時,他和科斯蒂——一個被驅(qū)逐出祖國的波蘭人同住一個房間。科斯蒂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準(zhǔn)備隱瞞自己的學(xué)識;他博覽群書,但總是對知識嗤之以鼻;他身上總是籠罩著某種神秘色彩。這個波蘭人給拉里帶來了很大的精神震撼,他在激發(fā)拉里對一系列宗教問題的好奇心的同時,也深化了他對宗教本身意義的認(rèn)識,從而極大促進(jìn)了拉里的精神成長。與第一階段類似,這一轉(zhuǎn)向同樣沒能從根本上解決拉里的倫理困境,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這一轉(zhuǎn)向促成了拉里下一階段的精神追尋。
在經(jīng)歷農(nóng)場事故后,拉里前往德國波恩,并由此開始了他以宗教為名的第三段精神探索:“他是在尋求一種哲學(xué),也可能是一種宗教,一種可以使他身心都獲得安寧的人生準(zhǔn)則”。拉里是一位不斷被罪惡問題困擾的新教徒。然而德國當(dāng)?shù)氐纳窀竻s告訴拉里:“你與信仰之間的距離不會比一張香煙紙的厚度大”。這個時候拉里面臨的倫理困境更像是一種信仰危機(jī)。拉里對基督教教義仍有懷疑,他不明白為什么無所不能的上帝要創(chuàng)造這樣一個不完美、散布著邪惡的世界。此后,他先后前往西班牙和塞爾維亞,并最終在東方印度宗教里找到了答案,尋得了內(nèi)心的平和。值得一提的是,拉里并沒有轉(zhuǎn)向傳統(tǒng)的宗教教條,而是一直在尋找真正能為心靈提供指導(dǎo)、重視個體心靈體驗(yàn)的宗教。拉里作為毛姆筆下的人物,和《月亮與六便士》中的主人公一樣,在現(xiàn)實(shí)與理想、物質(zhì)與精神之間毅然選擇了后者。拉里面臨世俗生活和精神追求的倫理困境作出了他自己的倫理選擇,并最終獲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和心靈上恒定的平和。之后,拉里更是毅然決然地把自己僅有的財產(chǎn)分給了親友,回到紐約當(dāng)起了出租車司機(jī)。對拉里來說,工作只是維持基本生活的工具,過多的財產(chǎn)只會成為精神的枷鎖,成為沉溺物質(zhì)享受的誘惑,更重要的是精神世界的滿足和探索。
拉里作出的倫理選擇所經(jīng)歷的這三個階段,從某種程度上詮釋了人的精神和靈魂獲得拯救的三個重要條件——知、行和信仰。這對20世紀(jì)上半葉的美國社會甚至現(xiàn)代社會無疑是一種映射和諷刺。20世紀(jì)上半葉是歐洲文明大動蕩的時期,一方面,從戰(zhàn)爭帶來的經(jīng)濟(jì)衰退中恢復(fù)后,歐洲社會物欲橫流;另一方面,戰(zhàn)爭的慘無人道也迫使歐洲人“從工業(yè)革命帶來的科技進(jìn)步與福利社會的美夢中醒來”[7],重新審視西方文明。最初的拉里在經(jīng)歷一戰(zhàn)的殘酷后也不免感到困頓和迷惘,但他沒有放縱自己沉溺于當(dāng)時物欲橫流、金錢至上的社會環(huán)境,而是試圖為自己、也為所有人的精神荒原尋找出路和生機(jī)。毛姆筆下的拉里對外在物質(zhì)的輕視和對內(nèi)在精神的重視一方面契合了一戰(zhàn)帶來人心靈上的迷惘與失落的時代語境,另一方面也為現(xiàn)代精神危機(jī)敲響了警鐘。幸福并不取決于物質(zhì),對精神世界的忽視終將導(dǎo)致自我毀滅,心靈的滋養(yǎng)和精神生活的富足才能帶來人生真正的滿足感。可以說,拉里在那個時代的倫理困境下作出的倫理選擇具有一定的倫理教誨,能夠激發(fā)當(dāng)今時代批判性和啟發(fā)性的精神探尋。
結(jié)語
文學(xué)倫理學(xué)批評理論為探求毛姆長篇小說《刀鋒》中關(guān)鍵人物拉里在那個時代下面臨的倫理困境及其作出的倫理選擇提供了有力的理論借鑒。毛姆的一生處于一個“西方文明的弊病顯露無遺、精神世界荒蕪和信仰失落的時代”[7]。他筆下的青年主人公拉里對精神世界的追求,對善惡的包容無形中敦促了人們在物欲橫流的時代關(guān)注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這也為緩解現(xiàn)代精神危機(jī)提供了有益借鑒,只有通過知識和實(shí)踐不斷完善自己,堅(jiān)定自己的信仰,填補(bǔ)精神的空虛,才不會在挫折或困難中迷失自我,走向邪惡和墮落,甚至自我毀滅。誠然,聚焦于主人公拉里一個角色面臨的倫理困境及其作出的倫理選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刀鋒》中伊莎貝爾、索菲和艾略特等人的倫理困境和倫理選擇也值得探討,屆時也會有一個對比的視角,對這部作品倫理價值的解讀也會更加全面。從文學(xué)倫理學(xué)批評的視角解讀《刀鋒》,探求毛姆筆下的倫理機(jī)制與倫理訴求,挖掘其文本背后蘊(yùn)藏的倫理價值,為深入解讀這部經(jīng)典作品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為應(yīng)對現(xiàn)代人的精神危機(jī)提供借鑒和參考。
注釋:
①后文中出自聶珍釗學(xué)者的引文出處同此,不再另外標(biāo)注。
②后文中出自毛姆《刀鋒》原文的引用皆為此出處,不再另外標(biāo)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