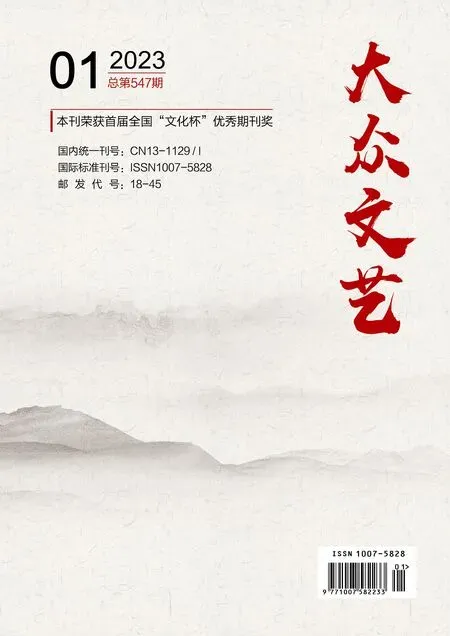懸疑話劇《深淵》中的“窺視者”建構
汪小嵐
(上海師范大學,上海 200233)
話劇《深淵》是以充滿驚悚與布滿懸念的兇殺案為外殼,將性侵與“美狄亞”式的復仇議題相結合作為故事內核的懸疑劇。本劇講述了一個患有精神分裂癥的女兒曾多次殺人,其母親出自對女兒偏執的“愛”,竭盡全力保護女兒,幫助女兒洗清罪名,遮掩犯罪事實,甚至企圖替女兒頂下殺人罪名,步步走向深淵的故事。希區柯克指出:“觀眾的介入乃是制造懸念的基礎。”①[1]導演何念在故事內容與舞臺設計上的大膽嘗試與創新,是成功吸引觀眾投入到舞臺中去的強有力的吸鐵石,進而逐步誘發觀眾對情節發展與敘事線索的期待和預測。
一、窺視者的三重建構
(一)劇中的偷窺者——角色演員
房東小王是這部話劇中最顯性的偷窺者,他憑借“房東”這個特殊身份擁有開啟每個房客的房間鑰匙。由于掌握著管理各個房間鑰匙之大權,他把鑰匙視為窺視他人生活的便捷工具。鑰匙打開的不僅是房客的房門,同樣也緩緩打開了房東小王如同深淵一般觸不到底的貪婪窺視之門。當他偷偷打開他人房門后又私自在其家中安置攝像頭,此時的攝像頭成了房東窺視每個房客的貓眼,房東在他布滿了監視器的狹小逼仄的臥室里,宛如老鼠一般瘋狂地偷窺著每個人居住者的生活,如吸血鬼般貪婪地吮吸著每個房客不被人所知的秘密。
人為什么會有“窺視欲”?奧地利精神學派創始人弗洛伊德持有這樣的一個觀點:他把人們對他人世界充滿好奇心的表現和“窺看”的欲望視為性本能的一種,它起源于性的“窺視沖動”。②[2]大部分人通常會用合理的方式去發泄與滿足內心的好奇與窺視欲,而那些在兒童期窺探欲沒有得到滿足的少部分人,到了成年期后他們就會瘋狂地窺探別人的隱私,進而來滿足一種扭曲、變態的原始欲求,形成了一種變態的畸形人格。在弗洛伊德看來,“文明漸漸使軀體被遮蔽起來,然而性的好奇卻從未停歇,這種好奇只有通過窺探到性對象的隱私部分才能被得到滿足……”③[2]
女主角陳麗娟和女兒李婷兩人相依為命,共同生活在逼仄狹小的空間里。由于家庭里缺失男性角色,兩位女性就撐起了家庭的兩根大柱。沉默寡言的房東,時常獨自一人駝背穿梭在幽暗的小巷與樓道,他的生活宛如一潭死水,毫無生機。監控與監視器原本是新時代進步的產物,反而卻變成了達成房東本能欲望的便捷工具。房東在充滿黑暗、布滿眾多監視器的房間里大量窺視他人生活,以滿足自身的好奇與原始欲求,可謂是以一種畸形變態的偷窺者身份出現在劇中。
(二)舞臺上的偷窺者——攝影機
如果說把“攝影機搬到大街上去”增強了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中的紀實性,那么在話劇《深淵》中“把攝影機搬到舞臺上去”的新穎舞臺設計同樣大大加強了故事發展的現實感。在舞臺上鮮活地演繹故事情節的不再僅是演員,攝影師也觀眾席走向了話劇舞臺,構成了話劇演出的一部分。跟以往傳統固定的平面化舞臺布景與設置不同,話劇《深淵》掙脫了傳統舞臺設置的桎梏。升級版的舞臺設計營造出更為濃厚的懸疑氛圍,有著三層樓高的老居民樓拔“地”而起,通過設置360度無死角旋轉立體的方式極大還原了20世紀90年代重慶市井街坊的原貌。④[3]破舊狹窄的小巷、耀眼閃爍的霓虹燈、簡陋復古的小賣部以及具有時代感的古惑仔元素的加入成功營造了昏暗濕漉而極具犯罪動機的懸疑氛圍。在演出過程中,黑衣攝影師全程扛著機器近距離跟拍演員在相對封閉空間內的一舉一動。攝影師通過非常熟練的走位與運鏡角度,同時取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把劇中人物與關鍵道具的特寫與人物關系淋漓盡致地呈現在屋頂的三塊廣告牌上。該劇通過利用實時影像的拍攝方式,不僅能夠構建舞臺夢境,幫助觀眾制造幻覺,使觀眾獲得一種身臨其境之感,使其更加沉浸于呈現在舞臺上的故事當中;與此同時也增強了人物關系的緊張感與故事的節奏感,合理有效的彌補了傳統舞臺無法放大舞臺上的細節的遺憾。在劇中的攝影師宛如“狗仔”一般的存在,用鏡頭去窺視每個人的生活。
其中在展現母女二人在室內發生爭執與沖突的一情節時,黑衣攝影師架著攝影機在窗外偷窺拍攝,觀眾坐在觀眾席中隔著墻與窗戶也窺視著母女二人的一舉一動。攝影師不斷跟拍演員的過程也象征著同樣帶有好奇心的觀眾想要迫切了解事情發展的來龍去脈與真相,攝影師此時不僅是舞臺的記錄者、偷窺者更是一個訴“說”者。舞臺演員通過臺詞向觀眾傳達信息,而攝影機則依靠鏡頭向觀眾傳遞劇中人物關系微妙的變化以及危險關系。攝影師在舞臺記錄的一切通過以實時影像的方式滿足了觀眾的好奇心和窺視欲。可以說攝影師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們達到滿足原始欲求的媒介。
(三)舞臺下的偷窺者——觀眾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電影理論將電影屏幕看作是一面鏡子,觀看者在觀看電影的過程中產生了對影像的認同,即對“看”這一行為動作本身的認同。對電影的這種理解源自法國精神分析學家拉康的“鏡像理論”。在他看來,6至18個月的嬰兒就進入了“鏡像階段”。在此階段中,嬰兒從對“自我”的零意識逐步向具有“自我”意識開始過渡,由此嬰兒慢慢確立了“自我”與“他人”之間的對立。嬰兒通過鏡子識別到自身形象,逐漸意識到在鏡子中的自己就是完整的自己,進而對自身身份產生認同。
將“鏡像理論”運用在戲劇中,不難發現,在劇場觀看演出時的觀眾和在鏡子前觀察與審視自己的嬰兒擁有相似的情景。在該劇中駝背房東小王佝僂著身子蜷縮在椅子上,將視線投射到布滿房間的監視器當中,而監視器在無形中幻化成了電影的熒幕,無時不刻上演著女主角陳麗娟和女兒日常生活。而處在劇院中觀看演出的觀眾也是被困在座椅上,在切斷光源的黑暗封閉的場所里接受舞臺表演與實時影像。在這樣的一個情境中,鏡框式舞臺與實時影像的結合所產生的想象界便會使得那些處于沒有防備狀態的觀眾產生認同,在這一過程中,觀眾就獲得了像嬰兒初次認識自我時的快樂。
觀眾實際上是最大的“偷窺者”。如果說觀眾走進電影院,在相對黑暗的封閉場所里觀看銀幕獲得了一種心理滿足,那么當觀眾踏進劇院,在切斷光源的同等條件下,觀眾在觀看話劇的過程中,其實也是在觀看實時版電影。他們會下意識地把自己壓抑的欲望、悲憤或期待投射到劇中人身上,借助劇中人,通過依靠自己的想象,在意識上發泄自己的性欲和攻擊欲,最終在心理上得到報復性或勝利的滿足。如此一來,在相對封閉黑暗的環境中觀看影劇成以一種合理合法的方式來滿足觀眾窺視癖的途徑。
由于該劇是采取“一半影像、一半舞臺”的創作方式不斷推進情節發展,即時影像通過“直播”的方式被引入舞臺,一塊電子屏幕被懸置在“居民樓”上方任憑觀眾窺視室內劇情。因而實時影像的加入會放大舞臺上的各種細節,其鏡頭如實地呈現在大屏幕上,帶來了電影獨有的特寫與細節感。例如,在看似風平浪靜的家庭里,一只從行李箱掉出來的沾滿鮮血的手在無聲之中打破了原有的平靜,以及母親陳麗娟“殺人”后,女兒所表現出本能的害怕驚恐的表情以及劇中各個人物關系的微妙變化,都令人印象深刻并加深了觀眾對舞臺角色的認同感,并使之產生身臨其境的現場感。該劇通過實時影像的方式,能夠極大的加強觀眾的參與感、體驗感與現場感,也就是將“缺席視為在場”,于是觀眾在劇場內通過多種方式的凝視進而得到了滿足。
二、在建構與解構之間:新窺視的生成
懸疑話劇《深淵》通過革新舞臺設計,運用具有先鋒實驗性質的多視角創作形式,打造了一場立體多維的視覺盛宴。在這場視覺盛宴之中,戲里戲外都有人扮演著“窺視者”身份,每個人都處于黑暗之中,觀察著他人的生活。劇中的房東小王、舞臺上的攝影機與觀眾席中的觀眾均為窺視視角下的三條分支,而創作者則是這三條分支的建構者。歸根結底,這三重“窺視者”身份的建構是編劇與導演有意而為之的產物。
首先,編劇通過將駝背房東小王塑造成在外沉默寡言,獨來獨往,充滿神秘感但實則具有窺視癖,對樓下母女的生活產生畸形般的好奇,并時常獨自在家盯著監視器窺視他人生活宛如變態的人物形象。一方面,編劇通過塑造一個在外戴上面具與人友好相處,在家脫下面具暴露真實本性的人物形象,其中巨大的反差性使得房東小王這一人物更加豐滿立體與真實;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房東變態般的窺視,使得警方能夠在其家中的監視器找到李婷人格分裂的畫面,不僅給警方提供破案線索,也能讓觀眾從客觀視角去觀察人格分裂下的李婷的行為。其次,導演將攝影機搬上舞臺,宛如狗仔一般的黑衣攝影師手持攝影機,跟隨著劇情的發展、演員的走位進行實時攝影。一方面,可以看出導演想要試圖打破傳統戲劇的單一媒介,企圖加入實時影像的方式幫助觀眾制造幻覺,通過放大舞臺上的關鍵性道具與人物表情使得觀眾能更加沉浸于故事當中;另一方面,觀眾能夠將“缺席化為在場”,將自身代入到架著機器的攝影師中去,將自己幻想成舞臺上的攝影師去近距離窺視角色的生活。最后,坐在觀眾席中的每一位觀眾不僅僅是買票看戲的觀看者身份,他們還擁有著第二身份——窺視者身份。觀眾前方的鏡框式舞臺就類似于一個巨大的監視器,導演牢牢抓住“每個人都有窺視他人隱私的欲望”的關鍵點,通過將舞臺升級成旋轉立體的三層居民樓與實時影像的加入,使觀眾能夠處于全知視角去觀看舞臺上每個角色的生活,進而使觀眾產生窺視他人生活的刺激感與緊張感,帶給觀眾新奇體驗。
從劇本內角色形象的塑造再到劇本外舞臺技術的革新,編劇與導演在不停地嘗試建構多重窺視。但是創作者在努力建構窺視的同時,其新穎的建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同時也在解構原本試圖建構的窺視效果。舞臺上有觀眾能看見的東西,也有觀眾看不見的東西,創作者大膽地將實時影像的敘事手法加入舞臺,以模擬窺視的視角來幫助觀眾營造窺視氛圍,但是原本是被遮蔽的部分又被影像赤裸真實地呈現在三塊大屏上,這種窺視方式下的“窺視”還稱得上是窺視嗎?攝影機的加入達到了導演預期想要建構窺視的神秘效果,但與此同時也正是實時影像的加入將其逐步拆解。當然舞臺上也有攝影機看不見的地方,由于不同于電影可以運用多臺攝影機進行交叉、平行、全方面拍攝,戲劇舞臺上的攝影機只能拍攝局部的舞臺內容,因此攝影機所拍攝的畫面是有限的。這就使得利用攝影機模擬窺視視角建構窺視的同時,被解構的窺視也只是局部的有限的。因此,話劇《深淵》就是在不停地建立多重窺視,同時也在不斷地瓦解部分窺視的過程中向前推進的。
三、沉浸式體驗的媒介表達——跨媒介、融媒介
話劇藝術的展現,從最初觀眾的場下視角到現如今更強調跨媒介手法的運用。這種方法的運用,也是如今話劇市場對于沉浸式表達的追求信號和媒介風向標。以話劇《深淵》為例,對于人格分裂的表演方式主要有兩種聲音:一種是堅持一個人分飾不同人格,例如:希區柯克《驚魂記》。一種是多個人分別飾演不同人格。其實這兩種方式本無絕對的好壞之分,在藝術領域里這種絕對化地審美呈現本就是不存在的。而在《深淵》中,對于人格分裂的展現則選擇了后者,兩個演員飾演兩個不同人格。這與電影《神探》有異曲同工之妙。其實這種劇場表演選擇兩個人表演不同人格更照顧到觀眾的觀賞感受。一般來說,觀眾對于整部劇情和人物性格把握上則是較為生疏的。因此如果選用一個人飾演不同人格,很容易引起觀眾的觀感迷惑,尤其是當觀眾思想游離時,再次進入劇情,則有點不知其所以然,也無法更好地沉浸式感受話劇藝術。因此在分飾人格的選擇上,也是對觀眾能否沉浸觀看話劇的換位思考。
其次,在話劇藝術的媒介貫通上,現如今話劇更多地強調一種沉浸式觀感效果,這在過去是很少去表現給觀眾的。以話劇《心迷宮》為例,第一場兇殺案發生在開演前不久,被害人溺水身亡。案發地是一方不大的池塘,位于吊腳樓右側的制高點,看上去像在山林之中。但是,作為觀眾而言,如何更切身去體會整個案發過程,這在過去的話劇表演中是很少去提及的。但現如今通過高清水下攝像頭和大屏幕,可以使觀眾更清晰地看到角色從拼命掙扎到死亡的全過程。這種痛苦的掙扎通過大屏展示,也更能引起觀眾注意,讓觀眾沉浸式體驗感更強。除此之外,在《心迷宮》中,還有一個新的媒介方式改變就是觀眾直接去舞臺中當村民,參與到故事中。這種參與方式完全打破了原有的角色變化。最初話劇表演中,演員和觀眾既是統一的但又是對立的。但這種讓觀眾參演到村民的新方式則完成了話劇的統一。舞臺上和舞臺下的區別則不僅僅只是觀賞效果遠近角度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身份的變化。從觀賞者到參演者的轉變,更能帶動觀眾對于話劇的積極性以及進入話劇情節的沉浸感。
總之,通過跨媒介和融媒介的綜合運用,沉浸式表達實現了跨越發展,但是在整個沉浸式觀看體驗上,仍有許多尚待思考的地方。尤其是對于懸疑話劇這一特殊話劇劇目而言,實現沉浸式表達也是從話劇劇目中的出圈表現。
結語
隨著話劇的不斷發展,傳統話劇也在不斷推陳出新其新的模式。而整個出新方式的再構就是實現沉浸式表達。其中第一個出新的點是戲劇張力更加注重窺伺感的營造。而在舞臺技術的革新上,每一個環節都在突破原有傳統話劇的設置。例如“窺視者”從角色演員、攝影機、觀眾三個不同維度出發,去聯系編劇導演和觀眾之間的戲劇默契。這種窺視感,在為創作者帶來快感的同時,也給觀眾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奇感。因此對整體感受的把握,也是對其沉浸感的重視。這對于現如今話劇市場和未來話劇市場而言,是尤為關鍵的。
除此之外,現代戲劇沉浸表達的另一個關鍵之處是注重媒介的運用。它在打破原有話劇呈現方式的基礎上,以大屏的方式給觀眾更直接的感官體驗,而且也可以加深觀眾對劇本的內容。總之,話劇發展在不斷推陳出新,結合新的時代特點,新的創作方式,給觀眾更加沉浸式的體驗。
注釋:
①弗朗索瓦·特呂弗.希區柯克論電影[M].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51頁.
②劉紹龍.對電影《后窗》的精神分析解讀.[J].時代文學(下半月),2010(9).
③同上.
④蘇杭.凝視深淵的勇氣與情感觀原創懸疑劇《深淵》[J].上海戲劇,2020(05):2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