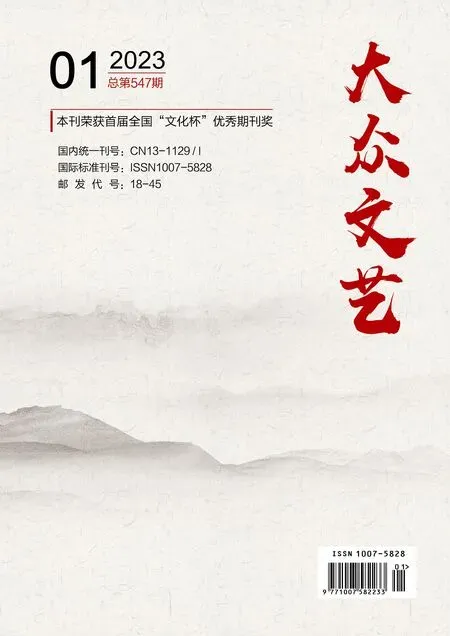近年來國產(chǎn)電影中地理空間的轉(zhuǎn)換研究
李昱嶠
(中央戲劇學(xué)院,北京 100085)
空間作為電影重要的敘事元素和表意元素,是電影“視覺符碼”的重要載體。海闊在《電影敘事的空間轉(zhuǎn)向》中提及,“如果分析電影敘事的空間,需要從兩個方面,一是電影敘事形式的空間建構(gòu),二是電影敘事內(nèi)容的空間建構(gòu)。”[1]其中“敘事形式的空間”,指創(chuàng)作者通過視聽手段構(gòu)建出的空間,而“敘事內(nèi)容的空間”,則指電影劇本階段建構(gòu)起來的空間。由此,在電影創(chuàng)作的劇本階段,空間建構(gòu)就已經(jīng)作為重要的敘事元素存在,但很多時候,創(chuàng)作者容易忽視空間的建構(gòu)意義。
空間是電影理論中一個龐雜的課題,其中涉及的理論并非本文的篇幅能及,因此,本文擬從電影敘事內(nèi)容的空間建構(gòu)中,著重提取地理空間轉(zhuǎn)換這個角度,重點分析近年來國產(chǎn)電影中出現(xiàn)的地理空間轉(zhuǎn)換現(xiàn)象。此外,本文探討的地理空間并非虛構(gòu)和魔幻的地理空間,而是真實的地理空間;并非自然地理空間,而是人為地理空間,是創(chuàng)作者依據(jù)現(xiàn)實的地理空間建構(gòu)的一個完整的、觀眾有認可和感知的地理空間。如電影《地久天長》中,北方小城鎮(zhèn)地理空間的建構(gòu),敘事圍繞著傳統(tǒng)北方工業(yè)工廠、工廠筒子家屬樓和北方水庫等地展開;再如電影《江湖兒女》中,南方沿江城市地理空間的建構(gòu),敘事圍繞著輪船、沿江碼頭和南方街道等地展開。
一、南方與北方地理空間的特性
對于國產(chǎn)電影中出現(xiàn)的地理空間構(gòu)建,小城鎮(zhèn)一直是很多導(dǎo)演傾向去探索和呈現(xiàn)的角落,有學(xué)者曾研究認為,小城鎮(zhèn)空間是“介于發(fā)達城市和自然村落之間的一種空間類型”,即一種兼具“城市”和“鄉(xiāng)村”特色、體現(xiàn)中國現(xiàn)代化發(fā)展進程特殊性的“夾層空間”。近年來,許多電影以北方小城鎮(zhèn)空間為地理空間背景,如電影《鋼的琴》(2011)、《山河故人》(2015)和《白日焰火》(2014)等。北方小城鎮(zhèn)空間作為城市和鄉(xiāng)村之間的土地,一方面“遠離鄉(xiāng)村”,一方面“渴望城市”,它是摻雜著城市文明和農(nóng)業(yè)文明的交界地帶。北方小城鎮(zhèn)空間某種程度上代表著我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一種空間縮影,當(dāng)下的中國正處在發(fā)展和變化之中,時代的焦慮和小城鎮(zhèn)空間的表征有著千絲萬縷的關(guān)聯(lián),相較于南方一些城鎮(zhèn)的發(fā)展,北方小城鎮(zhèn)的發(fā)展受到了很多方面的制約,傳統(tǒng)工業(yè)難以轉(zhuǎn)型、地理位置因素、人民思想局限等等,因此,北方小城鎮(zhèn)空間的出現(xiàn),不是偶然,而是一批導(dǎo)演針對時代變遷和社會發(fā)展的對話。以北方小城鎮(zhèn)空間為敘事基調(diào)的影片也總能帶給觀眾一種封閉和局限的觀感,電影《江湖兒女》中,敘事的初始地理空間設(shè)定在一個以傳統(tǒng)工業(yè)為經(jīng)濟支柱的北方小鎮(zhèn)中,此時的這里正處于社會轉(zhuǎn)型期,影片3分鐘處出現(xiàn)的城市俯拍,右側(cè)的低矮樓房和左側(cè)的平房相呼應(yīng),灰蒙蒙的城市若隱若現(xiàn),北方小城鎮(zhèn)地理景觀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一種壓抑和局限的感受不訴自明,有效表達了城市化進程和社會變遷等時代背景。
相較于北方小城鎮(zhèn)地理空間呈現(xiàn)出的封閉和局限質(zhì)感,南方城鎮(zhèn)的地理空間在國產(chǎn)電影中則傾向傳遞出一種疏離和漂泊的空間氛圍。電影《地久天長》中,麗云和耀軍夫妻從北方城鎮(zhèn)移居至南方漁村,在南方地理空間中,雜亂的汽修店坐落在不知名的海域旁,居住場所和工作場所沒有明確的劃分,觀眾很難感知到這里的空間范圍,人物在南方地理空間中的漂泊感被清晰的感受和辨識。電影《江湖兒女》中,巧巧從北方小城鎮(zhèn)輾轉(zhuǎn)來到南方城鎮(zhèn)奉節(jié)(重慶城鎮(zhèn)),在南方地理空間中,不明方位和空間范圍的建構(gòu)方式再次出現(xiàn),巧巧漂泊在南方的碼頭邊、街道中和群山里,陌生地理環(huán)境帶來了人物對于所處環(huán)境的疏離感受。
此外,南方地理空間中的意向符碼也同樣增加了人物在南方地理環(huán)境生存的漂移感。如船只的呈現(xiàn),麗云和巧巧都乘坐了船,讓人物出現(xiàn)在漂泊感聚集的船只上,一方面輔助人物表意出他們的內(nèi)心空間,另一方面也在敘述南方地理空間的空間特性;再如江與海的呈現(xiàn),巧巧和麗云都曾注視著連綿無邊的海水和江水,讓人物面對著沒有盡頭的江水和海水,一方面顯現(xiàn)出人物的渺小和無助,另一方面也在暗示人物在南方空間的生存現(xiàn)狀。
二、“北方至南方”與“南方至北方”的地理空間轉(zhuǎn)換路徑
以上簡要概述了近幾年國產(chǎn)電影中,北方地理空間和南方地理空間呈現(xiàn)出的空間特性,由于國產(chǎn)影片中北方和南方地理空間呈現(xiàn)出的巨大差異,使得這兩種地理空間之間的轉(zhuǎn)換為敘事提供更多可能。電影《江湖兒女》中的地理空間轉(zhuǎn)換路徑為:北方小城鎮(zhèn)(山西大同)-南方城鎮(zhèn)(重慶奉節(jié))-北方城鎮(zhèn)(山西大同);電影《地久天長》中的地理空間轉(zhuǎn)換路徑為:北方城鎮(zhèn)(內(nèi)蒙古)-南方小漁村-北方城鎮(zhèn)(內(nèi)蒙古);電影《天注定》中的地理空間轉(zhuǎn)換路徑為:北方小城鎮(zhèn)(山西-烏金山)-南方城鎮(zhèn)(湖北宜昌)-南方城市(廣州/東莞)-北方小城鎮(zhèn)(山西-烏金山)。梳理近年來國產(chǎn)電影中出現(xiàn)的地理空間轉(zhuǎn)換路徑,大致可以分為“由北方至南方”和“由南方至北方”兩種,這種地理空間轉(zhuǎn)換并非偶然,而是在敘事內(nèi)容初期就構(gòu)思好的一種空間敘事策略,沒有這種地理空間轉(zhuǎn)換,敘事將不能成立,這種地理空間轉(zhuǎn)換的建構(gòu)是影片中不可或缺的敘事元素和表意元素。
在“北方至南方”的地理空間轉(zhuǎn)換路徑中,一種產(chǎn)生動機是“逃離”式的。北方小城鎮(zhèn)封閉“無隱私”式的生活氛圍,熟悉的空間和場景都在牽動著悲情的體驗,人物在傷痛的過往中難以釋懷,這讓他們無法在故鄉(xiāng)繼續(xù)生活,他們想要告別過去、想要在新的空間場景中放逐和麻痹自我,并試圖尋找到可以解脫和救贖的出口。例如麗云耀軍夫婦(電影《地久天長》中的人物)和斌斌(電影《江湖兒女》中的人物)和,在這種動機之下的由“北方至南方”的空間轉(zhuǎn)換,是人物想要告別過去而選擇的一種“逃離”式的出走行為。另一種產(chǎn)生動機是“追尋”式的。在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南方和北方發(fā)展不均衡,這讓許多北方小城鎮(zhèn)中的人們對于南方地理空間心存向往,無論是張晉生(《山河故人》中的人物)還是斌斌(《江湖兒女》中的人物),北方小鎮(zhèn)地理空間中的人們對于南方地理空間的向往,是人物想要更廣闊生活方式的一種“追尋”式的出走行為。
在“南方至北方”的地理空間轉(zhuǎn)換中,人物從南方空間重回北方空間之中,這種“歸來”式的地理空間轉(zhuǎn)換,多由南方地理空間所呈現(xiàn)出的漂泊感引發(fā),如前文南方地理空間特征中所提及,南方地理空間帶給異鄉(xiāng)人的漂移疏離感,會讓“出走”的人們萌生“歸來”的意圖。斌斌(《江湖兒女》中的人物),他未能在南方城市完成自己的“宏圖偉業(yè)”而“回歸”故土;麗云耀軍夫婦(《地久天長》中的人物),他們未能在南方顛沛的生活中釋懷過往,也選擇了“回歸”故鄉(xiāng)。當(dāng)“逃離”者和“追尋”者真的來到了南方地理空間,實現(xiàn)了“由北至南”的空間跨越,空間變化與社會轉(zhuǎn)型帶給人們的焦慮,在前往區(qū)別于想象中的南方城市后,在疏離中拼搏與掙扎過后,人們開始懷念故土,對故土的思念和對漂泊的厭倦,讓這些“出走”者們最終選擇“歸來”。
“由北至南”的“出走”和“由南至北”的“歸來”,這兩種地理空間轉(zhuǎn)換的產(chǎn)生都伴隨著時間的跨度。分析梳理《地久天長》《江湖兒女》和《天注定》等具有明顯地理空間轉(zhuǎn)換的影片便可知,這類影片都橫跨了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光,且這類影片都在表述著相似的主題,即歷史長河中的個體命運,也就是時代變遷之下的人們。龍迪勇在《空間敘事學(xué)》中提及:“所有的歷史事件都必然發(fā)生在具體的空間里,因此,那些承載著各類歷史事件、集體記憶、民族認同的空間或地點便成了特殊的景觀,成了歷史的場所。”[2]由此,當(dāng)創(chuàng)作者傾向于表達歷史中的事件時,就需要具體的空間來幫助其完成表達,電影《地久天長》中當(dāng)麗云耀軍夫婦再次回到故鄉(xiāng),經(jīng)歷了“改革開放”的北方小鎮(zhèn),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使得地理空間的加速生產(chǎn)滲透到了各個角落,高樓林立的新城景觀成為新的地理空間表征,工廠和筒子樓作為“歷史事件”和“集體記憶”被留在了過去,繁華的新城成了下一個新的“歷史的場所”。同樣,在電影《江湖兒女》中,“回歸”故鄉(xiāng)的斌斌坐在新修好的高鐵站里,他看著那些新建的高樓,此時的彬彬和他熟悉的故鄉(xiāng)都被留在了過去,新空間所帶來的情緒記憶正在蔓延。
地理空間的轉(zhuǎn)換伴隨著時間的流逝,時間和空間這兩個電影敘事的重要元素,在創(chuàng)作者構(gòu)思之初便相互輔助、相互鏈接。時空變化共同完成了歷史的訴說,表達著創(chuàng)作者對于歷史和時代的看法,成為他們表意時代變遷的必然選擇。
三、地理空間轉(zhuǎn)換作為空間敘事的有效途徑
20世紀后期以來,西方人文社會科學(xué)的研究者們開始逐漸“把以前給予時間、歷史和社會關(guān)系的社會青睞,逐步轉(zhuǎn)移到空間上來。”[3]這種“空間轉(zhuǎn)向”思潮也直接影響了電影領(lǐng)域,電影創(chuàng)作者和理論研究學(xué)者紛紛把注意力轉(zhuǎn)移到空間領(lǐng)域,而地理空間作為空間敘事的重要組成,也更多地被提及。海闊在《電影敘事空間文化研究范式》中所指“無論是自然的,還是社會的,地理空間成為人物存在以及情節(jié)發(fā)展的依據(jù)。”[4]地理空間和人物及情節(jié)的息息相關(guān),也意味著地理空間轉(zhuǎn)換對人物形象塑造和敘事主題表意都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
(一)地理空間轉(zhuǎn)換與人物塑造
地理空間作為承載著人物生存發(fā)展的大環(huán)境,其變化影響著人物內(nèi)心空間的同時也在塑造著人物,很多時候,當(dāng)代人的生存困境,呈現(xiàn)為空間化的戲劇困境被展示出來。電影《地久天長》中,麗云和耀軍夫婦在經(jīng)歷喪子之痛后,對二人最有效地塑造來自他們決定離開故鄉(xiāng)前往南方,他們在南方漁村過著麗云口中“時間靜止等待變老”的生活,南方小漁村的孤島空間間接表達了人物內(nèi)心的絕望和悲痛,也輔助塑造出麗云這個絕望且堅毅的平凡女人。
地理空間轉(zhuǎn)換為人物塑造構(gòu)建了不同的環(huán)境和場景,讓人物在其中充分的成長和變化。電影《天注定》中,生活在北方小鎮(zhèn)中的大海,連一封舉報信都寄不出去,閉塞的地理環(huán)境帶給他無處發(fā)泄的憤怒,從而致使他選擇走向“滅亡”的方式如此的血腥;生活在南方村落中的三兒,做一名殺手的原因是待在鄉(xiāng)村里沒意思,這種極度無聊且無望的地理環(huán)境,構(gòu)建出這個人物的犯罪動機和內(nèi)心空間;生活在廣州大城市的小輝,過著螻蟻般沒有尊嚴的生活,大城市的輾轉(zhuǎn)漂泊讓他對生活失去了信心,而選擇縱身一躍。以上這些人物的塑造都與具體的地理空間轉(zhuǎn)換路徑相聯(lián)結(jié),地理空間變化作為人物重要的行動軌跡變化,輔助創(chuàng)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時,也表意著人物的心理狀態(tài)。
電影《江湖兒女》中的人物巧巧,她孤身一人從北方空間前往南方空間尋找愛人斌斌,新的地理空間是她建構(gòu)性別主體意識的外在刺激力。一方面,在南方地理空間中發(fā)生的一系列事件,有效幫助巧巧建構(gòu)了屬于自己的“性別主體意識”,例如當(dāng)她面對想要強暴她的摩托車司機時,巧巧機智脫身駕車離去的身影似乎在暗示著,此時的巧巧已不再是斌哥的“附屬”,她是漂泊在新空間中的堅強個體。另一方面,南方地理空間使巧巧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剛剛出獄的巧巧漂泊在陌生的南方景觀中,無依無靠的生活讓她成長并激發(fā)出她的潛力,巧巧意識到任何人都是不可靠的,她需要自己找到自我的價值和位置。她用一支玫瑰花在陌生人的婚宴上吃飽;她裝成小三的姐姐騙取負心漢的錢財;她放棄火車上遇到的男人獨自回到故鄉(xiāng)。是這段南方空間下的塑造,讓巧巧這個人物成長、豐滿、并擁有光彩。
(二)地理空間轉(zhuǎn)換與主題敘述
電影的敘事策略和電影的主題表述,都需要合適的地理空間作為影片發(fā)生和發(fā)展背景,不同的敘事空間具有不同的表征意義。一部影片的主題建構(gòu)和空間選擇息息相關(guān),地理空間作為空間敘事的重要組成和有效途徑,即為影片敘事呈現(xiàn)背景和底色,又為影片主題表意提供敘述的可能。
分析《地久天長》《江湖兒女》和《天注定》等出現(xiàn)明顯地理空間轉(zhuǎn)換的影片,不難梳理出,地理空間轉(zhuǎn)換的同時也帶來了時間的流逝,這些電影似乎都敘述著一個相同的主題——大時代變遷之下,小人物的生存與掙扎。福柯在《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下文》中指出,“我們的時代焦慮與空間有著根本的關(guān)系,比之時間的關(guān)系更甚。”[5]電影《地久天長》中橫跨了30年的時光流轉(zhuǎn),麗云耀軍夫婦經(jīng)歷了“公有制改革”“計劃生育”“下崗潮”“城鎮(zhèn)化建設(shè)”等一系列的歷史事件,地理空間的轉(zhuǎn)換讓他們成了時代的見證者和參與者,當(dāng)夫妻倆時隔數(shù)十年再次回到故鄉(xiāng),一側(cè)是新建起來的高樓大廈,一側(cè)是低矮的老式街區(qū)和破舊廠房,夾在其中的二人張望著“新”與“舊”的更迭,至此,影片主題得到了真切的表述,即歷史與個體命運的交織,歷史運動往往是造成人物命運的根源。
電影《江湖兒女》中,小人物巧巧和斌斌是時代轉(zhuǎn)型中被過濾出去的邊緣人,他們從國有工廠走向體制外,開始建立屬于他們的“江湖”體系,卻沒想到被“城市化進程”中鄉(xiāng)村來到縣城的“新勢力(年輕后生)”而擊垮。心懷志向的斌斌來到新的地理空間,他試圖再次找到自己的個人價值,可飛速發(fā)展中的社會早已容不下曾經(jīng)的“大哥”,至此他淪喪在物欲和無序中。在時空變遷的跌宕中,人物在社會中尋求自我認知的過程,即是創(chuàng)作者想要呈現(xiàn)的主題表達——變革中的城鎮(zhèn)以及城鎮(zhèn)中的小人物,關(guān)注城鎮(zhèn)的歷史變化及人們的生存現(xiàn)狀。
結(jié)語
電影作為圖像藝術(shù),需要空間的表意特征,作為敘事藝術(shù),需要空間的敘事建構(gòu)。地理空間是電影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故事發(fā)生的背景,也是人物存在和情節(jié)展開的根據(jù)。在敘事內(nèi)容層面,地理空間轉(zhuǎn)換的建構(gòu),一方面幫助創(chuàng)作者完善敘事內(nèi)容、為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可能。另一方面,創(chuàng)作者將自身對時代變遷的體悟注入地理空間轉(zhuǎn)換的建構(gòu)之中,城鎮(zhèn)景觀的迭代與某個集體或個人的命運相聯(lián)結(jié),使觀者體悟到個體命運在時代浪潮中的跌宕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