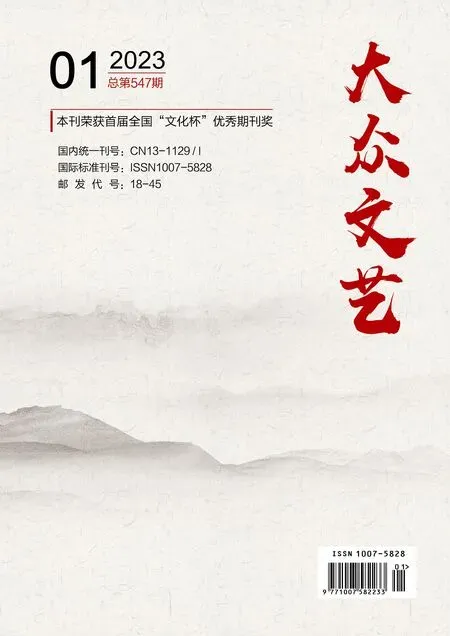德里克·賈曼電影中欲望主體的確立
楊晶晶
(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上海 200062)
德里克·賈曼(Derek Jarman,1942-1994)同格林納韋被彼得·沃倫稱作英國電影“最后的新浪潮”,他將矛頭對準其時電影商業化發展、挖掘英國傳統文化價值的主流規訓,晚年身患艾滋仍堅持為同性戀維權,利用影像意圖打開容納異質性的合法渠道。尤其以傳遞的酷兒意志為要,賈曼視理性主體為批判對象,挖掘人性中潛藏的自由性欲。
賈曼對個體自由欲望的肯定與法國思想家喬治·巴塔耶的欲望觀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在巴塔耶處,“欲望”作為個體內驅力促使人類進化的歷程按“三界”直線展開,即動物世界、世俗世界、圣性世界。遵循黑格爾否定辯證法邏輯,世俗世界在否定動物世界原始欲望的理性秩序中建立自身,主要表現為對死亡和性的禁忌;圣性世界對此理性進行否定,以色情為僭越禁忌的典型回溯被壓抑的動物性。由此,巴塔耶“通過揭示出世俗(理性)的欲望之下所存在的‘秘密的欲望’,通過把它提升為顛覆、消解具有自我同一性的主體和同質世界的手段,最終使它變成了反對理性主義的大旗。”①
以異質性的力量破壞物質化、功能化、世俗化的理性世界,讓欲望的隨機狂熱壓倒克己復禮的苦行,是賈曼和巴塔耶共有的追求。巴塔耶成體系的理論,為從欲望主體建立的維度研究賈曼電影中的酷兒意志提供了支撐,賈曼的影像世界和哲思與之巧妙扣合。社會生活的物質世界和宗教信仰的精神世界構成賈曼影像中的世俗整體,賈曼在對世俗世界的雙層否定下引渡到對同性戀酷兒意志的彰顯,及異質性欲望主體的合法確立。
一、批駁恐同的禁忌話語
世俗世界的建立以男權中心主義為主導話語,異性戀傳統的話語思維充斥“恐同”意味。塞奇威克也曾指出:“恐同癥是異性戀婚姻為主的父權制度的必然結果之一。”因而,“恐同”作為官方默認的黨同伐異手段,昭顯對以資本主義(父權制)社會為同質性、理性秩序代表的僭越行為的否定。首先從整體語境入手,賈曼的批判即從資本主義社會的理性秩序開始,呈現自私物欲與消費主義相譜成章的撒切爾時代的荒誕詭譎。
基于曾經舞臺設計的經驗,賈曼擅長對想象空間進行戲劇化的布置,在沒有具體所指的影像空間內部構成超現實景觀。《花園》(1990)中對商業廣告戲仿的場景內,巨大的電子廣告屏作為背景播放著自然景觀、人文建筑,畫面左側一穿著潮流的男子自縊掛于半空,伸出發黑的舌頭,右側西裝革履的男子在一摩托車前方舞蹈,最終自縊者睜眼復活和舞蹈男一起興奮展示各色信用卡。演員表演的事實空間和背景暗示的抽象空間被拼貼在一起,廣告屏進行了流動的空間的視覺化概括,影射追求經濟效率的現代化社會,兩名演員在表演中實現一次消費推廣。兩種空間重疊,各非常態元素之間缺乏明確關聯,構成對現代性物質社會被異化的意義指涉,割裂、無厘頭是其實質,社會秩序這一大他者的話語被賈曼塑造為戲謔的笑柄。賈曼更是從拍攝技術上反主流意愿,使用經濟實惠的超8攝影機②進行創作,拆解出象征界理性中潛藏的“失序”危機。超8攝影機可進行拍攝及放映速度的調整,脫離常規24幀/秒的規定,其物理機制如疊影重拍成為賈曼創作中的重要手法。理性秩序忙于籌劃,在工業發展、現代化進程下的利益追逐中,戰爭作為理性外爆后的失控結果而出現。《戰爭安魂曲》(1989)基于對權力擴張的反思,疊影技術將戰爭殘酷畫面和主體的憤恨、恐懼在同一時刻表達,于在場和不在場之間游蕩,形成情緒張力,強化反戰立場。同時,疊影技術反映出賈曼經由傳統體系培養下的涂層繪畫觀念,傳統文化形式溢出“如畫”觀感成為自我觀念表達的借徑,被納入賈曼先鋒性的一部分。
對追求同一性、功能化的整體社會語境批判,即否定了“恐同”話語思維存在所需依附的合法情境,賈曼打開了異質性可進入的豁口,在具體的主體間關系中顛覆其可靠性。主要依托恐同群體與同性戀群體的人物關系展開,一方面,基于前者對后者凝視的生成,在象征界對想象界的規訓中,營造“他人即地獄”的恐懼。《花園》中,恐同群體的視點對同性戀者進行主觀的描摹,攝影機強制入侵私欲領域,它的可公開性對同性戀構成威脅,作為大眾之眼的隱喻施行主觀暴力。同性戀者常被置于一群男性之中,被擠壓在畫面邊緣成不平衡構圖,嘲笑聲和扭曲高傲的表情就是表達主體,暴力有聲化、可視化,借由恐同彰顯出的男性氣質展開對同性之愛的殖民。另一方面,在這種惡化狀態之下,同性戀群體的陰柔、痛苦身體是其間強弱關系的直接影射。同性戀整潔的衣著作為一種精神性純凈的外在延伸,是賈曼對同性之愛圣潔的宣揚。被霸凌中,他們被扒開衣服、被潑澆不明液體,在蒙太奇段落中被建構出禽類動物的侮辱性形象,同性戀者被恐同者玷污,話語權缺失而不具有攻擊性成為其時的先天預設。最終,恐同群體與同性戀群體被設置為施虐者與受虐者的關系,恐同的禁忌話語被揭露為權力不對等的產物,道德倫理的恥感被弱化,同性戀主體的合法性被轉化為基于人權的平權伸張。
丑化基于資本主義同質性社會的恐同禁忌話語,將“他者化”的隱形暴力過程可視化,反思恐同話語敘述如何打壓、丑化同性戀者及相關事件,以鞏固異性戀常規化主體,提示出福柯揭露的話語的霸權性,使得觀者情感認同上對此構成排斥與不信任。最終,恐同思維下的敘述成為一種價值判斷上的不可靠敘述,其偏見色彩引出的解構空間隨之擴大,揭露并進一步批駁世俗世界理性主體自私、排他、克己的殘暴行徑。
二、顛覆基督“愛”之信仰
基督教是西方價值觀的源頭,其神性是人對理性的至高追求。《圣經》作為基督教主要思想的記錄,成為對個體的人進行理性規束的準則,全知全能的上帝在經典的文本中復活,是對上述可把握的物質世界之外的未知恐懼的想象性征服,也是在巴塔耶的欲望觀關照下,表明恐懼作為存在消亡意識的構成對“死”之禁忌的訴求。基督教神學系統中,“愛”以對信仰臣服的姿態作為死亡的對立面被確立,“這一宗教觀念具有雙重意義,首先是愛上帝,然后是因為愛上帝而愛他人。”③對此文化傳統中理性主體的否定、對禁忌的僭越自然需要完成對“愛”的顛覆,經對《圣經》拆解重組,“質詢上帝”成為賈曼的影像中最具特色與批判力的部分。
《花園》中最直接的呈現即是上帝形象與同性戀者同構。上帝以傳統認知的白衣形象出場,以十字釘刑為標識,顯性的傷口攜著人類的原罪意識,兼有不順從規則而被懲罰的痛恥感。影片中的兩種符碼又進一步附著在同性戀者的形象上,同性戀者被世俗群體鞭笞也即被釋作基督受難記。圣母瑪利亞懷抱幼時耶穌的場景被挪用進影像,影像中也不斷穿插進賈曼兒時與母親互動的家庭影像,同構另一組母子關系,而賈曼最終成為一名同性戀者,兩者共同指向對上帝同性戀取向的猜疑。又如片中上帝與男同接吻的片段,他們被一群舉火把的行刑者包圍成視覺中心,一方面可以看作影片對上帝性取向的直接認定;另一方面,是對圣經內容的戲謔,其寓意曖昧含混。圣經中也曾出現同性之吻,即猶大對耶穌的出賣之吻④與圣彼得和圣保羅在殉教前的圣吻⑤,且諸多相應題材的繪畫與該畫面構圖相呼應。其一,若延續前述男同被賦予上帝身份的判斷,則是上帝-男同的關系被置換為猶大-耶穌的關系,以表上帝為宗的基督信仰實是對同性之愛的不義背叛;其二,此吻則是在對上帝同性戀人格化后的結果,直接指向對整個宗教系統的諷刺,上帝只是宗教信仰的傀儡,當以同性戀者身份暴露自身,也同樣面臨“殉教”的境遇。無論如何理解,始終都是對上帝、對信仰的褻瀆,其最終目的,是要完成賈曼從道德上對宗教世界以愛為幌子的批判,片中圣誕老人鞭笞男同致死,其原本作為慶祝基督誕生的施惠者形象不再,剩下對生命的漠視和踐踏。
在從圣經文本內部道德規范的運行邏輯進行批判之外,賈曼更從外部現實的角度反思當時西方社會對“上帝”之名的濫用。以二戰為典型,倚靠上帝之愛,假借其普世性展開利益爭奪。《戰爭安魂曲》戲仿圣經“替罪羊”的戲碼,蒙太奇段落將羊、天使、屠殺場三個元素拼貼結合,暗諷戰爭利益關系下粉墨政客將將士作為替罪羊殺害而掩飾他們才是幕后黑手的真相。戲劇化的場景布置,明暗對比的造型效果加之飽和的色彩,戰爭的真實殘酷被表現主義的形式建構著,悲愴感受在虛實的縫隙間綿延。自稱信仰基督的后基督徒,是追逐自身私利卻謊稱“基督徒”的現世人群,“愛”作為超驗道德成為理性籌謀的工具,用以圓洽理性逐利的極端情形,與片中為傷者無聲吶喊、超度的基督徒護士形成鮮明對比。以“愛”的信仰“殺”人,西方世界理性主體實際的殘忍構成信仰世界中的自我反諷。
如尼采在《反基督》中所述,基督教是對現實生命價值的高傲否定,在它超驗性道德背后是對個體欲望釜底抽薪式的閹割,“從根上摧殘激情就意味著從根上摧殘生命:教會的實踐是與生命為敵。”⑥個體成為理性功能訴求的工具,而基督教本身也面臨被工具化的險境。賈曼對《圣經》的拼貼消解了敘事邏輯,意義曖昧含混,意義確定的權力散落在每個知覺主體處,彌散在個體主觀性判斷中,對抗英國商業消費的主流美學規范,更企圖僭越基督教世界,滿足解放個體、獲取自由的訴求。
三、回歸欲望的本真存在
巴塔耶提出,動物性的性在人的主體構成中無法被理性絕對化約,即使是在世俗世界的秩序中,人有著對禁忌突破的沖動。這樣的沖動作為潛藏的欲望,是自主權開啟的驅動力,“尤其是神圣欲望中的愛欲,以色情為代表,它既是對被壓抑的獸性的回溯,又是對消解自我的瞬間體驗的不斷逼近。”⑦干擾同質化的形成,誕生出一個“圣性世界”,理性主體將在此處沉淪、分崩離析。賈曼作為同性戀者,在他的影像中無時不流露著對這種色情或隱或顯的表達訴求,開啟生命欲望肆意蔓延的場域。
從影像的隱喻性來看,色彩是賈曼的特色語言。賈曼喜好交叉使用多色濾鏡,和被捕捉的物象共同突出低明度、高飽和的色彩印象。在有限的畫面空間里,色彩多樣繁雜,形成強烈跳動的視覺“刺點”,生成知覺主體未經改造的生理本能反應,如歌德曾對色彩進行過的分類,這種反應進而能調動起積極或消極的情緒。賈曼有序地交替運用濾鏡色表達同性交歡寧靜自然、萬物生長肆意野蠻、恐同群體囂張跋扈等情緒經驗。在一種由多色而來的感覺的雜多中,或頹靡、或熱烈,畫面抽離現實經驗形成超現實的末世景象觀感,朝向“自我消盡的圣性欲望”。《花園》中大片象征禁忌的鮮艷罌粟,自我傳播或根莖傳播的植物,影射著同性間內在情感的活躍自由,在這個無序的圣性空間內,同性之間是神圣的歡愛,受到模仿古代巨石陣壘起的條狀“龍牙”石的守護。一如賈曼以粉色裝飾一對男同和一個嬰兒構成的異質家庭形態的場景,是一個“粉色弗洛伊德(Pink Floyd)”⑧寓言,對快樂原則下潛意識欲望的索回,同性之愛的圣性便是來自現實原則壓抑下的本我動物性的回溯。賈曼對花園的建造將色彩、物質材料重組為新的意義整體,在矛盾、雜亂的視覺體驗中增強異質性張力,開啟了對自我生命體驗和感知的表達,花園本身成了他和他的酷兒圈子感官上的隱居之地。
借用各種媒介在影像中制造出的“光”,也是賈曼的一種隱性表達。光高頻出現在《天使的對話》(1985)內青年男子間的互相尋找中,他們所處環境抽離現實,是高度抽象化的欲望空間,光是對欲望的認可和指引。而刺眼的陽光也是尼采宣稱“上帝已死”的重要信號,陽光的強烈時刻標志對舊有道德與價值的重新評估。巴塔耶沿用尼采的陽光概念,他的小說《天空之藍》中不受任何約束的托普曼沉浸在耀眼光芒中,消除了一切外在束縛。宗教啟示、上帝顯圣般的“光”,具有與之相反的意義,此處光的圣性不再依附于理想、至高的上帝,而是撇開一切理性主義對主體的定義,論證個體存在的本質。在此狀態下的色情,“是經過人性改造過的神圣的‘動物性的性’,是神圣的色情,是對人身上那些遭到禁止的自然部分的苦澀的回望和留戀。”⑨賈曼進一步在對男性肉體的儀式性膜拜中,明確了對色情肉體的神話化。對一男子進行洗禮,為他穿戴王冠和披風,男子手持權杖,接受另一男子的臣服及親吻。破除自柏拉圖時起的靈肉對立,顯現身體歡騰的活力。
影像中的元素和視覺主體不遵從線性的敘述邏輯,人物的行為也沒有明示的行動元,皆游離在時空中,這個上帝已死的世界讓一切獲得了解放。賈曼因而可以自由操控幻象性的影像時空,承襲文學實踐中對色情推崇的策略,在越界中對教會和法律譴責、拒斥的罪惡、淫穢進行復活,通達欲望主體合法存在的圣性之域。
結語
自柏拉圖起,人的欲望受制于理性和符號秩序,作為主體的性質被確定,后來更是在弗洛伊德處被強調壓制的必要性,因而人的欲望始終匱乏、渴求被填補和滿足。德里克·賈曼作為一名同性戀者,亟須打破對欲望的囚禁,他肯定異質力量的否定性與批判性,在宣求酷兒權益中為自我定位。這樣的立場使得賈曼對抗著主流體制,體現在他的影像中,則是實驗性的影像形式生成的解構性、批判力量。借英國傳統文化元素及經典文本,在現實與超現實的拼貼中創造與經驗間的疏離感,賈曼朝向個體欲望本身的存在,這不是在單純地尋求自我救贖,正如他靠影像建立起的超越世俗的觀念:物質現實世界及其基督宗教世界不應成為自我持存的支撐。賈曼在欲望主體下有著和巴塔耶同樣的主張,即是開啟不受政治、道德、物質等干擾的本真存在的大門。
注釋:
①程黨根.巴塔耶的“圣性”欲望觀[J].南京社會科學,2006(6):62.
②超8攝影機:電影界主流創作設備是16毫米和35毫米規格的攝影機,超8小型攝影機最初為滿足業余電影市場需要而生產,它使用超8毫米膠片,放映速度為18幀/秒。
③胡偉希.論悲憫與共通感——兼論基督教和佛教中的悲憫意識[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04):49.
④猶大背叛耶穌時,以吻為讓敵人識別耶穌的信號。
⑤據《新約圣經》,在古羅馬時代,圣保羅讓追隨者們用圣吻互相問候致意,同性間的圣吻作為早期基督教儀式被保留下來。
⑥[德]尼采著,周國平譯.偶像的黃昏[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6:29.
⑦馬秋穗.僭越與違抗:喬治·巴塔耶的“欲望論”[J].甘肅社會科學,2011(2):45.
⑧粉色弗洛伊德:又被譯為粉色的夢境,是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用以解釋本我與潛意識欲望的一種符號。
⑨程黨根.巴塔耶的“圣性”欲望觀[J].南京社會科學,2006(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