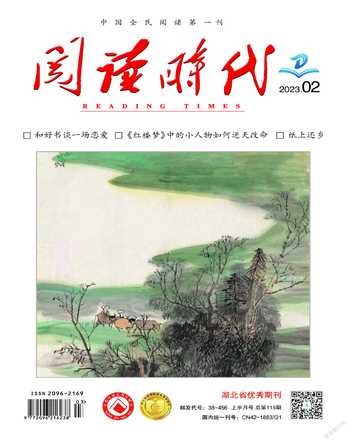綽號見高下
張勇
綽號,是人類的一大獨特發明。古今中外,不少人物,不論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都有一個與其身份、氣質、特點相符的綽號,說起其人,往往不提其名,而是先說綽號。有時候,一個響亮的綽號極可能蓋過其真姓大名,比如《水滸傳》中的許多人物。
比較常見、也是較為通俗的綽號,有“母老虎”“母夜叉”“鐵公雞”這些含有貶義的;也有“神算子”“小諸葛”“萬人迷”這種語帶褒揚的。因綽號的特殊性,基本都是非褒即貶,極少有中性的。正因如此,我們通過綽號,基本就可以看出一個人品性的高下了。
因受評書或武俠小說影響,我們對處江湖之遠的豪俠們的綽號往往比較熟悉,而對居廟堂之高的官員綽號相對陌生,其實,通過他們的綽號不僅能見性格人品,更能看到其官德之高下。
漢代的劉寵,歷任縣令、太守、太尉等要職。他任會稽太守期間,郡內太平,政績顯著,因而被提升為將作大匠。臨行前,郡內六位白發老翁,為表民意,均出一百文錢相送,不收下就不讓劉寵離開。劉寵無奈,只能收了每人一文錢,留下“一錢太守”的美名。北魏元慶智,性貪鄙,作太尉主簿時,事情無論大小,總要先得賄賂,然后再處理,十來個錢、或者二十來個錢都收,被人稱為“十錢主簿”。兩個綽號看似差不多,然為人為官,高下立判。
古時,人們多以“青天”來贊譽那些廉潔奉公、愛護百姓的官員,如包拯被稱為“包青天”,海瑞被叫作“海青天”。除了“青天”,還有不少表示贊頌、崇敬的綽號——后漢楊震,任東萊太守,路經昌邑縣,此縣縣令王密曾是楊震舉薦的秀才。王密得知楊震途經此地,便去拜見楊震。夜間,王密以十金相贈。楊震不解地說:“我了解你,你不了解我,為什么呢?”王密說:“夜里沒有人知道的。”楊震厲聲斥責道:“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說沒有人知道呢?”王密羞愧地退出。楊震因此事而被后人稱為“四知先生”,名聞天下。明代范景文,歷任兵部侍郎、工部尚書、內閣大學士等要職,位尊權重,卻清正廉明。當時,許多親朋好友常登門相求辦事,均被范景文一一謝絕。為表自己的清廉之心并杜絕親朋好友的請托,范景文特意在衙門堂鼓邊放置了一塊牌子,上書“不受囑,不受饋”六個大字,并放出話:“要是有人違犯,莫怪翻臉無情。”范景文的做法讓老百姓交口稱贊,大家尊稱他為“二不公”“二不尚書”。后來,有正直之人以范景文的勤政廉政為內容撰寫了一副對聯,上聯是:“不受囑,不受饋,心底無私可放手”,下聯是:“勤為國,勤為民,衙前有鼓便知情”。
清官有綽號,貪官也“絕不示弱”,除了前面談到的“十錢主簿”,還有——南朝梁魚泓做過南譙、竟陵、新興、永寧等地太守,他經常對人說“:我當一郡太守,要搞他個四盡:水中魚蟹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谷盡,村里百姓盡。”百姓惡其貪,稱之為“四盡太守”;唐時,有個侍御史名叫嚴升期,特別愛吃牛肉。巡查時,他所到州縣烹宰的牛便極多。他是一個貪官,問題不論大小,只要交納金銀,就一概不予追究。此人所到之處,金銀價格暴漲。時人譏諷其為“金牛御史”;唐文宗時,裴顏祺官拜翰林學士。當時翰林院有個規定:日光照到甬道之第五塊磚時上朝。裴顏祺性懶,總是等到日光照到第八塊磚時才到,人稱“八磚學士”,謂其經常遲到;五代時后唐的馬胤孫是個不通世務的書呆子。他身居相位,卻從不敢決斷政事,朝政任人擺布。馬胤孫上朝不開口議論,不開印辦事,在家不開門接見士大夫,時人譏稱其為“三不開宰相”;南宋寧宗時,李汝翼任九江元帥,此人貪欲十足,連營中最窮的士兵也不放過,規定他們每天交一雙草鞋給他。士兵們私下稱其為“李草鞋”;明末崇禎時,右僉都御史、湖廣巡撫宋一鶴善于討好上級。到任后照例要持名帖參見上司。當他得知上司楊嗣昌的父親大名為鶴時,便在名帖上把自己的署名改做“一鳥”,以示避諱、尊重,時人稱其“鳥巡撫”。
官員的一言一行,都被百姓看在眼里,記在心里。勤政愛民、清正廉潔的好官、清官,人們以雅號相贈,反之,只能獲得諢號、惡名。
(源自《西安晚報》,郭旺啟薦稿)責編:楊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