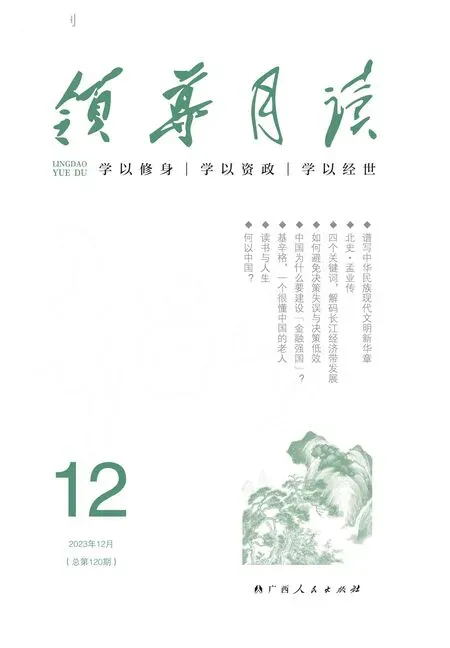九章·涉江
[戰國]屈原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登昆侖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茍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
(原文據中華書局1996年版《屈原集校注》)
【譯文】
我從小就對奇裝異服特別喜好,到如今年歲已老,興趣卻毫不減少。腰間掛著長長的寶劍啊,頭上戴著高高的切云冠帽。綴著明月珠啊,身佩美玉串串。世道混濁沒有人理解我啊,我也要遠遠地離開這個喧鬧的世界。駕起青龍白龍車啊,我與舜帝同游天帝的玉園。登上巍巍的昆侖,品嘗玉花的佳肴。我要與天地比壽,我將如日月星辰一樣將萬物照耀。痛心啊!南方并沒有人理解我,天一亮,我就渡過長江和湘水。
登上鄂渚我回頭眺望啊,唉,絲絲寒風凄苦悲涼。讓我的馬兒在山邊漫步,把我的車兒停放在林旁。我駕一葉扁舟上溯沅水啊,齊力搖起船槳,拍水擊浪。船兒隨波起伏不肯前進啊,陷入漩渦打轉波蕩。清晨時我從枉陼出發,傍晚時我落宿于辰陽。只要我的心端正坦蕩,雖處窮鄉僻壤但又有何可傷!
【簡析】
《涉江》為《九章》中的一篇,是屈原晚年被流放于楚國江南地區時所作。全篇內容分為五段:從開頭至“旦余濟乎江湘”為第一段,述說詩人高尚理想和現實的矛盾,闡明這次涉江遠走的基本原因,以“奇服”“長鋏”“切云”“明月”“寶璐”等象征詩人高尚的品德與才能。自被流放以來,屈原的年紀一天天變大,身體也一天天衰老,可他為了楚國的進步,沒有放棄過,他堅持改革、希望楚國強盛的想法始終沒有減弱,決不因為遭受打擊、遇到流放而灰心。但他心中感到莫名的孤獨,“世溷濁而莫余知兮”,他的高行潔志不為世人所理解,這真太令人傷感了。因此,他決定渡江而去。從“乘鄂渚而反顧兮”至“雖僻遠之何傷”為第二段,敘述一路走來,途中的經歷和詩人的感慨。“乘鄂渚”四句,言詩人登上今湖北武昌西面的鄂渚,不禁回頭看看自己走過的路途,又放馬在山皋上小跑,直到長江北岸的方林才把車子停住。“乘舲船”四句,說詩人沿沅江溯流行舟,船在逆水與漩渦中艱難行進,盡管船工齊心協力,奮力用槳擊水,但船卻停滯不動,很難前進,此情此景正如詩人當時的處境。“朝發枉陼”四句,接著寫詩人的行程,早上從枉陼出發,晚上到了辰陽,足有一日行程,行程愈往西,詩人思想愈堅定。他堅信自己的志向是正確的,是忠誠的,是無私的。同時,他堅信無論如何艱難困苦,自己都不感到悲傷。原文其后三段依次寫進入溆浦以后獨處深山的情景,詩人從自己本身的經歷出發,聯系歷史上的一些忠誠義士的遭遇,進一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批判楚國邪佞之人執掌權柄而賢能之人卻遭到迫害的政治黑暗。合觀全篇,該詩充分表現了屈原雖身處僻遠荒涼的流放之地而與世隔絕,明知自己的結局是“愁苦而終窮”,但仍不變心不從俗,始終追求高潔的堅貞志向,表達了詩人對美好理想的追求、對黑暗現實的批判。從藝術風格上來說,全詩以寫實為主,寫景與抒情有機結合,比喻與象征運用嫻熟,又富有浪漫主義色彩。詩人以豐富奇特的幻想,創造了一個優美的神話世界,體現了偉大浪漫主義詩人高超的藝術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