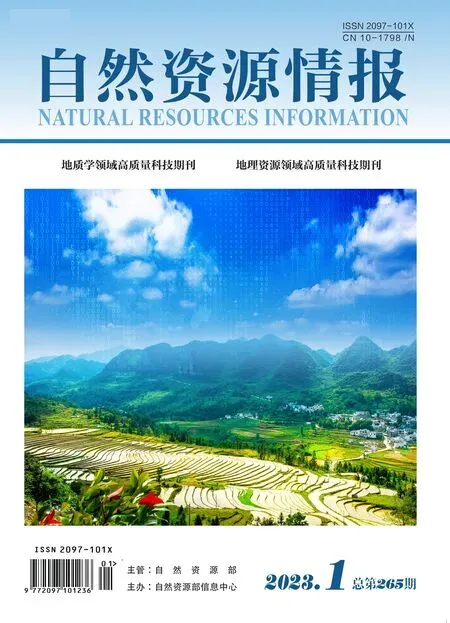農業生產效率與新型城鎮化耦合協調關系研究
——以四川省21個市(州)為例
程 婷,劉伯霞,2
(1.甘肅農業大學財經學院,甘肅 蘭州730070;2.甘肅省社會科學院,甘肅 蘭州730070)
相對于傳統城鎮化而言,新型城鎮化是與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的城鎮化[1]。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堅持走以人為本、四化同步、優化布局、生態文明、傳承文化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目前,中國已進入新發展階段,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和農業高質高效發展均處于關鍵時期。新型城鎮化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推進過程中,不僅能吸納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提高城鄉間生產要素配置效率,還能優化農村經濟結構,帶動農村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革,已成為破解“三農”發展難題的重要途徑[2]。農業現代化本質上就是農業土地產出率、勞動生產率和科技進步率不斷提升的過程[3]。目前,學者們基于定性或定量的分析研究,普遍認為農業生產效率和城鎮化之間具有正向的相互作用關系[4-6]。劉克非[7]、陳哲[8]等專門研究了城鎮化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趙麗平[9]等對1998—2014年全國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研究表明農業生產效率與城鎮化之間存在正向的相互作用關系;時悅[10]等以東北三省30個地級市 2007—2016年的數據實證分析了二者間的耦合協調關系,結果表明,各地級市的協調程度有明顯的區域差異性。
綜上所述,學術界對研究農業生產效率與城鎮化的關系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以下兩方面的研究中還存在可拓展的空間。一是就新型城鎮化這一概念而言,對其與農業生產效率之間的協調關系及協調度進行的研究較少;二是從研究區域來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國或省域層面,直接以四川省各市(州)作為研究對象,專門研究農業生產效率與新型城鎮化相互作用程度的相關研究報道較少。因此,本文基于對已有文獻的回顧,立足當前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時代背景,測算四川省21個市(州)農業生產效率與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及相互作用程度,以期促進四川省由農業大省向農業強省跨越,為制定實施區域協同發展戰略和政策提供理論基礎與現實依據。
1 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1.1 指標選取
1.1.1 農業生產效率評價指標的確定
借鑒郭軍華[11]、張紅彥[12]的研究,選取農作物總播種面積、農業機械總動力、有效灌溉面積、化肥施用量,以及農、林、牧、漁業就業人數作為投入指標,以農林牧漁業總產值作為產出指標(表1)。
1.1.2 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評價指標的確定
依據《國家新型城鎮化發展規劃(2014—2020)年》,并借鑒鄧靜[13]、鄭強[14]的研究,構建包括以經濟基礎、人口、社會基礎、資源環境等4個一級指標下的16個二級指標來衡量新型城鎮化水平(表1)。

表1 農業生產效率評價與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指標體系
1.2 數據來源
文中采用的數據來源于2011—2021年《四川統計年鑒》《四川農村年鑒》,以及各市(州)的統計年鑒和統計公報。
2 研究方法與模型構建
2.1 農業生產效率測算方法
DEA模型(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用來衡量多投入和多產出的決策單元相對有效性的一種方法,由美國著名運籌學家Charnes A和Cooper W. W.等[15]提出,常用于效率計算,但無法體現面板數據的動態變化。于是Caves D. W.等[16]根據曼奎斯特發展的距離函數創立了曼奎斯特生產效率指數。因此,本文運用DEA-Malmquist指數的方法,來測算四川省各市(州)農業生產效率水平,結合相關文獻[17-18],計算公式如下:
式(1)中,Dt(xt+1,yt+1)和Dt(xt,yt)分別表示在t期的生產前沿下,(t+1)和t期的距離函數值,Dt+1(xt+1,yt+1)和Dt+1(xt,yt)分別表示在(t+1)期的生產前沿下,(t+1)和t期的距離函數值,TFP表示全要素生產率,TFP(t,t+1)表示t期到(t+1)期的農業生產效率變化。
2.2 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指數測算方法
熵值法以其能克服指標變量之間信息交叉重疊和人為確定權重的主觀影響而廣泛應用于多指標綜合評價研究[19]。本文基于鄭強(2017)[14]改進的熵值法評價指標的權重,依據權重和評價指標標準化數值求出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具體步驟如下:
(1)數據標準化:
(2)比重變換:
(3)計算指標熵值:
(4)計算差異性指數:
(5)計算指標權重:
(6)計算新型城鎮化發展綜合指數:
2.3 耦合協調度模型
耦合協調度模型可以對不同系統和要素間的互動關系與協調程度進行分析[20],本文從全局視角分析四川省21個市(州)近10年農業生產效率(U1)與新型城鎮化(U2)之間關系,公式如下:
式(9)中,C是耦合度,C值越大,說明U1和U2間的相互作用越大,反之則越小。
式(10)(11)中,D是耦合協調度,T是綜合發展指數,α和β為農業生產效率與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的待定系數,U1和U2是互相影響且重要程度相當,所以該研究選擇α=β=0.5。借鑒學者羅小鋒[21]、蔣正云[22]等的研究,劃分如下等級區間標準。

表2 耦合協調度等級分類
3 實證結果及分析
3.1 農業生產效率與新型城鎮化測度
根據四川省21個市(州)農業生產效率與新型城鎮化測度結果,21個市(州)2011年的TFP指數全都大于1(表3),說明全要素生產率自2010年至2011年都有所提高。結合表3可知,各市(州)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指數自2011年至2020年均有了較大程度的增長,年平均增長率為8.15%。其中,成都、綿陽、遂寧、南充、眉山、雅安、巴中、阿壩和甘孜等9個地區,2020年與2011年相比出現成倍增長。具體來看,各市(州)農業生產效率與新型城鎮化水平都有明顯的區域差異。成都作為四川的省會城市,2011年和2020年新型城鎮化水平分別為0.409、0.946,是最小值甘孜州的11倍,絕大多數地區的新型城鎮化水平偏低。農業生產效率的測度體現為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同樣也具有地區差異。盡管成都2020年TFP指數小于1,表明與2019年相比有所下降,但2011—2019年的TFP指數均大于1,其余地區的TFP指數的增長率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總體來看,四川省各市州的農業生產效率和新型城鎮化水平的變動趨勢基本一致。

表3 2011年和2020年四川省農業生產效率與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指數對比表
3.2 農業生產效率與新型城鎮化耦合協調度測算
依據耦合協調度等級劃分標準,測算出四川省21個市(州)近10年農業生產效率與新型城鎮化耦合協調度值在0.326~0.707之間波動。成都與其余地區相比,農業生產效率與新型城鎮化協調水平一直處于首位,近10年耦合協調度平均值為0.644,2011—2013年協調度等級為勉強失調,2014—2018年一直處于初級協調階段,2019年其耦合協調度值為歷年最高(0.707),達到中級協調狀態,但在2020年下降為初級協調狀態。2011—2015年大部分地區處于輕度失調狀態,在2016—2020年間,處于瀕臨失調狀態的地區占大多數,四川省各市(州)2011年、2016年和2020年的耦合協調度趨勢變化見圖1。

圖1 四川省各市(州)耦合協調度趨勢變化
2011年有17個地區為輕度失調,到2020年有19個地區處于瀕臨失調階段。其中,2011—2015年,自貢、廣元、遂寧、內江、眉山、達州、雅安、巴中、資陽、阿壩、甘孜和涼山等12個地區均處于輕度失調狀態。自2016年開始,四川整體農業生產效率與新型城鎮化耦合協調度值有所提升。而德陽2011—2020年一直處于瀕臨失調階段,耦合協調度平均值為0.43;綿陽2011—2019年耦合協調度平均值為0.441,在2020年進入勉強協調階段;攀枝花2011—2012年為輕度失調階段,2013—2018年均處于于瀕臨失調階段,2019年耦合協調度值為0.508,達到勉強協調,但在2020年有所下降,為瀕臨失調狀態。總體來看,四川省各地區農業生產效率與新型城鎮化耦合協調度值呈緩慢增長態勢,且存在明顯區域差異,尤其是作為省會城市的成都,其近10年耦合協調度平均值是排名末位的甘孜州的1.8倍,空間布局呈“東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結合圖2可以發現,四川省農業生產效率與新型城鎮化水平耦合協調度較高的地區集中分布在成都平原經濟區和川南經濟區,川東北經濟區和攀西經濟區次之,川西生態經濟區最低。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四川省各地區的農業生產效率和新型城鎮化水平均穩步提升,其中2011—2020年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平均水平均大于1,2019—2020年的TFP指數為近10年最高,同時2020年新型城鎮化水平綜合發展指數也為歷年最高。但區域間增長態勢出現明顯差異,這與各地區發展基礎和條件密切有關,作為省會城市的成都由于具有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自然環境和經濟條件等,在農業生產效率和新型城鎮化水平的測度上均居高位,同時作為成渝城市群的核心城市,隨著戰略規劃實施和生產要素集聚,未來發展空間仍巨大。廣元、巴中、達州等經濟實力較小、農業發展基礎較弱的地區,雖然2011—2020年其新型城鎮化水平綜合發展指數和TFP指數在全省排名靠后,但其增長態勢較顯著,未來發展提升空間較大。
2011—2020年,四川省各地區的農業生產效率和新型城鎮化協調度總體處于較低水平,且提升較緩慢,但2018年以來提升幅度較大,大部分地區處于瀕臨失調階段。耦合協調度排名前5位的分別是成都、綿陽、德陽、瀘州和攀枝花,耦合協調度排名末5位的分別是資陽、涼山、阿壩、巴中和甘孜。可以看出,一些經濟發展較好、綜合實力較強的地區其農業生產效率和新型城鎮化協調關系也越好,而協調關系較差的地區通常其經濟水平也較差。分市州看,區域差異明顯。2011—2020年成都農業生產效率和新型城鎮化協調度平均值一直處于最高水平,比處于最低水平的甘孜州高83.4%;另外,廣元、遂寧、內江、眉山、廣安、達州、雅安、巴中、資陽、阿壩、甘孜、涼山等12個地區的耦合協調度值均低于平均水平,說明這些地區的農業生產效率和新型城鎮化水平互動關系較弱,也意味著要實現其良性互動尚存在較大提升空間。
4.2 建議
4.2.1 提高農業生產效率
四川作為全國農業大省、人口大省和糧食主產省份,鞏固和提升糧食綜合生產能力,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對于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產品產量,保障糧食安全有著重要意義。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一是要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因地制宜,發揮各地區域特色效應,從源頭減少“拋荒”“撂荒”現象。同時,各地農業管理部門要嚴格管控良田糧用,鞏固撂荒地治理成果,探索建立“空天地”一體化的耕地“非糧化”和“撂荒”監測信息平臺,堅決遏制耕地“非農化”、基本農田“非糧化”。二是打鐵還需自身硬,各地要強化科技興農、人才興農的意識,加大對農業科技領域的研發投入。重點培養一批“學農懂農愛農”的新型職業農民和農業職業經營管理者,全面提升農業從業者素質,在農業生產、消費等各個環節,發展和應用現代信息技術,結合市場需求做出及時的農業生產決策,推動農業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互促共進[23]。
4.2.2 提高新型城鎮化水平
推進新型城鎮化,一是要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加快補齊縣城城鎮化建設短板,推進公共環境、市政公用、教育醫療衛生服務等基礎設施建設提質升級。二是要接續優化產業布局,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減少對資源型產業的過度依賴。三是要堅持把以人為核心放在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首要地位,提升城市人居環境和功能品質,在推進農業人口轉為市民化的過程中,對農村轉移就業人員展開求職、就業技能培訓,加強培育新型職業農民,推進農業規模化經營,提高農業生產效率。與此同時,不斷提升城鄉居民歸屬感、認同感和幸福感,為高質量的新型城鎮化建設提供內在動力。
4.2.3 各市(州)應發揮比較優勢,實現聯動協同發展
四川省近10年農業生產效率和新型城鎮化水平均呈現穩步提升的態勢,但各市(州)間區域差異顯著,隨著人口和產業向優勢區域集中,一方面,各地區應發揮比較優勢。針對如成都、綿陽等發展較好的地區,應充分利用其基礎優勢,承載更多產業和人口,發揮價值創造功能,形成推動區域農業經濟和新型城鎮化高質高效發展的示范區與增長極。針對如廣元、巴中、阿壩等農業發展較差、城鎮化進程相對滯后的地區,應根據其自然環境特點和經濟基礎因地制宜發展。例如,川東北地區多為丘陵、山區地帶,因此要針對性地規劃適合當地特點的產業,做強川東北富硒茶、青花椒、木耳、核桃、油橄欖等產業帶和秦巴山區高山蔬菜產業帶,做大南充晚熟柑橘產業,做優廣元蒼溪獼猴桃產業,以特色優勢農業帶動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例如,甘孜州和阿壩州這兩個地區,其地形地貌復雜,人文與自然風光要素豐富,作為我國重要的水源涵養、水土保持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區域,有著極高的生態價值,因此,要堅持保護優先,創造更多的生態產品。另外一方面,各地區應該發揮區域聯動效應,協同發展,接續推進農業生產效率和新型城鎮化水平提升,促進兩者間更好地實現良性互動,推動區域間的基礎設施、產業分工、環境治理、對外開放、改革創新等協調聯動,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實現五大經濟區聯動協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