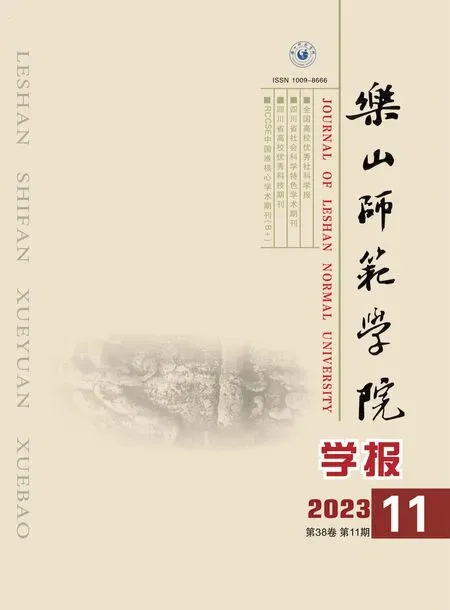宋人對遠域國家“拂菻”的想象與認知
王熙雨
(鄭州大學 歷史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
宋代,外部大環境多變,北方、西北、西南疆域較唐代縮減許多,難與先前一樣通達四方。在這個時期,宋與周邊王朝如北方遼、金,西北的西夏,南方區域性政權大理、交趾、占城等都直接接壤或距離較近,與這些國家通過民間交流、朝貢、貿易、戰爭等方式建立了直接且真實的交往。而在超遠距離的域外,宋人由于當時交通的落后與他國之阻礙,難以取得實際意義上的聯系。
今人根據宋人留下的繪畫與文獻才得以了解當時人們的想法。在繪畫方面,有關職貢圖的討論是宋人對拂菻看法的熱點之一。但以宋代李公麟的《萬方職貢圖》為代表的描繪朝貢盛況的作品,在地理上并沒有描繪真實的拂菻地理風貌與人文習俗,是朝貢體系下對自身的一種“帝國”的想象。在對于拂菻的文獻中,其位置考辨則為另一個熱點。對于拂菻的著述,今人多站在當下的視角,在語源、宗教文化上對其具體位置進行考證,且至今也無具體之定論。但鮮有人從宋人視角入手,在其文獻中尋找當時宋人眼中的拂菻位置的變遷,也少有人從宋人的視角看文獻中記載的其他拂菻器物、建筑、文化生活之變遷和異于前代之處。雖然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文獻中這種“詳實”的描述很難反應當時真實的遠域國家,文獻中時人的想象與認知也雜糅于文獻之中,無法準確區分①。但從這其中,宋人依然提供了時人看待西域、看待世界,甚至是看待自身的獨特視角。
一、宋人文獻記載中的拂菻地理空間
(一)文獻記載中的拂菻方位及其與“大秦”的關系
漢代張騫出使西域后,古人便開始了解西方世界。東漢和帝時期,甘英便被賦予了出使大秦的使命,雖然并未成功,但一個強大而富饒的遠方強國的形象卻深入人心。隨著時間的變遷,對“大秦”這一稱謂發生了一些變化,如黎靬、犁鞬、拂懔、拂菻等。我國史書最早記載“拂菻”②這一名詞始見于《前涼錄》[1],而后在《隋書》《舊唐書》中,均有與古稱“大秦”混用的拂菻國的描述。
以時間順序從宋人文獻中記載拂菻的成書年代來看,較早的為北宋初期的《太平寰宇記》,其載:“大秦國一名犁鞬又名拂菻國,后漢時始通焉。其國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2]3515。仁宗時代成書的《新唐書》中所載:“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國。去京師四萬里,在苫西,北直突厥可薩部,西瀕海,有遲散城,東南接波斯。”[3]6260可見在北宋前中期,宋人對于拂菻位置的描述是比較統一的,認為拂菻就是先代所言的“大秦國”,其位置就在京師四萬里外的西海邊。但緊接著之后,宋人文獻之中對于拂菻的位置描寫便出現了分歧,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元豐年間的拂菻國進貢或者其他海外的消息流傳入宋。《宋會要輯稿》中提及“神宗元豐四年十月六日,拂菻國貢方物,大首領你廝都令廝孟判言,其國東南至滅力沙,北至大海,皆四十程”[4]9777,神宗時代龐元英《文昌雜錄》之中則載“其三曰拂菻,一名大秦,在西海之北”[5]。可見,神宗之后,拂菻國的位置出現了不同于前代“西海國”的記述。
在此之后的南宋以至于元初,對于拂菻國的記載則更加混亂。周去非的《嶺外代答》中無“拂菻”而只有“大秦”,在其記述中“(交趾西北的細蘭海)渡之而西,復有諸國。其南為古臨國,其北為大秦國、王舍城、天竺國。”[6]75周去非認為的大秦國位置同北宋初年的一致,也位于西邊大海的周邊。趙適汝的《諸蕃志》中,其目錄中也不存“拂菻國”,但在大秦國的條目中,卻引用唐代杜環的描述:“拂菻國在苫國西,亦名大秦。”[7]12元初的《文獻通考》之中,拂菻與大秦的條目則同時出現,其所載吸收了《宋會要輯稿》之中的“拂菻國南東至滅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東自西大食及于闐、回紇、達靼青唐,乃抵中國”[8]9397,又有前人描述“大秦一名犁靬,后漢時始通焉。其國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從條支西度海曲萬里,去長安蓋四萬里”[8]9377。對于拂菻與大秦同時出現并且地理記載不同的情況,馬端臨認為:“唐傳言其國西瀕大海,宋傳則言西至海尚三十程,而馀界亦齟齬不合。土產風俗亦不同,恐是其名偶同而非大秦也。今故以唐之拂菻附入大秦,而此拂菻自為一國云。”[8]9397可見由唐到宋,所記載的拂菻國位置發生了一些變化,即從圍繞著“西海”這一地理坐標向更遠的地方擴散。導致作者不敢將其歸為一國,但又因為宋之前史籍中確實又指出了拂菻與大秦為同一國家,所以馬端臨也只得把兩種記錄都采納于《文獻通考》之中。故由上述材料可知,實際上在宋人眼中,西方強國拂菻的位置是相對模糊的,“拂菻”與“大秦”應該是一個國家的認識在宋人之中也不絕對。在這里,西海這一地理意向起到了錨定的作用,所有關于拂菻國的地理描述基本都圍繞著西海周圍,且拂菻距離宋有四萬里左右。
(二)宋人想象中的拂菻位置與周邊環境
不同于上文所述的具體的位置描寫,較抽象的拂菻國位置敘述則是在景教僧人所作的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中所示:“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眾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9]186其說法模糊且浪漫,出現了“珊瑚海”“眾寶山”“仙境花林”與“長風弱水”等明顯不是具體地名的意向,這與此碑作者景教和唐僧人們有著密切的關系。夏德認為,這些拂菻僧人為更好的傳教而重新提及大秦國名[10],這暗合了中國古早史書之中的記述,方便其行動也增加了神秘感與知名度,同時還浪漫化了他們的所出生的土地。再加上從漢代以來對于大秦國多珍寶的描述,混同于一,對后世有著深刻的影響。宋人趙適汝的地理著作《諸蕃志》中就體現了對拂菻位置的浪漫描述:“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處,幾于日所入也。”[11]13宋人眼中的拂菻國究竟在什么地方至今也沒有一個明確的定論,雖然說法眾多,但由此可知的是,拂菻國確實是一個對于當時的宋人來說遙遠而神秘的國度,在極西且接近大海的日落之地。
在宋人的認知與想象中,拂菻確實為一個西方大國。時人給予其“西天諸國之都會,大食番商所萃之地也”[11]13的極高評價,并且其“小國役屬者數十”[8]9397,可見拂菻對周邊國家也有很大的影響。在其周邊的何國之中,“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畫拂菻諸國,東壁則畫突厥、婆羅門諸國王”[8]9350。也有當時宋人認為其是大國天竺國的宗主,“天竺國其(大秦)屬也”[6]95、“天竺國隸大秦國,所立國主,悉由大秦選擇”[11]13,雖今日也無見拂菻其控制佛教國家的其他說法,但可見其在宋人眼中的強大。史料也載“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8]9398這種見到來使便給予優待的政策與中原的朝貢貿易也有些許神似,展現了其大國風范。更加具有想象力的則是拂菻周邊“存在”的附庸西女國,“西女國,在蔥嶺之西。其俗與東女略同,種皆女子。多珍貨,附拂菻君長,歲遣男子配焉。俗產男子不舉。”[8]9391以今人之眼光來看,女兒國只是存于文學等奇幻故事之中,但受限于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周邊關系、交通條件、知識水平,宋人無法對各種傳說與記載作出有效的判斷。在趙適汝的記述中,稱西女國傳說的由來是“有一智者,夜盜船亡命得去,遂傳其事”[11]21。可是實際上有關拂菻派遣男丁去女兒國的記載在梁代《供職圖》中便存在,具體描述為“去波斯北一萬里西南海島有西女國,非印度攝,拂懔年別送男夫配焉”[12]。通過這些拂菻國附屬的西女國史料不難發現,對于這些超遠距離的域外國家,宋人對他們的認知是真實與想象雜糅在一起無法區分的。他們雖然可以認識到,那個從漢代發現的西方大國一直存在,而且影響著其周邊的很多國家。但是對其具體位置、其周邊國家的實際情況卻只有非常模糊的理解,其中還不乏很多當時人們的杜撰想象。可正是這些地理上的正史與故事、真實與想象交織在一起,才令我們得以窺見宋人對當時遙遠國度的看法。
二、宋人文獻中的拂菻國生活及物產
(一)城市居住環境
宋人對于拂菻這個國家的想象不僅體現在宏觀上強大的西域影響力,也體現在微觀上的精美高超的建筑器物,這些器物經過了多次的朝貢方物、使節敘述,再加上宋代拂菻國與宋并未形成連續的交往,其記載的“物”的意象很多與唐代相似,但充滿了西域國家的奇幻風情。首先是城市建筑,宋人有關其城市占地面積的記載見于《經行記》中“王城方八十里”[7]12,其城市不可謂不寬廣豪華,北宋都城汴京也只有“方圓四十馀里”,而舊京城更只有“方圓約二十里許”[13]19對于拂菻王宮“王宮有三襲門,皆飾異寶”[3]6260,“王所居舍,以水精為柱、以石灰代瓦,多設幃簾,四圍開七門,置守者各三十人。”[11]13其中較引人注意的是“水精柱”與“石灰為瓦”這兩個意象,《太平御覽》載“水精謂之石英”,同時指出其原產地,“水精出大秦、黃支國”[2]3593。水精也是珍貴的朝貢物品,如西域諸國向中原朝貢之時便進貢此物,“開元初獻鎖子甲、水精珠”[14]2815,“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水精盞,玻璃狀若酸棗”[14]2844。對于石灰,在宋人眼中,其是做瓦的材料,即“瓦作用純石灰[15]”。而這種無瓦卻直接用石灰為頂的建筑,在宋人的記述看來,也其并非簡陋,而是拂菻國民俗與建筑獨特的建造方式,這與《舊唐書》中對于拂菻國建筑的記載較為相似,且為一種較有技術含量的裝飾。不僅是王室,民間也亦是如此,“其俗無瓦,搗白石為末羅之涂屋上。其堅密光潤,還如玉石。”[16]同樣的《太平寰宇記》也載其民“無瓦,以白石塗屋上如白玉焉”[2]3515。像白玉的評價體現了宋人對其建筑技巧的稱贊,在記載周邊國家時,天竺國也受拂菻影響“所居以石灰代瓦,有城郭居民”[11]13。不同與其他國家的貧苦“官民悉編竹覆茅為屋,惟國王鐫石為室”[11]4,或“其人民散居城外,或作牌水居,鋪板覆茅”[11]5。也不同與強國大食王之奢華,且王與民貧富差距極大③。拂菻王宮除了水精柱外也與民居無大差別,拂菻王的建筑在精巧的同時十分可能也體現了其王室低調簡譜的特點,可能與宋人認知中的其佛教信仰相關。
除了以灰代瓦外,在拂菻人的屋頂之上還有兩種奇物。第一種為利用某種機械裝置汲水上房的機械裝置,可使水流沿房而下如瀑布。此記載可能最早出現于《舊唐書》,拂菻國人“乃引水潛流,上遍于屋宇[17]。而宋人也載拂菻人“至于盛暑,人歊煩,乃引水潛流上,遍于屋宇。機制巧密,人莫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檐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18]。可見這種裝置是安裝于屋頂之上的一種引水避暑裝置,其能讓水沿墻而上,并從房頂淋下降低房間溫度。這種裝置在唐宋皆出現過,名為自雨亭“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從檐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19]。說明在唐代,自雨亭屬于上層人士才能享受的奢華裝置。從宋代著名詞人秦觀《再賦流觴亭》中的詩句“仙山游觀甲寰瀛,不比人間自雨亭”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拂菻國這一機械裝置頗為贊賞,認為其能制造人間之仙境。而對于自雨亭這種中原存在但數量稀少的奇物,據宋人記載其遍布拂菻,可見在其國人能工巧匠眾多。第二種奇物為其城樓之上的黃金大鐘,此物也在宋人的著作中也被提及。“第二門之樓懸一大秤,以金丸十二枚屬于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于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有聲,金人即應聲引唱以記日,時毫厘無失。”[2]3516金人不知用何種礦石所制,但“其大如人”同時又可以“應聲引唱以記日時”,可見在宋人認知與想象之中,拂菻人建筑上有著獨特的風俗,且機巧玄妙眾多。
(二)豐富而獨特的物產
關于拂菻寶物眾多的描述史籍中屢見不鮮,早在三國時期便有記載④,宋時也載其有“土產琉璃、珊瑚、生金、花錦、縵布、紅馬腦、真珠”[6]95,“土多金銀,其寶夜光璧、明月珠、琥珀、琉璃、神龜、白馬、朱鬛、瑇瑁、元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瑪瑙”[2]3515,是名副其實的“重寶之鄉”。
而在其中,珊瑚便引起了宋人的特別關注,在宋代珊瑚的使用被看做是一件非常奢侈之事,英宗時期知太常禮院李育便奏言痛斥當時的奢靡之風,其中言道:“若魏明之用珊瑚,江左之用翡翠,侈靡衰播之馀,豈足為圣朝道哉!”[8]3464而正是這種中原王朝很少獲得的寶物,在拂菻國則可乘船用大鐵網直接從河中撈出,唐時的景教僧人就稱其國“南統珊瑚之海”[9]186,《新唐書》中便詳細地記述了拂菻人“種植”與采集珊瑚的過程,“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墮鐵網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三歲赤,枝格交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系網舶上,絞而出之,失時不敢即腐。”[3]6261而在《文獻通考》中,對種采珊瑚也有相近描述,而在種之前,還特別提到需要有人先潛入水下觀察有無珊瑚苗這一情況,“令水工沒,先入視之,可下網乃下”,在養殖階段則記錄了珊瑚頭年到第三年的變化,“初生白,而漸漸似苗坼甲,歷一歲許出網目間,變作黃色,支格交錯,高極三四尺,大者圍尺馀,三年色乃赤好。”[8]9398成語“鐵網珊瑚”便是出自拂菻人捕撈珊瑚的這一采集行為,比喻搜羅珍奇。
可見在宋代,人們對于拂菻寶物眾多的想象是持肯定態度的,而這種想象往往源于唐代的史籍記述,有明顯的繼承性,但是在《宋會要輯稿》當中,拂菻的物產則只有“產金、銀、珠、胡錦、牛、羊、馬、獨峰、杏、梨”這幾樣,而在其貢獻的方物之中,則只有“貢鞍馬、刀、劍、珠”[4]9777。考慮到宋代特別的政治形式與當時的地理環境,有記載的宋代拂菻來使的真實性也難以考證⑤,這也是馬端臨在對“大秦”與“拂菻”兩個條目之間是否真是一個國家產生的懷疑的原因之一。可以見得,這就和宋人整體對拂菻物產的認知與想象一樣,充滿著對當時史籍的描述信賴與對當時實際情況不符的矛盾。
三、拂菻人的生活和風俗文化
(一)拂菻人的相貌與服飾
相比于較為模糊的地理描述,宋代之前對于拂菻人的了解分為兩個明顯的階段。第一階段是東漢出使西域后,雖然沒有到達,但是帶回只言片語的信息,而這些信息在經歷數百年之后也變得更加符合當時人的邏輯范式。其描述始見三國時期曹魏郎中魚豢所作《魏略》⑥,《后漢書》中則提及其人相貌與其國名稱由來“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21]。在《晉書》中,大秦人穿著胡服與類似華夏相貌的記載也均被繼承。而在《魏書》之中則出現了“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外域謂之大秦”[22]的描述。可見在東漢到唐前,人們認為其國被取名“大秦”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其人長相與華夏相同且服飾禮儀可能同中國類似,并且在時人看來,戰國時期的強國秦在西方,故稱其為大秦。
第二階段始于唐代,隨著唐代大量佛教僧人不畏險阻前往西域求經,唐人對拂菻的認識又較之前有所變化。出現了不同于前代的描述,如“(拂懔國)境壤風俗同波刺斯,形貌語言稍有乖異[23]”,“男子翦發,披帔而右袒,婦人不開襟,錦為頭巾”[17],這些唐之后的史料認為拂菻人有著與鄰國波斯人大致相同的長相,而穿衣風格也非“類同中國”。這些觀點為宋人所接受,但也對其造成了困惑,在宋代對于拂菻的記述明顯的分為“拂菻”與“大秦”兩種。如《文獻通考》中記述的大秦國,依然沿用了前唐的大秦人長的類似漢人的看法⑦,而在其后的拂菻國則記述為“王服紅黃衣,以金線織絲布纏頭”,“貴人如王之服,或青綠、緋白、粉紅、紫褐,并纏頭跨馬”[8]9398,《宋會要輯稿》之中也有拂菻王“王服紅黃衣,以金線織絲布纏頭”、“首領皆如王之服,或青綠緋白、粉紅、褐紫,亦各纏頭”[4]9777的記載。同時也都并沒有對于拂菻人相貌身材的描寫,但從纏頭這一行為來看其應該是異于中原而更加傾向西域的文化。而在《諸蕃志》中的“大秦國”依然記載“其人長大美晰,頗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人,皆髦頭而衣文繡”[11]14。同樣以“大秦國”為條目的《太平寰宇記》也記載“十里一亭,三十里為一置,一如中土”[2]3515。由此可見,雖然在宋人眼中,雖然“大秦”與“拂菻”有時混用,但宋人對于“大秦”這一國家的認知更加趨向于這是一個有著漢人長相且帶有某種胡風的文明,甚至其國還存在“官曹”與“簿領”這些中原官職意象,而其名為“拂菻”時,這一國人的外貌認知則更像是域外的波斯諸國。
(二)拂菻人以農業為基礎的風俗文化
首先,對于宋人來說,拂菻應是一個有著農業文化的西域國家。《魏書》中便記載拂菻如中原一般“其土宜五谷桑麻,人務蠶田”[22],《文獻通考》雖無記述拂菻農業情況,但在記大食國時說“土多砂石,不堪耕種,無五榖,唯食駝、象等肉,破波斯、拂菻,始有米面”[8]9393。由此可見,在宋人眼中拂菻依然是農業國家,或種稻或種麥,也許兼而有之,而其作物產量高,國家富裕,“其谷常賤,國用富饒”[8]9378。故在宋人的記述中,拂菻人也有農耕民族的習俗,“多工巧,善織絡”[11]14。而織布的原料則來源于其本地奇羊“織水羊毛為布,曰海西布”[3]6261。這說明了他們同中原一樣有畜牧業,但是“地多獅子,遮害行旅,不百人持兵器偕行,易為所食”[11]14。這明顯是繼承了前代拂菻記述中多獅子的印象,為此,宋人認為其畜牧業需要筑圍墻保護,“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于土中,候其欲萌,筑墻護之,恐獸所食也,其臍與地連,割之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遂絕,逐水草,無群。”[8]9377所以在文獻中看來,拂菻依然是一個類似中原的農業國家,可能也有“男耕女織”的樣貌,有“臍與地連”的奇羊,但因為獅子猛獸多,故放牧十分兇險,需要圈養。
其次,對于拂菻國社會民俗的記述的內容較少,史料中只可窺見一二。在中原人看來,拂菻是一個娛樂活動發達的國度,拂菻舞蹈在宋人眼中評價便頗高:“裾翻莊蝶,翩翩獵蕙之風,來復來兮飛燕,去復去兮驚鴻。善睞睢盱,偃師之招周伎;輕軀動蕩,蔡姬之詟齊公。則有拂菻妖姿,西河別部,自與乎金石絲竹之聲,成文乎云韶咸夏之數。”[24]同時民間藝人技藝也相當高超,拂菻有能吐火的奇人是自三國時代便有的記述,《魏略》中載有“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20]860而在后世則將其取名為“幻人”,凸顯其奇特,《后漢書》中則有記載域外藩國進貢幻人,“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25]。盡管自后漢書后,再無進貢幻人的文獻記錄,同時對幻人的記載也逐漸變少,但唐人的《隋書》中卻記有“幻人吐火,千變萬化,曠古莫儔”[26]。至宋代,幻人已經不再只是口中吐火,成為了“能發火于顏,手為江湖,口幡眊舉,足墮珠玉”[3]6261的樣子,也有“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幡眊亂出”[8]9377的記載。
從開始的“口能吐火”到宋代“能額上為炎燼,手中作江湖”,其變化可能是宋代發達的民間娛樂,即瓦肆勾欄的發展所致。宋代中原民間便有許多民間藝人可表演吐火,他們“有假面披發,口吐狼牙煙火,如鬼神狀者上場”,同時更有甚者從事危險性極高的表演,每當有社火時,民間藝人們“殿前兩幡竿,高數十丈,左則京城所,右則修內司,搭材分占上竿呈藝解。或竿尖立橫木列于其上,裝神鬼,吐煙火,甚危險駭人,至夕而罷”[13]758。高超的宋代藝人表演使得時人對于異域的民間表演想象的要求也有所提高,從文獻中窺探異域表演的提升也恰恰反映了中原本土的民間表演藝術之進步。以上種種零碎的文獻記載拼湊了一個宋人認知與想象中經濟發達、娛樂繁多的農業國拂菻的社會文化圖景。
(三)拂菻人的政治與宗教信仰
對于其政治與宗教文化,古人對拂菻的認知與想象也呈現出明顯的兩階段,且以宋代為分界。宋前之人對拂菻的印象多是一個貴族共和制的國家,且一般沒有討論其宗教信仰,可能認為其為世俗國家。如早在三國時期的描述“其制度,公私宮室為重屋,旌旗擊鼓,白蓋小車,郵驛亭置如中國”,“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20],到唐代“有貴臣十二人共治國政,常使一人將囊隨王車,百姓有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還宮省發,理其枉直。其王無常人,簡賢者而立之。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17]。而到了宋代,雖然在宋初依然有如唐人大秦為世俗共和國的描述⑧。但隨著時間流逝,之后的宋人則認為其為是一個絕對的佛教國家。
對于“成為”了佛教國家的拂菻,拂菻王變成了一名宗教君主且再不可隨意罷黜,其“王少出,惟誦經禮佛,遇七日,即由地道往禮拜堂拜佛”[11]14,因為國王每日誦經念佛,固定的時間前往佛寺拜佛,所以“國人罕識王面”[6]95,拂菻君主充滿了宗教的神秘色彩。另有記載拂菻王參加其國家重要的佛教儀式“每歲遇三月入佛寺燒香,坐紅床,人升之”[4]9777,這與宋之前的認識大不相同。其次,拂菻作為一個宗教國家,其貨幣正面均為佛教意象,“以金銀為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名,背鑿國王名,禁私造”[4]9778,也有說法為“面鑿彌勒佛,皆為王名”[8]9398,這種說法更加的體現了宋人想象的其君主專制的特點。
另外,多部地理著作記載了拂菻為佛教大國天竺國的宗主,如“遠則大秦為西天竺諸國之都會”[6]74、“天竺國,隸大秦國,所立國主,悉由大秦選擇”[11]14。由此可見,在宋人的想象之中,拂菻徹底的變成了一個佛教國家,這種變化可能源于唐代對于西域的發現與了解。因為之前古人便認為拂菻可能為西方世界的一個強大中心,而佛教又是從西域傳入的,天竺是西邊的一個佛教大國,掌控它的國家自然而然也會是一個佛教國家。而宋代因為地理環境阻隔與南北對立的環境也使其注意力多放于北方,即“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虜”[27]。故對于西方的世界,其繼承并改造了唐人對于拂菻國的想象,使其成為了一個充滿佛教文化色彩的君主專制國家。
四、結語
葛兆光先生曾指出,雖然對于遠域國家的認識隨著古代王朝的對外交往變得越來越豐富,可這對于古代的文人、史官來說卻并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古典的歷史文獻依然是他們知識的重要來源,他們依然會選擇百年前,甚至更古早的記述原封不動的繼承。“提供異域知識的所謂‘古典’主要是古代的歷史著作,如《史記》《漢書》等對于異域的記載,常常是后來想象的基礎,而且這種記載以‘歷史’的名義享有‘真實’,以至于后人常常把這些本來記載于文史不分時代的文字,統統當做嚴謹的歷史事實。”[28]但通過宋人對遠域國家拂菻的描述,卻可發現事實并非完全如此。
在地理與周邊環境的記載中,宋人因為對西域的掌控較前代大幅減弱。一方面,拂菻的具體位置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在宋人文獻中變的模糊不清。他們也并沒有完全以史料為準,其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也對“拂菻”是否就是“大秦”產生了疑問。但另一方面,因為交通阻斷,許多前代的瑰麗想象,如西女國等,則被宋人文獻繼承了下來。
而在拂菻的工巧與物產中,唐代出現的,而非更古老的描寫則被宋人文獻廣泛記載。這可能與宋人較為相信四通八達時的唐人敘述,如自雨亭、“石灰代瓦”、“鐵網珊瑚”等。另外較前代不同是,其也出現了“拂菻”與“大秦”兩國物產不同之記載,其都為宋人呈現了一幅獨特的遠域國家景觀。
在對其國人的記載中,書有依循古人的“大秦人”時,其國人樣貌與制度則多有中原痕跡,這便沿襲了早于唐代時期人們對世界的理解。但宋人在記“拂菻人”時,其相貌則更加偏向當時的西域人。另外,在“幻人”的表演技能與拂菻國家的政治制度上,在進入宋代之后其文獻內容發生了許多變化,可見宋人對文獻的認知與想象是根據前代的文獻或實踐與本國認知的變化相疊加而成的。
總的來說,文獻之中的遠域國家的記載與同時期的繪畫有較大區別,是保有理性、不少贊美且盡量中正平和的論述。雖然文獻的記載有如葛兆光先生所指出之弊端,但宋人文獻中對超遠域外國家的想象有異于同時代的繪畫作品,圖畫多以朝貢圖的形式對域外國家之人進行描寫,其本質是通過域外遣使來貢凸顯中國之強大,是宋人“天下觀”的某種體現。而對于遠域國家的文獻中情形則不太相同。對于域外國家的富饒、器物之精致都有詳細的描寫,對不同國家的珍寶、工巧也有詳盡描述,這些域外大國是強大且自信的。另外,關于域外國家的文化描寫則頗具矛盾與趣味,同時加上來使夸張的敘述和坊間傳聞,對于宋人來說,拼湊出了一個既有繼承前代,又有本朝特色的超遠距離域外國家的想象與認識。
注釋:
①關于對宋代有關拂菻的繪畫的討論,林英的《唐代拂菻叢說》(中華書局,2006 年)第四章通過比較隋唐五代和北宋時期的拂菻圖指出,由于五代以后東西文化交流的衰退,中國畫史中的拂菻形象也完成了由實向虛的擅變,葛兆光《想象天下帝國——以(傳)李公麟<萬方職貢圖>為中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三期)對宋代人矛盾的天下觀與不同于歐美近代的民族主義雛形作了探討;林英(《唐代拂菻叢說》,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第185 頁。)對職貢圖的真實性作評價時說“筆下的拂菻沒有承載真實的地理知識,其成為遙遠而又神奇的西方世界的代名詞,是一個想象中的國度。”葛兆光(《想象天下帝國——以(傳)李公麟<萬方職貢圖>為中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三期)他認為李氏畫作象征著“中國在收縮的時代,卻想象自己在膨脹”,且“在有限制的‘國家’認知中,保存了無邊的‘帝國’想象。”對于拂菻位置的具體著述之猜想與考辨,今人著作有夏德《大秦國全錄》(大象出版社,2009 年)、林英《唐代拂菻叢說》(中華書局,2006 年)、張緒山《中國與拜占庭帝國關系研究》(中華書局,2012 年),期刊論文有張緒山《“拂菻”名稱語源研究述評》(《歷史研究》2009 年第5 期)、徐家玲《拜占庭還是塞爾柱人國家?:析<宋史·拂菻國傳>的一段記載》(《古代文明》2009 年第4 期)、武鵬《<宋史>中的拂菻國形象考辯》(《貴州社會科學》2014 年第5 期)等,其主要內容基本為對史籍中所載拂菻相關的錢幣、人名、地名、國名進行考證。故本文中所指的“想象與認知”為一個整體,其為宋人看待外部世界之方式。
②原文為宋代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卷758《器物部三》,“張軌時,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作奇狀,并人高,二枚。”
③《諸蕃志》,卷上《大食國》,第15 頁。其原文“其居以瑪瑙為柱,以綠甘為壁,以水晶為瓦,以碌石為磚,以活石為灰……民居屋宇,與中國同”。
④魏晉時代所記載物產則更為豐富,見《三國志》卷30《烏丸鮮卑東夷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第4 冊,第861頁)。其載有“大秦多金、銀、銅、鐵、鉛、錫、神龜、白馬、朱髦、駭雞犀、玳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瑪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虎珀、珊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流離”。可見其珍寶豐富。
⑤詳見張緒山《唐代以后所謂“拂菻”遣使中國考》(《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6 期)其認為《宋史》中“拂菻”為一個塞爾柱人國家。
⑥原文為《三國志》卷30《烏丸鮮卑東夷傳》,第4 冊,第858 頁。“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于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
⑦原文見《文獻通考》卷339《四裔考十六》,第14 冊,第9377 頁。原文為“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或曰本中國人也。”
⑧原文為《太平寰宇記》卷184《四夷十三》,第9 冊,第3515 頁。原文為“貴臣十二共理國事,其王無常人,簡賢者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