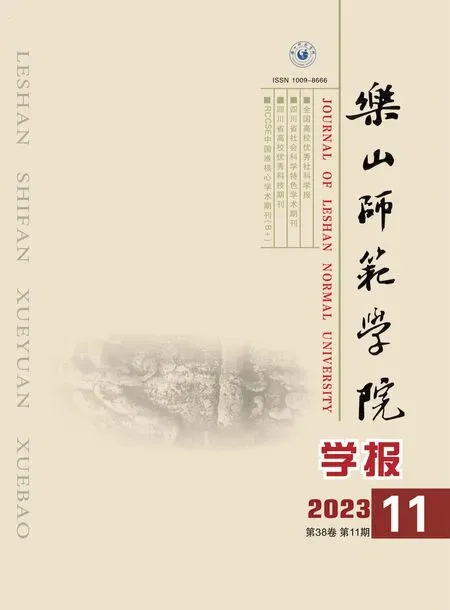《敦煌亡文輯校與研究》序
伏俊璉
(西華師范大學 文學院,四川 南充 637002)
悼念去世的同類,是諸多動物的本能。人對其親朋好友的離世,總是充滿悲悼之情。《詩經》中的《綠衣》,劉大白《白屋說詩》就認為是悼亡詩。“綠兮衣兮,綠衣黃里。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絺兮绤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詩中反復詠涵的是一件普通的“綠衣”,正是這件普通的衣服,勾起了他無限的傷感。因為這件綠衣,是他的愛妻曾經穿過的。現在物是人非,觸目傷心,“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潘岳《悼亡》),“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開”(元稹《遣悲懷》),只能一遍遍呼喚“曷維其已”?“曷維其亡”?還有《唐風》中的《葛生》:“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后,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后,歸于其室。”劉大白《白屋說詩》和聞一多《詩經通義》都認為這首詩是悼亡之作,先師郭晉稀先生《詩經蠡測》從之,并且補充了劉氏和聞氏的未密之處。這首詩真是哭著寫出來的,詩人站在愛人的墳前,看著荒草叢生的墳塋,想著他(她)孤獨地躺在地下,形單影只,五內崩裂,恍惚凝癡。春夏秋冬,日日夜夜,無盡的思念,“惟將終夜長開眼,報達平生未展眉”(元稹《遣悲懷》)。清人陳澧《讀詩日錄》曰:“此詩甚悲,讀之使人淚下。”
《列女傳》記錄的《柳下惠誄》是現存最早的誄辭:“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門人從之以為誄,莫能竄一字。”柳下惠是公元前七世紀中葉的人,這篇誄辭當產生在這個時代。誄辭先敘寫功德,次哀悼去世,再評價并給予謚號。這一三段體式奠定了后世的這一類文體的基本格式。大約一個半世紀后,魯哀公十六年(479)四月,孔子卒,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吊,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這篇誄辭完全是發自內心的自然話語:老天爺呀,你為什么這樣不仁,連一位老人也不放過,留下我孤孤單單一個人,誰來保護我呀!傷心呀,仲尼!沒有你,吾誰與歸!
先師郭晉稀先生在《古代祭文精華序》中寫道:“人世間最大的悲哀,莫過于生離死別。或則夫妻同室,一死一生,生者既衿幬冷清,死者更冢穴荒涼。或者手足情深,一存一亡,存者既雁行折序,亡者更孤骨埋魂。或子女祭父母,生者既哭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死者不復顧復提攜,浩然長逝。或父母吊夭殤,死者本幼未成德,生者則悲實依心,自然‘情往會悲,文來飲泣’。或以今人吊昔賢,如賈誼吊屈原,陸機吊魏武,死者既雄才抱恨,生者只好望古長嗟。更有為國從戎,槍林彈雨,舍命成仁;亦有救援不至,殺身取義。從古至今,死者既不可勝數,傷身之故又何可勝言。死者本情實可哀,生者遂悲從中來,作文吊唁。”所以,天下的文章,“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詞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韓愈《荊潭唱和詩序》)。南朝梁蕭統《昭明文選》中,就有“誄”“哀”“吊”“祭”四類作品,宋人《文苑英華》中有“謚哀冊文”“謚議”“誄”“碑”“志”“墓表”“行狀”“祭文”等類,明人《文章辨體》和《文體明辨》列有“誄辭”“哀辭”“祭文”“吊文”四類,下及清姚鼐《古文辭類纂》、曾國藩《經史百家雜抄》專列有“哀祭類”作品。“哀祭類”是中國文章中最富有真情的文類。
哀悼類作品的發達,與古代繁富的悼祭儀式關系密切。《儀禮》十七篇,而有關哀祭者即達七篇之多。《禮記·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經,莫重于祭。”“五禮”(吉、兇、軍、賓、嘉)貫穿在喪葬、祭祀、加冠、結婚、朝會等各種活動中。古人認為天地、宗廟、神祇關系到國運之興盛,宗族之延續,故祭祀之禮排列在五經之首,程序很多。如剛剛去世的士人,就有招魂、哭喪、告喪、洗尸、飯含、易服、送魂、停殯、修墓、入殮、吊唁、出殯、下葬、喪服、守孝、掃墓、祭祖等儀節,每一個儀節就有相關的致哀之辭。
然而我們現在看到的祭悼儀式和祭悼文辭,幾乎都是貴族文人層面的。而下層老百姓的祭祀形式、祭祀文辭,流傳下來的很少。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唐五代宋初的寫本,有數量不少的祭文、亡文,內容都是悼念死者的。過去這類文章的匯集校錄比較零散,現在作者把它們全部匯集起來并加以校注和研究。關于祭文,作者在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結題成果《敦煌喪葬文書輯注》(巴蜀書社,2017 年)一書中已經加以輯錄整理,共得包括書儀祭文和實用祭文文鈔在內的150 余篇。亡文的數量更加可觀,有170 多個寫本,加之《為亡人舍施疏》等40 多個寫本,數量在200 個以上,近700篇。根據這些寫本,作者完成了60 余萬字的書稿《敦煌亡文輯校》,并于2019 年獲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立項,2023 年撰成《敦煌亡文輯校與研究》(上下冊),并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該書上冊為“輯校篇”,作者在充分吸收前輩學者校勘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新輯錄亡文400余篇,并以寫本為底本對這些亡文進行了詳細校錄。這些整理好的亡文為認識和研究中古時期我國民間的悼亡祭祀活動和相關應用文的使用情況,提供了非常珍貴的原始材料。與過去學術界對敦煌亡文的輯錄和校勘相比,敦煌亡文輯校更關注寫本的整體,在這方面也做了有益的探討,這是值得稱道的。一個寫本,它上面可能抄寫了體裁、內容不同的文本,這些文本之間是有關聯的。通過認真閱讀,揭示它們之間的關系,探討寫本制作者的用意,這是寫本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有些寫本的內容是分時段抄錄的,抄寫的人也不同,各自間的確很難說有聯系。但有一些寫本從字跡判斷就是一個人抄寫的,內容各式各樣。那么,寫本制作者為什么要把很多不同的內容抄錄在一個寫本上呢?如果回到當時的情境,這個寫本可能就是一個齋會的司儀平時準備的備忘錄。還有一些寫本,我們綜合其上抄寫的不同體裁的文本,可以恢復一個動態的立體的儀式過程。例如本書中《敦煌喪儀中的“勸孝”》一文就是專門探討這個問題的,作者注意到敦煌寫本中有祭文、亡文等復雜多樣的應用文獻夾雜佛教歌曲、俗講、變文等講唱文學作品的現象,而這類現象可能與敦煌寺院入破歷中反復出現的一項“勸孝”活動收支記錄密切相關。
1925 年,著名學者劉復先生整理出版了他在法國抄錄的104 種各類文本,名曰《敦煌掇瑣》,《前言》中他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書名叫掇瑣,因為書中所收,都是零零碎碎的小東西,但這個小字,只是依著向來沿襲的說法說,并不是用了科學的方法估定的。譬如有兩個寫本,一本寫的是《尚書》,一本寫的是幾首小唱,照著向來沿襲的說法,《尚書》當然比小唱重要到百倍以上,《尚書》當然是大的,小唱當然是小的。但切實一研究,一個古《尚書》,至多只能幫助我們在經解上得到一些小發明,幾首小唱,卻也許能使我們在一時代的社會上、民俗上、文學上、語言上得到不少的新見解。如此看所謂大小,豈不是適得其反。”根據散存的敦煌亡文寫本,作者發現,始死、舉發、臨壙、七七、百日、一周(小祥)、二周(中祥)、三周(大祥)、忌日、遷葬、招魂等喪葬場合均有設齋延請僧道,以追悼亡者,并為生者祈福的儀式。而這些儀式上均有宣讀亡文的環節。敦煌的亡文中,雖然沒有韓愈的《祭十二郎文》、歐陽修的《祭石曼卿文》那樣的大文章,但它們卻是當時老百姓生活中運用的文辭,我們通過這些亡文,可以了解當時唐五代宋初西北地區普通人的生活、知識、信仰、語言。而這些亡文寫本,更是一個個鮮活的祭悼儀式的生動呈現。
除注重寫本形態的描述,探討寫本各種文獻之間的關系之外,“輯校篇”在字詞考證方面亦頗見功夫。除綜合運用音韻、文字及與傳世文獻互證等方面的知識和方法之外,本書還綜合考慮抄手書法、書寫習慣等,以便對寫本中存在的疑難字詞作出更加客觀合理的推斷。如《臨壙文》中,“卜(或“擇”)善(或“勝”)地以安墳,選××而置墓”是一慣用句式,共有13 件不同寫本使用了這種句式,而其中“××”一詞,出現了兩種寫法,一是“吉祥”,二是“吉晨”。寫為“吉祥”者,如S.5573《臨曠(壙)文》:“遂能卜善地以安墳,選吉祥而置墓”、S.6417《臨曠(壙)文》:“于是擇勝地以安墳,選吉祥而至(置)墓”,其他的如P.3765、Φ.263、P.2483、P.2991V、P.4694V、Φ.263+Φ.326V、北圖“藏”字026V(7133)等寫本中的《臨壙文》亦寫為“吉祥”。寫為“吉晨”者,S.5957《臨曠(壙)文》、S.6417《臨曠(壙)文(二)》兩件均寫作:“遂以卜勝地以安墳,選吉晨而置墓。”“吉祥”“吉晨”兩種寫法都正確,還是其中一種寫法是錯誤的,以往的一些校錄研究未加區分,本書明確指出“吉祥”誤,“吉晨”是。首先,作者從語法結構、詞語搭配的角度論證了“選吉祥”之誤,“選吉晨”之確;進而以《臨壙文》近義語段“選此吉晨”“揀擇良日”等印證了“選吉晨”之確;最后從抄手書寫習慣和近音誤讀的角度討論了寫本誤“晨”為“祥”的兩種可能:
“祥”為“神”之筆誤,而“神”乃“晨”之音誤。敦煌愿文中“晨”或“辰”屢見寫為“神”者,如P.2237《安散(傘)文》:“今燭(屬)三春影月,四序初神(辰)”,同卷《燃燈文》:“乃于新年啟正之日,初春上月諸神(辰)”。P.2237V《亡兄苐(弟)》“故于此晨”之“晨”原卷即先誤寫為“神”,后旁改為“晨”。蓋抄手由“辰”而誤為音近字“神”,進而承“吉”而筆誤為“祥”而已。
“祥”為“長”之音誤,而“長”為“辰”之形誤,即抄手誤以“辰”為“長”,進而受其前“吉”字之連累,寫為音近誤字“祥”。“祥”寫為“長”者,如S.6417《燃燈文》(擬):“次為己躬寶壽延祥(長),合宅吉慶之福會也。”
以上推論是合理的。
《敦煌亡文輯校與研究》下冊“研究篇”,作者對亡文做了諸多的理論方面的探討:從寫本出發,對亡文的定名和分類做了詳細的梳理和闡發,進一步厘清了亡文和祭文的區別與聯系,對亡文的結構和亡文結構與祭祀儀式之間的關系有了更明確的認識;從亡文文范制作和亡文文稿撰寫的角度分析了敦煌亡文編選撰寫的全面實用性和開放靈活性;從儀式推進、倫理教化、生命關懷、世俗祈愿等方面闡釋了亡文的佛教實踐功能;以講唱文學和民間應用文的視角,從模式化創作與簡便實用、駢儷文風與至情至性、結構嚴謹與藝術張力三個方面,概括了亡文的創作特色;結合敦煌地區亡文的應用情況,從口耳相傳的儀式文學與民間抄寫的角度,審視了寫本中的借音字的類型、成因,以及對借音字的處理問題,等等。這些研究工作都是很有意義,也很有啟發性的。比如作者對敦煌亡文藝術性有深切的關注和獨特的認識。敦煌亡文模式化創作的特征非常明顯,這既是佛教文體儀式化發展的結果,也是當時佛教世俗化加劇的現實表現。但程式化、批量的生產和加工并不能完全掩蓋敦煌亡文至情至性的一面。亡文中不僅具有傳統祭文所特有的的“哀傷情重”的特點,還具有佛教應用文體所特有的“凄美華麗”的風格。有的直抒胸臆,呼天搶地。“所以母思玉質,斷五內而哀悲;父憶花容,叫肝腸而寸絕”(S.343《亡女文》)寫出了父母撕心裂肺的喪子之痛。“至孝等自云福(禍)愆靈祐,舋隔慈襟。俯寒泉以窮哀,踐霜露而增感。色養之禮,攀拱木而無追;顧復之恩,仰慈尊而啟福”(P.3562《亡考(一)》)道出了子欲養而親不待的無奈和悲痛。有的委婉曲折,寓情于景,更顯悲戚色調。“隴樹茫茫兮,白楊衰草;窗前寂寂兮,明月空堂。趍庭而魄散魂消,陟屺而槿枯蘭謝。遂使哀孝等痛乖嚴訓,恨隔母儀。醴泉涌而血淚難干,猿啼午夜;玄寢歸而靈筵空在,霧淹九泉。”(P.3981《亡妣》)茫茫隴樹、衰微白楊、稀疏草地、空堂明月,以形色營造悲涼;猿啼午夜、霧淹九泉,以聲貌訴哀,與至孝的哀情交相呼應。“秋風而橘樹含霜,鯉庭香墜;夜月而蘭花泛露,岱岳魂飛。”(P.3981《亡考》、P.2820《亡考》)、“愁云幕幕(暮暮),悲風樹之難期;若(苦)霧蒼蒼,恨嚙指之何日。”(S.5639+S.5640,S.530V《亡妣文》)“橘樹含霜”“蘭花泛露”“岱岳魂飛”“愁云悲風樹”“苦霧恨嚙指”,都將景物擬人化,展現出恨之深、悲之切,這都是借以抒發追福之人的哀切情感。亡文還能和“唱導”融合在一起,于“號頭”或“齋意”等結構段落處吟誦齊言韻詩。P.2044V《亡文》(擬)的“號頭”“修矩(短)之分,鬼神無改易之期;否泰之時,真俗有嘆傷之典。苗而不秀,宣交(父)之格言;林茂風摧,先儒之往教。歷觀前使(史),何代無斯者焉!”前插入了一首七言律詩:
稽首金容相好前,淥煙起處睹飛仙。
祥云了繞空中結,五天羅漢降清筵。
鄭重玉毫生福惠,眾人莫鬧片時間。
跪悉(膝)捧爐生帝(諦)信,疏文具載說來看。
詩歌前兩聯描摹出齋會現場之熱鬧情形,后兩聯勸眾人莫吵鬧,靜心傾聽宣誦亡文。這可以算是亡文誦讀開始前的一篇“押座詩”。再如P.3163V《陽都衙齋文》“齋意”部分這樣寫道:
比望長居人世,與彭祖齊年;何期命謝丹霄,魂魄歸于逝水。謹課芭(蕪)詞,乃為誦曰:
雁行悲失序,□(鶴)林折一支(只)。
手足今朝斷,賢兄何日期?
小弟肝腸烈(裂),兒女哭聲齊。
傍人皆泣淚,□(鄰)舍少衣恓(依棲)。
可見,亡文的制作除了引導亡齋儀式進行之外,用至美至情的言辭來表達活著的人對逝者的深深的悼念追福、對在世者的殷切祈愿,從而達到與神溝通且引導眾生往生極樂的目的才是其核心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