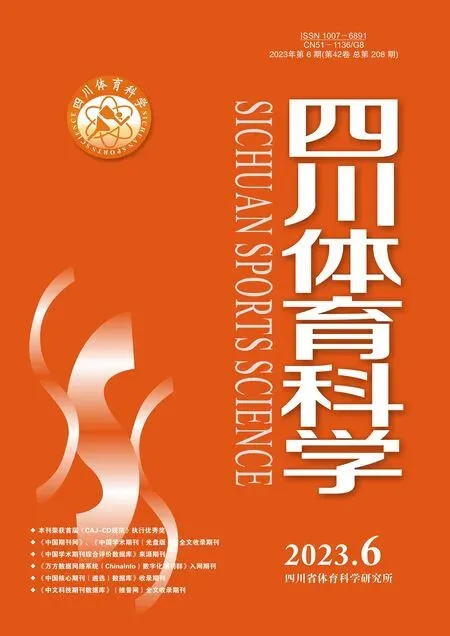遺忘與回歸:阿細跳月的具身性分析
汪超偉,萬 義
遺忘與回歸:阿細跳月的具身性分析
汪超偉1,萬 義2
吉首大學體育科學學院,湖南 吉首,416000。
本研究基于身體現象學理論借用文獻資料法、田野工作法等方法對阿細跳月進行具身性研究并得出結論。研究的主要價值在于,國內學者對阿細跳月的研究重點在它的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等方面,遺忘了身體的重要性;研究發現律動性是阿細跳月與身體交流的結果,實用性阿細跳月與身體圖式交融的體現,社會性阿細跳月與身體交往的呈現,聯動性是阿細跳月與具身模擬交涉的再現。最后,隨著人們身體認識的不斷加深,具身性這個視角必然會在體育研究中掀起一股浪潮。
阿細跳月;離身性;具身性;身體現象學
1 被遺忘的身體-阿細跳月的離身性分析
中國古代哲學一直都是一種以身體為主的哲學,身體始終都在中國哲人研究的中心[1],如孟子曰“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餓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再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王夫之曰:“身而道在”。這些無一不為其印證。不過在西方哲人眼里,身體和靈魂是對立的,柏拉圖更是直言:“我們如果想接近知識和真理,必須遠離肉體,因為肉體充滿貪欲玷污了靈魂”,這個時候身體和靈魂還是混合在一起,只是靈魂的地位更高而已,因為身體的存在會使靈魂墮落。真正使身體被遺忘的始作俑者是,近代以來的認識論哲學把身體看作純粹的物質性,它與心靈和靈魂的地位無法相提并論[2],身體變成了物質的范疇,被人們所遺忘。
“身體被遺忘的原因肇始于西方傳統哲學崇尚理性的思維方式”[2],我國學界也是沿用西方傳統哲學的理性思維方式進行科學研究。即使在體育界學者在對民族傳統體育進行研究時,往往避開它作為民族傳統體育對身心健康發展的有益影響,把研究重心放在文化價值和經濟效益,比如有學者在對“阿細跳月”進行研究時認為“由文化心理建構實現民俗體育在社會變遷中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3],過分強調文化在民俗體育發展作用,忽視了人的身心感受也是民俗體育發展的重要原因。同樣我國學者在對于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評審中也是過多考量它的社會價值、文化價值、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4],而忽略了它作為一種體育項目最本質的效用,體育是一種以身體運動為基本手段促進身心發展的文化活動[5]。這種忽視人本身的社會價值、文化價值等的研究是一種離身的研究。身體現象學強調返回事物本身,意思就是在民族傳統體育研究過程中返回到參與者在參與民族體育運動過程中最直接的、原初的體驗。
海德格爾認為,我們周遭的事物是作為“用具”為我們所感知,對體育項目的感知也是一樣的,在它因能帶來人們歡樂而被感知,并不是因為它的文化價值。比如我們要對阿細跳月進行認識,要主動參與其中,跟著節奏跳起來,切身感受它的律動,而不只是從理性的角度思考它的社會價值、文化價值、經濟效益。梅洛-龐蒂認為我們是以身體為基礎認識世界的,因此我們在思考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時,也應該“讓身體活動回歸它應有的位置,重構體育生存的發展和基點”[6]。民族體育的研究應該關注身體,用具身的觀點重構體育運動的價值和意義,用身體去認識世界感知世界的變化。
2 本體回歸——阿細跳月的具身性分析
1942年的一個夜晚,天氣也許是晴朗的,有一群人闖進了大山深處,被一簇火光和旋律吸引,追尋著光和樂的痕跡緩緩地走過去愈走愈近,歡快的調子越發的清晰,當他們臨近時看到一群身著民族服飾的少男少女們,伴著歡快調子盡情的舞蹈,這群人被這場景深深地扣在了原地,沉了進去。“舞是生命情調最直接、最實質、最強烈、最單純而又最充足的表現”[7],它以節奏和舞姿動員生命、表現生命、強調生命。這群人就是以聞一多先生為首的采風隊,這支舞蹈就是后來聞名遐邇的阿細跳月。阿細跳月通過聞一多先生帶出大山后為世人所關注,所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以律動性為出發點,以身體現象學理論為立論依據,分析阿細跳月與身心的關系。
2.1 律動性是阿細跳月與身體交流的結果
舞是生命情調最直接、……的表現。宇宙的本質是運動,生命的本質也是動,舞蹈的本質更是有節奏、有位點動[7]。阿細跳月正是這樣的一種節奏的動,它的基本動作是向前跑三步,然后停兩拍再向前一抬腳,同時拍手就地跳轉[8]。阿細跳月的律動性實現了人與舞蹈和諧發展的有節奏的動[7]。舞蹈通過身體表現生命機能,表現優美,表達愉悅。阿細跳月正是憑借這種律動性,所以才會讓阿細人如此著迷,以至于“大三弦一響,腳底板就癢”“活著不跳樂,白在世上活”。聽到音樂的節奏,身體自然而然的就帶到那個舞蹈的世界中,身體嵌入環境與環境相融合,這是一種生命的表演,音樂響起生命情緒異常興奮,阿細人需要阿細跳月來釋放他、宣泄它。
吉布森在吸收海德格爾“用具”思想提出來了動允性,它指的是行動的機會或行動的可能性同時它又是一種關系屬性[9-10],它是律動性把人、音樂、舞蹈三者聯系在一起的可能性和機會。動允性解釋了律動性為什么能讓阿細人在跳月的過程中著迷。換言之,不具備阿細文化的人參與“阿細跳月”時也能著迷,當然我們不能忽視文化背景對人的影響,除了文化背景之外,周遭的環境對人也是巨大的,具身認知學者人,大腦嵌入身體嵌入環境三者融為一體,認知是具身的。動允性是生命有機體與生存環境之間的互補與互動的整體關系,它既不屬于物理范疇,又不屬于精神范疇,但它又客觀存在,可以感知到,使生命有機體的行為成為可能性,即它能為我做什么,怎樣為我做。它能為我們做什么呢?它能使阿細人伴著大三弦的樂聲開心的舞蹈。
2.2 實用性是阿細跳月與身體圖式交融的體現
梅洛-龐蒂認為身體圖式是身體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和對身體姿態的整體感悟[11],這說明身體圖式是身體對世界感知的基礎。“舞人的身體是活動的雕刻”[7],在跳月的過程中身體圖式幫助舞者整合對舞的知覺,協調各個感官,使其根據節奏齊同律動。
阿細跳月是阿細人在祭祀密枝神儀式中最為重要的一環。在祭祀儀式中,三弦樂響起阿細人在畢摩的帶領下跳月,通過跳月來表達對神靈和祖先的尊敬,祈求來年的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它其實就是一種對生命機能的總動員,是一場生命機能的表演。可以設想一下當時的情形,三弦樂響起阿細人身處祭祀最重要的一環,情緒是緊張的、興奮的,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壓迫,他們需要一種暢快的、劇烈的、有節奏的動,來釋放它、宣泄它、緩和它,“情緒產生于大腦、身體和環境的互動與耦合之中”[12]。身體圖式為舞者們提供他們的身體的某一部分在做某一動作時,其他身體部分的位置變化的信息[11]136,使他們的情緒在舞動中得到釋放和宣泄。在律動的過程中,阿細人做到了祭祀神靈的同時,也使整個身心得到了發展。
阿細跳月同時也是阿細民族得以延續的重要手段,在傳統社會里阿細跳月是阿細男女青年交際的重要媒介,他們會在跳月過程中尋找自己的心儀伴侶,然后變換隊形男女對舞[13]。阿細男青年們要抱著重達4-5kg的大三弦伴奏跳月,有時會累的滿頭大汗,但仍然盡情舞蹈。通過自己男人的陽剛之氣和嫻熟的舞蹈來吸引心儀的姑娘,這是力與火之歌。阿細跳月的舞步很簡單,但正因為簡單才包含無限的復雜。異性看到自己跳月時,異性自身的相似活動的身體圖式也會被喚醒,會瞬間明白自己的意圖,此時舞蹈是一種表達愛意的身體語言。它能在這個曖昧的過程中,將外部環境和雙方內部環境中的重要因素整合入自身的組織中[14],使雙方迅速接受到彼此的求愛信息,幫助男女雙方確定關系,也使民族得以更好地延續。
隨著時代的發展,阿細跳月的祭祀性功能逐漸式微,男女青年交往的媒介作用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它為阿細族人帶來的經濟效益的功能。精通阿細跳月的老人對阿細跳月進行編排和改編,然后再教授給族人,學會跳月的族人通過旅游管理公司從事舞蹈表演增加收入,現在的阿細跳月與傳統相比雖然形式有所改變,但是其中的文化內涵沒有變化[15]。表達最原始生命機能的動,并沒有因為商業化而改變和減弱。此時,阿細跳月的主題更多的是賡續民族傳統,增加民族收入。此時的表演除了對神的獻技之外,增加了娛人的效果,更能體現阿細跳月作為一種傳統民族體育活動的綜合性,在發展中進行活態傳承。自從意大利神經學家發現了鏡像神經元系統后,為認知的具身性提供了神經科學證據,不具備阿細文化背景的人在觀賞阿細跳月的過程中,體會到舞蹈帶來的歡快是因為我們大腦中的鏡像神經元再起作用,我們的身體圖式能通過舞者的肢體動作,來理解阿細人的故事和阿細人的文化,以及阿細人奔放開朗的性格。身體圖式是一種完形是在感知世界中對身體的整體感悟,而不僅僅是在體驗中建立的單純的結果。很多專家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提倡去商業化,但阿細跳月的商業化改進中,除了增加了阿細人的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使更多的人了解了阿細跳月,使觀者體驗到生命的真實感,這也是阿細跳月的意義所在。
2.3 社會性是阿細跳月與身體交往的呈現
大三弦響起,或由作為舞者自己身體的跳動而直接經驗,亦或由沉浸在三弦樂和舞蹈共同營造的環境中受到感染的觀者的間接經驗,都會有一種我作為自己的肉體而活著的感覺,從而得到一種滿足。但這種滿足感還算不得是極致的感覺,極致的感覺是自己和大家一起活著。我們的活,有“他人”的存在。“當我呈現給他人時,我必須是外部的,他人的身體也必須是另一個他自身”[16],我們自身與他人的活彼此印證,相互支持,互為補充。這會使得每一個人的活都是真實的、穩固的,這樣的滿足才是最極致的滿足。使整個社會群體和諧的生活,便是阿細跳月的社會功能的最高意義,而當前阿細跳月最高的社會功能便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由和諧意識而發展和延伸的一種民族團結和社會秩序便成了社會功能性作用。關于這個功效聞一多先生講的最好,“跳蹈中,他們在完全統一的社會態度下,舞群的感覺和動作正像一個完全的統一體”[7]。在西方把舞分成兩種分別是操練和模擬,有些人認為模擬是指的模擬技巧本身,而通過舞蹈過程中統一的社會感知力,可以得出模擬是模擬其中逼真相容的情緒,情緒本身又是產生與大腦、身體和環境的互動與耦合之中。
阿細跳月的起源很多說法,有“撲火說”也有“祭火說”,還有祭祀密枝神的火崇拜說等等[17][18][15]。對于它的起源我們暫且不做真正的界定,可以明白一點,無論是哪一種起源,阿細跳月都是阿細族人在一種動機和一種情緒的驅使下為了達到一定目的而進行的活動。而情緒又是一種積極的行動傾向,是在理解環境意義基礎上的具身行動[9]。三弦樂響起的那一剎那,舞者的身心便被帶到先祖生活的那個時代,去追尋阿細文化形成的根基。任何一個高級文化的形成都是以社會各個成分的一致有序的合作為基礎的[7],阿細先民正是以阿細跳月來訓練這種合作。這是阿細跳月作為一種舞蹈發揮的最為實際的社會功能,是人們在舞蹈的過程中,達到一種潛移默化的合作訓練,這種合作的意識更像一種與生俱來的感覺,在無形之中就加深了彼此理解與情感,動作的意義往往不是呈現出來的,而是被理解的,也就是被他人的行為的重新把握[11]。因為彼此相知,我們往往就能從彼此行為之中感到善意,阿細跳月正是一種能營造融洽氛圍和友好環境的舞蹈,這也許正是它能一直被阿細族人傳承至今的重要原因。團結協作、頑強拼搏,一直以來都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阿細跳月在無形之中一直都在訓練阿細人民這些優良的品格,也正是具備這些品格,才使得阿細人民無論在多么艱苦的環境都能保持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身隨心動,阿細跳月正是通過表達活著的極致滿足感和維持民族團結與潛移默化訓練阿細人協作的社會性來保障彝族阿細支脈的賡續發展。
2.4 聯動性是阿細跳月與具身模擬交涉的再現
當我們買了一袋蘋果走在路上,遇到一個小朋友直勾勾的看著袋子里的蘋果,我們可能會下意識的從袋子里拿一個遞給他。我們為什么能理解小朋友的意圖呢?按照具身模擬的觀點,我們可以根據自身的動作方式去理解他人行為的意圖。就好像在傳統社會里,阿細男女青年會通過跳月進行交流,并確定關系。他們也是通過彼此的行為來理解彼此的意圖。
具身模擬理論認為,我們在理解他人的行為時,是把自己的行為與他人的行為進行匹配,從而理解他人的目的。當阿細族人拿出大三弦時,族人早已心領神會,他們在意識深處就開始了跳月的準備,因為我們在理解他人的動作時除了對自身行為進行匹配之外,還會把他人的行為看成有行為意圖的[19],三弦樂一響舞者們就已經預設到了結果,具身模擬除了具有行動模擬之外還具有預期的作用[20]。比如在傳統年代阿細男女青年會在載歌載舞中尋找心意的對象,一旦找到他們便會變換隊形男女對舞,阿細男女青年通過舞步來判定自己心儀的對象是否鐘意自己,這樣方便自己進行下一步的行為,在具身模擬看來人們每一個行為都是在前一個行為的基礎上發生的[19]。
阿細跳月也是一種戰前動員舞,戰爭發生之前,通過跳月來激發和鼓舞戰士們的士氣,人們在面臨比較熟悉的事物時能更快的激活鏡像神經元,阿細族人從小就在家庭的熏陶下接觸阿細跳月,因此在那個情況下跳月最能激發勇士們的熱血,戰爭來臨前的壓迫感劇烈的、集中的,他們需要一場更加劇烈和集中的運動來釋放它,舞者們一方面通過跳月來釋放風雨欲來的壓迫感,另一方面通過跳月來激發和調動勇士們保家衛族的勇氣。舞者們和勇士們以及普通阿細族人正是通過跳月這一活動,心與心彼此相交同仇敵愾。勇士和普通族人雖然沒有直接參與跳月,但是大腦中鏡像神經元已經感知到了舞者們的行動,他們的身和心已經在這一場戰前舞中融為一體了,它把生命完全動員了起來。
3 從身體遺忘到回歸本體:阿細跳月研究的必然選擇和時代要求
現象學一直強調返回事物的本身,意味著阿細跳月的研究,要圍繞它原初性、本質性進行探討,任海學者也強調讓身體運動回歸到他應有的位置,重構體育生存和發展的基點[6]。讓身體運動回歸阿細跳月的本位,因為只有動起來我們才能真正領略阿細跳月的風采。生命機能的本質是動,阿細跳月是一種有節奏的動,千百年來它承載了歷代阿細先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對惡劣環境的反抗。這些內涵只有通過沉浸式參與才能真正的理解并傳承,只作壁上觀是不可能了解它的真意,更不可能理解大三弦一響腳底板發癢的真諦。有學者建議通過教育手段把阿細跳月編排成課間操的形式進行推廣[21],這是一種值得肯定的推廣形式,但這種推廣阿細跳月最初的文化內涵又留下幾分?我們批判阿細跳月的離身研究,強調身體的重要性,所意指的不僅僅是阿細跳月,而是整個民族傳統體育研究,民族傳統體育盡管具有豐富的文化價值、社會價值,但這些項目的本質要為人服務,它們存在的目的是,一切為了人、發展人、完善人。我們對它們的探討應該以身體為主,返回身體本身,探究它們如何能作用人的身體,就像詹姆斯?吉布森所說的那樣,它能讓我做什么,怎么為我所用。
21世紀的時代主題是以人為本,以人為出發點,樹立以人文為本的價值取向,為了遏制慢性流行病,滿足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的需求,體育全面融入生活勢在必行[22]。如何把體育全面融入生活,其中一個重要手段就是體育研究對象回歸身體本體,民族傳統體育的研究要以人為本,人的發展是體育研究最永恒的話題。阿細跳月的研究也要以人為本,強調它的人為性和為人性,回歸到人本身是阿細跳月研究進程的必然選擇也符合時代的要求,我們不能否認阿細跳月的離身性研究取得的成就,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當前阿細跳月離身性研究的不足,以及如何挖掘符合時代發展的阿細跳月的身體意義。
4 結 語
在上文中,我們追溯到身體被遺忘被忽略的歷史。隨著現象學的興起,經過一批又一批的現象學家的努力,人們逐漸認識到身體在認識世界的重要性,從而有助于我們重新審視體育運動的意義。現象學強調身體的主體作用,人們的一切行為都是身體在感知、身體在說活、身體在思維。我們從身體現象學的角度去思考阿細跳月時就會發現,身體是阿細跳月律動性的實現方式,阿細跳月的文化功能、聯結功能、經濟功能都是為身體服務的,只有人的身體才能實現它成就它。雖然現在國內體育學者對身體現象學的關注度不是很高,但已有學者在武術研究和學校體育研究中運用身體視角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23-24]。21世紀是以人為本的時代,在不久的將來體育界一定會掀起一場關于身體哲學、具身性研究的浪潮。
[1]張再林.作為“身體哲學”的中國古代哲學[J].人文雜志,2005,(02):28~31.
[2]毛華威.梅洛—龐蒂身體現象學研究[D].吉林大學,2019.
[3]唐艷華,劉文沃,NI Yi-ke.“國家在場”:“阿細跳月”傳承中的文化心理建構[J].廣州體育學院學報,2020,40(01):75~78+95.
[4]王書彥,韋啟旺,張英建,等.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認定制度探析[J].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14,48(12):23~27+36.
[5]楊文軒,陳 霆.體育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6]任 海.身體素養:一個統領當代體育改革與發展的理念[J].體育科學,2018,38(03):3~11.
[7]聞一多.神話與詩[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114.
[8]徐麗華.云南彝族舞蹈與民間傳說[J].大舞臺,2012:107~111.
[9]葉浩生.身體的意義:從現象學的視角看體育運動的認識論價值[J].體育科學,2021,41(01):83~88.
[10]蘇佳佳,任 俊.關系屬性:動允性概念的方法論蘊含[J].心理學探新,2021,41(03):214~218.
[11]莫里斯?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M].姜志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137~138.
[12]葉浩生,蘇佳佳,蘇得權.身體的意義:生成論視域下的情緒理論[J].心理學報,2021,53(12):1393~1404.
[13]李先國.論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的變遷——以“阿細跳月”為例[J].體育與科學,2012,33(01):40~43.
[14]何 靜.身體意象與身體圖式——具身認知研究[D].浙江大學,2009.
[15]萬 義.村落社會結構變遷中傳統體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以彌勒縣可邑村彝族阿細跳月為例[J].體育科學,2011,31(02):12~18+35.
[16]Merleau-Ponty M.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M].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2.
[17]葛永才.彌勒彝族歷史文化探源[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64~67.
[18]顏其香.中國少數民族風土漫記(中)[M].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2001:459~462.
[19]崔中良.身體現象學視域下的他心直接感知研究[D].大連理工大學,2020.
[20]葉浩生,曾 紅.鏡像神經元、具身模擬與心智閱讀[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04):97~104.
[21]黃 儉.非物質文化遺產(舞蹈)校園傳承的創新策略[J].舞蹈,2016,(12):58~59.
[22]任 海.聚焦生活,重塑體育文化[J].體育科學,2019,39(04):3~11.
[23]金玉柱,郭恒濤. 中國武術“道·術”關系的身體哲學考釋[J].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19,53(09):61~66.
[24]段麗梅,戴國斌,韓紅雨. 何為學校體育之身體教育?[J].體育科學,2016,36(11):12~18+49.
Forgetting and Returning: A Physical Analysis of the Moon Jump
WANG Chaowei1, WAN Yi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Scienc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Based on the body phenomenology theory, this study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field work and other methods to make a specific study of the Moon Jump and draw conclusions. The main value of this study is that domestic scholars focus o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 of the moon, but forget the importance of the body. It is found that rhythm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A-thin moon jump and body, practical A-thin moon jump and body schema blend, social A-thin moon jump and body interaction, and association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A-thin moon jump and embodied simulation negotiation. Finally, with the deepening of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body,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ment is bound to set off a wave in sports research.
A fine moon jump; Detachment; Embodiment; Phenomenology of body
1007―6891(2023)06―0098―04
10.13932/j.cnki.sctykx.2023.06.21
2022-10-30
2022-11-28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與話語體系建構研究,項目編號:22BTY089。
G85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