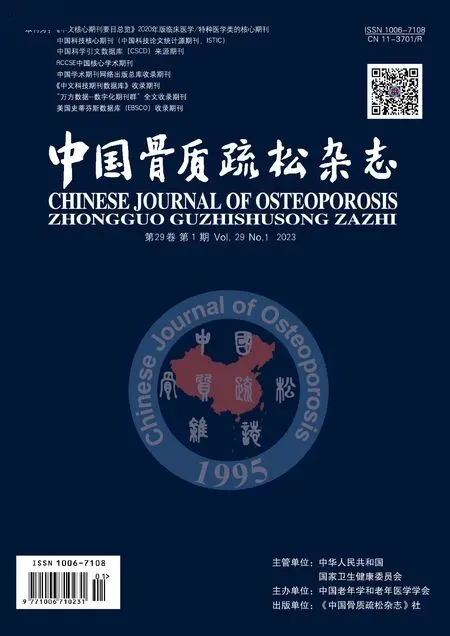肌肉含量指標對絕經后女性骨質疏松癥發生風險的預測價值分析
許海娜 莫國應 朱焱安苗苗吳春艷方月 冉利梅,*
1.貴州醫科大學公共衛生與健康學院,環境污染與疾病監控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貴州 貴陽 550025
2.貴州省荔波縣人民醫院,貴州 黔南州 558400
3.貴州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健康管理中心,貴州 貴陽 550004
骨質疏松癥(osteoporosis,OP)是常見于絕經后女性的全身性骨代謝病,頻發于絕經后5~10年內,已成為全球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之一。我國50歲以上女性OP患病率約占32.1%,明顯高于歐美國家[1]。OP雖可防可治,因經濟水平、地域差異等,致診療率低,加強篩查與識別高危人群是我國重要的防治策略[2]。國內外研究顯示[3-4],低肌肉量、低骨量是OP的風險因素,在更年期女性中較常見,尤其在絕經后加速。雖既往研究已證實肌肉量與骨密度(bone mineraldensity,BMD)間的關系,并提出診斷低肌肉量的不同指標及其截止點,但對絕經后女性肌肉量指標與BMD間的關系以及針對絕經后女性肌肉量指標及其截止點對各部位OP發生風險的預測價值研究較少。本研究擬通過分析四肢骨骼肌含量指標與絕經后女性各部位BMD的關系,篩選預測絕經后女性各部位OP發生風險的肌肉含量指標及其截止點,為基層及社區醫院提供篩查OP高危人群,提高診療率及防治OP策略提供臨床指導及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回顧性研究,隨機選取2018年1月至2021年10月于貴州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健康管理中心的1 366名絕經后女性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年齡≥40歲自發性閉經至少12個月;②無肌病、腫瘤和傳染性疾病等;③未確診OP及服用抗OP藥物;④未患骨代謝病及長期服用骨代謝藥物等。排除標準:①體內有金屬植入物者;②雙側卵巢切除史;③近半年使用減脂或激素治療藥物;④肝腎功能異常、糖尿病等。本研究由貴州醫科大學附屬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受理號:2021150k),所有參與者對本研究知情同意。
1.2 研究方法
1.2.1脂肪及肌肉含量相關指標:身高、體質量、腰圍由執業護師測量,并根據公式計算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體質量(kg)/身高(m)的平方。采用韓國鴻泰盛IOI305生物電阻抗體成分分析儀(BIA)[5-6]測量體脂率、內臟脂肪面積及四肢骨骼肌量(appendicular skeletal muscle mass,ASM)。
根據ASM計算經身高、體質量指數、體質量調整后的四肢骨骼肌含量相關指標如下[7-8]:①ASM:即雙上、雙下肢骨骼肌量總和(kg);②四肢骨骼肌質量指數(ASMI):ASM/身高的平方(kg/m2);③四肢骨骼肌肉量與BMI比值(ASMBMI):即ASM/BMI;④四肢骨骼肌體重比(SMI):ASM/體重×100%(%)。
1.2.2骨密度測量:用美國GE公司LUNAR Prodigy的雙能X線吸收法(DXA)測量BMD值。檢前由專業醫護將受檢者個人信息錄入系統,每日測量前為保證儀器變異系數在合理范圍內,需精確校正。
1.2.3骨質疏松癥診斷標準及分組:對于絕經后女性,骨質疏松組,T≤-2.5;骨量減少組,-2.5
1.2.4脂肪指標診斷標準:中國肥胖工作組[10]:BMI<18.5 kg/m2為體重過低;18.5 kg/m2 1 366名絕經后女性中,OP組肌肉含量均低于非OP組。除腰椎BMD間的SMI和內臟脂肪面積及大粗隆、全髖BMD間的ASMBMI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各部位不同BMD間脂肪、肌肉含量指標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1。 表1 研究對象各部位骨密度分組一般資料[n(%)]Table 1 Analysis of general data of BMD group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ubjects[n(%)] 續表1 研究對象各部位骨密度分組一般資料[n(%)]Continued table 1 Analysis of general data of BMD group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ubjects[n(%)] 續表1 研究對象各部位骨密度分組一般資料[n(%)]Continued table 1 Analysis of general data of BMD group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ubjects[n(%)] 大粗隆和全髖BMD與ASMBMI無相關性(P>0.05),腰椎和股骨頸BMD與ASMBMI呈正相關(r=0.085、0.066,P<0.05),腰椎、股骨頸、大粗隆、全髖BMD與ASM、ASMI呈正相關(r=0.369、0.298,0.366、0.297,0.366、0.369,0.362、0.360,P<0.05),與SMI呈負相關(r=-0.095、-0.122、-0.195、-0.177,P<0.05)。 單因素分析中,ASM、ASMI與各部位OP相關;SMI與股骨頸、大粗隆、全髖OP相關;ASMBMI與腰椎OP相關。脂肪指標作為協變量納入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ASM和ASMBMI與股骨頸和腰椎OP關聯強度最高(OR=3.699、2.235,P<0.05),詳見表2。ROC曲線分析證實了ASM和ASMBMI是預測股骨頸和腰椎OP發生風險的最佳指標,其曲線下面積(AUC):0.67、0.55,截止點:17.2、0.74,靈敏度:66%、50%,特異性:60%、59%(P<0.05)。 表2 肌肉含量指標預測OP發生風險的回歸分析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uscle mass index to predict the risk of OP 絕經后女性的骨形成和骨吸收呈負平衡,易致骨丟失,適當的負重和肌肉量對骨骼的機械應力及成骨刺激均有益,利于維持骨重建、調節骨量、增加骨穩定性。骨-肌雙向串擾是通過細胞、骨、肌和其他生長因子介導[11],以調控骨代謝和(或)肌肉生長。本研究納入近年國內外提出并廣泛使用的4項反映肌肉量的指標,即ASM、ASMI、ASMBMI、SMI,用于預測OP發生風險的價值分析。 4項肌肉指標中,ASM反映的是四肢骨骼肌量總和,因體型不同對肌肉量存在潛在影響,國內外學者[8,12-14]通過校正體型相關變量,得出ASMI、ASMBMI、SMI。肌肉量指標通常用于診斷肌少癥的截止點分析[15-16]、骨骼肌含量參考值范圍制定[17]以及反映中老年人群的增齡性疾病,如骨質疏松癥、肌肉減少癥等研究[18-20]。但其用于預測OP發生風險的研究較少。本研究發現,各部位BMD均與ASM、ASMI、ASMBMI呈正相關,與SMI呈負相關。與Xu等[21]研究結果相同,與楊秀琳等[22]和Qi等[23]得出的BMD與ASMBMI、SMI、ASMI無關結果不同,原因可能在于研究對象的選取。研究發現OP呈增齡性增長,嚴重可導致脆性骨折的發生,女性在絕經后5~10年高發。中國女性平均絕經年齡為49.5歲,而本研究選取的絕經后女性主要集中在50~59歲,為脆性骨折的高發年齡段。相較于楊秀琳等[22]的青年女性和Xu等[21]的男性研究對象,存在年齡及激素水平上的差異。女性絕經后,BMD和肌肉量便以每年10%~15%和1%~2%速度流失,是絕經前的2~3倍。因此,該人群的肌肉量與骨密度的關系不能以其他人群結果加以解釋。 OP是一種增齡性疾病,隨著年齡的增長,骨-肌細胞的間充質干細胞的分裂分化能力降低,導致其向脂肪細胞而非肌肉和成骨細胞分化的傾向。本研究發現BMI、腰圍和體脂率越低,OP檢出率越高,相反,診斷腹型肥胖的金標準內臟脂肪面積指標越高,OP檢出率越高。國內外學者[24-26]則表示脂肪量與肌肉和BMD有關且以各種機制影響肌-骨量,如骨脂肪細胞中雄激素芳香化過程可轉化為雌激素刺激絕經后女性的骨形成。Saarelainen等[27]對198名絕經后女性研究結果顯示,超重和脂肪分布會影響肌肉量及BMD的測量,因此控制脂肪成分十分必要。本研究測量并控制了腹型肥胖常見指標BMI、腰圍、體脂率及內臟脂肪面積,結果顯示,4項肌肉含量指標中,僅ASM和ASMBMI及其截止點分別對股骨頸和腰椎OP發生風險有預測價值,而ASMI并與絕經后女性OP無關聯,驗證了既往研究[28]的結論。 本研究發現,OP組ASM和ASMBMI均低于非OP組,初步驗證了肌肉量對OP的保護意義。骨骼肌含量影響骨強度及抗骨折能力,年齡、遺傳、內分泌等多因素作用[29-30]及肌肉指標的不同截止點是造成骨骼肌量丟失或低肌肉量的原因,而低肌肉量又是低BMD的危險因素[31-32]。基于此,本研究顯示,ASM<17.2 kg和ASMBMI<0.74預測絕經后女性股骨頸和腰椎OP風險關聯強度最高。受試者在這兩個指標小于截止點發生OP的風險是大于等于截止點的3.699倍和2.235倍。與楊秀琳等的ASM<16.35 kg和ASMBMI<0.71預測跟骨OP風險的肌肉指標相同,但截止點存在較小偏差,其原因可能因其測量部位是跟骨及測量BMD工具是超聲骨密度儀,非DXA。Miranda等[33]用美國國立研究基金會推薦的ASM<15.0 kg、ASMBMI<0.512預測絕經后女性股骨頸和腰椎部位,僅ASM<15.0 kg和本研究ASM<17.2 kg預測股骨頸OP風險相同,而其ASMBMI與腰椎OP不相關與本研究相矛盾,且肌肉指標的截止點均存在顯著差異。其因在于種族間差異,骨骼、總體質量和體成分可能影響骨量和肌肉的關系,而ASM又是按比例影響骨量,易造成ASM對BMD影響結論偏差,因此通過身高、BMI等成分指標校正算出的肌肉含量指標截止點存在差異。雖國內外對肌肉量和BMD間的關系廣泛討論,但目前對肌肉量指標及其截止點、診斷標準、評估方法仍未明確。尚需進一步明確相同肌肉量指標及其截止點分析各群體中肌肉量和骨密度之間的關系,以及對其不同測量部位OP發生風險可能性的評估。本研究未能比較圍絕經期與絕經后間肌肉含量指標的預測價值。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未能解釋因果關系,未來研究加入骨代謝指標和肌肉含量指標對OP預測效能的比較勢必更有意義。 綜上,肌肉指標與BMD相關,ASM<17.2 kg和ASMBMI<0.74是OP的最佳預測因子。肌肉指標可獨立預測OP的發生風險,測量肌肉量的體成分分析儀器較測BMD的雙能X線吸收儀成本低、便捷,為各級各類醫療機構實現OP初篩提供實踐參考價值,以提高我國OP診療率、加強篩查和識別高危人群。1.3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絕經后女性各部位骨密度間各變量的比較



2.2 骨密度與肌肉含量指標的相關性
2.3 肌肉含量指標對OP發生風險的預測價值

3 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