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說AI人工智能算法在藝術(shù)領(lǐng)域的利弊得失
編輯:劉小賤 文:林路
人工智能在一般技術(shù)領(lǐng)域中的運用,一直是掌聲不斷。然而一旦到了藝術(shù)創(chuàng)作領(lǐng)域,就會出現(xiàn)極端的兩極對峙:有人歡呼雀躍,有人黯然神傷。這里面的緣由,值得剖析一番。
專欄作者

林路
攝影媒體人
上海師范大學攝影專業(yè)教授、攝影專業(yè)碩士生導師,上海市攝影家協(xié)會副主席,上海翻譯家協(xié)會會員,藝術(shù)策展人。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英文縮寫為 AI 。眾所周知,它是研究、開發(fā)用于模擬、延伸和擴展人的智能的理論、方法、技術(shù)及應用系統(tǒng)的一門新的技術(shù)科學。
其實,人工智能只是計算機科學的一個分支,它企圖了解智能的實質(zhì),并生產(chǎn)出一種新的能以類似于人類智能的方式做出反應的智能機器,該領(lǐng)域的研究包括機器人、語言識別、圖像識別、自然語言處理和專家系統(tǒng)等。令人感興趣的是,由于人工智能可以對人的意識、思維的信息過程進行模擬,盡管不是人的智能,但能像人那樣思考,也可能超過人的智能——有點聳人聽聞?更有意思的是,人工智能在一般技術(shù)領(lǐng)域中的運用,一直是掌聲不斷。然而一旦到了藝術(shù)創(chuàng)作領(lǐng)域,就會出現(xiàn)極端的兩極對峙:有人歡呼雀躍,有人黯然神傷。這里面的緣由,值得剖析一番。
我們知道,人工智能涉及到計算機科學、心理學、哲學和語言學等非常廣泛的學科,幾乎遍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所有學科,其范圍已遠遠超出了計算機科學的范疇。從思維觀點上看,人工智能不僅限于邏輯思維,更重要的是通過形象思維、靈感思維才能促進人工智能的突破性發(fā)展。于是,人工智能在藝術(shù)領(lǐng)域的風生水起,也是必然的。尤其是人工智能繪畫,更是突破了人類自身的極限,從而讓繪畫分析進入到一個更為廣泛的視野中,以人文精神為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打開繪畫藝術(shù)的新領(lǐng)域。而且這時候的人工智能繪畫,不僅僅是人們所認知的神秘、絢麗、深沉、復雜、時代感強,體現(xiàn)出非凡的想象力,更重要是的,引發(fā)超出我們預料的諸多應接不暇的難題。
從最早 AI 繪畫 MidJourney生成的數(shù)字油畫,參加美國科羅拉多州博覽會的藝術(shù)比賽奪得了第一名開始,就引發(fā)了網(wǎng)絡上巨大的爭論。過不了幾年,DALL-E的出現(xiàn),AI 開始擁有了一個重要的能力,那就是可以按照文字輸入提示來進行創(chuàng)作!這樣一種跨界的藝術(shù)思維轉(zhuǎn)換,讓聞知者大腦都來不及轉(zhuǎn)向,就進入了輕松實踐的狂喜之中。隨后,2021年 1月開源了新的深度學習模型 CLIP(Contrastive Language-Image Pre-Training), 又成為更先進的圖像分類人工智能。最令人恐懼的是,它搜刮了40 億個“文字—圖像”訓練數(shù)據(jù)!通過海量的數(shù)據(jù),再投入讓人咋舌的昂貴訓練時間,CLIP模型終于修成正果。
也許有人會問,這么多的“文字—圖像”標記是誰做的呢? 40 億張啊,如果都需要人工來標記圖像相關(guān)文字,那時間成本和人力成本都是天價。而這正是CLIP 最聰明的地方,它用的是廣泛散布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圖片,卻也為日后的運用埋下了伏筆!
然而就在不久前,AI 研究人員一個算法上的重要迭代,就把 10年后我們才可能享受到的 AI 作畫成果直接帶到了當下所有普通用戶的電腦前!你只要體驗過當下以 Stable Diffusion 為代表的最先進 AI繪畫模型所能觸達的藝術(shù)高度,也許可以歡呼雀躍——“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這兩個曾經(jīng)充滿著神秘主義的詞匯,同時也是人類最后的驕傲,其實也是可以被技術(shù)解構(gòu)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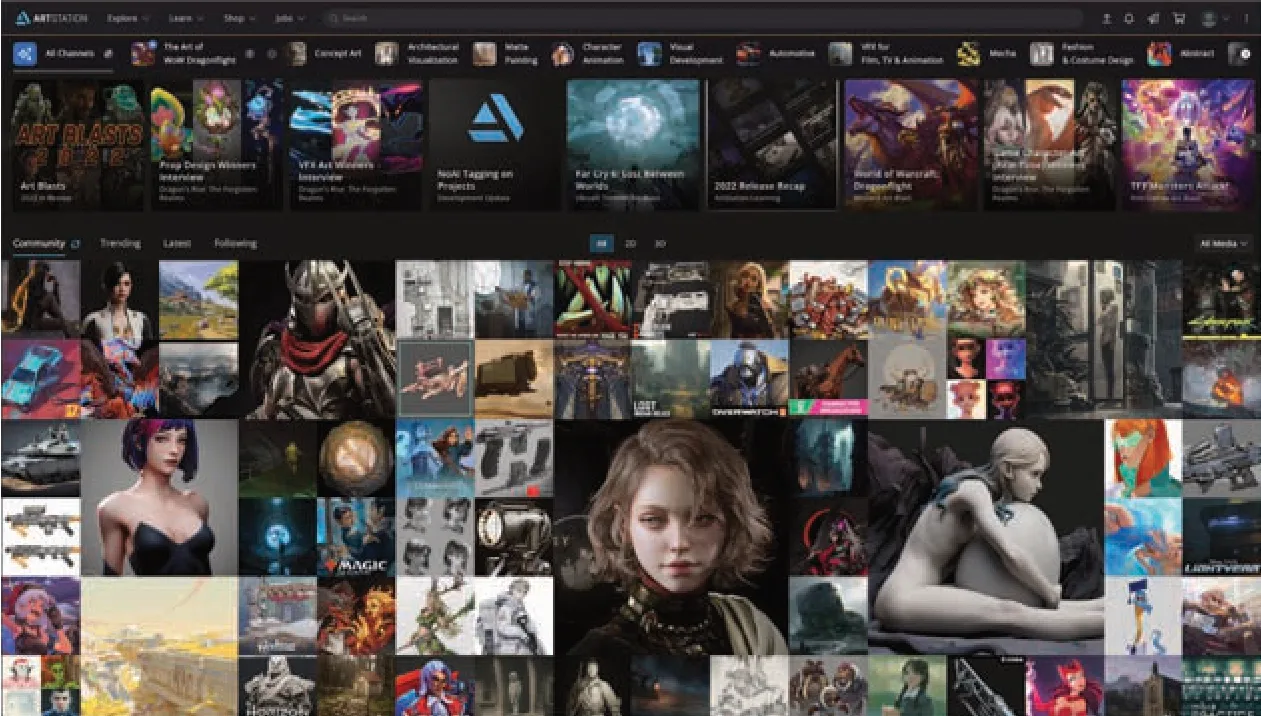
Artstation 上充滿著藝術(shù)家的作品,但他們大多抵制 AI 制圖
網(wǎng)絡上甚至有人斷言:對人類靈魂神圣至上說法的擁護者而言,當今 AI 繪畫模型所展現(xiàn)的創(chuàng)造力,是一種對信仰的無情打擊。所謂靈感、創(chuàng)造力、想象力,這些充滿著神性的詞,即將(或者已經(jīng))被超級算力+大數(shù)據(jù)+數(shù)學模型的強力組合無情打臉了。
只需投放幾張圖片,輸入一串文字,現(xiàn)實生活的照片就轉(zhuǎn)變成了二次元世界或油畫風格,就是沒拿過畫筆的人也能“創(chuàng)作”,讓 AI 繪畫一時間成為各大網(wǎng)站的流量密碼。但在受到用戶熱捧的同時,AI繪畫立馬遭到大批畫家的抵制,不少畫家已將“禁止投放作品進入AI繪畫系統(tǒng)”加入個人簡介。全球知名視覺藝術(shù)網(wǎng)站ArtStation 的上千名畫師發(fā)起聯(lián)合抵制,禁止用戶將其畫作投放AI繪畫系統(tǒng),認為任由系統(tǒng)學習模仿畫作是在侵犯版權(quán)。接著, 標有“ NO TO AI GENERATED IMAGES(對 AI 繪畫說不) ”的圖片刷屏網(wǎng)站,也推出了特定功能限制 AI 繪畫系統(tǒng)采集數(shù)據(jù),畫師可自行選擇是否被 AI使用作品。
其實,這絕非是 AI 所引出的話題。試想一下 20 多年前,數(shù)碼技術(shù)的初創(chuàng)時代,不是也曾經(jīng)出現(xiàn)了數(shù)碼復制挪用的諸多涉及版權(quán)的公案?狼煙四起爭吵了半天,有人想出了一個主意,就是在你已經(jīng)挪用修改的作品上放上一個圓形加上斜杠的圖案,以表示這是經(jīng)過數(shù)碼技術(shù)修改后的畫面,而非簡單的使用。這個圖案使用了一段時間,很快就廢棄了。因為這一切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為一種拿來主義,你是否加上了自己的原創(chuàng),而非簡單地照搬。這樣一來,似乎一切爭議就此煙消云散。
然而也有人因此得寸進尺——他們認為攝影的挪用不僅僅局限于經(jīng)典的繪畫或攝影作品,還可以是直接翻拍他人現(xiàn)成的攝影作品,轉(zhuǎn)而成為新作。這些被拍攝的攝影作品大多為雜志上的商業(yè)廣告,然后被放大,放在畫廊中展出。理查德·普林斯是這種“挪用藝術(shù)”的先驅(qū)人物之一——他自 20 世紀 70年代開始涉足這樣的藝術(shù)形式,從拍攝諸如鋼筆、家具之類的廣告攝影作品入手,然后開始拍攝更注重表現(xiàn)力、影響力的廣告,如萬寶路廣告。他的理由是,拍別人現(xiàn)成的攝影作品,可以得到他自己創(chuàng)造不出來的畫面。他甚至打了比方,說這好比從收音機里聽一些曲子,感覺上總好過自己一個人在家里用音響放出來的效果。1992年,他還為自己的藝術(shù)手法辯護說:“沒人關(guān)心這種作品。如果說到偷,要想偷東西,當然是去銀行了。2005年,他的一幅“萬寶路牛仔”的“挪用”攝影作品,創(chuàng)下了攝影作品的拍賣紀錄,達到120萬美元!盡管他的做法曾經(jīng)引起原創(chuàng)者的憤怒,他也曾因為有過一次被訴上法庭的敗訴,但是在更多的場合,他是一個“挪用”的成功者。
關(guān)鍵是,在技術(shù)的成本上,AI 畫作不僅本身成為商品,生成畫作的關(guān)鍵詞也被拿來售賣,某電商平臺顯示,2.8 元即可購買上百組生成關(guān)鍵詞。更有 AI 繪畫的線上教學課程現(xiàn)身市場,以培訓“AI 插畫師”為名,傳授“馴化 AI”經(jīng)驗,售價在 39—100 元之間。此外,AI 繪畫還被運用于元宇宙領(lǐng)域,出現(xiàn)了相關(guān) NFT 產(chǎn)品。
尤其困難的是,《著作權(quán)法》規(guī)定的作品是由人來完成的作品,即使是法人作品,實際上也是由具體的人來完成的。AI顯然并不是具體的人,因此不應該被視為著作權(quán)所有人。然而也有人認為,AI 由人創(chuàng)造,因此 AI 或 AI 的創(chuàng)作者享有著作權(quán),但時至今日,還沒有一個有影響力的判決出來佐證這一觀點。盡管 Pixiv 在不久前宣布會為 AI 生成作品添加標識,同時增添相關(guān)的篩選功能。網(wǎng)站的 AI 作品將會與通常的作品完全劃分。這和當年的數(shù)碼技術(shù)標識如出一轍,估計出現(xiàn)后,也會很快消亡。
更有意思的話題接踵而來——比如,一位土耳其的攝影師利用 AI 技術(shù),開展了“如果什么都沒發(fā)生( As If Nothing Happened )”這一項目,模擬出一些早逝的名人如果仍在世,現(xiàn)在會是什么樣子。這位土耳其攝影師阿爾珀·耶西爾塔斯(Alper Yesiltas )將制作的圖像發(fā)布在個人社交賬號中,立即引來了不少網(wǎng)友的追憶和懷念。李小龍、邁克爾·杰克遜、貓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等等影視歌星均讓人大呼“回憶涌上心頭”“真的好像什么都沒發(fā)生一樣”。
有人問:如何避免這些已逝去的名人的肖像權(quán)問題?耶西爾塔斯回答:“這個項目純粹是出于個人的好奇心。因為我認為用作素材的照片已經(jīng)是眾所周知的公共領(lǐng)域的照片。我認為這些照片肖像權(quán)的所有者可能不想聯(lián)系我。我只在我的個人賬號上分享了這些作品,突然整個世界都感興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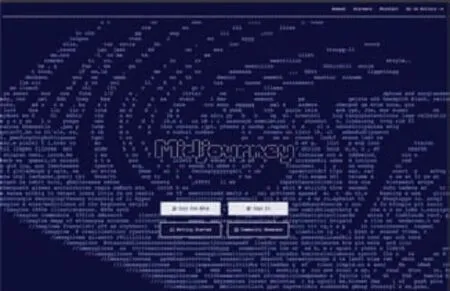
目前還在測試階段的 Midjourney 促使著 AI 制圖迅速成長
他的回答很巧妙,如同打了一個擦邊球,一時間讓人不知所措。
這讓我想到了將近30年前的一則案例——美國廣播公司曾評出十大爭議雜志封面,其中《新聞周刊》于 1994年6月27日版刊發(fā)前美國橄欖球巨星 O.J.辛普森(O.J.Simpson)的面部照片,而《時代周刊》刊登了同一張照片,卻用數(shù)碼技術(shù)進行了修改。修改了什么?僅僅是將辛普森的臉部膚色加深了一些,更黑了一些。那意味著什么?諸多的聯(lián)想讓你自己去完成:關(guān)于種族歧視,關(guān)于社會等級……僅僅是深了一點的膚色,就引發(fā)了如此波瀾。更何況如今的 AI 的“肆意妄為”,我們只需要退回到當年的原點,也就容易釋懷了。只要你的作品不是對名人的惡意攻擊或者帶有人生侮辱,帶著放松的心態(tài)呵呵一笑,管它是 AI 還是普通的數(shù)碼技術(shù)!
還記得當年一幅為法國著名時裝品牌伊夫·圣·洛朗名之為“鴉片”的香水所拍攝的廣告?攝影家史蒂夫·梅塞爾之前在世界上各類雜志的影像都沒有任何爭議。但是這幅模特兒索菲·達爾在深色背景前僅僅戴著珠寶和穿著高跟鞋的畫面出現(xiàn)在英國街頭時,卻引起了強烈抗議。也許畫面的含義過于露骨了,英國廣告標準局最終要求在街頭廣告牌上撤下這幅廣告。所以,技術(shù)的運用不是問題,關(guān)鍵是你的底線是否符合日常的道德規(guī)范,或者符合一個時代、一個地域的文化準則和審美趣味。其實每當一種新技術(shù)出現(xiàn)時,會有人黯然神傷,就是因為他們一股腦地將責任推到了技術(shù)的層面,這就有點簡單化了。
AI 繪畫,或者更廣泛的,AI 生成內(nèi)容領(lǐng)域(圖像、聲音、視頻、3D 等)還會發(fā)生什么,讓人充滿了遐想和期待。尤其是隨著技術(shù)的進步,總會在不斷促使完善相關(guān)的保護機制。只是保護機制的出現(xiàn)始終晚于技術(shù)的成熟,所以為什么最早打擦邊球的獲勝者,才是最高級別的人工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