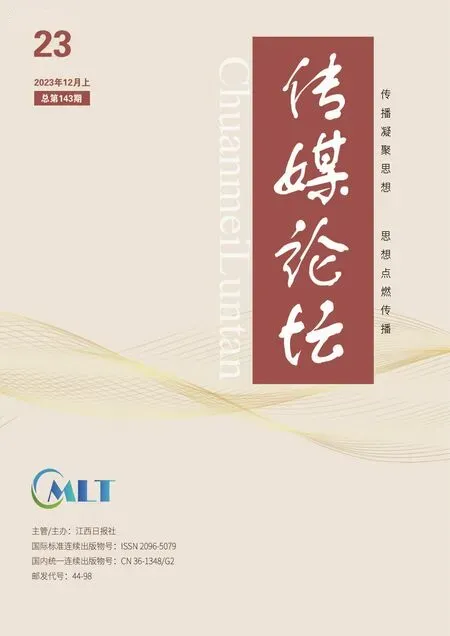人工智能時代提升朗誦能力的路徑探究
李 飛
人工智能合成音在當下的應用比較廣泛,技術日趨成熟,逐漸打破了之前語言機械單一,缺乏語氣和語流的技術壁壘。這對播音主持教學也帶來了著極大沖擊。面對技術的革新,播音主持專業的學生首先要提高自己的朗誦技能。因為朗誦藝術凝聚了播音主持專業有稿播讀中的核心技巧。結合教學實踐,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提高朗誦的語言技巧,面對AI智能合成音的挑戰。
一、理解稿件,尋找情感依托
對于稿件的理解,大的方面可以從文章的寫作背景、作者所處的時代,作者的寫作風格,文章的主題等方面切入。小的方面,要對文章中的借代、隱喻、用典進行細致的分析,尤其是中國古典詩詞。
如李清照的詞中常出現“黃花”一詞。在朗誦她的詞時就需要了解她寫作的時代背景、個人的人生境遇,在深入理解文本的基礎上才能找到情感依托,為情真意切的表達做準備。以《醉花陰》為例,結尾三句“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進一步明確她因別離而相思,因相思而憔悴。此詞寫于崇寧二年(1103年),是她嫁給太學生趙明誠的第二年,由于丈夫“負笈游學”,加之重陽佳節,對丈夫有著濃濃的思念。除了詞人的丈夫在佳節遠游,因為她的父親李格非身陷朝廷黨派斗爭,她與父親也不能相見。這一年,她的父親李格非被列入元祐黨籍,不得在京城任職。由于朝廷黨爭激烈,其父“元祐黨人”的罪名也株連到她身上。多重心事的交織,讓詩人憔悴不堪,也倍感孤寂。易安巧妙使用了“珠簾”這一帶有阻隔感的意象,讓西風卷起珠簾,驚窺到簾中人已消瘦如斯,給人帶來的視覺沖擊力更加強烈;使用“瘦”字時,不直說人之瘦,而是與節后即將不斷衰萎的黃花對比,人比花瘦,情感力度也更進一層。通過深入理解文章中的核心詞語,明白其深意,理解作者的境遇,這樣在朗誦中才能有情感依托,調動起播講欲望。
二、通過聯想想象,引發情感共鳴
在全面理解稿件的基礎上,在朗誦時,還需要演播者通過想象,將一個個文字符號變成活動連續的畫面或場景,設身處地地感受文本作者所處的環境,理解文章想要傳達的情感意圖,這樣更能調動自己的情感,實現朗誦者與文章作者、演播者和朗誦作品的共鳴。
而這些共鳴,通過聲音的呈現,讓聽者也能通過想象,身臨其境地走入文本內容所營造的場景當中,和朗誦者一起置身情景交融的境界,領悟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意蘊。如李白的《清平調·其一》對楊貴妃花容月貌般的美麗的描述:“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作者沒有直接描述楊貴妃的樣貌,而是借云朵聯想到她飄逸華美的衣裳,更有一種風姿綽約之美。對于她的容貌,作者借牡丹卓爾不群之姿贊嘆其國色天香之貌。因此這種美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作者運用借代和比喻來描繪傳達,這就需要朗誦者和聽者一起運用想象聯想,進入詩人營造的意境。
又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這四句詩中不帶“孤寂”一詞,但寫出了在寒冷寂靜的環境中,一位老漁翁竟然不畏嚴寒風雪的專心垂釣的形象。老漁翁的身影雖然孤獨,性格卻顯得清高孤傲,這也映射了作者的心志。在朗誦時,只能通過想象和聯想來體味作者的這種人生況味,走進這種寂寥、孤寂之至又不失追求和等待的心境。通過聯想想象,借助于意境的營造,最終實現朗誦者和聽者在情感上的共鳴。
三、運用節奏技巧,提高語言的感染力
宗白華先生在《美學散步》中這樣論述:“藝術家往往傾向以‘形式’為藝術的基本,因為他們的使命將生命表現于形式之中。”[1]各門藝術的藝術傳達方式都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制作方法和表現手法,這使得藝術技巧和手法在藝術傳達中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2]
朗誦藝術是情感、聲音與氣息的融合,也需要運用藝術技巧和手法,將文本的內容和其背后的情感傳達出來。在面對人工智能合成語音帶來的沖擊時,朗誦的聲音想要具備生命活力,亟須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一)要解決節奏平的問題
經過對稿件的理解,通過想象聯想激發起極強的播講欲望,但如果沒有恰如其分的語言技巧,這些情感通過單一的聲音外化出來,仍舊不具備感染力,缺乏生命活力。藝術技巧的運用像鹽溶于水,有味無痕。
要彰顯朗誦的生命活力,打破朗誦中容易出現的“讀書腔”“念書調”,需要我們掌握聲音高低和文本內容的配合,如“百煉成鋼”一詞,聲音形式會高而強一些,而詞語“花紅柳綠”則顯得低而柔一些。同樣是低而柔的“曉風殘月”,氣聲會多一些,相對偏虛,情感偏冷。
又如當代作家張永枚的《斧頭之歌》,在關于抗美援朝期間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中,“白色的羽毛。云,白色的鳥群。”這句話一共出現了三次。根據上下文的內容,“白色的羽毛。云,白色的鳥群。”這句話的三次出現需要運用不同的聲音形式進行演播。它第一次出現是在開頭部分。因此,在朗誦時,選用陳述的語氣,聲音相對柔和,情緒波動不大。在它第二次出現時,是在一位朝鮮阿瑪尼被敵人炸死后,當志愿軍班長看到老婦人的血流了一地,想到她對志愿軍深深的愛和無私的幫助,憤恨地說道:“雪,是白色的羽毛嗎?云,是白色的鳥群嗎?不,雪是漫天凝結的淚花。”在該處朗誦時,“云”和“雪”的聲音比較急促,以偏強的實聲為主。這句話第三次出現,是在“斧頭以頑強的生命在班長手中飛舞砍吶,朝敵人砍去!美制的鋼盔栗子殼一般地裂開。斧頭在殺殺的歌唱,一首復仇之歌。帶血的斧頭,冒著熱氣。敵人的尸體,縱橫在腳下。班長屹立在戰友們中間,手里緊握著老婦人留下的斧頭。”這個敘事段落之后,結合上文,此時朗誦的語氣是一種釋然的,悲壯的情感交織。因此,在朗誦該句話時,聲音音高稍強,與第二次的表達相比,語速稍快一些,聲音稍顯明亮一些,但情緒是悲壯的。
在語速上,要輕重緩急進行結合。根據語意和作者情感的變化,讓語言節奏賦予變化。如讀到《口技》:“遙聞深巷中犬吠,便有婦人驚覺欠伸,其夫囈語。既而兒醒,大啼。夫亦醒。婦撫兒乳,兒含乳啼,婦拍而嗚之。又一大兒醒,絮絮不止”時,語速要舒展。而到了“當是時,婦手拍兒聲,口中嗚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夫叱大兒聲,一時齊發,眾妙畢備……凡所應有,無所不有。”,語速達到全文里最快的部分。通過抑揚頓挫的節奏之美,讓真摯的思想感情更加完美和諧地呈現出來。
(二)要解決情感單一缺乏主次之分的問題
一篇文章作者在寫作時就注重敘事的主次之別,有的內容三言兩語簡單概括,有的洋洋灑灑成百上千字細細描繪。因此,我們在朗誦時要依托文本,將情感進行濃淡、輕重的區別,而不能字字用情、句句著力。在語言表達上做到,準確、鮮明、生動。例如《白楊禮贊》:“它沒有婆娑的姿態,沒有屈曲盤旋的虬枝,也許你要說它不美麗——如果美是專指‘婆娑’或‘橫斜逸出’之類而言,那么,白楊樹算不得樹中的好女子;但是它卻是偉岸,正直,樸質,嚴肅,也不缺乏溫和,更不用提它的堅強不屈與挺拔,它是樹中的偉丈夫!”根據語意不難發現,重點句子是“更不用提它的堅強不屈與挺拔,它是樹中的偉丈夫!”這一句,在朗誦該句時就需要情濃而聲高,語速稍微偏快。
又如朱自清的散文《背影》,雖然細膩描寫了與父親分別的場景,但縱觀全文,重點內容是作者兩次感動落淚的地方。分別是:“我看見他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和“我望著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里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里,再找不著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中不禁又簌簌地流下淚來。”有了對文章的主次把握和情感濃淡的區別,語言才會更加豐富生動。
除了以上兩點,想讓語言表達技巧更接近完美,還需要在朗誦之余,練習基本的語音發聲,讓吐字圓潤舒展、富于變化,掌握情景再現、內在語、對象感、語氣、停連、重音、節奏這些語言表達中的內外部技巧。最終達到恰切的思想感情與盡可能完美的語言技巧的統一。
四、真情實感貫穿朗誦創作始終,彰顯聲音的活力
情感是藝術構思和創作不竭的動力,藝術家只有在熾烈情感的澆灌下,才能完成藝術創作。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這樣解讀情感在藝術創作中的意義:“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感是藝術創作的內在生命和靈魂,沒有審美情感就沒有藝術。著名匈牙利音樂家李斯特認為:“音樂是不借任何外力,直接沁人心脾的最純的感情的火焰,它是從口吸入的空氣,它是生命的血管中流動著的血液。”狄德羅也同樣指出了情感在藝術創作中的重要性,認為“沒有感情這個品質,任何筆調都不能打動人心”[3]。朗誦作為語言藝術也亦是如此,它的音韻之美,它的意境之悠遠朦朧,直擊人心的情感沖擊離不開創作者熾烈真摯的情感。
例如,作家臧克家在《有的人》一文中,總結了截然不同的兩種人的選擇和歸宿,以此來歌頌魯迅先生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高尚節操和精神。正如詩中所寫:“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在朗誦該作品時,朗誦者需要深切感知作者對欺壓人民的貪官污吏和腐敗統治者的深惡痛絕,和對魯迅這樣像野草一樣甘愿奉獻的仁人志士誠摯的愛和發自內心深處的贊揚。同樣都是活著,一個充滿著作者的鄙夷和否定,一個流露著作者的贊美和歌頌。作為朗誦者,也需要像作者那樣有著發人深省的情感的迸發,用真情實感來傳達作者針砭時弊、振聾發聵的心聲!
讓朗誦向生活汲取那些親切真摯、鮮活動人的情感,才是有聲語言的創作源泉,我們積極的人生態度、豐富的生活情感、主動的內心體驗才是有聲語言的源頭活水。“讓朗誦映照生活”,生活中的許多事情就可以使我們“思接千里,觸類旁通”,就可以使我們打開心靈,張開觸角,在朗誦中學會感悟、在生活中學會欣賞,學會為“真、善、美”感動,學會為“假、惡、丑”憤怒、用詩文培養自己“審視美的眼睛”和“辯音律的耳朵”、更重要的是用朗誦培養自己“健康而濕潤的心靈”。在朗誦創作中,需要在藝術體驗、藝術構思、藝術傳達中將真情實感貫穿始終,始終秉承“傳情達意,心口如一。”
例如,在朗誦當代詩人艾青《光的贊歌》這篇歌頌光明、鞭撻黑暗的政治抒情詩時,需要理解作者對于光明的解讀,正如詩中所寫到的:“每個人的一生/不論聰明還是愚蠢/不論幸福還是不幸/只要他一離開母體/就睜著眼睛追求光明。世界要是沒有光/等于人沒有眼睛/航海的沒有羅盤/打槍的沒有準星。”詩中除了對光明的贊揚,也有對害怕光,制造黑暗,維護黑暗勢力的人的抨擊和斥責。作者在詩中這樣斥責道:“但是有人害怕光/有人對光滿懷仇恨/他們占有權力的寶座/一手是勛章、一手是皮鞭/一邊是金錢、一邊是鎖鏈/進行著可恥的政治交易/完了就舉行妖魔的舞會/和血淋淋的人肉的歡宴。”
真情實感的擁有,需要朗誦者在演播時,多一些“童真”,少一些功利。如明末思想家李贄的《童心說》里所倡導的,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學存真去假,真實坦率地表露作者內心的情感和人生欲望。即文中所說的“童子者,人之處也;童心者,心之初也。”[4]又如作家林語堂在四十歲生辰所寫的自壽詩中表述的:“一點童心猶未滅,半絲白鬢尚且無。”擁有一個“童心”才會讓情感更加誠摯和純真,才能通過鮮活的聲音將情感傳遞出來。
音色承載著質感,呼吸承載著生命,言語承載著精神。切切實實地讓受眾感受到傳播主體和他們是同質的肌體,是親切的靈魂[5]。唯有如此,我們的聲音才真正擁有了生命的活力,我們的朗誦才不會畏懼科學技術帶來的沖擊和壓力,讓有聲語言散發著不朽的生命活力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