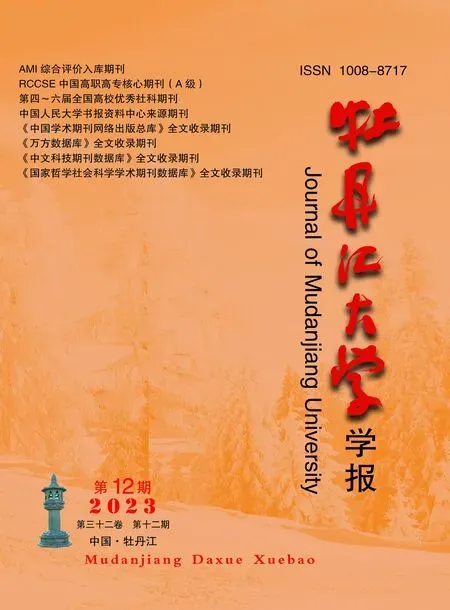論殘雪《天堂里的對話》中女性的分裂心理
申朝暉 王晨瑾
(延安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陜西 延安 716000)
殘雪的作品具有鮮明的個人風格,始終向人的潛意識領域進行深度開掘。她早期的短篇小說《天堂里的對話》即是建立在內心世界的文本,作品以“我”與“你”靈魂式的對話,以及“我”出發去“追尋”自我為主線展開的。殘雪曾在訪談中表示,除了愛情和一切美好深切情感外,這篇小說還有很多其它的讀法,“可以看作自我精神分析,也可以看作作者的創作談,還可以看作對于人性的這些層面的感悟”[1]91。當前有關殘雪及其作品的研究,雖然也有涉及這篇小說,但尚缺專門性研究。在進行文本細讀分析后,本文把《天堂里的對話》看作是一場“自我尋找的冒險歷程”。
從現代意義上來說,自我并不是完整統一、凝固靜止的,而更可能呈現為支離破碎的狀態。因此,“對自我看待的自審過程就是一個充滿矛盾與痛苦的過程,‘自審’將自我進行審視、剖析、解構,在此過程中必然伴隨著自我的分裂”,分裂并不單指“被迫的割裂與粉碎”,也有“主動的增值與提升”,還有“自我‘肯定質’與‘否定質’的互動與更替”,但“更多的是一個不斷裂變的動態過程”[2]76-77。殘雪也說過自己“寫的就是靈魂的故事”,而“藝術家遲早要跟靈魂遭遇。分裂,分裂成幾個部分”,這種分裂“男女都有”,但女性比男性敏感,更易造成心理上的矛盾和分裂,由此具有“那種獨特的詩意”[3]34。《天堂里的對話》沒有明顯的邏輯脈絡和故事情節,就連人物也是模糊的、符號化的,但文本內容有明確的指向:“我”是女性,“你”是男性。對比殘雪之前發表的《污水上的肥皂泡》《山上的小屋》等小說中呈現出的駭人變態的場景與陰郁冷漠的氛圍,《天堂里的對話》透射出了許多溫暖的抒情色調,然而書名中的“天堂”二字,表明整篇小說仍未建立在現實中。作者似乎對現實有種不信任感,在她筆下,“現實”污穢不堪,“天堂”里才會出現亮色,然而“我”依然會感到孤獨、焦慮與恐懼。殘雪說,《天堂里的對話》等作品都是“焦慮、惡心、不滿,以及振奮與幸福摻雜在一起的產物”[4]111。黑暗與光明、失望與希望,在這個“天堂”內共存,從中可窺探出現代女性心靈深處分裂的兩極,在不斷地拉扯、糾纏與抗爭中,最終走向了“追尋之路”的過程。
一、理性與欲望
根據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自我”處于前意識,一半處于意識領域,另一半與現實世界相聯系,具有理性的作用,壓抑完全浸在潛意識中的代表欲望的“本我”。“自我的要素,一是沖動,一是理性,作為人而言,理性鉗制沖動并承擔沖動的后果才是有精神的人。”[5]24在《天堂里的對話》中,主要人物是“我”和“你”,但這兩者其實是同一個人撕裂出來的兩個靈魂。“殘雪小說中的人物是靈魂的各個部分。在小說中,以女性身份出現的人物往往是靈魂里最有詩意的那個部分,靈動又飄逸;而以男性身份出現的人物則帶有強烈的自審傾向,二者總是相互補充又相互促進,推動著文本向前發展。”[6]70因此,關于“我”的視角的語言描述多帶有感性詩意,如形容“我”的雙腿像水草一樣在空中蕩動,眼淚像是雨滴。而“你”則觀察蜜蜂、獨自一人守望,顯出冷靜沉穩的一面,“你站在那里審視我,黑眼睛異常嚴肅”[7]10。“你”不確定“我”什么時候出現,怕一不小心“我”與“你”擦肩而過。“我”,也就是本我,有時會浮出潛意識領域,無法抑制的欲望沖動可能會在現實世界中釀成糟糕的后果,比如暴力行為,因此,擁有理性的“你”守在意識領域,隨時把控住各種本能感覺,防止“我”闖入與現實世界相聯系的前意識領域中。
“我”是屬于感性的那方,每次見到“你”,就忍不住不停地想要跟“你”說很多事情,這是因為,女性具有強烈的傾訴欲望。但女性也能控制住自己的情感,有幾次,“我”想跟“你”說一些事,最終“我”還是克制住自己,轉而訴說其他事情。這是理智在女性心理上的體現,說出口的,并不是心底真正想說的話。有時“我”也有些控制不住自己,而“你”會平靜地讓“我”一定不要急躁。在相識第二天,“我”和“你”一起嬉鬧,踩死了許許多多的小毒蛇,并且在所有扣眼都插了一朵金銀花。我不再感到一絲懼怕,因為“你牽著我的手”[7]7。在《圣經》里,魔鬼撒旦化身為蛇引誘亞當和夏娃吃下禁果。“我”和“你”踩死小毒蛇,可以說是在消除威脅,拒絕各種誘惑,還插滿有解毒功效并寓意“真愛”的金銀花,表示內心的堅定、純凈。有了“你”的存在,“我”害怕的情緒會消失。可見,理性可以有效對付“恐懼”,而且有理性的指引,人的行為會更穩重踏實,變得越來越成熟。
小說開頭,夜里“我”第五次聞到夜來香的味兒。“你”告訴“我”夜來香的秘密,叫“我”等待,這是理性克制自己去盲目行動。“夜來香”既是美好的象征,也帶有誘惑性。夜來香的香味兒一次比一次濃烈,對“我”的誘惑力越來越強。“湖水”是欲望,“鈴鐺”晃動發出的聲音,寓意著悸動搖擺的心情,也是“秘密”的呼喚。“鈴鐺”在一棵銀杏樹上,銀杏樹在湖心水的深處,也就是在欲望的深處。“我”在聞到夜來香的味兒之前,會感到焦躁不安,常想落入欲望之湖,變成自由自在的魚不受拘束。但是,“你”總會阻止“我”。“我搖晃了一下,正要掉下湖去,你攙住了我的腰”[7]5。本我想要掙脫理性,“你干嗎攙住我的腰”,“我”自愿墜入湖中,想要變成魚兒自由自在地游來游去,找到那棵銀杏樹,“在那濃密的葉片間棲息”[7]6。一方面是欲望誘惑,另一方面是理智克制,在雙方拉扯對抗中,最后還是理性戰勝了欲望,“我”不忍心落入湖中變成魚兒離開“你”,決定要和“你”在夜晚一同尋找夜來香,并且“你在門外,我在屋里”[7]8。女性雖說情感豐富,相比男性更多以感性為主,但始終還是不能沒有理性在席。“現代性之于女性的過程,就是女性自我從非理性到理性的探求過程。”[8]40那么,為何是“你”在屋外,“我”在屋內呢?
二、屋外與屋內
與《山上的小屋》一樣,《天堂里的對話》里也有一間“小屋”。在《山上的小屋》里,“山上的小屋”時有時無,象征“我”內心向往的世界的不確定性;而在《天堂里的對話》里,“你”是從有星光的地方走來,“小屋”在桑樹下,都是可確定的美好世界的象征。兩篇小說里的“我”,都有一個自己居住的屋子。不同的是,在《山上的小屋》里,“我”的“家”代表了現實生存環境,主要是由父親、母親、妹妹形成的緊張的人際關系;在《天堂里的對話》里,如果說整個故事里的世界是人的心靈世界,那么“我”居住的“黑屋子”則是更個人、更深層、更隱秘的內心領域。這個“黑屋子”里,基本只有“我”在,連“你”也只有偶爾才能進來。
“我”居住的地方是“熄了燈的黑屋子”。為什么不開燈呢?對于“我”來說,作為內心世界物質化的屋子,尤其屋內是安全的,這種安全感從上到下、從左到右都將自己緊緊包圍。熄燈后,光源消失,在黑暗中視覺受阻,感官會變得更加敏銳,靈魂更容易潛入自我內心深處。黑暗也因難以被眼睛看到,將“我”藏匿起來,給予“我”安全感。這種安全感,來源于生命本初就是誕生于黑暗之中。作為“生命之源”假說之一的大海,其深處就是黑色的。孕育生命的子宮內部也是黑暗的,如一間“黑屋子”。“我”靜靜處于生命意識誕生的原始之所,沒有干擾,沒有人侵犯獨屬于自己的潛意識領域。“白晝與光明是意識的同義詞,而黑夜與黑暗則是無意識的同義詞。”[9]133白天,人在塵世奔波,是屬于現實世界的,而夜晚多與自己獨處,屬于內心世界。處于深層潛意識的“我”想要脫離純粹的內心世界,結果是“眼珠變成奇怪的顏色,再也區分不開白天和夜晚了”[7]10,也就是處于現實與自我意識的交界了。完整的靈魂不可能僅屬于純粹的現實世界或者純粹的精神世界,而是現實和精神交混在一起的存在。女性在某些方面與兒童的心理相似,比如幼小的兒童不能分辨主觀和客觀,也因此女性多與兒童一樣擁有無窮無盡的幻想,想象力極其豐富。在晚上,光線被吞噬,黑夜淹沒白晝中清晰的現實,形成曖昧不清的感覺。一切變得不確定,也就意味著擁有無窮無盡的可能性,人的想象力變得更加自由自在。“對于敏感到多少有點神經質的女性來說,黑夜無疑是更適合于她們靈魂飛翔的所在。”[10]如文中“我”會飛,“我”會變成白色的鯨魚從被子里游出來等。
在“黑屋子”里安全,但“我”也并非想要一直囿于屋內。“我”在屋外飛翔,也想要接觸外在的世界,但同時又對屋外的世界抱有警惕心,原因有兩點:一是恐懼。白天,有對人的恐懼。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隔絕的,沒有人會理解自己,反倒會傷害自己。比如,“我”到荒坡上等待夜來香的味兒,這種行為卻被一些“人”譏笑,他們還用弓箭朝我射擊,將我的白色外衣“射得千瘡百孔”[7]6。而到了晚上,總有一個黑影出現在門邊,只要“我”一閉眼,黑影就會逼近“我”,用手抓“我”的頭發。“我”不敢睡,晚上心驚膽戰地檢查房屋的大門和窗戶,不明白黑影是如何進到屋子里的,只知道有時黑影絕對進不來,“那是當你坐在門外的時候”[7]8。“黑影”可以看作是“危險”的象征,也可以說是女性對危險感到本能地害怕、恐懼的具象化。人在睡覺時意識防守最弱,“危險”與“恐懼”都會趁虛而入,需要“你”守在黑屋子門口也就是潛意識外圍,處理各種負面東西,這樣深層意識才會變得平靜安寧,“我”往往能睡著。“我”是如此害怕,如此脆弱,需要“你”的守衛、保護。這也是“我”信任“你”,希望“你”在屋外,“我”在屋內的原因。除此之外,“我”的飛行能力也是有自保作用的,亦或正是為了自保,“我”才擁有這個能力,因為“我”飛起來時,會在所有人的視野范圍內消失得無影無蹤,不被任何人發現、察覺。如果出現了恐怖、危險的東西,“我”就可以很輕松地躲避開。這是女性在可能潛伏危機的黑夜里,能夠躲避危險的希翼。二是懷疑。個體對外界抱有不信任感,“我們這里的夜晚沒有星星,只有一個剪紙般的假月亮”[7]10。“星星”“月亮”象征美好,這里卻沒有“星星”,連“月亮”在“我”看來也是假的。除此之外,靈魂與靈魂之間也是不確信的,“我”對“你”的存在產生懷疑、感到無措,因為“你”隨時都有可能在茫茫人海中不見蹤影,“成為無數陌生面孔中的一個”[7]14。無論是他者還是自我分裂的靈魂都千變萬化,無法百分百地對其掌握、了解,這也造成個體甚至對自身的存在也表示懷疑,“有很多人為的東西證實我們是不存在的,我們只不過是那些飄忽不定的粉蝶”[7]14。
屋外是那樣危險,有許多讓“我”焦慮不安的不穩定因素存在。在《山上的小屋》中,“我”也是待在自己的“家”里,但“家”的窗戶“被人用手指捅出數不清的洞眼”[11]339,破壞了屋子的安全性,屋內將被迫承受屋外目光的窺視,屋外世界是在“我”非自愿情況下通過洞眼進入屋內。但是,在《天堂里的對話》里,“我”是主動打破了“黑屋子”的封閉性,“我用一把剪刀將屋頂剪一個洞,伸出狂亂的腦袋,仿佛聽見了隱隱傳來的轟響”[7]9“槐樹的枝丫一作響,我就忍不住把屋頂剪一個洞,好掉下來一束光。我的屋頂已成了一個漏勺了”[7]10。天上沒有星星,月亮也是假的,但“我”仍相信會有真實的星光月色,希望真正美好光明的事物會出現。另一個靈魂“你”也對“我”說:“你的房子,窗戶一年四季總是敞開,你不甘心,生怕放過了路上那些影子。”[7]11可見,雖然屋外可能會有種種不測,屋內舒心安穩,但是“我”并非完全封閉自己,而是希望外界的“光”降臨,渴求遇到心靈相通的“影子”。這樣,“屋內”與“屋外”形成一種分裂心理:是停留在屋內這個專屬自我的世界,還是前往屋外去主動追尋?
三、等待與追尋
內心潛意識的沖動總迫使人行動,而理性總努力讓人停下,不要貿然行事,由此造成女性在下決心做事時常會瞻前顧后、猶猶豫豫,出現再三反復的分裂心理。“你”是一種冷靜等待的形象,一開始夜來香的氣味出現時,“你”就對“我”說:“你只能等待。”[7]6這個地方干旱寒冷,又有很多毒蛇,“我”心里很想問“你怎么竟能在同一個地方等待那么長的時間”[7]7。當“你”走出門外,看見“心臟皺縮成一顆干檸檬”[7]9,其實看到的是枯萎的心靈世界。“我一直待在這地方和干旱搏斗。”[7]10“我不時種一點什么,但從來沒成活過,因為天不下雨。”[7]10雨是求不來的,想要拯救干旱的命運,只能靠自己去尋求解決辦法。“干旱”意味著許久沒有新的事物出現,也生長不出新的生命,同時還意味著“一成不變”。“不知從什么時候起,生命就朝一個方向無限地延續著,空泛而單一,沒有任何明顯的標志將它區別成一些階段。”[7]10時間和空間似乎都停滯了,沒有任何變化,如茫茫大海波瀾不驚,四周都是一個模樣。現實生活日復一日,靈魂如機器按照既定程序運轉,產生的虛無感使“我”想要做出改變。“對于重復而單調的模式化的日常生活,殘雪筆端的人物常常會因此感到難以忍受甚至窒息,因而左沖右突,作出開拓生活可能性的種種選擇。”[12]
明明黑夜里危機四伏,“我”懼怕黑夜,“你”也勸告“我”,不要在夜里出去,“以免遇到意想不到的傷害”[7]12,但“我”還是離開了“黑屋子”,穿過高樓、樹林、崖石。與“干旱”一樣,這些東西雖然也是組成內心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太過古舊無光,色調灰暗,死氣沉沉,不再新鮮富有活力。“我”要的不是這些。接著,“我”想起一種照片,“每次在我看到它時,我就找到了準確的答案,而一旦它消失,又重新成為一個謎,于是找到的答案也遺忘得干干凈凈”[7]13。事物如果消失了,其意義價值似乎也消失了,“我”從中得出的答案也變成了不實際的存在,會對它產生質疑,質疑它真的是自己所要找的答案嗎?這種照片也并不是說出現就出現,“只是在你完全忘記了它時,它才赫然出現在你的眼前”[7]13。追尋之物并不是想得到就能得到的,奇妙的是,有時不再把它放心上,不再那么在意它,不把它看得太重要,它反而會在不經意中出現。照片里的人也不是固定的,有時是那個人,有時又是另一個人。也許,追尋的答案并不是恒定的,并不存在唯一的標準答案。
“在深沉的睡眠里,那種冷的火焰就燃燒起來,光芒射穿我的五臟。”[7]16那是靈魂的光,是屬于自己的,每個個體都有屬于自己的光。“但我的光并不照亮我自己,靈魂永遠處在昏暗之中。”[7]16只有自己一人是不行的,要靠照亮他人,才能確定靈魂在閃耀。“我”可以從“你”的眼睛里看到“我”的光,然而,由于“我”與“你”的一次分歧,使“你”的眼睛變成兩小塊“平板的黃玻璃”,不再能映照出“我”。“我”也許正是發現了這一點,才會開始“追尋之旅”。“我”到了許多城市,遇見許多人,但他們的眼睛也都是“平板的黃玻璃”,混濁黯淡。“我”并沒有放棄,而是下定決心必須要去繼續尋求,從許許多多的黃玻璃中“去尋求照亮那昏暗的眼睛”,然而如果真的找到,又要面對“可怕的深淵”[7]16。追尋之旅似乎永無終點,找到所謂答案后,又會冒出新的問題。同時,“你”也在阻止“我”的行動:“你也許會去找,但永遠也無法確定。”[7]14-15“你只能回來,不可能有出路的。”[7]18“你”和“我”呈現兩種相反的心理,撕裂得越來越厲害。“我”不愿回頭看“你”,“我”還是繼續走著追尋的路,即使不知結果如何,即使還是緊張不安,懼怕人群,“我”仍在許許多多的人中間進行著“尋找”的工作。這時,出現了一個女人,也是自我分裂出來的一個靈魂。“她”說“我”什么也不能證明,“她”見到過很多眼睛發光的人,但他們一個個都拿自己毫無辦法,毒蛇、狼,還有一些植物也在威脅著“我”。這說明了追尋之路不會是一帆風順,會出現很多艱難險阻,種種困境都是需要“我”去面對、解決的。
“我”依然堅持自己的選擇,也許“要走遍天涯海角”,而“你”也依舊固守原地,“始終留在原地”[7]18。“你”始終選擇等待,處于不動的狀態。這種停滯,不止是空間上的,也是時間上的,生命也處于停滯、凝固狀態,就像“我”之前一樣,所以“你”會始終年輕。“我”雖然會老去,但是生命不再一成不變,追尋路途中看到的,遇到的所有人、事都會是寶貴的財富,是“我”存在過的證明。追尋之旅就是整個“人生”,生命不會因為一步一步走向死亡而失去光芒,靈魂經歷了這個過程才會更加閃耀。“殘雪其實并不怎么在意找尋的結果”,尋找的過程以及在這整個過程中,小說人物或靈魂的困惑和堅定,才是重點[13]。“尋找過程本身就是意義。”[13]當“我”再與年輕的“你”相見時,將是代表重生的春天,冰川破裂將化為春水重新流動,那是萬物復蘇、充滿希望的新開始。
在小說《天堂里的對話》的結尾,“我”與“你”化為了兩株馬鞭草,同是馬鞭草卻又不是一株,正是代表了一個人分裂但又統一的靈魂。“我”與“你”分開,去追尋,而與“你”在一起,“我”就不會害怕,“我”和“你”就這樣永存下去,永恒地在這個世界舞動。分裂心理因為帶有對未知的恐懼,所以是痛苦的,但也是展開探索與追尋工作必不可少的,所以也是幸福的。否定“你”的決定的同時,靈魂閃爍著積極追尋自我的努力。殘雪認為“過程就是本身,目的是無,因為人最終是無,生命就是一個過程,永遠要找,永遠要那個東西,那是一個理想”[3]51。是停留在原地,還是展開積極的行動去追尋,也是女性當前所處的生存困境。現代女性有充沛的情感與浪漫的幻想,但也清楚現實的殘酷嚴峻。她們在分裂心理下不斷自審,冷靜地剖析自我也是一種追尋自我的過程,從而積極地去作出決定、展開行動。“女性生活在變動不居川流不息的大千世界里,要想在這個世界上尋找并確立自我的人格與價值,既不能靠天賜,也不能指望別人給予;不僅必須靠自我奮斗來實現,還須靠自我批判來激勵。女性角色的文化解放必須依賴于女性自主意識與自審意識的雙重確立。”[8]157女性要明白“我就是我”,要尋求的并不是像男人那樣做人,而是要“做自己”。追尋,是追尋真、善、美,追尋愛與溫暖,追尋生存意義,也是追尋自我的過程。靜止的結果是保持現狀,一味地等待不會等來理想的結果。因此,即使追尋的過程漫長而望不見頭,即使在追尋的過程中會遇到很多困難,女性終要依靠自己,追尋屬于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