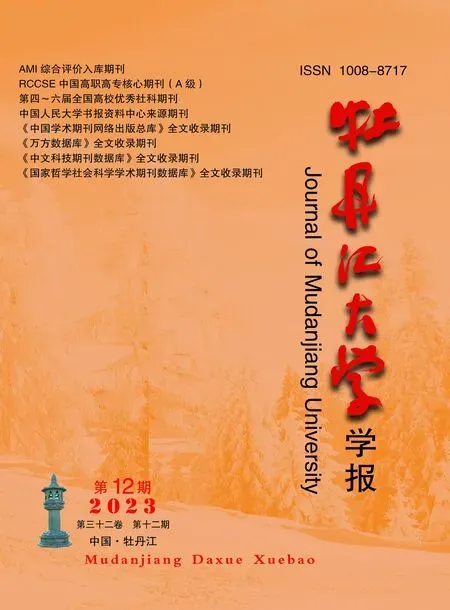張謇實業救國的思考
——企業命運與國運的關系
陳冬雪
(中央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081)
張謇,1853年出生于海門長樂鎮,是我國近代著名的實業拓荒者。毛澤東在全國政協會議期間,會見民族工業代表人物時曾說:“講到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習近平總書記赴南通考察,贊揚張謇是民營企業家的楷模,愛國企業家的典范,號召企業家向張謇學習[1]。縱觀張謇一生,以救國為起點,將愛國的紅線貫穿始終,開辟了無數新路,加速了南通的發展,推動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現階段,中國正處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期,研究張謇實業救國思想,學習張謇愛國精神,對激發人民的愛國熱情,發揮人民力量,推動中國發展意義重大。
一、實業救國的緣起
思想既源于實踐,又指導實踐。思想的萌發是主觀與客觀雙重作用的結果。張謇實業救國思想的提出,既受到儒家傳統文化的影響,又受到民族資本發展的推動,更是深處國家危難之際做出的現實抉擇。
(一)儒家傳統文化的塑造
儒家傳統文化的影響是張謇形成實業救國思想,踐行實業救國擔當的重要原因。文化對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張謇前半生都在全力備戰科舉考試,都是在學習儒家經典中度過。張謇3歲始讀經書,5歲進入私塾,15歲時完成四書五經的學習,42歲考中頭名狀元。由此可見,張謇從幼年到中年經歷了近40年的名教生涯。究其前半生,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也許不是他42歲時的考中,而是他所走過的漫長的讀書生涯和經歷過的冗長的科舉考試。長年累月的理論學習和實踐經驗的探索積累致使張謇滿腹經綸,儒學成為其知識構成的核心。他踐行著儒家經典所強調的經世致用的品格和剛健有為的價值追求。一方面,儒家經典的長期學習浸染塑造了張謇經世致用的實踐品格。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張謇,厭惡坐而論道,倡導經世致用,他寧愿做一絲一毫有用的小事情,也不愿意做只知道坐而論道的官員,力求改變以往知識分子在人民大眾心中只會坐而論道的刻板印象[2],主張“士負國家之責”。另一方面,深受儒家文化熏陶,造就其剛健有為的高價值追求。《周易·乾·象傳》中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取自積極向上,永不停止之意,也是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一個重要方面。儒家文化強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每個人都是責任的主體。張謇在此思想的指引下將其剛健的品格展現得淋漓盡致,也正是在這種家國責任感的驅使下興辦實業的,正如他在代吏部侍郎所寫的書稿中提到的“天下事成敗在人,而所以成敗者天”[3]。認為事物的興衰成敗在于個人,表現了其強烈的責任意識,這為他后期興辦實業,挽救國家危亡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二)民族資本發展的推動
民族資本的產生發展為張謇的實業救國思想奠定了社會基礎。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民族資本開始逐漸發展,它雖實力有限,但影響巨大,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傳統人士的傳統價值觀念,為民族資本的產生奠定了基礎。一方面,甲午戰后,救亡圖存的愛國浪潮洶涌澎湃,能人志士紛紛涌入,民族資本迅速發展。以上海為中心的三角洲地區,如火如荼地進行著辦廠熱潮,不久之后這股熱潮就涌入到了張謇的家鄉——南通。在辦廠的熱潮中,張謇走上實業救國道路也就更加順理成章了。另一方面,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面臨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束縛,如何擺脫束縛、減少壓迫,獲得某一方面的支持似乎變得必不可少。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渴望得到清政府的支持與庇護,但是洋務企業的失敗又讓人們懼怕與清政府的交往,甚至將日常與官府交涉視為畏途。因此,他們迫切需要一種力量既能保護他們免受官吏的騷擾與苛捐,又能獲得政府的必要支持與保護,士紳階層則成為最好的媒介,當時既受官府愛戴又受大眾歡迎的張謇則成為了不二選擇。這恰好又與張謇所主張的“商自經營,官為保護,紳通官商之情”理念相一致。他們心中的理想方案則都是各司其職,既各自獨立,又彼此聯系。如:“商管銀錢帳項買賣,紳管學習機器教訓學徒,官主保護而不侵權,即有事涉衙門,有紳承當不累商民,無所疑懼。”[4]張謇與其他一些開明紳士應運而起,既向政府為民間資本發展謀取更大的便利自主權,又為政府向民間募集資本。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張謇走向了實業救國道路,這是符合時代潮流的必然選擇。
(三)時代危機的催促
張謇所處的是內無和平,外無國權,外國資本加緊侵略中國的時代。甲午的戰敗,《馬關條約》的簽訂是張謇下定決心走向實業道路的直接原因。他曾上書請求推遲換約時間,也曾“臺民布告天下之文”,但都未改變簽訂喪權辱國條約的結局。在得知條約簽訂的當晚,他一字一句地在日記上記錄下合約條款的內容,并在旁注明:“幾罄中國之膏血,國體之得失無論矣。”[5]認為條約的簽訂,賠款的危害,幾乎是耗盡中國所有的血汗,也未曾考慮國家體制的得失。張謇認為不讓洋商在中國內地建廠是普通百姓謀生的一線生機,現如今,簽訂了通商新約,利益被各國均沾,中國人民獲利的渠道大大減少。針對此次合約的危害,張謇曾指出:“此次和約,其割地駐兵之事,如猛虎在門,動思吞噬;賠款之害,如人受重傷,氣血大損;通商之害,如酞酒止渴,毒在臟腑。”[6]他認為此條約的簽訂在軍事上相當于將老虎放在了自身門口,賠償錢款給人民帶來沉重負擔,通商的危害則如喝了毒酒,更是傷害五臟六腑。資本滲透是“心腹之患”,“以我剝膚之痛,益彼富強之資,逐漸吞噬,計日可待。”[7]條約的簽訂使得西方列強獲得了在中國合法辦廠的權利,為西方的經濟入侵大開方便之門。外國商品在中國肆意橫行,民族危機逐漸加深。面對危機的加深,工業的不興,許多愛國精英大呼發展實業以挽救國家,張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認為洋務派“以兵強國”“以商求富”只能輔助強國,唯有發展實業才能真正救國。這里的實業是涵蓋農、工、商的新式實業。由此,張謇在時代危機的催促下走上了辦廠救國的道路。
二、實業救國思想的實踐
張謇既繼承了早期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思想,也借鑒總結了西方資本振興實業的成功經驗,并結合當時中國的具體國情提出了實業救國的方法策略。張謇具有宏觀的實業思想,所進行的實業實踐范圍廣泛,涉及工業、農業、商業等多個方面。
(一)工業救國:大興棉鐵主義
吳昌碩先生曾在張謇的挽聯中寫道:“ 救世曰棉鐵政策,縱更世變,此語可長懸國門。”[8]這既是對張謇事業精髓的寫照,也是對張謇一生貢獻的概括。張謇主張以實業救國家,以棉鐵興實業。所謂棉鐵主義,廣義上是指輕工業和重工業,狹義上則是指棉花和鋼鐵,這既是張謇實業救國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畢生所實踐的重點。棉鐵主義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第一,從西方發展資本主義并取得成就的經驗來看,重視棉鐵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棉和鐵在工業的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棉是人們生活所需的必需品,也是聯系農業和工業的橋梁與紐帶。鐵是工業生產的基本資料,是國家工業體系的基礎,連接著眾多工業部門。第二,棉鐵主義的提出是資產階級改良思想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早期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就已將眼光投向商業,特別是注重商品的流通,強調了商業的重要性,但是過于片面地強調了流通的作用,忽視了生產的作用。張謇認為當時中國的出路在于工業,而工業的出路則在于棉鐵。因此,他的目的是發展中國的輕重工業,建設近代的工業化國家。第三,中國的棉鐵業受資本入侵的影響最大。中國在對外貿易中長期處于逆差地位,尤其棉鐵進口眾多,可見棉鐵所被分利最多,受資本主義侵略最大,“進口貨之多,估較價格,棉織物曾達二萬萬以外;次則鋼鐵,他貨物無能及者。”第四,發展棉鐵有利可圖。從當時中國現有的經濟基礎和現實國情來考量,棉鐵二者不可齊頭并進,理應有所側重。棉作為紡織的基礎,強調輕工業;鐵作為工業的基礎,強調重工業。張謇抓住了近代發展民族工業的重點,關鍵在“農工商之至大者曰棉鐵”[9]。即,要以棉鐵為中心,圍繞其建立一系列的工農商部門來振興實業,發展近代民族工業。相較于發展鋼鐵業而言,棉業發展周期短,利潤較高,而且通州的產棉基礎好,可利用當時優越的地理條件發展棉紡織業。反觀發展鋼鐵工業,需要投資金額較大,收益周期較長。因此,張謇率先發展了棉紡織業。張謇的看法和觀點是正確的,在中國政治飄搖、經濟落后的大背景下,優先發展需要耗資巨大的重工業并不可能成為現實。因此,張謇從棉紡織業入手,他認為棉織業“ 需費無多而收效最速”,所以他創辦了紗廠,獲得了巨大的收益。
(二)農業救國:興辦墾牧公司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既關乎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也關乎各行業的發展問題。張謇出身農家,深知農事之苦,認為中國人民飽受西方欺凌的原因在于中國農業生產的落后。因此,他高度重視農業,視農業為實業的基礎。“天下之大本在農”,“國以農工為本”[10],他對農業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在此基礎上,他提出改良農業,既在理論上提出新的農本思想,又在實踐中積極踐行大農業方針。張謇創辦大生紗廠需要優質的棉花原料,既為了給自己企業提供原料,也為同西方資本爭奪“通產之棉”。張謇興辦多個墾牧公司,他先后創辦20多個鹽墾公司,投資更是高達2119萬元。在墾牧公司的經營方面,張謇向往資本主義性質的大型農場。張謇的農本思想與傳統意義上那種“農本商末”思想有著根本的不同,他雖認為農業很重要,但是商業也同樣重要,農業是商業的原料來源。他明確指出:“天下之大本在農,今日之先務在商,不商則農無輸產之功”[11],可見他雖重農卻不抑商。張謇的農業思想并不局限于土地和種植兩個方面,而是一種大農業思想,涉及到農林牧副漁等各個方面。他重視農業的循環生產,如在《通海墾牧公司集股章程啟》中提道,將畜牧列在種青的后面,種植棉花、大豆、粟、麥的前面,畜牧所產生的肥料,既可以改良土地,畜牧所賣的利息又可以疏通渠道[12]。他也非常重視林業的發展,是我國植樹節最早提倡者之一。他認為我國森林采伐嚴重,國家應該加大經營,獎勵種植樹木。他還提出具體的舉措,如根據造林的面積和種植株樹的多少,分等級進行褒獎[13]。其對林業的重視可見一斑。面對清末時期日俄侵略我國東本,大肆砍伐掠奪我國林木資源,張謇主張加大東北森林資源的開發與監督保護。張謇也很重視漁業,面對德國在我國膠州灣強設漁業公司,張謇主張開辦我國漁業公司,減少列強對我國漁業的經濟侵略,并且主張:“各省派兵兵艦為周巡保護,其費由漁業公司酌量籌助,在國際則保有海權,在外交則稍伸公法。”[14]
(三)商業救國:農工商一體化
商業與工業有著密切的聯系。黃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維新思想家喊出“振興商業”,康有為提出“興實業”,這些人的主張都沒有準確把握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直至張謇提出“實業救國”,他將實業與救國相提并論,認為發展實業可以挽救國家危亡。針對商業救國論,張謇曾發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務立國,此皮毛之論也,不知外洋富民強國之本在于工”[15]這樣的感嘆。即世人以為西方立國的根本是商業,但這只是看到了其外在的皮毛,工業才是西方立國的根本,西方國強民富的根本在于工業的強大。他雖重視工業,但并非片面地反對商業,而是批駁有人混淆了農、工、商三者的關系。他對三者的認識十分清晰,他認為“蓋農不生則工無所作,工不作則商無所鬻”[16],即沒有農業則無法生產,無法生產則無法買賣通商。因為當時的工業原料主要來自農業,商業發展的來源是工業產品的制造。張謇非常重視商業,將振興商業提高到保護國家、維護主權的層次上來,甚至還發出了“以商界保國界,以商權張國權”號召。為了振興商業,張謇也采取了一些舉措,如他倡議在各省設立商務局,在貿易興盛的地方設立“商務公所”,等等。張謇重視商業還體現在經營大生紗廠時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上。張謇處在西方貨物充斥中國市場的時代,他深知只有不斷學習增強國人的商戰意識和商戰知識,中國的商業才能獲得較快的發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在某些方面張謇也積極效仿“西法”,如創辦股份制公司,創新企業經營管理模式,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發展全鏈條式企業,形成以大生集團為中心的企業集群,都是張謇重視商業,以求以振興商業來達到挽救國家危亡的目的。
三、張謇實業救國的評價
張謇以愛國為出發點,以救國為目的,創辦了一系列企業,興辦了一系列教育、慈善公益機構。胡適曾評價張謇“偉大的失敗的英雄”,他認為張謇開辟了無數新路,興辦了實業教育,幫扶了一眾人民,是非常成功的。但同時是又失敗的,他的失敗則是由于實業擔負過于宏大,最終未能一一實現,最明顯的則是大生紗廠最終被銀團所接管。胡適的觀點也是目前學界普遍認同的觀點。但評價歷史人物不能離開其所處的時代,時代的不同,得出的結論不免帶有局限性。所謂的失敗更多的是指大生紗廠被外國銀團接管,但無論是胡適還是眾人都沒有站到當時的背景下去考慮、去評價,畢竟胡適評價張謇時距離當時事件的發生已過去數十年,任何人都沒有辦法完全公正客觀地去評判,只能最大限度地減少自己的主觀意識來進行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從大生企業的發展和影響來看張謇是成功的。他雖命運多舛,但其精神永存。
大生集團經歷了從初創到發展,從發展到繁榮,從繁榮再到易主的三個過程四個階段。第一,從企業自身看。企業本身并非沒有資金,也不缺乏資金生產的能力,而是將資金墊付在其他實業公司和地方慈善公益上了,又加之一廠、二廠既沒有公積金存款,也沒有流動資金可用,所以出現了大生紗廠一廠、二廠的負債現象。因此,企業的自身并沒有問題,甚至可以說是其他實業拉跨了大生集團。第二,從被銀行接管的紗廠經營狀況來看。評價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結論也各不相同。從企業的歸屬來看,張謇喪失了企業的歸屬權,從短期來看的確是失敗的,企業發生了易主。但是從長期來看,這并不意味著真正的失敗。多數企業都要經歷一個起伏的過程,大多企業的壽命都是有限的,如“跨國企業的平均壽命是四十到五十年,美國企業的平均壽命是8年,甚至62%企業的壽命不足五年,一般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是三到四年”[17],但是大生集團企業的平均壽命是五年,可見大生企業的不凡。第三,從企業經營實力來看。紗廠的歸屬權雖然有所改變,但是企業的經營實力依然存在。如大生一廠被接管后,雖有困境但仍在獲利,紗廠易主后仍獲利頗豐,離不開張謇當時奠定的基礎,正是張謇大力推廣種植優質棉,大大降低了原料成本及對外的依賴。第四,從大生紗廠的影響來看。大生紗廠無論是對當時的紡織業還是現代的紡織業,甚至對整個近代工業的發展都有著不可磨滅的正向效應。
事物的發展變化是內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大生紗廠歸屬權的改變是資本積累不夠、經濟基礎薄弱、經營管理不善、社會制度腐敗、國家動蕩不安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紗廠被銀團接管是外部環境不善所造成的。當時國內國際形勢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國內政府的腐敗,國外列強的入侵壓迫,引起了棉紡織市場的變動,到了1922年紗廠虧損更加明顯,如“每生產一包16支紗,便會虧損14.75兩”[18],這并不是張謇創辦的紗廠所獨有的現象,而是國內各個紗廠所共有的現實情況。因此,不能把紗廠虧損易主的責任完全歸咎于張謇,根本原因在于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和國際經濟形勢的壓迫。因此,張謇是成功的,張謇的實業救國精神更是值得被永久銘記的。
四、有關張謇實業救國的思考:企業命運與國家命運的關系
(一)國運造就企業
企業命運與國家發展息息相關。企業的良好發展需要社會的穩定和國家政府的支持。張謇棄官從商,走向實業,既是張謇的個人抉擇,也是符合時代發展潮流的必然選擇。張謇曾言:“大凡失敗必在轟轟烈烈之時”,1922年,正如張謇所預料的那樣,他的實業開始由輝煌走向了衰敗。事業的衰敗雖有經營不善,被地方公益慈善所拖累之因,但究其根本還是當時社會大環境導致了大生紗廠的易主。大生紗廠位于通海地區,農村紡織業基礎好,既有豐富的原料基礎,又有一定的技術基礎。大生紗廠的機紗70%為專供關莊布的原料,而關莊布又以東北為銷場。隨著日本入侵東北,關莊布的銷量驟減,日本在東北口岸進口棉布由1913年的100萬上升為1922年的124萬。關莊布輸送到東北的數量則由1920年的157 400件下降到104 348件,關莊布逐漸被排擠出中國市場,這直接導致了大生紗廠的虧損。由此,張謇的商業帝國也開始逐漸衰落。日本在商業上取勝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機器技術的先進,而在于日本侵略者通過簽訂不平等條約形成了部分壟斷,而且還把持著海關和金融物價。將張謇與日本實業家澀澤榮一進行比較就會發現,澀澤榮一的成功和大生紗廠的易主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是否擁有政府的援助與支持。政府助力的缺場,民族市場保護的缺乏,使得關莊布在東北失利,從而導致大生紡織系統受到災難性影響,大生企業集團也不免受其所累。當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運動蓬勃開展時,企業就會獲得蓬勃發展的機會。當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運動稍有松懈,給了帝國主義可乘之機時,中國企業就會面臨巨大的生長壓力。如甲午戰后,中國救亡圖存運動蓬勃發展,企業相應地也獲得了較好的發展機會,就在這時大生紗廠趁勢而起,抵制歐美日貨運動聲勢浩大,民族工業不斷興盛。歐戰發生時,帝國主義列強無暇東顧,大生紗廠獲得了較好的發展機會,整個民族工業也大為發展。歐戰之后,帝國主義列強卷土重來,加之國內的災荒不斷與軍閥混戰,導致經濟落后,大生紗廠破產。由此可見,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敗最終導致了大生紗廠的衰敗。
(二)企業折射國運
企業的命運折射出國家的命運,企業的發展展現出國家的實力。孟晚舟被困1028天后平安歸國,展現了中國的強大實力,正如孟晚舟所言:“祖國是我們最堅強的后盾,只有祖國的繁榮昌盛,企業才能穩健發展,人民才能幸福安康。”每一個企業健康發展的背后都離不開國家的支持與保護。張謇大生紗廠的衰敗是當時社會背景下國家落后、政府無所作為的必然結果,華為科技水平的不斷提高,是中國政府強大后盾的顯現。企業的良好發展可以為國家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企業的健康發展展示出國家的強大實力,可以彰顯國家的實力水平,進而影響國家的命運。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國制造業穩居世界第一,中國制造業屢創奇跡,牢牢站穩世界C位”,顯示了我國的制造實力,奠定了我國制造業強國地位的基礎,企業的蓬勃發展預示著國家興旺發達的前途命運。總而言之,企業與國家共生共榮。國家的成功依賴企業的良好發展,企業的健康發展取決于國家的成功。國家大環境對企業的影響是巨大的,現階段的中國同近代社會中“實業救國”的背景完全不同,現在中國有著先進的技術,穩定的環境,為企業的健康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平臺與機會,讓每一家企業都有機會大有可為。任何企業都不可能孤立于國家之外,要有社會擔當,要做利國利民之事,不要做害人害己之事,要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為國家發展貢獻力量。
(三)國運與企業命運同頻共振
一方面,企業的發展離不開國家的穩定與庇護。正如威廉·鮑莫爾等學者所認為的,企業家精神的發揮,企業的進步離不開一個穩定、法治的社會環境。也正如亞當·斯密所提出的,國家具有保護社會安全、人民不受欺辱、建立某些公共機關和公共工程的職能,有責任也有義務為企業的健康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大生紗廠失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國家的衰敗不堪,缺乏穩定的社會環境。由此可見,只有國家強大、穩定,企業才能健康發展。企業的發展離不開國家的支持與援助,企業與國家榮辱與共。通過將張謇與澀澤榮一對比,我們就會發現國家政策、政治制度和社會際遇都對企業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首先,從國家的政策方面來看。張謇與澀澤榮一都出生在富裕小農家庭,同樣遇到國家被侵略,心懷攘夷的心境,但是國家資本積累水平的高低和國家實行的對待政策不同,最終導致了二者興辦企業最終命運的不同。澀澤榮一34歲辭官從商,他認為發展商業最重要的是建立現代金融制度,很快明治政府就采納了其意見并且積極完善金融制度。因此,以澀澤榮一為首的許多日本企業家可以利用積累的資本發展企業。反觀中國的張謇,清政府不僅對金融無能為力,而且更是無從籌措資金,將發展企業、振興實業的重擔全部落到企業家自身的肩上。其次,從社會際遇方面來看。澀澤榮一比張謇所處的機遇要好得多。一方面,他在28歲時就有了出國學習增長見識的機會,而張謇究其一生只有51歲時出國去日本學習參觀了兩個月,并且澀澤榮一學習歸國后,政府急攬此類人才,澀澤榮一進入政府,明治政府重視人才,任人唯賢的精神可見一斑。另一方面,反觀張謇,多年科考未中,得中之時已到中年,在此之前可謂滿腔抱負無從實現。澀澤榮一經營了500多家企業,組成了屬于現代產業的重要部門,張謇的實業活動則只局限在固定的范圍領域,偏僻的農村,限于紡織業等輕工業部門[19]。最后,從政治制度來看。政治制度對企業發展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張謇因制度的限制不得不停止企業經營,對限制其企業發展的官僚制度進行批判,如立憲運動、地方自治等,不得不既操心經濟又操心政治,為這兩方面的現代化而努力,而日本主張通過改革促進企業家的活動,澀澤榮一只需要專注于經濟的現代化就可以了,二者興辦企業的結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