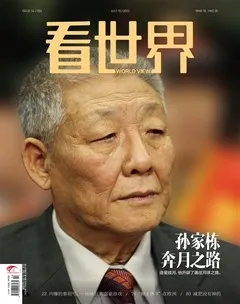來自加爾各答的文藝“廢青”
索那瑜

2022年2月26日,印度加爾各答,街道上的彩色涂鴉
我的許多現年40余歲依然頹廢的印度文青、廢青朋友們,大多來自加爾各答。他們才華橫溢卻沉溺于酒精與毒品,頹廢在家里,吃家里的、用家里的,卻對爸媽很不客氣。他們是印度“垮掉的一代”,或者應該說,他們是“垮掉一代”的下一代—更垮的一代。
“文”青是文藝復興的孩子,印度的文藝復興則是英國殖民主義的逆子。英屬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殖民起始于孟加拉地區的加爾各答,西風自此吹入南亞大陸,帶入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西方理性、自由、民主的價值。
一般認為,孟加拉文藝復興運動由18世紀理性主義社會改革者與反殖民運動者拉姆·莫漢·羅伊(1772—1833)開啟,一直到20世紀詩人泰戈爾(1861—1941)達到頂峰,是豐富且矛盾的運動:一面羨慕與吸收著西方的文明,一面“發現”屬于自己“東方”的獨特價值,在反西方中西化,在反殖民中走向現代。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加爾各答的街上,有許多洋腔洋調,穿西裝、彈鋼琴、拉小提琴、愛好文學、喜歡高談闊論的“拔卓佬”(Bhadralok)。拔卓佬字面意思是“舉止優雅之人”,其實是個反諷,指的是特別造作、自以為比他人高尚文明的有錢大佬。
文藝復興的遺產在今日依然可見,孟加拉人崇尚人文,婚喪喜慶常以大套書籍為禮品。“書”是階級與文化的象征,也是極為高級的“家飾”。

詩人泰戈爾

理性主義社會改革者與反殖民運動者拉姆·莫漢·羅伊
“小叔叔”赫伯特
印度加爾各答“垮掉的一代”指的是1947年印度獨立后出生的一代,他們之中許多人是在難民營長大。
印度獨立是個應該集體哀悼的事件。英國殖民時期的孟加拉邦被分割成東西兩半,東部歸給以回教徒為主的巴基斯坦,名為東巴基斯坦(而后爆發解放運動,巴基斯坦獨立立國,為今日孟加拉共和國),西部則屬于印度教徒為多數的印度。大多數的回教徒遷移到東孟加拉,印度教徒往印度遷移。
印巴分治是人類史上慘絕人寰的百萬人大流亡,期間發生無數印度教與回教徒的沖突,數十萬人死亡,許多女人在遷移前就被家族被迫“自殺”以防旅途中她們的貞節受損。本來屬于拔卓佬天下的加爾各答,在獨立后瞬間變成巨大的難民營,到1970年代,來自東孟加拉的難民高達500萬人。
這些在獨立后出生的孩子們在文化與政治皆動蕩的70年代正值叛逆的青春時期。蘇曼·穆霍帕迪亞導演的孟加拉電影《赫伯特》(2005)把這一代人的瘋狂、荒唐與失落描寫得極為入微。
主角赫伯特的爸媽是典型的拔卓佬,爸爸穿西裝打領帶非常帥氣、媽媽身著印度紗麗甚是嬌媚,他們將自己的第一個兒子取了洋人的名字“赫伯特”。爸爸是位電影導演,家中時常派對夜夜笙歌,他也常在片場與女演員打情罵俏。赫伯特的父母早死,電影以爸媽的鬼魂在空中拍攝兒子的一生來呈現,也象征著“垮掉的一代”活在燦爛輝煌的文藝復興爸媽的目光下與陰影中。
赫伯特自小是個“文青”,如有激動之情,則寫詩抒發。他的“神秘的長大”是從接觸馬克思主義開始。印度獨立后,西孟加邦有很活躍的左派運動,孩子們自小從大人那里獲得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品。1967年納薩利地區農民武裝起義激發了70年代的加爾各答青年反抗運動,一面讀書、吟詩、喝酒狂歡,一面密謀槍支運送、埋設炸藥等事務。加爾各答遍地烽火,中學生與大學生時常在街頭與警察玩捉迷藏。
赫伯特年紀比反叛的孩子們略長10歲,屬于他們的“小叔叔”,走路和長相都非常怪異。跟在反叛的隊伍中,意外發現自己與死者對話的特異功能。大家伙因而起哄,做起裝神弄鬼通靈的生意,一面通靈騙錢、一面喝酒搞革命。
不久,赫伯特被科學運動理性主義者舉發,勒令歇業,心生絕望,割腕終結生命。弟兄們組成送葬隊,搖旗吶喊一路喧鬧,一路抬著赫伯特的遺體與床墊送入焚化爐。這一瞬間,床墊爆炸了,原來,內有炸彈。警方納悶,這位死者究竟是哪里來的恐怖分子?電影,是從這里開始說起的……
“接送”勒戒所
我的文青朋友巴蘇,今年43歲,差不多也是“小叔叔”赫伯特的年紀,如今已戒毒8年,一面在勒戒所工作,一面寫小說、寫兒童廣播劇、偶爾與朋友一同拍小電影。這幾年他時常把吸毒的文青朋友們“接送”去勒戒。
“接送”原文是英文“pickup”,在此,是印度勒戒圈的“行話”。“接送”顧名思義是把吸毒者接去勒戒中心,然而這個過程操作起來并不輕松,通常是由爸媽與勒戒中心密謀,在吸毒者半夜昏睡的時刻將數名來自勒戒中心的大漢放入家中,潛入房間趁其不備將其抓上車。如果時機沒算準或就是運氣不好,“接送人員”沖進房間時對方恰巧醒著,就不免一陣拉扯與拳打腳踢。“接送”工作風險很高,通常由“專業”人士負責。
印度加爾各答“垮掉的一代”指的是1947年印度獨立后出生的一代,他們之中許多人是在難民營長大。

1900年,加爾各答街上的“拔卓佬”
勒戒中心如同監獄,一旦進去,至少3個月,通常長達1年,其間親友只能在特定時間探望。勒戒中心聚集的多是戒毒多年已被社會邊緣化的粗漢,他們平日很少講英文,但有趣的是,他們的“行話”里面卻有“pickup”這么一句英文。
某日我的朋友巴蘇徹夜難眠,因為他為好友魯督爾安排了“接送”。這個安排的念頭起緣于他的另一個好友近日因用毒過量意外過世,為了避免同樣的悲劇重演,巴蘇決定找魯督爾地父母商量,共同做出如此決定。
巴蘇可以把小弟當成人肉書架,小弟頭頂著書,方便大哥邊走、邊吸煙、邊閱讀。

孟加拉電影《赫伯特》劇照
巴蘇的第一部實驗性短片作品《永遠不再》拍攝于2007年,亦是紀念他另一個吸毒過世的朋友。而那段時期,巴蘇自己也沉迷于煙酒毒品,為了獲得足夠的煙酒,他加入地下組織,獲得“同志”們悉心的“照顧”。他跟著人們到鄉村地區做組織工作,某日半夜酒醒到草叢撒尿,不慎踢到地上一大包硬物差點摔倒,一看,原來是一大包槍支。
巴蘇的爸爸屬于地主階級的婆羅門家庭,媽媽來自東孟加拉,小時候在難民營長大。媽媽那頭的親戚們住在難民營,居住環境的簡陋與骯臟與巴蘇家里有天大的差別,巴蘇小時候若去難民營營區找表哥表弟玩耍都會盡量避免上廁所,從小他就學會長時間憋屎憋尿。巴蘇自己家坐落于加爾各答的核心老城區,他自小是孩子王,也是爸媽眼中的天才。
7歲時巴蘇寫了首孟加拉文的短詩,被刊登在雜志上,也常率領街坊的孩子們把電器都拆開來研究,做各種荒唐的實驗。在大家都還在唱泰戈爾歌時,10多歲時巴蘇已懂得聽巴布·狄倫、李歐納·柯恩、平克·佛洛伊德與披頭四,懂得讀《百年孤寂》。不過,加爾各答的文青不是憂郁多愁、離群索居那一類人,他們永遠呼朋引伴、總是結黨營私。
“你是我的英雄”
20歲時,巴蘇組成文藝小幫派“世界”,自己當老大,有好幾個聽其使喚的小弟。大哥不僅提供煙酒大麻的服務,也教導小弟們如何寫小說。小弟對大哥唯命是從,例如巴蘇可以把小弟當成人肉書架,小弟頭頂著書,方便大哥邊走、邊吸煙、邊閱讀。他們甚至制作了一份“入會申請書”,只有“荒唐度”達標者才有資格入會。
不過也有煙酒不沾的禁欲文青。例如《永遠不再》的音樂配樂者什洛夫,大學主修物理,畢業后“廢”在家里過著修道人般自我規律的日子。他潛心研究物理學與音樂并自學電吉他與編曲,創作許多融合東西方風格的樂曲,達到頗高的境界。
《永遠不再》如果沒有他的配樂,將遜色許多。什洛夫父親早逝,母親獨自撫養這個文青米蟲,頗為認命,從不指望兒子找工作賺錢養家。在加爾各答,許多家庭都有這樣的不知是清醒還是瘋癲、上進還是頹廢、有用還是無用的孩子。
與70年代轟轟烈烈的文青相比,巴蘇這一代人凄涼許多。大革命的時期已經過去,他們擁有的是小瘋小癲、小文學小電影與酒精毒品帶來的小刺激。關于“世界”,無論是想要創作世界文學還是制作世界電影的雄心壯志已成一場虛夢。
夢醒的巴蘇把同樣迷惘的兄弟們一一“接送”到勒戒中心,在勒戒所中建立早睡早起、每日清潔打掃的僧侶般或監獄式的集體生活,他自己也不免要定期經歷一次次自我懷疑的危機,一次次與自我摧毀的沖動對抗,在“一天過一天”中尋找微小的“活下去”的意義與價值。
我時常跟他說:“你是我的英雄。”這是句真心話。
特約編輯姜雯 jw@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