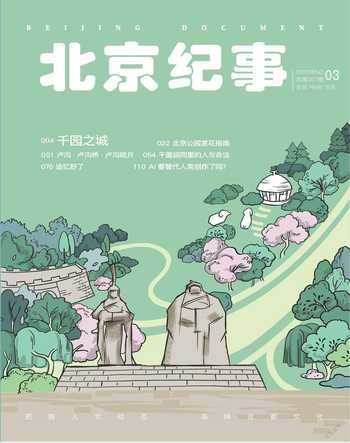時光里的摩天輪
姜思琪

車子在西五環的八角橋上飛馳,這是一座高架橋,兩邊是那么空闊,每走到這里的時候總有種飛上天際的錯覺。有一次孩子忽然指著遠處的摩天輪問我那是什么,臉上全是好奇和驚喜。孩子沒見過摩天輪,我并不感到驚訝,在他們這個聲光電器應有盡有的時代,摩天輪已經不足以成為那種強烈的吸引。孩子說它好像一個巨大的表盤,只是時針太多了,看不出它指向的是幾點。我忽然一驚,是啊,每一條橫臂都是它的表針,它就這樣不緊不慢地走著,看不出流轉,卻偷偷帶走了年華。
1986年,長安街西邊豎起了一座摩天輪,與南邊龍潭湖的北京游樂園摩天輪遙相呼應,成了西邊的制高點。如果說依湖而建的北京游樂園天然帶著一種逛園子的親切,那么石景山游樂園就是當時最摩登的。一水的歐式建筑,有古堡、鐘樓、吊橋,有哥特式的尖頂屋子,有仿大理石的巴洛克式噴水池,長著翅膀的“卷毛兒”小天使雕塑偶爾出沒在草叢里、甬路旁,國際復古范兒十足。那時候的北京人還沒怎么見過洋樓,在改革開放不久建了這么一座沾著“洋”氣的游樂園,可想而知得有多火爆。
石景山建園的第二年我才出生,我和這座摩天輪算是同齡人。
90年代坐過摩天輪的孩子,現在都成了孩子的爹媽,那時候對去一趟游樂園的期待猶如去赴一場隆重的、百年不遇的盛事一樣。假如從前問我:是去坐摩天輪,還是去看奧運會開幕式?我一定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那時的孩子生活很簡單,家門口的小花園一跑就是一整天,干脆面里攢的“水滸卡”也能擺弄一上午。游樂園是遠在天邊的,不看電視廣告根本就不知道,看了就放不下。有一陣子,每天晚間新聞的天氣預報總要報一句:石景山游樂園氣溫多少度,背景畫面里那座摩天輪就牢牢地種在我腦子里,像一個揮之不去的夢幻,時不時就來撓一下。
那時候住在首鋼大院的孩子得有多幸福,對于我們這樣家不住在西邊的孩子,能去一趟石景山,真就比過年還要興奮了。后來我父親調到首鋼廠工作了一陣,每周末我們能去看他,也就能有機會去游樂園。那時候從南邊奔到西邊堪比登天,要倒好幾趟公交,最后輾轉坐上一號線就算大功告成,即便這樣,有游樂園在前邊等著,翻山越嶺也不嫌累。
從地鐵出來的那一站叫“八角”,一直覺得這地名很奇怪,既沒有遍地賣茴香大料的,地形也不是有著“八角”的八邊形,后來一查地方志才知道,這地方很有歷史。八角村的祖先是明朝時候從山西洪洞大槐樹遷來的,來的時候有八個姓氏的大家族,所以開始叫“八家子”,“八角”是洪洞縣的口音,叫著叫著被訛成了“八角”,地名就這么語焉不詳地傳了下來。后來的公交地鐵站名上在“八角”的后面加了一個“游樂園”,洪洞縣的先人已進了典籍,家族印記卻從歷史里被帶到了現代,“八角游樂園”這個站名一直保留著。以至于很長時間我認為石景山游樂園是八角形狀的,像古代算八卦時擺的某種陣仗,這種帶著威儀的神秘感增加了我對它的崇拜。
第一次坐摩天輪是哭著下來的,不知怎的原本那么期待,一見它就腿軟了,而且越走近越被震懾得瑟瑟發抖。90年代的孩子,還沒怎么見過這樣的龐然大物。老摩天輪的艙是鐵架的,四面的玻璃門顯得挺單薄,等到艙轉到眼前的時候會有點輕微的共振,一開門四面玻璃顫巍巍的嘩嘩作響,生怕會散了架。越往上升高就越不能平靜,電機聲一直嗡嗡的,老怕它不轉了或者突然加快速度,可它仍舊慢悠悠地轉著。越慢越不能踏實,云就這樣被踩在腳底下,那會兒的高樓還不多,最顯眼的就是中央電視臺,除了它就是一片矮平房,往下看只有空蕩蕩的云和大地,沒著沒落。父親讓我往遠處看,給我指首鋼,講那個高塔是干什么用的,讓我看遠處國貿的京廣中心,說那是京城的第一高度,告訴我家在什么方向……我根本聽不進去,一直閉著眼。不知道有多少孩子像我一樣沒出息,下來的那一刻就已經覺得挺丟臉的了。就這一次,喚醒了我的羞恥感,以致很長一段時間不敢再看它。
此后的日子,就這樣和它失之交臂了,就是去游樂園也再不提摩天輪的事。幸好除了摩天輪,還有游泳場。現在的露天游泳池幾乎絕跡了,一律被送進了穹頂暖箱里改良成了溫泉,舒適沒得說,但少受了一份在太陽底下暴曬的罪,就總覺得少了點什么。石景山就連游泳池也是帶著“洋范兒”的,當年的人造波浪池和沙灘就是今天看來也一點都不露怯,“激流勇進”是當年最時髦的,隊伍可以排成三道城墻。泳池是露天的,更衣室也略顯露天了點,弄幾個圍擋幾組木頭柜子就算是“更衣室”了。幸好小孩子不用更衣,泳衣套里面,忽沓忽沓的就去蹚水了。游泳場常是人山人海,太陽曬得沒處躲,一鉆進水里就什么都忘了。陽光下漫著消毒水味,那樣的空氣碰撞出一種最原始的純粹,那時候的快樂很簡單,用帆布鐵架圈出一塊池子就能樂一下午,北京孩子就是容易知足。
游樂園被一條鐵軌斜斜分割成了南北兩邊,也許是無奈之舉,建園的時候在這上面架了一座鐘樓塔橋作為連接,卻陰差陽錯的成了標志景觀,然而這條神秘的鐵軌直到現在也不知道它通向何方。從前有兩種猜測,其一是說它通往首鋼,大概是運材料一類的內部鐵軌。1990年代的時候很多人都有著對鋼鐵的記憶,廠房、大院、蘇式建筑的筒子樓、冷卻塔的大煙囪,還有熔鑄時的通紅與火熱。那個時代鋼鐵是希望與誕生,首鋼人是自豪的,懸于天際的摩天輪就曾是熔爐里的一塊鐵,它的每一條鋼筋都鑄進了汗水與熱愛,鐵軌上銹蝕的味道就是曾經的見證。
另一種說法是通往西山的,是地鐵一號線的一個秘密接駁口,這當然有點無稽之談,因為如今它已經廢棄不用了,成了“網紅”拍照地。從前下邊是攔著的,多年以后開放了,我第一次站在這條鐵軌上時,卻感到了一種手足無措:往前走或往后看都是茫茫無際,它的來處與去處只有遠方,不知道是時間把它帶來的,還是它要載著光陰到時間的盡頭去。與緩緩輪轉的摩天輪一樣,它們都應是時間的載體,它們會舊,可時間不會停,假如有一天鐵軌到了盡頭,摩天輪轉不動了,時間會搭載別的機器帶我們去遠方,直到“我們”也沒有了,就只剩下了遠方。
老摩天輪拆除的時候,石景山冷寂了。當天有很多人跑來合影,幾乎是沒有年輕人,要么鬢發星星,要么將軍肚滿,眼角的細紋已經藏不住年齡,還有人特意戴上了紅領巾,滿是滄桑的臉都笑得像個孩子。童年不該有眼淚,揮別的時候只可以帶走懷念。可對于我,或許連懷念都沒有資格,那唯一的一次父親帶我坐摩天輪,我都沒有睜開眼好好看。拆下來的舊鐵架艙各種顏色的遍地是,這里曾裝下一代人赤橙黃綠的各色的夢。
很長一段時間,石景山游樂園從我的生活里淡去了,即使在信息爆炸的當下,關于它的消息也是零星的,曾經有一陣子以為它閉園了,其實它一直還在,只是摩天輪沒有了。現在孩子們還是會去,只是我已經不再是孩子了。成長可能都要經歷這一過程,曾經特別在意的,忽然在某個節點上變得不再重要,那是因為生活的軌道已經改變,讓一個中年人再興致勃勃地期待坐一次摩天輪,難免會別扭得有些可笑。然而很多事會像一個結留在心里,說不清為什么。
首鋼廠也搬走了,留下舊的廠房和一些殘跡,像1990年代許多退下來的軍工廠一樣,紛紛改成了文創園區,供人們懷舊、瞻仰。滿是文藝范兒的園區是年輕人的最愛,可年輕人沒經歷過鋼鐵時代,他們沒有懷念,只有對那個時代的遙想。時間是公平的,一代人就應該有一代人專屬的記憶,正如日夜不停的摩天輪,這一圈的客人下了艙,再接上另一撥客人,看似是輪回,其實人已經改變了。
直到摩天輪復生了,我與它的重合又讓我相信生活更像是一個圓,這一回它更像是從未來過來的,艙體被設計成了球形,還用了單向透視的玻璃。沒想到第二次坐石景山的摩天輪卻是在而立之年以后,不得不說現在的孩子已比我們小時候強太多,兒子第一次坐摩天輪就興奮地讓我給他指這邊是什么地方,那邊是什么建筑。往東看去,長安街上的地標已經多到數不過來,車水馬龍,無限繁華,很多新蓋的大廈我都說不上名字。匆匆奔忙的車流是生活的酸辛,時尚的購物街上翻涌著熱辣,林立的寫字樓里交織著揮汗如雨的咸澀……站在摩天輪上面看它們,生活百味全變成了俯視。
孩子問我家在哪兒?我說順著中央電視臺往南看——越看越茫然,它已經不是唯一的高度了。我還想看看首鋼,可是已經被眼前的高樓“一葉障目”了。我原本以為跟著它轉一圈會喚回那些遙遠的回憶,誰知只是跟著它又往前走了一圈。也許正如孩子所說,摩天輪像一只時鐘,只知道不緊不慢往前走,人們可以一遍遍坐,它卻從不會停下來等著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