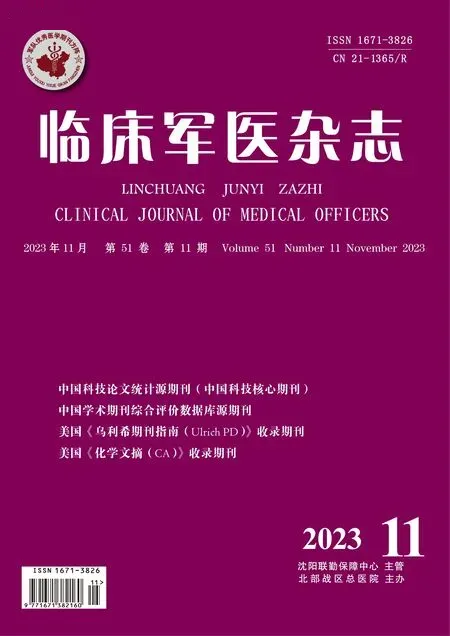腸道營養干預在中期肺癌患者中應用價值及其對生命質量影響
王 園, 楊 懿, 任福強, 牟云飛, 黃 鑫, 董 佳
1.成都市第三人民醫院 胸外科,四川 成都 610014;2.北部戰區總醫院 軍人門診,遼寧 沈陽 110016
肺癌是臨床較為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1-11],治療方法包括外科手術、放療、化療、分子靶向治療及免疫治療等,其中,放療和化療是中晚期肺癌的主要治療手段,是達到臨床治愈的重要方法。但在肺癌的發展過程中,患者當前或潛在的營養問題均會導致不良預后的比例升高。晚期腫瘤患者的營養風險發生率在40%~80%之間,機體營養狀態差會造成免疫功能下降,感染風險上升,隨之而來的是住院時間延長,家庭經濟負擔加重[12];同時,肺癌導致的營養不良會進一步造成患者生活質量下降,死亡風險上升[13]。我國的肺癌患者營養風險篩查及干預起步較晚,大多肺癌患者的手術治療、放療、化療的耐受能力較低,因此,在對肺癌患者給予常規抗腫瘤治療的同時及時實施相關的營養干預對于患者的預后意義重大[14]。腸道營養干預可起到保護中晚期肺癌患者腸道黏膜屏障的作用,有效調節免疫功能紊亂,具有較高的應用價值。本研究旨在探討腸道營養干預在中期肺癌手術患者中的應用價值及其對生命質量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成都市第三人民醫院自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收治的存在營養風險損傷的83例中期肺癌手術患者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確診為肺癌,肺部占位性病變,病理檢查為陽性[15];分期ⅡA~ⅢA期,接受了根治性手術治療;意識清晰,能夠溝通。排除標準:存在定向力障礙;站立姿態不穩定;進食障礙;大量腹腔積液;內分泌疾病造成體質量發生變化;水腫;近3個月大量使用糖皮質激素。將患者隨機分入常規組(n=41)和干預組(n=42)。常規組中,男性24例,女性17例;平均年齡(55.89±5.62)歲;平均體質量指數(23.55±3.47)kg/m2;腺癌25例,鱗癌12例,鱗腺癌4例;TNM分期ⅡA期8例,ⅡB期15例,ⅢA期18例;低分化15例,中分化13例,高分化13例。干預組中,男性22例,女性20例;平均年齡(55.33±6.07)歲;平均體質量指數(23.78±3.24)kg/m2;腺癌27例,鱗癌10例,鱗腺癌5例;TNM分期ⅡA期7例,ⅡB期14例,ⅢA期21例;低分化14例,中分化15例,高分化13例。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患者及其家屬均簽署知情同意書。本研究經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
1.2 研究方法 常規組接受常規飲食干預,干預組接受腸道營養干預。兩組均治療2周。常規飲食干預:根據患者具體的飲食習慣和口味愛好制定食譜,多進食蔬菜和水果;以高維生素、高蛋白飲食為主,禁食生冷、刺激性食物,加強營養儲備;對于化療患者,初期多飲水,增加木耳、芹菜、黃瓜、香菇、瘦肉等食物的攝入,保持大便的通暢。腸道營養干預:實施腸內營養支持治療,在術后24 h經口腸道營養治療,營養治療的配方主要以高熱量的蛋白質為主,蛋白質的配比按照1.5 g/(kg·d),熱量配比按照105 kJ/(kg·d),在對患者進行膳食指導的基礎上,采用脂肪乳、葡萄糖、乳清蛋白粉、微量元素等輔助治療。
1.3 觀察指標 比較兩組治療前后的營養風險評分、營養指標水平及生命質量評分。對入組患者開展問卷調查,收集一般資料,同時對其開展營養風險篩查。營養風險篩查主要利用營養風險工具進行,該工具是由歐洲臨床營養以及代謝協會提供的,主要包括疾病的嚴重程度、人體參數測量、體質量指數、近期的體質量變化情況、膳食攝入情況及年齡的評分,評分總分為7分。分別在治療前和治療2周后抽取患者5 ml的空腹外周靜脈血,用全自動生化儀(西門子公司)檢測血紅蛋白、轉鐵蛋白、總蛋白、白蛋白、前白蛋白水平[16]。分別在治療前和治療3個月后對患者的生命質量進行評價,評價方法參考文獻[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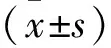
2 結果
2.1 兩組治療前后營養風險評分比較 常規組和干預組治療前營養風險評分分別為(3.88±1.18)分和(3.59±1.15)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常規組和干預組營養風險評分分別為(2.15±0.44)分和(1.48±0.57)分,均低于治療前,且干預組低于常規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2.2 兩組治療前后營養指標水平比較 干預組血紅蛋白、轉鐵蛋白、總蛋白、白蛋白、前白蛋白治療前后差值分別為(13.33±2.52)g/L、(0.86±0.23)g/L、(12.11±2.35)g/L、(15.04±3.52)g/L、(113.61±25.89)mg/L,均高于常規組的(9.25±2.32)g/L、(0.30±0.15)g/L、(6.84±1.80)g/L、(9.40±4.08)g/L、(71.68±27.08)mg/L,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2.3 兩組治療前后生命質量評分比較 干預組生理功能、生理職能、軀體疼痛、一般健康、精力、社會功能、情感職能、心理健康、總評分治療前后差值分別為(7.28±2.15)分、(11.34±2.82)分、(7.52±2.31)分、(10.85±3.11)分、(8.43±3.11)分、(16.35±5.51)分、(7.63±3.19)分、(10.18±4.09)分、(10.27±4.04)分,均高于常規組的(3.11±1.27)分、(5.04±4.24)分、(3.25±1.72)分、(3.73±2.29)分、(3.89±2.37)分、(8.03±5.22)分、(3.66±2.37)分、(5.27±3.24)分、(4.25±3.31)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3 討論
肺癌患者早期無典型臨床癥狀,容易被忽視,在確診時多數已進展至中晚期,無法采用手術治療,而多接受放療、化療等,可獲得一定的治療效果。化療治療中晚期肺癌雖然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疾病,但疾病仍會繼續發展;此外,肺癌屬于慢性消耗性疾病,隨著肺癌進展,腫瘤細胞對于營養物質的掠奪能力提升,當患者的營養物質供給平衡被打破后,機體會逐步出現營養不良等臨床癥狀[18]。同時,在肺癌患者治療的不同階段均會一定程度上抑制消化系統功能,進而誘發自身蛋白成分的消化,最終損傷自身免疫功能。有研究報道,腫瘤患者發生營養風險的概率>40%,而在對腫瘤患者的放療和化療過程中,較差的營養狀況會造成患者放療和化療的耐受性下降,免疫功能降低也會加重病情,影響患者的生命質量[19]。因此,在對腫瘤患者的早期治療過程中,有效的營養干預性治療對患者預后的改善具有重要意義[20]。
本研究結果顯示:常規組和干預組治療前營養風險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常規組和干預組營養風險評分均低于治療前,且干預組低于常規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這提示,腸道營養干預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肺癌患者的營養風險。其原因可能是:肺癌患者治療過程中容易出現低氧血癥、血液灌注不足等情況,進一步誘發腸道黏膜細胞萎縮、腸壁通透性增加,導致腸道菌群易位、內毒素進入血液;患者在放療和化療的聯合作用下會發生自身免疫機能下降;消化道、胸部、喉部及食管受損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吞咽功能障礙,造成營養狀態失衡;常規飲食干預無法很好地改善患者營養狀態,而腸內營養干預通過在營養素中加入免疫調節性成分,刺激免疫應答機制,提高營養狀況,使營養風險評分下降[21]。
有研究報道,在對存在營養風險損傷患者的腸道營養干預治療中,患者的各項營養指標均得到改善,相比常規的營養支持性治療,腸道營養干預能夠根據患者的每日營養需求,通過腸內營養和腸外營養等多種措施提高其生命質量[22]。本研究中,干預組血紅蛋白、轉鐵蛋白、總蛋白、白蛋白、前白蛋白治療前后差值均高于常規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這提示機體的蛋白質供給平衡得到恢復。
本研究結果還顯示:干預組生理功能、生理職能、軀體疼痛、一般健康、精力、社會功能、情感職能、心理健康、總評分治療前后差值均高于常規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實際的肺癌治療的整個階段,患者的活力及情緒表達均較為低沉,但對患者進行腸道營養干預治療可提升其生活質量[23-24]。有研究指出,在對腫瘤患者的治療中,腸內營養干預可以改善晚期肺癌患者的營養狀態,對其免疫力提高具有重要意義[25]。因此,建議在臨床治療中及時引入腸道營養干預,提升患者的生命質量。
綜上所述,及時通過營養工具評估營養風險并對處于治療過程中的中期肺癌手術患者實施腸道營養干預可提升其生命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