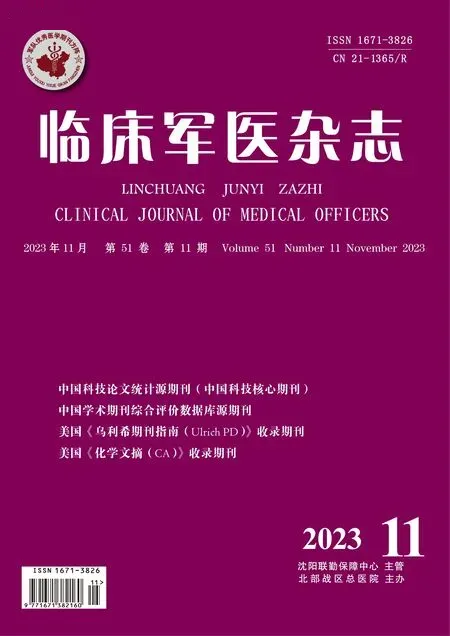類器官在生物醫學中研究進展及應用
孫廣晨, 李宏宇, 陳 江, 王煜曄, 高 聰, 劉小毓, 常旭東, 韓 杰, 王詩雨, 高 飛
1.錦州醫科大學北部戰區總醫院研究生培養基地,遼寧 沈陽 110016;2.北部戰區總醫院 消化內科,遼寧 沈陽 110016;3.大連醫科大學,遼寧 大連 116000;4.中國醫科大學,遼寧 沈陽 110000
在生物醫學領域,動物模型和二維細胞系模型常被應用于探索發育和疾病機制、評價藥物效果及毒性、了解細胞信號通路等方面,但這兩種模型均具有局限性。動物和人類之間的物種差異決定了動物模型可用性有限。而二維細胞系模型因缺乏結構和維度,無法完全模擬出細胞與細胞之間或細胞與基質之間的相互作用,這導致其無法充分揭示組織中細胞的功能和細胞間的信號交流[1]。相比于上述兩種模型,三維培養的類器官不僅能夠高度模擬來源組織的結構和功能,且可在體外增殖過程中始終保持基因組的穩定性。因此,類器官技術已被廣泛應用于建立生物樣本庫,進行高通量篩選,研究發育和疾病機制,指導臨床個性化用藥等諸多方面。本文就類器官在生物醫學中的研究進展及應用作一綜述。
1 類器官的發展歷程
類器官一詞最早于1946年在一項病例報告中作為畸胎瘤的同義詞出現[2]。受限于當時的技術水平,類器官的實現僅有理論可能,直到20世紀80年代, Bissell和Peterson發明了三維細胞培養技術[3],類器官技術具有了可行性。2009年,Sato等[4]利用小鼠富含亮氨酸的重復G蛋白偶聯受體5陽性(leucine-rich repeat-containing G-protein-coupled receptor 5-positive,LGR5+)干細胞,在體外培養出無間充質微環境的小腸隱窩-絨毛結構,該類器官模型重現了隱窩樣區域和絨毛樣上皮區域的三維結構。2011年,Sato等[5]構建了人腸道類器官及結直腸癌類器官,腫瘤類器官被成功建立。
隨著類器官技術逐漸發展為獨立的研究領域。2014年,Lancaster等[6]對類器官這一概念進行了系統、精確的定義,即從干細胞或器官祖細胞發育而來的器官特異性細胞類型的集合,并能夠以與體內相似的方式經細胞分序和空間限制性的系別分化而實現自我組建。類器官研究不斷深化,多種類器官不斷被成功構建,包括但不限于腦、肝、肺、腎、胃、垂體、內耳、食管、氣道、胰腺、乳腺、膀胱、卵巢、結腸、視網膜、甲狀腺、心血管、輸卵管及子宮內膜等類器官,其中,不僅包括正常器官組織的類器官,還包括其腫瘤組織的類器官,以及相應的類器官芯片體系。2021年,類器官技術被列為中國“十四五”重點研發計劃重點專項。2022年,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了基于類器官芯片技術獲得臨床前數據的新藥(NCT04658472),開始進入臨床試驗階段。
2 類器官的構建
培養類器官的干細胞來源分為多能干細胞(pluripotent stem cells,PSCs)和成體干細胞,其中,PSCs包括胚胎干細胞和誘導多能干細胞(human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hiPSCs)。此外,患者來源的類器官(patient-derived organoids,PDOs)因通常用于腫瘤患者的建模和藥物篩選,也被稱為腫瘤類器官。
獲取培養類器官組織樣本的方式包括手術切除、穿刺活檢、液體樣本等[7]。初步處理組織樣本后(切除非上皮組織),通過機械解離和(或)消化解離(如膠原酶、胰酶、DNA酶和解離酶等)使其產生單細胞或小細胞團,再將其鋪在3D細胞外基質中,最后添加包含多種生長因子的培養基進行培養。常用的基質膠有Matrigel、Geltrex和Cultrex等,其為分離自Engelbreth-Holm-Swarm(EHS)小鼠肉瘤的可溶性基底膜提取物,主要成分包括層粘連蛋白、Ⅳ型膠原、硫酸乙酰肝素蛋白聚糖和巢蛋白,基質膠的作用是為干細胞提供具有支架功能的三維環境,并允許細胞在支架上聚集、增殖及遷移[8]。
生長因子的選擇會因培養的組織類型不同進行調整,如在培養人小腸類器官需加入胃泌素、煙酰胺、轉化生長因子-β抑制劑和p38抑制劑[5]。培養腫瘤類器官時,為了減少克隆選擇,避免混淆藥效,往往選用減少生長因子的培養基[9]。但培養基一般包含以下4類生長因子:促進干細胞生長、增殖及分化的Wnt信號通路激活劑,如Wnt-3a[10]、R-spondins[11];促進干細胞擴增的轉化生長因子-β/骨形態發生蛋白信號通路抑制劑,如Noggin[12];促進上皮細胞增殖的酪氨酸受體激酶配體,如表皮生長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EGF)[13];抑制干細胞凋亡的ROCK抑制劑,如Y-27632[14]。類器官的培養方法多樣,除了通過基質膠細胞支架方法培養,Capeling及Neal等[15-16]分別使用懸浮培養法和氣液界面法培養出了腸道類器官。此外,PDOs的培養方法還包括微流控培養法、旋轉生物反應器法等[17]。
3 類器官的應用
3.1 發育模型 既往研究多使用小鼠等動物模型分析人類大腦的發育和功能,但人類大腦與小鼠大腦間存在較大差異,而人腦類器官的發育過程與人類胎兒腦相似,為研究供新的思路[18]。Fleck等[19]利用人腦類器官繪制出人類大腦發育圖譜,使用CRISPR-Cas9技術確定了對大腦不同區域的神經元發育具有重大影響的基因開關。Revah等[20]成功將人皮層類器官移植到大鼠大腦中,以此探究大腦的連接性和功能性。此外,心臟、肺、肝、腎、腸道、骨、輸卵管和子宮內膜等諸多類器官也已經用于人體發育、功能、代謝及組織間相互作用的機制研究中。
3.2 疾病模型 類器官在功能和結構上與人體真實器官高度相似,因此,能夠用來建立疾病模型,探究疾病的發生與進展機制,開發新的治療策略。法布里病是一種由半乳糖苷酶α基因突變引起的X連鎖溶酶體貯積病,由于缺少人體實驗模型,該病的研究和治療受到了限制。Kim等[21]使用hiPSCs衍生的腎類器官和CRISPR-Cas9(成簇的規律性間隔的短回文重復序列)基因編輯技術成功對法布里病建模,揭示了法布里病與球狀神經酰胺(Gb3)和谷胱甘肽之間的關系。Papes等[22]借助人腦類器官揭示了病理性轉錄因子4(transcription factor 4,TCF4)突變如何影響人類神經組織,即TCF4功能喪失導致Wnt信號轉導減少,SOX基因表達降低,最終導致體外祖細胞增殖減少,這意味著利用基因治療工具恢復該基因功能有望治療皮特-霍普金斯綜合征。類器官已經成為許多疾病治療和機制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包括先天性心臟病[23]、炎癥性腸病[24]、肝損傷[25]、唐氏綜合征[26]、阿爾茲海默病[27]、帕金森病[28]、2型糖尿病[29]、常染色體隱性多囊腎病[30]等諸多疾病。值得注意的是,類器官模型還能夠模擬病毒或細菌感染的過程,在研究幽門螺旋桿菌[31-32]、寨卡病毒[33-36]、諾如病毒[37]、輪狀病毒[38]、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2[39]、人乳頭瘤病毒[40]等病毒的感染和腸道菌群及其代謝產物[41-43]對人體的影響中是具有重要價值的3D模型。
3.3 藥物篩選 與傳統的動物模型和2D細胞模型不同,3D培養的類器官模型能夠準確地模擬出器官的三維結構,在異質性和遺傳特征上與原始組織保持高度一致,不僅能實現單次超過5 000種藥物的篩選,還能夠兼顧個體對藥物的敏感程度[44],其高效性和精準性在藥物篩選方面顯示出了巨大的潛力,極大地節省了新藥研發的時間和成本。Gupta等[45]通過靶向藥物篩選,確定其能夠維持FANCD2和RAD51的活性,發現延緩順鉑誘導下腎類器官損傷模型慢性腎病進展的藥物SCR7(一種DNA連接酶IV抑制劑)。Herpers等[46]對結直腸癌PDOs生物庫和配對的健康結腸黏膜樣本進行大規模雙靶點抗體(bispecific antibodies,bAbs)功能篩選,發現了MCLA-158,這種bAb能夠特異性觸發LGR5+腫瘤干細胞中的EGF受體降解,對健康LGR5+結腸干細胞的毒性最小。
類器官還能夠高度復刻臨床患者的藥物反應[47],用來評價藥物的效果和毒性。Zhang等[48]通過肝類器官觀察到與藥物性肝損傷患者臨床表現相關的泰諾福韋-伊那吉韋相關肝毒性。疾病和藥物的影響往往涉及多個器官。Rajan等[49]建立了一個包括腦、心臟、肺、肝、內皮和睪丸6種類器官的集成系統,相比于孤立環境下的單一類器官模型,該系統能夠復刻器官之間的相互作用,綜合模擬藥物在體內的代謝和毒性情況。
3.4 基因工程 能夠穩定傳代培養的類器官為基因編輯提供了平臺,使基于體外3D模型的基因修復成為可能。此外,類器官技術聯合基因編輯技術還有助于建立既往無法在體外重現的疾病模型[50],且該模型可以用于藥物的效果評價和篩選。囊性纖維化是由于囊性纖維化跨膜傳導調節因子(cystic fibrosis transmembrane conductance regulator,CFTR)基因突變所致,此疾病曾經無法治愈且具有致命性[51]。2013年,Schwank等[52]使用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通過同源重組糾正了囊性纖維化患者來源腸道干細胞類器官的CFTR基因位點。
3.5 腫瘤 腫瘤患者的腫瘤表型在治療過程中不斷變化,這種異質性導致了腫瘤原發和獲得性的耐藥性,治療失敗及病程的進展和惡化,成為針對廣泛患者人群臨床試驗的一大障礙[53-54]。既往人源腫瘤細胞系移植(cell-derived xenograft,CDX)模型和人源腫瘤組織異種移植(patient-derived xenograft,PDX)模型常用于腫瘤研究,但CDX模型在體外培養過程中不斷適應環境及被環境所選擇,無法準確概括腫瘤的異質性[55];PDX模型則面臨著成本高昂、移植率低和倫理等問題[56]。而腫瘤類器官模型能夠在體外穩定保存母體腫瘤的遺傳特征、藥理學特征、形態特征、組織學特征及分子特征[57],作為疾病模型,可以應用于開發藥物、指導個體化用藥、研究腫瘤的發生及發展機制。
腫瘤類器官可用于尋找生物標志物及潛在的治療靶點,并針對該靶點開發新型抗腫瘤藥物[58]。Kryeziu等[59]研究發現,在33種在研抗腫瘤藥物中,相比于初始性直腸癌肝轉移PDOs,復發性直腸癌肝轉移PDOs對第二線粒體衍生的半胱天冬酶激活劑模擬物LCL161的體外敏感性最強,并通過功能分析和基因表達進一步解釋了產生該結果的可能原因。因此,作為一種可能的實驗性療法,LCL161或可被用于治療肝切除術后或標準系統治療后復發的轉移性直腸癌。
臨床常用的抗腫瘤藥物包括細胞毒藥物(如環磷酰胺、甲氨蝶呤、順鉑等)、靶向藥物(如靶向EGFR、HER2、MET等靶點的藥物)、免疫治療藥物(PD-1抗體、PD-L1抗體)等。實際應用中,往往采取多手段聯合治療,基于腫瘤類器官的藥物敏感性檢測可以指導患者選擇個性化藥物,提高臨床療效,減少不良反應。Wang等[60]針對化療和靶向治療進行了基于肺癌類器官的藥物敏感性測試(lung cancer organoids-based drug sensitivity tests,LCO-DSTs),研究表明,藥物敏感性與臨床反應的總體一致性可達83.33%,提示LCO-DSTs在精準醫學指導用藥中具有巨大潛力。
Buti等[61]通過對胃類器官的培養,揭示了細胞毒素相關基因A(cytotoxin-associated gene A,CagA)的致癌機制,在幽門螺旋桿菌感染期間腫瘤抑制因子ASPP2被CagA破壞細胞極性,若能干擾CagA-ASPP2的相互作用,則可以防止細胞極性的喪失,并減少細菌在體內的定植。Yao等[62]從接受了新輔助化療的局部晚期直腸癌患者中建立了一個活體類器官生物庫,經臨床試驗數據證實,直腸癌類器官真實地再現了直腸癌的病理生理學和遺傳變化。
3.6 再生醫學 作為供體器官,類器官不僅安全、穩定、可塑,并且獲取方便。值得注意的是,其安全性不僅體現在移植部位精準,且多數類器官移植手術以微創形式操作,還體現在來源于自體細胞的類器官能夠使免疫排斥風險最小化[63]。Watanabe等[64]詳細描述了如何將腸道類器官移植到葡聚糖硫酸鈉鹽誘導的結腸炎小鼠模型中,為腸道類器官移植治療難治性潰瘍性結腸炎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目前,除腸道類器官之外,肝、腎、膽管、胰腺、淚腺、唾液腺等類器官的移植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應用。
4 總結
類器官的設計在不斷完善[65],但作為仍在發展中的前沿技術,類器官仍有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類器官在應用和培養方面需要標準化,例如目前常用的基質膠之間往往存在批次間的差異,不同研究團隊的類器官培養方法也不盡相同,進而影響實驗的準確性和可重復性。此外,應當制定具有統一標準的類器官培養方案,并保障質量、滿足大規模生產需求[63]。除技術問題,類器官衍生出的倫理問題也需要重視,如關于長期儲存和使用類器官所需的捐贈者授權和倫理審查類型。因此,確立類器官的道德和法律地位需要進行倫理討論和實證研究,尤其是人腦類器官[66]。
類器官技術的發展趨勢是進一步突破單一技術的局限,與實時成像、基因編輯、器官芯片、生物打印、微流體等技術互相融合。Geyer等[67]利用基于微流體的胰腺導管腺癌類器官系統揭示了缺氧條件對治療效果的影響。Tran等[68]通過實時成像技術篩選出了247種能夠阻止囊腫形成但不抑制類器官生長的蛋白酶抑制劑。因此,“類器官+”技術將為生物醫學發展可能會遇到的問題給出新的解答方法。
綜上所述,類器官已經應用于諸多領域,成為精準醫療、藥物開發、發育和疾病機制研究、再生醫學等領域不可或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