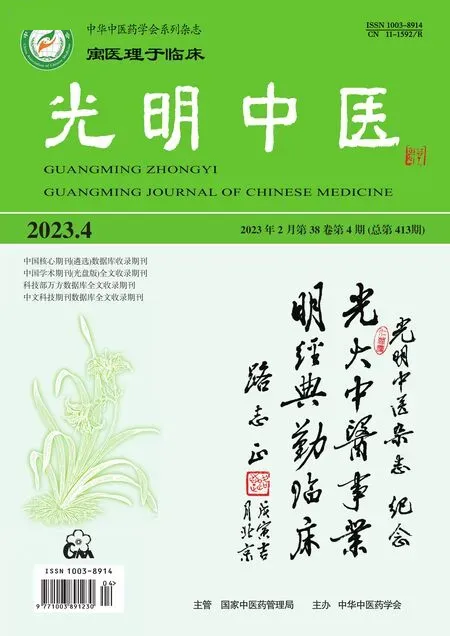驗方平郁方治療帕金森病抑郁30例*
藺通通 盧正海 楊麗芳 徐偉娜 馬春巖
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又稱震顫麻痹,由英國醫生詹姆士·帕金森于1817年首次報道及系統描述[1],是一種常見于中老年的神經系統變性疾病,近50%的帕金森患者伴有抑郁(PDD)[2],嚴重影響患者的工作和生活質量,治療上常以服用抗抑郁藥改善癥狀,主要以鹽酸文拉法辛緩釋膠囊為代表,但常易引發惡心、口干、頭痛、出汗(包括盜汗)等不良反應,患者依從性差。近年來濰坊市中醫院腦病科運用驗方平郁方治療帕金森病抑郁患者30例,取得顯著的療效,并與鹽酸文拉法辛緩釋膠囊治療帕金森病抑郁患者30例療效作對比,總有效率高,且無不良反應,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60例帕金森病抑郁患者均為2020年10月—2021年12月在山東省濰坊市中醫院就診,其中男33例,女27例;年齡最小43歲,最大77歲;其中43~45歲6例,45~60歲23例,60歲以上31例。隨機分為試驗組30例,對照組30例。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1.2.1 納入標準帕金森病抑郁(PDD)目前暫無統一診斷標準,2006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在《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3](簡稱DSM-IV)的基礎上制定了PDD的臨時診斷標準[4]:①使用納入診斷途徑來對癥狀進行評估:僅評估和計數抑郁癥狀,不管其與PD是否有關;②當診斷亞臨床或輕度抑郁時,不把興趣減退作為核心癥狀診斷標準;③對于有運動癥狀波動的患者,要在PD開期進行評估;④對有認知功能障礙的患者進行評估時,可由看護人協助;⑤愿意并能配合完成漢密爾頓抑郁量表24版(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24 item,HAMD)[5],且入選患者HAMD≥8分;⑥簽署知情同意書。
由于PDD某些表現與PD的運動癥狀及其他非運動癥狀表現重疊,此標準雖對PDD診斷的敏感性高,但特異性不強。除了依據臨床診斷標準,也可根據部分評價抑郁癥狀的量表對PDD進行協助診斷。根據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運動障礙及帕金森病學組所制定的帕金森病診斷標準或診斷符合原發性PD診斷標準,除外帕金森綜合征、帕金森疊加綜合征及PD癡呆患者,同時抑郁患者的診斷均符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CCMD-Ⅲ)》[6]的抑郁診斷標準可診斷為PDD。中醫辨證要點[7]:①心情抑郁,情緒不寧,胸脅脹滿疼痛,痛無定處,善太息,脘悶噯氣,不思飲食,大便失常,或表現易怒易哭,女子月經失調;②舌紅苔薄膩,脈弦。
1.2.2 排除標準①存在失語、嚴重聽力或視力障礙、嚴重心肺肝腎功能不全或昏迷而不能配合完成相關量表;②合并惡性腫瘤等其他全身性嚴重疾病。
1.3 方法
1.3.1 試驗組藥物選擇:平郁方基礎方:柴胡12 g,川芎12 g,香附9 g,枳殼12 g,陳皮9 g,菊花6 g,薄荷9 g,郁金9 g,合歡皮12 g,白芍12 g,玫瑰花12 g,甘草6 g。同時根據患者的臨床癥狀適當增減藥物,如患者噯氣頻作、脘悶不舒,加用木香、青皮、旋覆花、代赭石、姜半夏理氣和胃、降逆止嘔;兼有食滯胃脘者,加用萊菔子、焦三仙、雞內金消食化滯;兼見腹脹、腹痛、腹瀉者,加干姜、炒蒼術、茯苓、白豆蔻、厚樸燥濕健脾、行氣止痛;熱勢較甚,口苦便結者,加用龍膽草、川楝子、牡丹皮、炒梔子、生大黃等。所有中藥飲片均由山東省濰坊市中醫院藥劑科提供,飲片均按《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有關規定,選用色、氣、味俱佳的地道藥材,并達到無蟲蛀無霉,潔凈無雜質,與標準品比較無明顯差別。服藥方法:每日1劑,水煎2次,共計取汁約500 ml,分早、晚餐后1 h各溫服1次,連服12周。
1.3.2 對照組藥物選擇:給予鹽酸文拉法辛緩釋膠囊(由愛爾蘭輝瑞有限公司駐中國惠氏制藥有限公司生產,批準文號:國藥準字 J20160079)治療。服藥方法:早餐和食物同時服用1片(75 mg/片)。連服12周,前4周若無效,則服用劑量及服用頻次根據病情變化遵醫囑。
1.4 療效判定標準分別對入組患者進行治療前后HAMD量表評分各1次,其中HAMD<8分為無抑郁癥狀,8~20分為可能有抑郁癥,20~35分為肯定有抑郁癥,>35分為重度抑郁。總有效率=(治愈+顯效+有效)/總例數×100%。

2 結果
2.1 2組患者治療前后HAMD比較治療前2組HAMD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2組HAMD評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試驗組較對照組降低更明顯(P<0.05)。見表1。

表1 2組患者治療前后HAMD比較 (分,
2.2 2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經治療,試驗組臨床療效總有效率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且無不良反應。見表2。

表2 2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例,%)
3 討論
隨著帕金森病的發病率逐年升高,且呈年輕化發病趨勢,嚴重影響患者的工作和生活質量,家庭負擔沉重,越來越得到世界各國醫學家的重視及深入研究,并發現在帕金森病的發病過程中,以感覺障礙、睡眠障礙、自主神經功能障礙、精神障礙為主的非運動癥狀也是帕金森病常見和重要的臨床征象,可以發生于以靜止性震顫、肌強直、運動遲緩、姿勢平衡障礙為主的運動癥狀出現之前、甚至半年或之后[1]。國外報道帕金森病抑郁的發生率波動在2.7%~90%,可見抑郁已成為帕金森病患者非運動癥狀的最常見表現,導致患者日常活動功能明顯受損、社會適應能力及日常生活質量嚴重下降,給患者本人、家庭及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患者自責、自罪、絕望心理更嚴重,同時抑郁的出現也可導致帕金森患者的功能鍛煉、癥狀改善及生存質量的提高等嚴重受阻,并有可能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最終導致的結局是患者致殘率顯著增高、生存質量水平嚴重下降[8]。因此盡早識別和防治帕金森病抑郁等非運動癥狀, 改善患者的生存質量,是至關重要的。而目前用于抗抑郁的藥物大多存在依懶性,且常導致患者肝腎功的損害,同時常易引發惡心、口干、頭痛、出汗(包括盜汗)等不良反應,加重患者的痛苦不適感,患者依從性差,經濟負擔重。而中醫藥治療帕金森病抑郁,藥物靈活多樣,療效顯著,安全性高,且價格低廉。在中醫學中,帕金森病屬于“顫證”范疇,抑郁屬于“郁證”范疇。《素問·至真要大論》曰:“諸風掉眩,皆屬于肝”,其中“掉”字即為肢體震顫搖動。明代樓英《醫學綱目云》指出:“風顫者,以風入于肝臟,經絡上氣,不守正位,故使頭招面搖,手足顫掉也”。《證治準繩·雜病》:“肝主風,風為陽氣,陽主動,此木氣太過而克脾土,脾主四肢,四肢者,諸陽之末,木氣鼓之故動,經謂風淫末疾者此也。亦有頭動而手足不動者,蓋頭乃諸陽之首,木氣上沖,故頭獨動而手足不動。散于四末,則手足動而頭不動也。皆木氣太過而兼火之化也”,表明肝臟在顫病中的重要作用[7]。郁證這一病證名稱首見于明代虞摶《醫學正傳·郁證》,并由此開始明確將情志之郁作為郁證的主要內容。明代徐春甫《古今醫統大全·郁證門》云:“郁為七情不舒,遂成郁結,既郁之久,變病多端”。在中醫基礎理論中認為肝為風木之臟,主疏泄,其氣升發,喜條達而惡抑郁。而肝臟的生理功能即包含調暢人體氣機及調節人體精神情志……濰坊市中醫院腦病科基于中醫學理論,加之總結多年的臨床經驗,認為顫證和抑郁的發病均與肝臟關系最為密切,“木郁達之”,故以疏肝清肝、行氣解郁為治則,自擬平郁方治療帕金森病抑郁,療效顯著。如《證治匯補·郁證》曰:“郁病雖多,皆因氣不周流,法當順氣為先,開提為次,至于降火、化痰、消積,猶當分多少治之”。本方中柴胡苦辛微寒,歸肝膽經,功擅條達肝氣而疏肝結,為君藥。川芎味辛氣溫,入肝膽經,能行氣活血、開郁止痛;香附微苦辛平,入肝經,長于疏肝行氣止痛,兩藥合用共助柴胡疏肝解郁,且有行氣止痛之效,緩解帕金森患者肌強直的疼痛不適,同為臣藥。陳皮理氣行滯而和胃,加之醋炒更入肝行氣;枳殼疏肝理脾、行氣止痛;“肝為剛臟,體陰而用陽”,故選用理氣藥,需要注意忌剛用柔,防香燥耗陰,尤其對久病陰血不足之體,更當謹慎,故加用玫瑰花、薄荷等藥性平和,理氣而不傷陰;加用炒白芍養血柔肝、緩急止痛,與柴胡相伍,養肝之體,利肝之用,且防辛香之品耗傷氣血,無論郁證新久,均可適當選用。《臨證指南醫案·郁》指出治療郁證:“不重在攻補,而在乎用苦瀉熱而不損胃,用辛理氣而不破氣,用潤滑濡燥澀而不滋膩氣機,用宣通而不揠苗助長”,郁證一般病程較長,用藥不宜峻猛,宜輕靈,苦辛涼潤宣通,勿投斂澀呆補,重濁滋膩,故加用菊花、郁金、合歡皮行氣解郁,活血清心,俱為佐藥。甘草調和藥性,且與白芍相合,增強緩急止痛,減輕帕金森患者的軀體肌肉強直,是為佐使。本方既充分發揮中醫藥治療顫證的優勢,同時注重郁證等精神治療的重要作用,標本兼治,療效顯著,價格低廉,不良反應少,安全性高,值得臨床推廣,以減輕更多帕金森病抑郁患者的病痛,增加患者的幸福感。